 (攝影/Chen Meng-Ping,提供/吳明益)
(攝影/Chen Meng-Ping,提供/吳明益)
在和吳明益聊他最新長篇小說《單車失竊記》其中那諸多似真非假的細節時,他提及王家衛《阿飛正傳》,最後梁朝偉那段經典的兩分半鐘。
「我想王家衛一定看過無數的景,對那小閣樓的房間有他的勾勒──鏡子在這、窗在這、燈在這、光要這樣進來;他從哪裡揀硬幣、點鈔票、拿紙牌、梳頭髮……以他這樣一位了不起的導演,他看到這個空間時,動線就已經在他腦中完成了。」但他會向梁朝偉交代得這麼細嗎?可能不。他也許只告訴他:你要怎麼摸都隨便,反正摸完就出門。而所有的成全,就在梁朝偉離開前熄燈的那一瞬間。
「梁朝偉關燈的動作,一定得是拉那麼一下。如果他是伸手往牆上去切開關,就什麼都錯了。」雖然觀眾不見得會很清楚地知道哪裡有問題,但就是不對勁,「一切就會減了五十分。」就那麼一下,它甚至不到一秒,卻是至關緊要,是一旦錯了,便將導致全軍覆沒的動作。
對吳明益而言,無論是導演、演員,或小說家,能不能察覺「那麼一下」的重要,即是身為創作者的敏銳度──關於如何用細節,建構出一個讓觀看者自然融入、毫不起疑的真實世界。「你知道,其實這些都可以模糊化。」吳明益這麼說,但他並不這麼做。
在《單車失竊記》中,最是充滿了這樣的細節工夫。或者說,如他所鋪陳的,整部小說的起點,來自一個讀者的提問:在《睡眠的航線》最末,主角父親的那輛腳踏車,到哪裡去了?
我們很難向吳明益追問出這個讀者、這個問題是否真的存在。他編織入事的虛實,交錯得太過緊密,近乎無法分割。例如《睡眠的航線》是吳明益2007年的作品,也是《單車失竊記》的「我」的作品;而在段落之間,又時常可見《天橋上的魔術師》《蝶道》《迷蝶誌》等影子。讀著讀著總讓人混淆:吳明益本人,就是那個「我」嗎?(但不是,書中主角姓程)。小說允許虛構,吳明益這次幾乎不虛構,「這部小說,只要是具體的東西,我都不將它虛化。」完全具體的年代、可追尋的地理位置,讓小說立在一個我們自身所生活著的、實在的世界,再埋入虛虛實實的人物事件。「我們當然可以架空,通通將它變成『T市』,所有的一切自己命名。但我想要的是,讓這一代的讀者和上一代的讀者,相互有了一個通道。」彷彿走在歷經數世紀不變的老城區,你和幾百年前的人們,踩踏在同一條街道上。「那讓你要進去那個歷史時空、思維模式,都會容易得多。」
如是,他讓自己也成為小說中一根不可撼動的樑柱,「他」就是支撐起整部小說最關鍵的細節。甚至在訪談間,提及書中主角的父親,吳明益脫口而出的是「我爸」,那真讓人以為他為了解開父親失蹤的謎而追起了老單車。當然吳明益並沒有個失蹤的父親,但他的確追起了老單車,持續至今。
「我也曾經是個講究腳踏車愈輕愈好的人──9公斤以下、XTR傳動系統等等,不過這些意義很快就消失了。」當他把目光轉到老單車的領域,其中的邏輯令他著迷,「老單車的重點不是『這輛車當時價值多少』,而是『這輛車現在有多完整』。」即使是當年不怎麼樣的廠牌,只要零件、部位完整,大家就會認為它很「全」。台灣受過日本殖民統治,有著日本的影響;而日本又因明治維新,學習、模仿著歐洲西方國家。輾轉改到台灣,我們成了混日混歐混美的第三手。「你從中可以知道台灣在世界史的位置──很邊緣的邊緣,尾巴的尾巴。」即使是一輛單車,都寫著時代的語碼,「如果你能讓『時代的東西』恢復、保存下來,那就變成一種心意。」

 吳明益收藏的幸福牌單車。(攝影/郭上嘉)
吳明益收藏的幸福牌單車。(攝影/郭上嘉)
為了書寫《單車失竊記》,吳明益做了台灣單車史的年表、蒐集滇緬戰役裡某場局部戰役的資料、蒐集彼時台灣的物價指數……各種細微的物事,成了他電腦裡的各種檔案夾,七八成的精力都在耙梳這些絕大部分沒用上的資料裡,「寫小說」似乎退到最微不足道的位置。不明究理的人可能以為他要寫的是近似陳柔縉作品的時代生活史。「沒辦法。小說為了要創造出一個真正存在的世界,很多東西都需要扎實。」網路上得來的資料是不扎實的,沒有血肉。寫單車,不是只知道一部單車長怎樣就可以,而要像修車修了一輩子的老師傅,只需對車打量個兩眼,就能鐵口直斷:「你這螺絲換過了。」你問他為什麼知道?他答:「我怎麼不知道。」你再問他是怎麼知道的,他回:「我就是知道。」好似一切早已長進他的身體裡──吳明益說,要到這樣的地步。
「所以寫小說最好的狀況是,它本來就是你有點興趣的東西,為了完成這部小說,你會去鑽研更深,驅使自己成長。」這是小說寫作者的成就感來源,也是寫小說的迷人之處。「為了解決小說裡的相關問題,你一定要費工夫。」
問他為了這部小說的種種,究竟追細節追到多深?他搖搖頭。「我已經不知道該怎麼講了。」他時常陷入「如何印證」的焦慮,好比為了確認軍用單車放槍的位置,專程跑去日月潭看老單車展,而非一筆簡單帶過了事。「這些行為可能一點意義都沒有,只是它變成一種職業的焦慮。我認為要有這個欲望,才是一個好的寫作者。若活在創作的狀態裡,卻連這種欲望都沒有,覺得『這樣寫就好了』,自信認定世界都在掌握之中,在我的標準裡,這樣的寫作者就是……就是不夠。」他語調溫和,然不帶一絲折衷。
有幸追到細節,還要會打磨。「像是修老單車的磨電燈,裝錯了,怎麼磨都不會亮。」當所有環節都到位,你轉起踏板,略帶期盼地看著眼前的老燈,似從夢寐中醒覺一般由暗漸明,亮了前方。「講故事是很基本的能力,但文學不是相聲,文學是文字,要怎麼用文字將故事的光帶出來,打磨出小說感,這是小說家的才能。」每個作家都在自己小小的世界裡努力,用細節把自己打磨出來。「我做不到事事懂,但假使有個東西已經端到面前來了,我就不能放過它。我只是這樣想。」
如是所有心力的投入,所有細節的緊緻,只為了翻頁的一個瞬間。「你不可能要求讀者花的時間和你寫的時間一樣,沒有人這樣享受藝術的。」一部拍了十年的電影,觀眾也不過給個兩小時。「我要做的是,無論看得多快多慢,都要帶給你某種衝擊。」不管翻到哪一頁、讀到哪一段,瞬間就要刺進心底──如果打造得夠扎實,應該就能做到。「寫小說的人,就是夢想寫出一部這樣的小說。」吳明益說。
那就像他在書中敘寫的修燈經過:我裝上罕見的幸福牌磨電燈,用手空轉起腳踏車的踏板,那踏板帶動鏈條、齒輪,沙沙答答答答沙沙地響了起來,胎皮因而與發電器的膠頭磨擦,產生了六伏特的電流。當那電流以我聽不到的微細聲響滋滋擦擦地從電線傳到燈座尾端通過鎢絲,發出溫暖明亮的微熱光芒時,我也有了一種和標本剝製師完成林旺標本時,那種身處聖殿的感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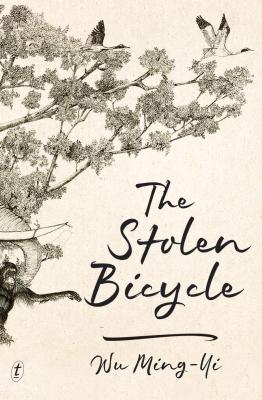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