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近日發生的事往前溯:藝人購買未成年少女被性侵的犯罪實錄案件、#Me too事件、狼師們紛紛逃過法律制裁,循著這條流淌著少女血的路徑向前,回到2017年,那年,我們讀到被老師強暴的房思琪的血淚,林奕含也在同年結束生命。
讀者們的普遍願望:不要再有下一個房思琪。但痛心的是,這八年間,仍有一個又一個房思琪,或者現身,或仍躲藏在蝕骨腐肉的創傷記憶裡。
如同林奕含回應讀者問題時所言:「我自己所認識的那些『房思琪們』。」複數的房思琪仍在新聞版面上繁殖、輪迴。
少女的血,未曾乾涸。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仍繼續讀《房思琪的初戀樂園》的緣故。
2025年,游擊文化再版《房思琪的初戀樂園》,除了小說,特別收錄林奕含的婚禮致詞、2017年臺北國際書展「讀字迷宮」新書發表會、公共冊所座談會,以及Readmoo「閱讀最前線」的訪談與獨白。在小說出版後的公開場合座談中,林奕含希望讀者可以「與思琪同情共感」,可以站在思琪的鞋子裡,「讓觀看的人、讓在閱讀的人能夠一步一腳印地、逐步逐步地去感同身受思琪的痛苦。」房思琪們無法言說的苦難,無法選擇的劇痛創傷,林奕含工筆寫了下來。
●
「妳有選擇。」
這句話出自於房思琪仰慕的伊紋姊姊之口。去療養院探視過瘋了的思琪、讀完房思琪日記之後,伊紋對怡婷說:「妳有選擇。」身為思琪「靈魂的雙胞胎」,怡婷可以假裝思琪的故事不存在,世上沒有人以強暴小女孩為樂,只有馬卡龍、手沖咖啡和進口文具的安逸世界,但她也可以選擇:「請妳永遠不要否認妳是倖存者,妳是雙胞胎裡活下來的那一個。」
「妳有選擇。」
「妳可以放下,跨出去,走出來。但是妳也可以牢牢記著,不是妳不寬容,而是世界上沒有人應該被這樣對待。」伊紋提醒怡婷,選項還包括「妳可以把一切寫下來。」
林奕含寫下房思琪的故事,動員的不是憤怒,而是她對受苦少女們的同理,以及她對文學、文字、修辭無比的熱愛。從痛苦中誕生的敘事力,明亮且鋒利,不僅要說,且要「疊床架屋」、「用各種很華麗的,也許文字遊戲」、「奇詭的修辭法」(林奕含語),協助因羞恥、恐懼而噤聲的房思琪們,說出來。
●
於是林奕含賦予房思琪一副聲帶──由深厚的文學底蘊、敏銳思緒所構成──將言語作為自我保護與辯護的工具,如同張亦絢在〈羅莉塔,不羅麗塔:21世紀的少女遇險記〉中所言,房思琪「一步步趕上對她極度不利的『語言差』」之後,「以對手(老師)的語言反擊他」,在這場讀來酸楚的「語言馬拉松」中,思琪以犀利的話語權展現能動性。
在被宰制、凌虐、上對下的不平等關係中,房思琪逐步以遠遠勝過李國華的銳利,以及對文學的精熟挑戰「對手」,她靈活動員語言,熟稔調度經典,在早慧的才女面前,李國華不過是一個「連俗都懶得掩飾的」教書匠,只是「胡蘭成縮水了又縮水了的贗品」。即使沒說出口,思琪不斷在內心嘲笑李國華的粗鄙,包括:對典故不熟,錯將趙合德記成趙飛燕;貧乏且制式的陳腔套語:「老師總是在照抄他腦子裡的成語辭典」。她鄙夷李國華全面性化《紅樓夢》等中國文學經典,將精深內容簡化成「嬌喘微微」幾個字,這令思琪震撼又傷心:「紅樓夢對老師來說就是這樣嗎?」儘管李國華總愛在思琪面前展示博學,生產字詞,但被思琪冷眼識破,反諷他是「一個該上課時不上課而下課了拚命上課的人」。
這也是為什麼小說常常出現此刻的思琪「很快樂」,因為她正在內心悄悄偷渡、搬移著文學、語言、字詞,質疑看來無比巨大、實則脆弱的「老師」,因此當李國華將十萬塊紙鈔塞到思琪的書包裡時,思琪瞬間想到「這人倒是很愛隨便把東西塞到別人裡面,還要別人表現得歡天喜地」之際,她充滿痛楚,卻也「快樂地笑了。」這種快樂,是悲傷到極致、痛苦至深淵的自我協商過程,是她保護僅剩的愛與柔情的倖存之道,她在龐大的痛苦岩層中鑿取小小的快樂火光,淒慘的文學取暖:「文學的生命力就是在一個最慘無人道的語境裡挖掘出幽默,也並不向人張揚,只是自己幽幽地、默默地快樂。」
坦白說,這不但無法令人快樂,傷痛的力度反倒更深,房思琪的快樂不過是整棟痛苦大廈上隨風飛舞的小小旗幟罷了。快樂,在此也深具反諷意涵,如同林奕含解釋書名取名為「樂園」,即是反諷,因為「反諷是文學可以做到的最極致的事情。」
這種不得不選(或根本無從選擇)的快樂,其實才是痛苦所在。因此在專訪中,林奕含表示整個故事最讓她痛苦的問題是:一個真正相信中文的人,怎麼可以背叛超過五千年的、中國抒情詩的語境和傳統?李國華的粗暴不僅是脫下青少女的褲子,也是他剝除了文學的抒情傳統,以性化的方式誤讀文學,亂用典故。
巧言令色。
於是林奕含問:「藝術它是否可以含有巧言令色的成分?」又或者,「藝術從來就只是巧言令色而已?」
●
文學,陰性而感性的抒情傳統,足以對抗陽剛且粗糙的補習班國文老師的市儈語言,在被獵殺的痛楚時刻,為思琪打造一個私密而純淨的空間。文學,同時也為伊紋、怡婷、思琪築構一方淨土。伊紋是思琪、怡婷的「文學保母」,共讀杜斯妥也夫斯基,一起看電影《活著》──活著,多像是房思琪們艱難人生中的終極渴盼──她們的讀書會,珠寶般的時光,不僅伊紋提供文學養料,對於飽受家暴之苦的伊紋來說,「餵傷痕累累的她以精神食糧的」,也正是眼前這兩個「可愛的小女人們」。在思琪、怡婷這對靈魂的雙胞胎的眼中,伊紋姊姊始終是「美麗、堅強、勇敢的」女性,直探人性的文學經典,也替無處可逃的她們建造了一個容身之處,她們在文學中擁抱,相濡以沫。
即使思琪能清晰表述感受,精準地掌握了語言的多面性,面對被強暴的痛楚,她無法開口,同樣地,伊紋也是。在濃密的暴力面前,兩人皆失語:當伊紋載著思琪在城市裡閒晃,彼此無法直白告訴對方被施暴和性侵的事實,即使靠得這麼近,等待一個說出口的機會,「一個詞就好」,她們仍舊沉默,無法「像倒帶一樣從懸崖走回岸邊」。
雖然沒說出口,但怡婷與伊紋始終作為思琪內心的支撐。小說最末,當李國華將謊稱生理期的思琪綁成「螃蟹思琪」的過程,我留意到思琪腦海中浮現的都是與怡婷、伊紋相處的經驗,尤其是思琪想起過去和和怡婷練習說法文的時光,兩人像是開玩笑卻又如此認真地說「我愛你」。思琪也想起曾想要去陪伴伊紋的念頭。從這些細節可知,在最恐怖的性虐發生之前,思琪倚靠著和怡婷、伊紋說話的畫面,幫助自己的思緒「逃離現場」。雖然在書末林奕含回答讀者的問題時,認為怡婷從未理解過思琪。
但林奕含希望讀者可以與思琪同情共感:「我希望你可以站在她的鞋子裡。」
於是,即使這是房思琪們的毀滅樂園;甚至,這從來不是樂園,「它是一個充滿了各式各樣創痛的,關於很狹隘的婚姻的想像、各式各樣算計的地方。」但,林奕含一再強調,這不是一本憤怒之書,控訴之書。
如伊紋所言:「妳有選擇。」
面對最終「走向毀滅且不可回頭」的、沒有選擇的房思琪,林奕含選擇寫下故事,房思琪也曾以文學語言回擊,選擇讓自身充盈著柔情、慾望和愛。再次閱讀《房思琪的初戀樂園》的我們,也許可以選擇站在房思琪們的鞋子裡,同情共感,傾聽,擁抱,守護,與身邊的房思琪們,形成相互依靠的情感同盟。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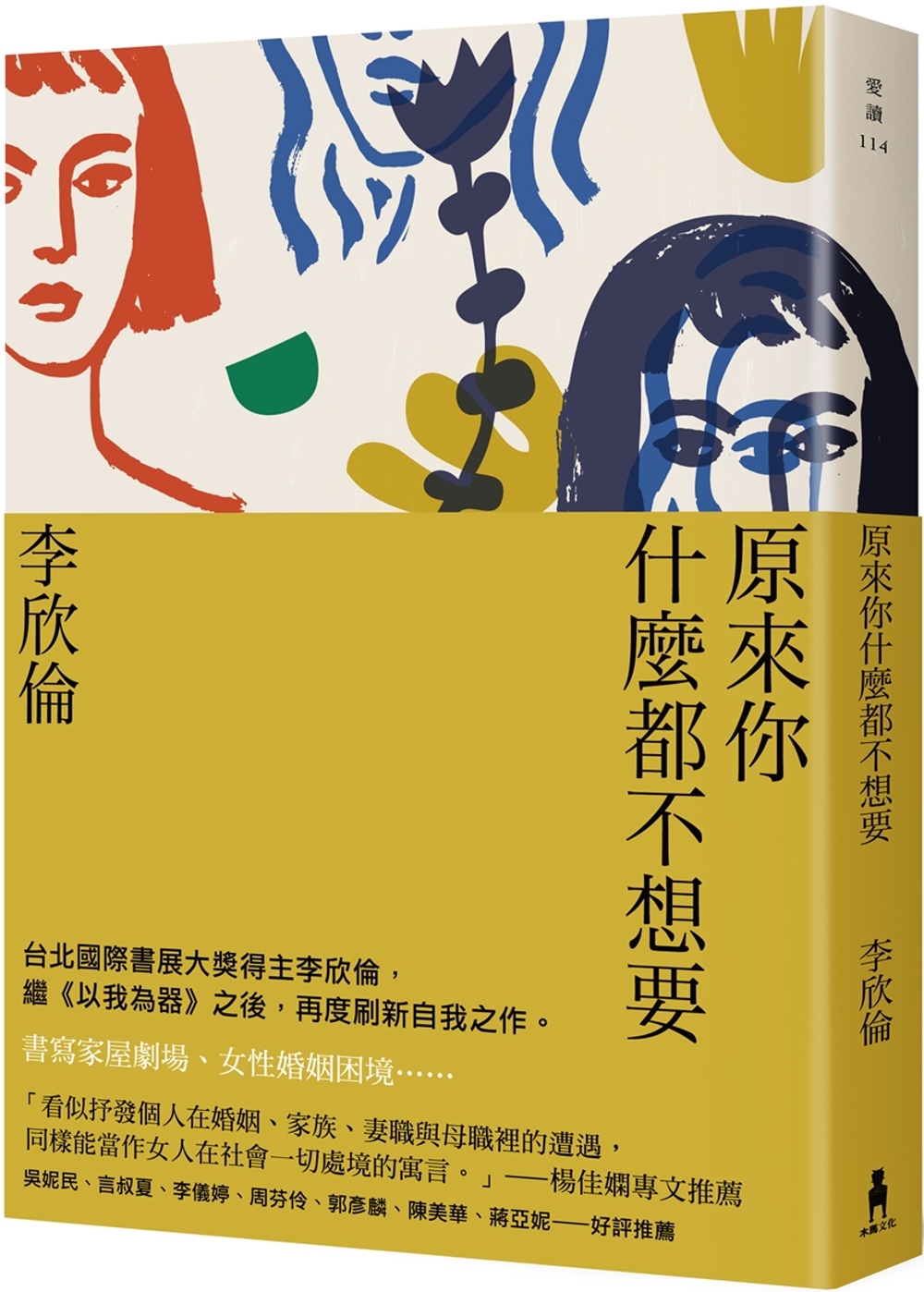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