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根廷作家瓦樂麗亞.丹托尼(Valeria Tentoni ,1985- )。Foto: Juan Manuel Foglia
阿根廷作家瓦樂麗亞.丹托尼(Valeria Tentoni ,1985- )。Foto: Juan Manuel Foglia
在幽暗的地方燒出火花────
當代的美洲文學,怎麼發聲?
怎麼更新人類的表達?
女孩是學法律的,後來沒當律師,決心發展文字的法。
第一次讀她的詩,感受到委身在輕巧之下的尖銳和苦味。委身,突顯了殉身意志的焰火多麼熾烈。不過,屈就並非單純作為一種關係位置,而是她駕馭了一種以柔克剛的敘事框架。
這首短詩——題目與四行詩句共同構成一組完整的語意——將我和你的關係類比於狗和主人的關係。我獻給你的聖物,在你眼底只是無用且被嫌惡的屍體。然而,我能給你的,已是我能擁有的最好的東西。
那東西甚至不是我向外攫取來的,而是我身上最珍貴赤誠的情感,脫下我帶來的東西,就是把我的一部分留給你,那是我的存在為這世界帶來的愛、信任與無私。
愛、信任與無私一向都是過度的。
超過你需要的,超過我們的關係所能承受的。壯烈而卑微。我的付出可以無極限,而你接收的侷限來自於我們的這份愛並不對等。
我不是盲目耽溺地奉獻,而是清楚認知到奉獻完全沒有價值。當我認知到我的情意是你不要的死鳥,那我就跳出了一廂情願的委身視角,客觀抽離地看待你我的關係,陌生化了我的純真和過度。
在這一首詩中,示愛僅是表象,女孩以柔克剛的敘事框架是反思關係的一座模型。
我忍不住問女孩,持續創作的內在動力是什麼?女孩說:「我真的不知道。我從小就一直有創造力。詩教了我很多關於我自己的事情,這是我無法透過其他方式達到的:她總是比我知道更多。」
詩,撐起比我更大的框架,去突顯我的思維過程,去突顯我和書寫的關係。
一個字一個斷句的選擇都能重新界定我跟我所書寫的一切的關係。這首詩的內容在背離它的題目,不是交待仇恨的內容,而是被仇恨激起的創作欲如何一步一步引我脫離了仇恨。
詩題直接作為詩的第一行,意義在於距離的取消。取消表達和表演的距離,以一種緊密的流速和連貫的語氣,將讀者捲進「我」的意識。我的意識是站在仇恨的外面而不是被仇恨包裹。敘事結構的第一部分,是我意圖跟仇恨近身對峙(詩的標題);第二是幻想我的藝術成就(詩的第一段);第三是自我催眠和自我賦權(詩的第二段);第四部分則是不再因被仇恨咬嚙而亢奮,不再成為仇恨的奴隸,於是才能入睡(詩的最後一句)。
我問女孩,在阿根廷可以安心寫作、安心入睡嗎?女孩說:「如今在阿根廷,一切都太瘋狂太悲傷,我們在工人階級的生活中找到一點空閒時,就必須寫作——除非有錢,不然從吳爾芙《自己的房間》以來,一切都沒有改變。我的處境還跟吳爾芙描述的一模一樣。現在我很難集中精神去寫作。」
我追問:那當妳進入難得的寫作狀態,妳和詩怎麼相互激勵?女孩回答:「詩有時是一份偉大的禮物,有時也是一種負擔,一種難以承受的渴望。很多時候,我強行放棄了將頓悟、經驗或直覺轉化為一首詩的衝動。但當我回答妳的提問時,我自然而然地想要告訴自己,詩確實是一份偉大的禮物:能夠關注小到一塊石頭、一杯水裡面出現的美和生命的偉大。詩為生活增添了一種神聖的光環,這是我們不能輕視的,尤其是在這樣一個懶惰和嚴酷的時代。詩訓練我們與神祕共存,不去相信單一意義:我認為這是任何人都可以使用的非常強大的力量。」
藝術為思維狀態帶來轉化,思維過程找尋適切的敘述口吻和敘事框架,在我眼中真正神祕的是,女孩在現實環境和創作空間裡的涉險行動:不放棄在夾縫中寫作,堅持以詩的目光去關注生命。我問她想跟台灣讀者分享她的哪一首詩?她說,想分享〈這是我的新年:〉,因為「寫的時候,想法如瀑布般傾瀉而下,落在我又喜又怒的可憐腦袋上。」
 Valeria Tentoni的詩集《反地球》
Valeria Tentoni的詩集《反地球》
「我」描述的那個人不等於那個人,就像別人描述中的我不等於真正的我。我不只是試圖看清愛情中的權力關係,也在釐清作者、書寫對象和作品之間的關係。當我意識到我在操縱語言和對象,書寫本身的暴力我根本無法置身事外。我不得不承認詩中散落的「這是我的」、「我不需要」、「我喜歡」、「我不在乎」、「我只想」,它們為曾經那個在愛情裡沒有選擇權的卑微落難者帶來宣示的凜凜威風。
如果我做錯了,那是因為曾有人錯誤待我。
題目〈這是我的新年:〉的冒號之後所揭露的,是掙扎矛盾的覺醒過程。整首詩的敘事搭建了一個反思的框架,呈現我的經驗如何成為我的情感教育和創傷,令我自欺欺人,在共犯結構中療傷並製造新的傷口。線性的世界觀,讓我無法脫困。當我誠實地面對自己,我知道心不在前面也不在後面,它在裡面,所以我要跳脫前面和後面的特定序列思維(我不需要你,十二月;必須再多一個,才能構成完美的數字……),脫離因果邏輯的陷阱(最重要的是,講述了他的拒絕。/他不知道,這改變了我。),避免再用謊言來安慰自己(蒼蠅堅持反對玻璃,因為牠們不應該/因為我們讓無形的東西變硬而受到懲罰。),就真誠地,保持沉默。
書寫自己的不再書寫。實實在在,停頓下來。寫作的挑戰不僅在於寫什麼和怎麼寫,還有,敬重空白,無畏推翻自己的敘述。就像女孩說的:「通常一首詩會出現停頓:這是顯而易見的,但如果我沒有可用的思想和精力,我就什麼也想不出來。我不按主題或目標寫作,而是一種勢頭,沒有什麼受控制。詩句也是一樣,我很狂野,很坎坷,我會修改好多次,但我永遠不會愛上修改這件事。一首詩的修改幾乎總是涉及減法。在詩中,我特別關心給沉默自己的空間。」
信任沉默,它會鬆動字句的意涵,讓一首詩曲折,生出自己的法。
作者簡介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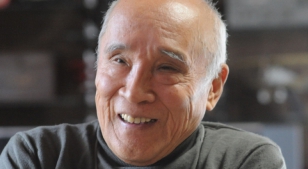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