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房思琪的初戀樂園》的英文譯者Jenna在談起語言時,眼裡閃著對某事抱著單純喜愛的光芒。《房》2017年在臺灣上市時,早已充滿話題性;到了今年(2024)五月英譯本出版時,在臺灣再度掀起大眾對此書及性別議題的討論。過去幾個月,Jenna以「《房》的譯者」身分,扛起了外界對性平、性暴力等沉重議題的種種叩問。但在這些討論之外,Jenna如何成為一位非英語母語的譯者?如何在美國出版業界求生存?如何從美國回望臺灣文學?
這回,我們暫時讓她卸去「《房》的譯者」重擔,請她從「作為譯者、作為Jenna」重新談起。
▌做翻譯是為了存活
翻譯的初衷來自對語言的熱情。Jenna說自己從小只要一接觸一個語言,就會著魔似地背誦、玩填字遊戲、做任何能暴露在該語言的事情。她發現通常只要三個月密集的「沉浸式學習」——包含認識在臺外籍學生、交筆友、看影集等等——就能熟悉一個語言。在大學前,她藉此方式學了英文、德文、西班牙文,後來念政大歐語系法語組。Jenna笑說,「我從小就想當七個語言的間諜。」
事實上,翻譯就是間諜。譯者在兩個語言文化之間,是雙方的盟友,也是雙方的叛徒。
Jenna會走上翻譯之路,一直都是務實的考量。「對我來說,翻譯是可以最直接和語言保持關聯的方式。」她在里昂第二大學交換時修讀應用翻譯組的課程,也在政大修完翻譯學程取得證書,儘管在紐約的新學院(The New School)取得創意寫作碩士,也有畢業所創作的小說初稿,但她並未投入寫作,而是開始接案做翻譯,因為這是可以最快有收入的管道。她坦承,「隻身在國外,最優先的考量都是存活。而且我身為非英語母語人士,選擇英譯,是因為英語受眾最多,市場最大,有更多工作機會。」從小對語言投入的愛,終究在她被疫情困於國外時,成為存活的資糧。

▌在美國出版圈,你必須被看見
在臺灣,大家想到「文學翻譯」,也許大多想到文字上的工作。然而,作為一位英語譯者,要將非英語文學推廣到英語市場,其實要付出許多超出文字之外的心力。
Jenna提到,以臺灣文學翻譯到美國為例,英語譯者時常需要肩負類似作品的經紀人角色。儘管有些作品會和版權代理公司簽約,但版代公司大多是一批一批地介紹臺灣作品,並以新書為主,讓國外出版社從一批批書單中挑選。這樣的推廣模式符合公司對公司的最大運作效益,但是難免有遺珠。因此,譯者就在大機構之間的隙縫中扮演重要角色,「譯者可以針對特定出版社偏好的出版風格,投遞客製化的書訊,介紹為何某某作品適合翻譯到美國書市、這本書在原語言文化的出版背景及影響力,再以美國近兩三年出版的作品來比較介紹。」Jenna在為《房》投稿時,就以《82年生的金智英》、《凡妮莎》等為比較書目,讓美國出版社掌握《房》如何對應到美國的出版趨勢。
投稿給出版社並非只是準備好資料而後大量寄出而已,要讓出版社編輯願意在茫茫信海中點開自己的信,社交人脈至關重要。因此,Jenna研究所畢業後就在五間出版社與非盈利機構實習,其中包括美國文學翻譯協會(ALTA)。ALTA是美國唯一的文學翻譯協會,提供大量資源培育新銳譯者,會員只要繳交年費,就能參與許多ALTA舉辦的翻譯講座與工作坊,從而結識其他語言的譯者,讓自己被業界相關人士記得。美國出版社也時常從ALTA的人際網絡尋找譯者,因此可說,ALTA在美國的翻譯出版圈極為關鍵。Jenna便是透過ALTA與臺灣文化部合作的「新銳譯者指導計畫」,牽線給三毛作品的英譯者傅麥(Mike Fu)當導生,並在與傅麥的交流中完成《房》的翻譯。
除了檯面上的機構活動,檯面下的社交也無法缺席。Jenna分享,「美國的社交文化就跟美劇演的一樣。例如有時是某作家主辦的派對,你不一定有邀請函,那麼就要看身邊有沒有人願意帶你進去。這種派對有許多社交暗號,像是dress code、該找誰打招呼、該透過誰才能向誰介紹自己的創作或譯作。」這些社交看似非常表面,但就算只有一面之緣,結果也可能有所不同。像是後來她投稿《房》的出版社編輯們,很多都是在作家派對、非營利機構的募款晚會、出版社辦的年度晚宴上攀談過的。

▌樂為臺灣文學推廣者
在臺灣,中譯本出版後,譯者通常很少受邀出席書籍相關活動。Jenna說,但是在美國,光是她在2023上半年簽約《房》,消息就透過上述綿密繁複的人脈網傳遞出去,也陸續收到活動及採訪邀約。《房》在2024年五月上市後,Jenna從五月底到六月初已經參加了6場新書活動,今年九月到十一月,還要再赴美跑22個新書活動、演講、工作坊。這些因美國的產業規模而生的大規模社交文化與打書活動,讓身在臺灣的我們難以想像。
一連串活動跑下來,Jenna觀察到,美國文學圈對臺灣文學還在認識階段。尤其,不少臺灣文學作品是純文學寫作風格,情節較隱晦而結局較開放,這和美國文學強調明確結局的敘事很不一樣。另外,諸如《房》動用了臺灣文學常見的敘事技巧,如意識流、跳躍及片段的敘事等等,多少會讓美國讀者困惑。Jenna也提到,「把臺灣作家介紹到美國文學圈時,明確的定位非常重要。臺灣作家的自介有時會有較個人化的資訊(如個性、座右銘等),但面對美國市場,需要直接明瞭地定位一個作家的寫作屬性、風格、主題、得過什麼獎以及這些獎的等級。」
中介兩種文化之間的差異,是Jenna從事翻譯、教授翻譯和寫作工作坊時的課題。她說,在教臺灣文學時會以主題來分類,例如原住民、LGBTQIA+文學等等,幫助學生更快定位作品及作家。由於來上課的學生多是臺裔美籍,有些能讀中文,因此她不只介紹已經有英文版的臺灣文學經典,也會推薦還有哪些值得翻譯的好作品、新作品。
她也觀察到,通常像「Writing about Languages」這類較為廣泛的課程名稱,能夠吸引到亞裔之外的族群。在這類課程,她會要學生書寫自己和語言之間的關係——這課題正是Jenna從「幻想成為七個語言的間諜」走到「在美國有自己出版品」的譯者之路。
因為熱愛語言,也讓語言帶著自己抵達遠方。或許Jenna下一次返台時會告訴我們,下一個讓她化身間諜傾心翻譯的,會是哪一本臺灣作品。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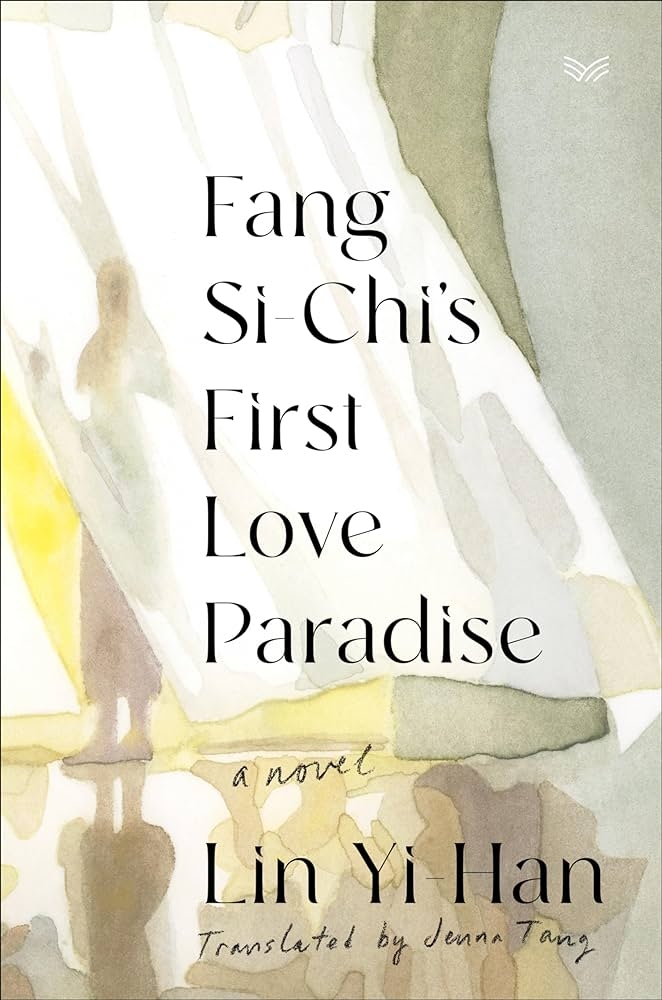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