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一向是作家敘事的關鍵詞,以女作家為例,杜潘芳格寫自身是「誕生在島上的一棵女人樹」,聶華苓也將自己形容是「根在大陸,幹在台灣,枝葉在愛荷華」的樹。施叔青的台灣三部曲中,樟木和樟腦則作為隱喻,樹木花果既標誌出台灣特殊的史地,又是多元族群的生命史。花,也從愛情分出多重枝條,從〈一棵開花的樹〉,到周芬伶回歸母土、獻給母系的花束,追溯建構女巫史的脈絡中,繁花盛開。在80後出生的女作家筆下,植物有了奇異而豔異的品種,向光植物與百合,各自綻出美麗的性別符號,所有的根、莖、花、蔓,皆散發著女女情誼的芳香。
可以說,在台灣文學;尤其是台灣當代的小說脈絡中,植物作為隱喻,業已森然,始終滿花。
即使如此,《滿花》仍開出新品種。在林文心筆下,植物並不作為國族象徵或愛情符碼,而以更本質卻幽微的姿態出現,本質指的是繁衍──即〈長生萬物〉中,她對咪咪的解釋:「從我的理解來說的話,對植物而言,死亡的概念應該是發生在不能繁衍」──幽微則在於作者雖以扎根、沃土、生長、滿花到結果的植物生長歷程為喻,但並不分神於草木花果的知識如何與故事精準對接(因此有了說好一個故事的餘裕),或讓植物有更多戲份,由此編織精緻且與主角人生緊密扣合的隱喻。林文心另闢蹊徑,她讓植物成為女性、女體的剪影,跡痕淡淡地,搖曳於敘事間,有時同步款擺,更多時候,訴說的是與植物生長意象逆反的故事,於是,幾篇女性物語便與題目之間,形成了意味深長的反差與張力。
例如〈扎根向下〉描述的甚至是「扎根」的反面,同時也改寫了「向下」的意涵,小說中的溫柔母親將嬰兒與自身拋擲而下,「扎根」不再是生長的必要條件,反倒促成徹頭徹尾的死亡(其實是「斬根」?)然而,這樣的死亡卻又提供了思索空間:在素描般的、寫意式的日常母職圖像中,我們可以用社會新聞事件填補那沒說出來的空隙,像是睡眠剝奪、母職(過度)勞動、憂鬱厭世、不知為何就成為母親等細節,最後推動了致命的「向下」,小說透過一個嬰靈敘說的重複性,似也暗示了母親因母職步上絕路,是個無法終結的悲劇。
除了絕望母親,《滿花》獻出了各式各樣的「母親」版本,包括:準備好健壯身體以成為母親、善盡母職的母親、想像即將有個男孩成型的母親、謊稱有個兒子並複製他人兒子人生的(偽)母親,這些母親們具備真實人性基因,例如為了打造閃亮未來,將能創造成就的女體拿來懷孕是否太浪費了?女同志的生子計畫和暗地競爭,隱微指向懷孕生子常是理想人生的絆腳石(〈沃土〉)。這可對讀Meghan Daum《為什麼我們不想生》中的篇章,理解女性對生子卻步的原因,只不過這些女作家最終選擇了寫作事業而非生子:Sigrid Nunez細數西方女作家生或不生的抉擇後,仍認為「最重要的事」是寫作;Kate Christensen也表贊同,她說:「別的事,成千上百」。女性主義史學家Peggy O’Donnell Heffington在《沒有小孩的她們》中的章節名稱不就是〈因為我們想要其他人生〉?以此詮釋了正值生育期的女性抉擇。
較諸於「別的事」長出來的投資報酬率,母職的「成就」相對模糊,終日勞動換來的總是無盡挫折。〈長生萬物〉中的「她」,費心於孩子教養,為了餵飽家人,認真學習料理,卻在一次看似微小的失誤上,迎來了女兒的憤怒。這篇小說除了果蠅、蘋果等值得追究的細節外,我以為豬肝料理的片段更為尖銳:小說先羅列出食譜繁複的細節,顯示主婦日常真是要了命的細瑣,但更致命的是,即便按部就班操演的「她」,卻無法徹底滌淨豬肝的血水,於是丈夫和女兒對「她」是否是稱職的母親,產生了懷疑、抱怨:魚沒熟、家好髒。再一次,「長生萬物」的植物意象有了逆反式新詮,耗盡養料,掏空自己,然後呢?欣欣向榮的美好未來始終未來,滋生的反倒是「我/妳不夠稱職的」指責與深層挫敗。
即使如此,母親仍令人嚮往,對於年輕女性來說,那或許是維繫愛情、改變現狀、晉升新人生的身份。〈滿花〉裡的大學女生「聽見他(戀人)對貓自稱父親的那一天,就是她的愛發生的那一天,隨後她也開始自稱是貓的母親」,於是當戀人內射,他們孩子的面孔就愈發清晰,不過兩人卻仍走上了「反曖昧期」,重瓣玫瑰在枯死前的盛放,如同她最終無效的力挽狂瀾。與其說這篇小說探究生養議題,我認為作者更細膩刻畫年輕女性的幽微心理和處境:對美好性體驗的嘗試,對家庭的模糊憧憬,然在避孕這件事上,卻也承受了不平等待遇。同樣地,「滿花」的意象再度與女性的生命形成高強度反差,滿溢出來的不是攀上頂峰(連分手前的性愛都反高潮);或至少搆到幸福邊邊的女性典範(那是什麼?是「真正」地熟成為一個母親嗎?)她,最終只能被棄。
那麼已停經的女性呢?〈貴子〉反倒提供了一個相對圓滿的版本,不同年齡的故事、情事、性事在此交會,失聯的人生,在一個幻想有兒子的女人口中,開枝散葉,竟成為與另一個年輕男子建立友誼的媒介,花粉一般。奇妙的是,前面幾篇小說中對幸福之家的憧憬和幻滅,竟在這篇小說中有了相對明亮且溫暖的結局,多元而包容的家悄悄形構,而第一篇那個將自己和嬰兒從頂樓拋下的女子,似乎也在另一個女人的回憶中再活了一次。
依循植物繁衍象徵意涵建立起來的五篇小說,不時可見林文心隱藏的「逆生長」線索,這些線索收束了女作家對女性、對母親情思、性事、家庭的詰問。於是,在繁花盛開的台灣文學及女性小說花園中,《滿花》仍開出亮麗新品種。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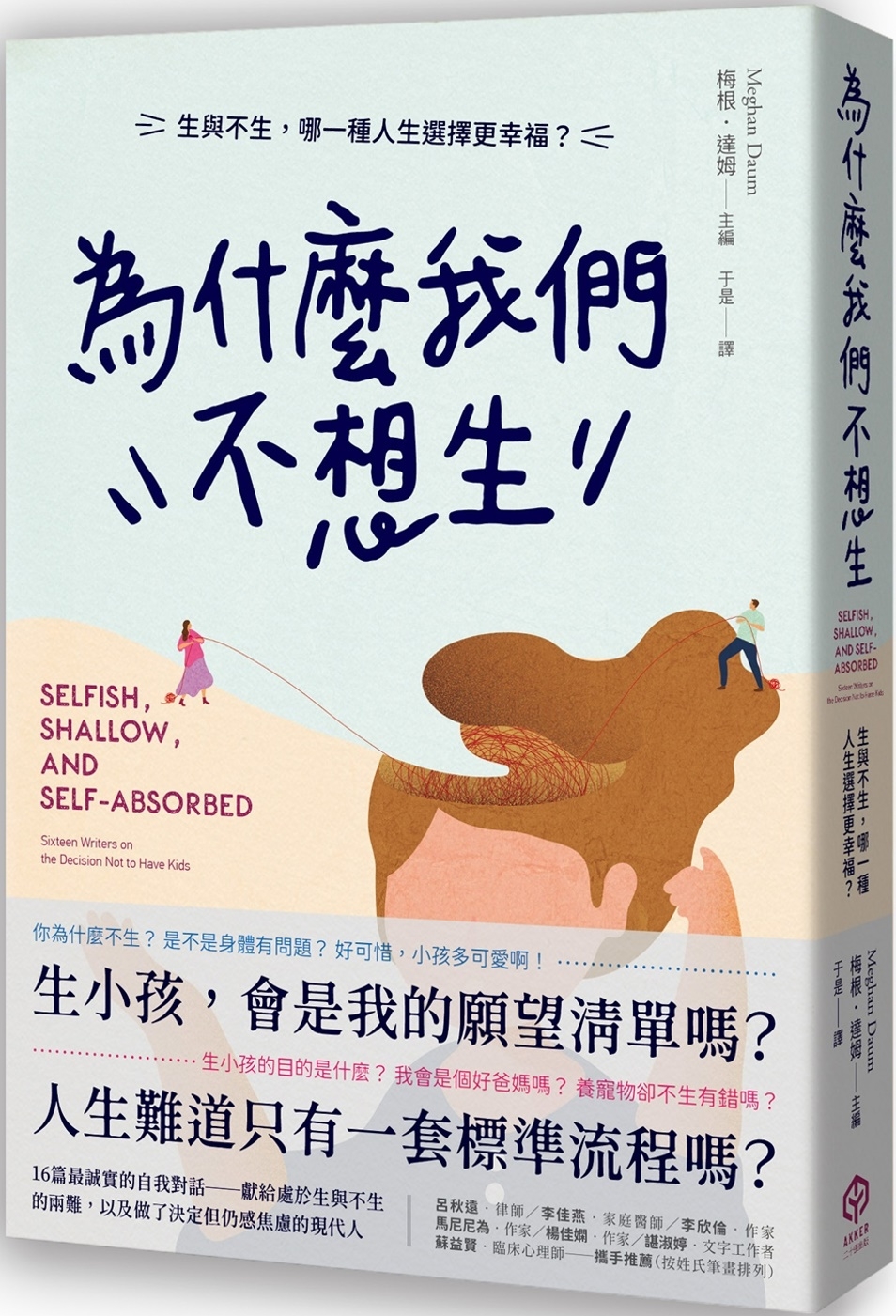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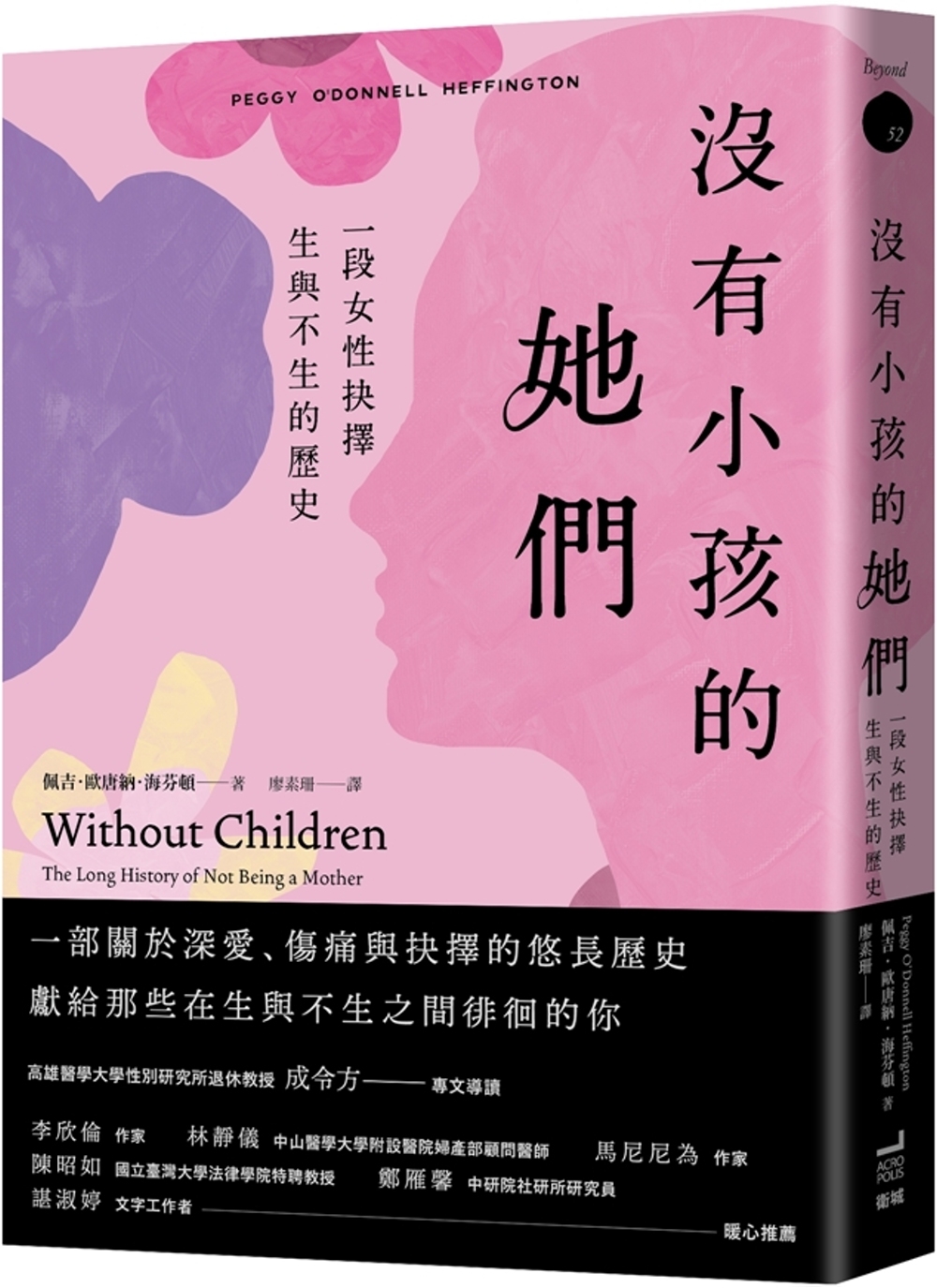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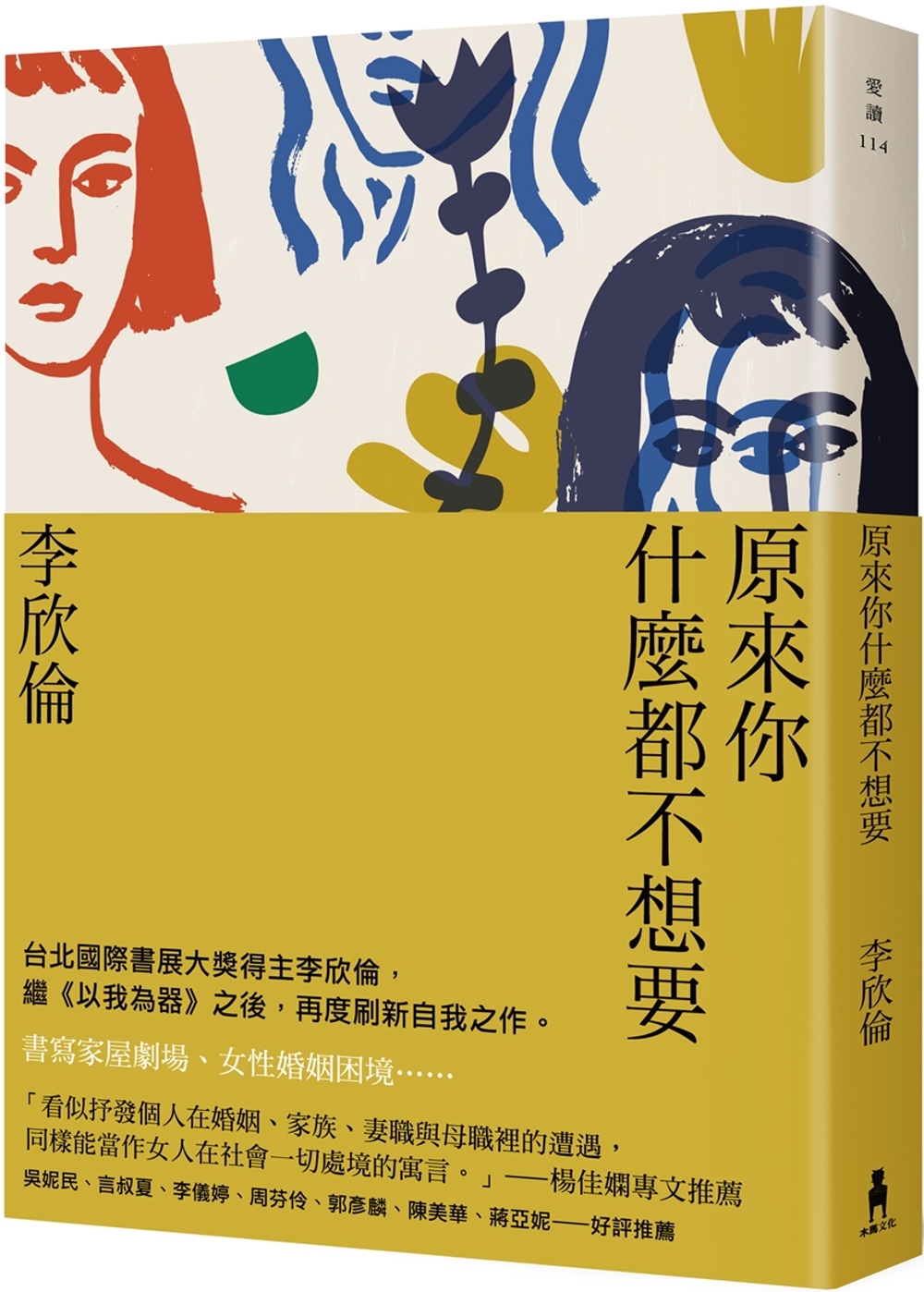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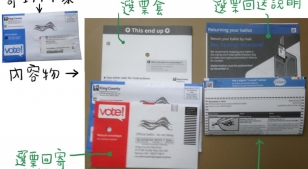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