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期熱播的影集《八尺門的辯護人》中有一段饒富意味的情節:
女學生應徵工讀生,誤成詐騙集團的車手。於公設辯護室服役的替代役男連晉平對女孩解釋:「妳沒有故意,妳不知道這是違法行為⋯⋯」話還未說完,便被公設辯護律師佟寶駒阻止,他對女學生說:「妳現在只有兩種選擇,認罪或不認罪,因為法官不會相信有人笨到不相信這是違法的事。」為此,二人起了爭執。
「我覺得這樣不對,她真的不懂,你為什麼不幫她爭取?」連晉平質問。
「司法系統就是這樣,有人會笨到被騙幾百萬,但法官卻不相信有人會為了幾千塊被騙去當車手。所以就連笨也有兩種標準,懂嗎?」佟寶駒說。
「不懂。」
「雙重標準,懂嗎?」
「不懂。」
「那求刑減刑,懂了吧?」
「不懂。」
然而,她笨嗎?什麼是笨?司法系統裡有關笨的雙重標準又是什麼?
民國八十六年的冬天(註一),某位女子遭綁,其夫接到綁匪電話勒索贖款,地點金額仍未確認,隨即又接到警方電話要他去認屍。女子被人發現陳屍山區,疑遭人勒斃。現場採到五枚指紋,卻苦尋不到兇手。警方收獲情報,有民眾說感到靈動,從中看見駕駛白色箱型車的男子是嫌犯,男子的身分是死者丈夫的高中同窗。警方以協助辦案的名義約談該男,他不知道此舉將改變自己的餘生。偵訊室裡的事,他後來寫進給親人的家書裡:警察對他言詞恐嚇,煙薰毒打,不吃不喝逾三十個小時,甚至威脅要對其家人做出一樣的事。惶恐害怕,疲憊至極,不堪負荷,最終於逼供下簽了自白書,被迫承認與死者有債務糾紛,相約見面,一言不合便以鞋帶將其勒斃,隨後駕車至深山棄屍。
警方憑此自白書,將其關押。但現場採集的跡證,無論毛髮、指紋、DNA,皆非該男子,連屍檢報告所稱之凶器亦非鞋帶。警方將其押至兇案現場進行模擬,可他陳述的內容與筆錄有諸多不符。眼見故事兜不攏,警方便示範、誘導他依筆錄內容說話。指認棄屍地點時,警方嚴詞告誡:「你現在說的時間方向地點都不對,你說,屍體丟在哪?是不是丟在那!」男子面露惶恐地附和:「對⋯⋯屍體丟在那……」
曾有新聞報導如此描寫:犯嫌的那句「對,屍體就丟在那」隨著筆錄與自白書被送進法院,他因此被判處死刑。
滿佈疑點的證據、矛盾百出的自白、充滿瑕疵的辦案內容,不僅無人聞問,更一次次上送到最高法院。男子數次否認犯案,哭訴自己是冤枉的,說了無數次「我是清白的」,但死刑依舊定讞。
事發僅兩年餘,三聲槍響,他被槍決了。
不實情報資訊、違法羈押、偵訊未全程錄影錄音、採集的DNA無法檢測、血型指紋毛髮都不是他、現場模擬存在誘導、自白書可能是遭刑求而簽下,全案定讞單憑一紙自白書,但,他死了。
死了,他沒有後來,世人還有機會看見真相嗎?
他笨嗎?
不只是他,類似的故事還有無數美麗島事件的受害者、王迎先、蘇建和、紀富仁、江國慶、徐自強、鄭性澤、謝志宏、沈鴻霖等。他們之中有人雖擁有了後來,但其後亦受困那段不堪回首的故事裡。他們也曾不止一次地問著:真相是什麼?
他們難道都是笨的嗎?
幾次與朋友們談起司法系統裡關於「笨」的雙重標準以及真相。曾於論述死刑議題的書中讀及作者藉台灣俗語的「雞卵密密也有縫」,談百密一疏,總有遺漏,此話不僅指一般人,同時更指執法者。若人總會犯錯,執法者難道不會嗎?倘執法者有錯,眾人該如何看見真相?朋友聞言後說:「這是因為『恐龍法官』太多了,如果他們有權決定最終的結果,他們就該要看見這些問題。」
人們談「恐龍法官」,指稱其不知人間疾苦,對受害者缺乏同理心,作出與民間意見相去甚遠的判決。但當指稱他們對受害者缺乏同理心時,那對於法庭上等待被仲裁的被告呢?若法庭是為了被告與真相而存在,法官不是神,無法窺見事件全貌,其所擁有的判決權是白紙黑字寫下來的條規,於此景況,他能做的是什麼?
多年前於法學課堂上,教授以「如果你是法官」為題,請學生重新觀看思考司法史上幾次具爭議性的判決,並問:倘若你是該案法官,你會作出相同的判決嗎?有位同學提出一個觀點,至今仍讓我印象深刻。他說:「如果審判非由法官意見做為唯一的決斷,而是由更多人共同審視,彌補社會經驗與個人觀點的不完備,或者減少政治力介入,結果是否就會不同?」
他所言即是近似「陪審團」制度的概念。然而,由更多人審視案件,真能彌補經驗與觀點的不足,更接近真相且作出相應的判決嗎?
《成為惡人之前》一書寫下映照出這些問題的可能路徑。
作者溫蒂.約瑟夫(Her Honour Wendy Joseph KC)擁有三十多年的律師與檢察官經驗,後被選任為英國中央刑事法院「老貝利」(Old Bailey)的法官。她藉六起殺人案(包含青少年持刀殺人案、母親殺嬰未遂案、青少年幫派鬥爭案、宗教名譽殺人案、軍人PTSD殺人案、受家暴妻子殺夫案),帶領讀者理解法界中各種角色的功能,英國陪審團制度的規定、內涵與底蘊,法庭秩序如何維護與進行,刑責該從何裁量,以及陪審員該如何看見、思考於法庭上所見的證據,並依此作出公正判決。法官的職責,是設法讓陪審員們更接近「真相」。
@EthicalForum excited to meet HH Judge Wendy Joseph at Old Bailey #InternationalWomensDay pic.twitter.com/v9yWO87Vzf
— WIEFF (@EthicalForum) February 12, 2016
書中,作者著墨最多的有二處:
一是量刑。書中案件看似「罪證確鑿」,於不明箇中曲折的人眼裡皆是罪無可恕;但真實並非平面,而是多維的,具有表裡,擁有毛細,持續呼吸。真實生於證據,證據雖不一定皆能抵達真相,卻可作為標誌,指引人們前行,前往更靠近真相的地方。身為法官的作者,協助陪審員細看多維證據的表裡毛細,與其共同呼吸,嘗試釐清事件的原貌。有了真相,才能判決,而後量刑。量是度量,罪惡無法度量,人性無可尺規,但社會若要穩定運作,法律為其秩序的根據。於是在書中,她藉規範與機制讓陪審員能有效地觀看真相,作出合理的判決,更依其量度相應的刑責。唯有真相現形才能讓法律發揮它應有的功能,如此,才可能以最適切的方式量度罪與罪人應當付出的代價。
二是關懷。關懷不是濫情,而是給予各方平等溝通的可能。法庭裡,加害者不一定是真正的罪人,受害者亦非絕對的無辜,不同視角裡,他們都可能是良善的一方。犯行或許僅一剎那,但罪惡並非瞬間生成,每種世人所以為的「惡」都有其歷程,有前因後果,如同人的成長都有一段漫長的故事;關懷亦不是憐憫,書中的她不談寬容,並非寬容如此艱難,而是陪審員的角色不是寬容罪犯的聖者,法官亦不是寬容罪犯的神。那麼,不具備寬容之心的人是正義的嗎?正義的本質是否應當包含柔軟的母性,如同悲憫之心?於是在書中,她從另一個角度談悲憫,悲憫應該是在罪惡形成之前,人們對於需要幫助的人伸出援手,對於逆境與痛苦給予關愛。不該在罪惡生成之後才展現正義的價值,這是彌補,而非救助。於此,國家在司法制度中應該扮演什麼角色?難道制裁罪犯就夠了嗎?如果國家無法找出有效預防罪案發生的機制,光是制裁罪犯,也只是亡羊補牢。唯有意識到這些,才可能達成犯罪防治。當社會無法防止一種可能的悲劇發生,悲劇就會因為社會的無能而持續存在。
台灣的「國民法官」制度已於今年元旦上路實施,雖與本書的英國陪審團制度有所差異,卻可作為借鏡,透過此書映照我國當前司法制度的問題,同時捫心自問,關於司法系統裡是否存在雙重、多重標準,我們是否有一天也可能因此被迫要裝「笨」,被迫承認不是我們所犯下的罪行。或者,我們未來也將會坐上陪審團的位置,到了那一刻,我們能否看穿偽裝,走入真相,作出相應的裁決?
詩人楊牧於1984年寫過一段詩句「有人問我公理與正義的問題」。詩句背景生成於美麗島事件之後與江南案之前,至今仍為許多後進引用與延伸。若有一天,當我們坐上陪審團席位,面對「公理與正義的問題」時,我們是否有能力回答所見所聞的一切疑題?我們能否認知到每一次判刑的確立,意味著整個社會都必須承擔此判決的後果,因為我們也可能是下一個受害者或加害者。
我們能否認知到在「成為罪人」之前,一切存有真相。如果沒有真相,我們如何定義罪責?如果沒有真相,我們又如何談論悔罪的可能?罪責若無法與悔罪有關,罪惡又該如何止息?在罪惡與罪罰之間,存在的是我們社會中的每一個人。判決若與真相無關,成為罪人的便是身處社會中的每一個我們。
我們能否於公理與正義之下,在那可能是惡人的面前,於他被判罪,確定為惡人之前,給他一段說出真相的時間。
註一:完整內容詳見公共電視紀錄觀點《島國殺人紀事2》,導演蔡崇隆。
註二:本文部分法學論述概念引用自《殺戮的艱難》、《扭曲的正義》、《無罪的罪人》、《死刑肯定論》、《冤罪論》、《與死刑拔河》、《思索斷頭台》。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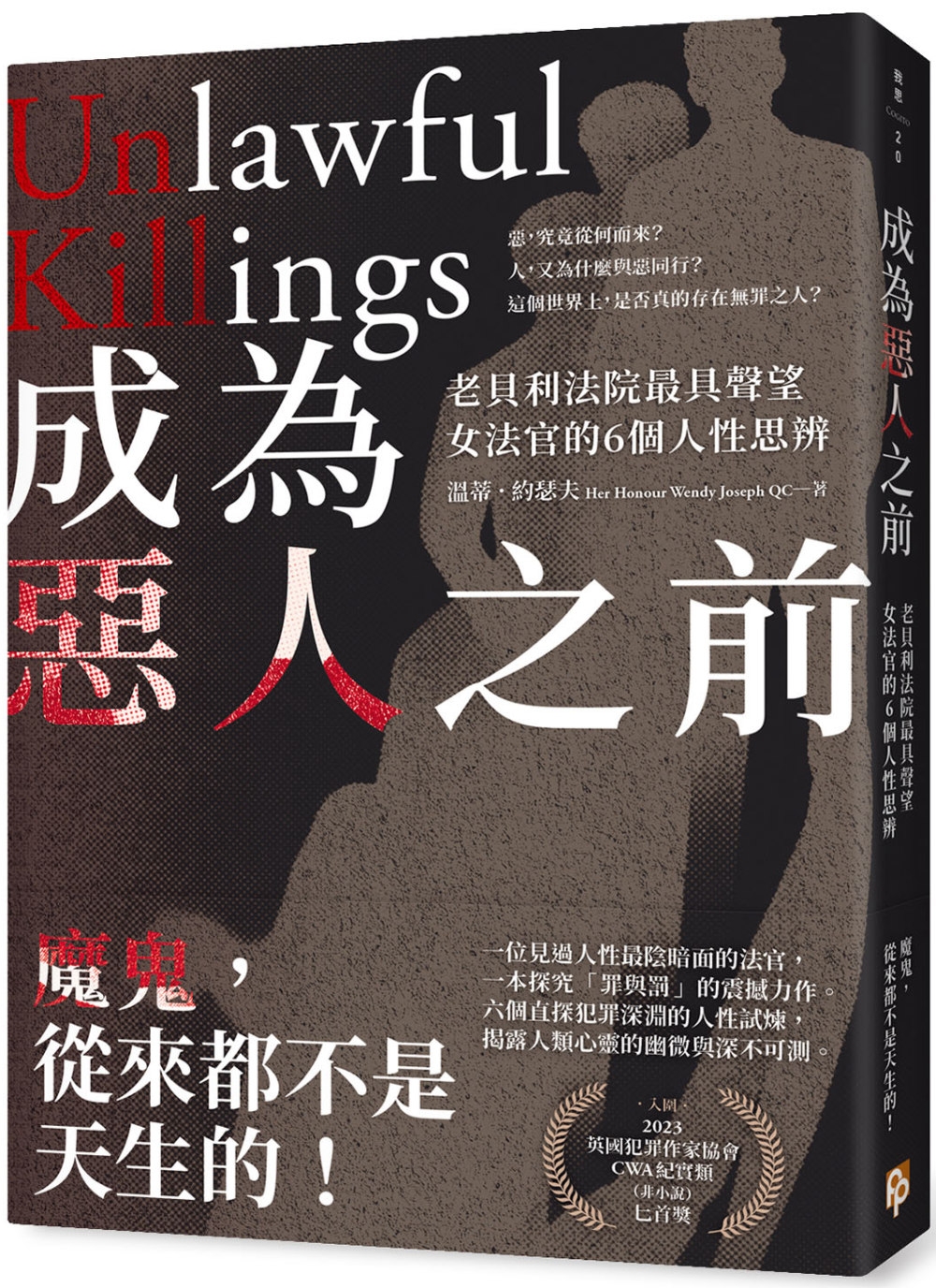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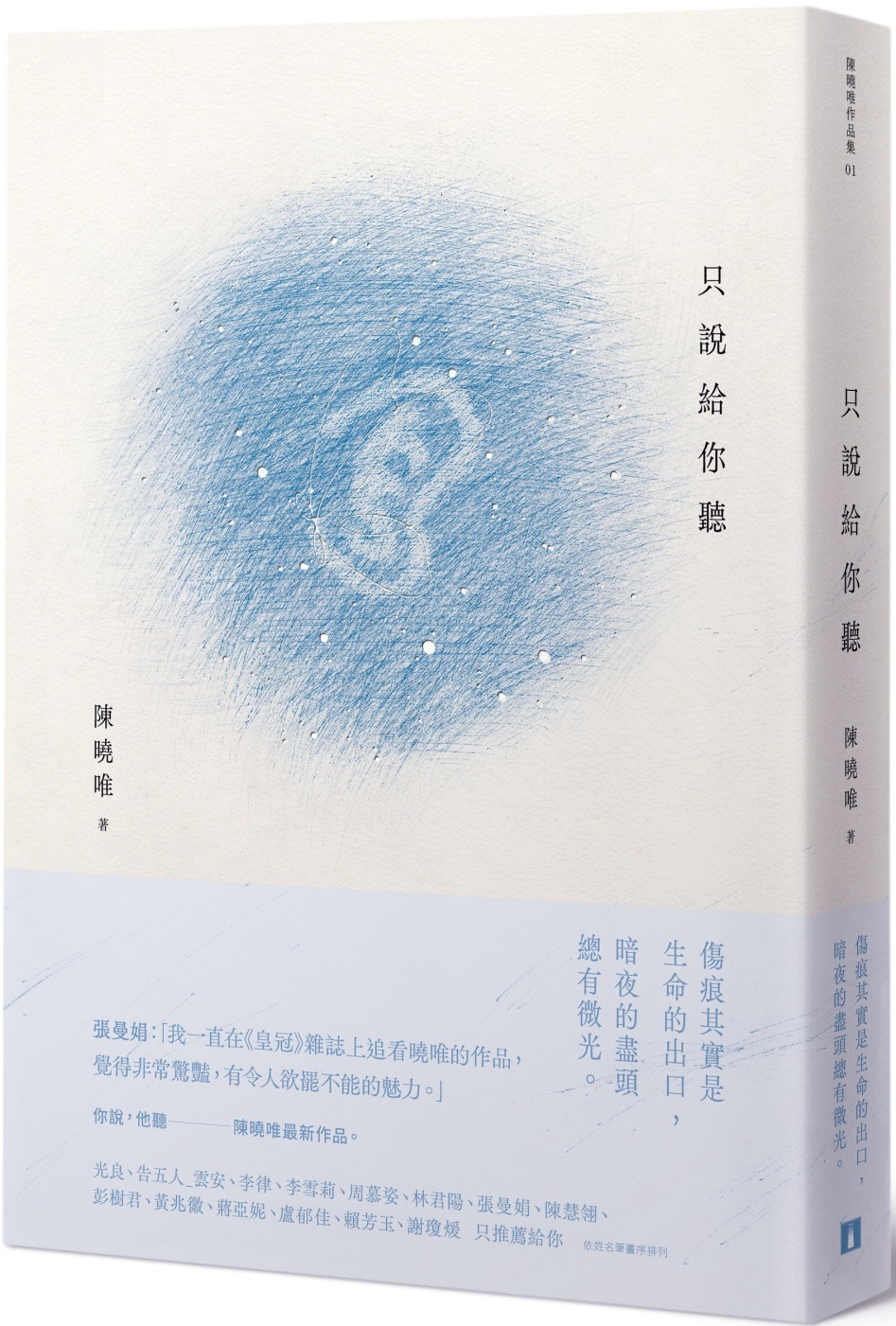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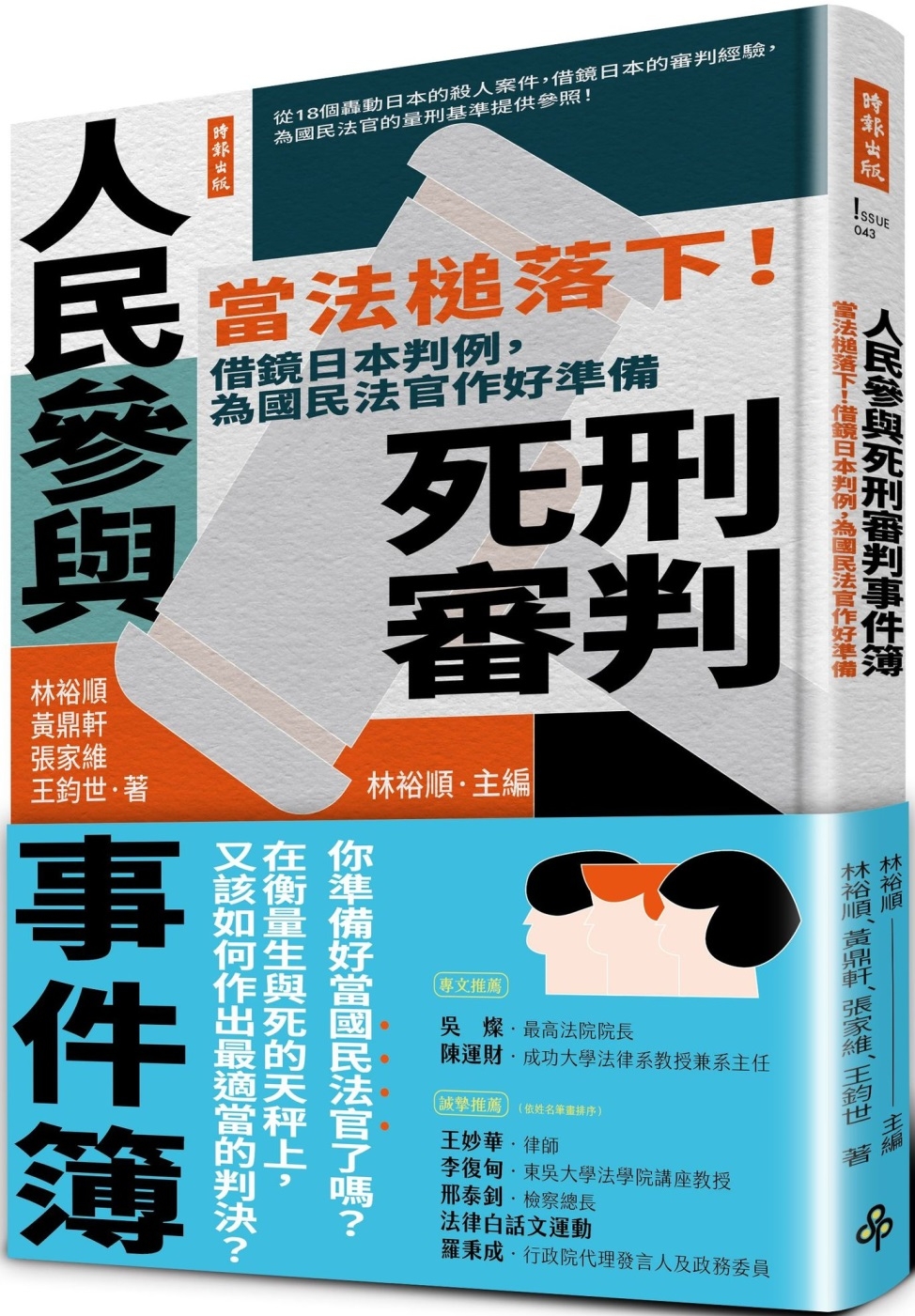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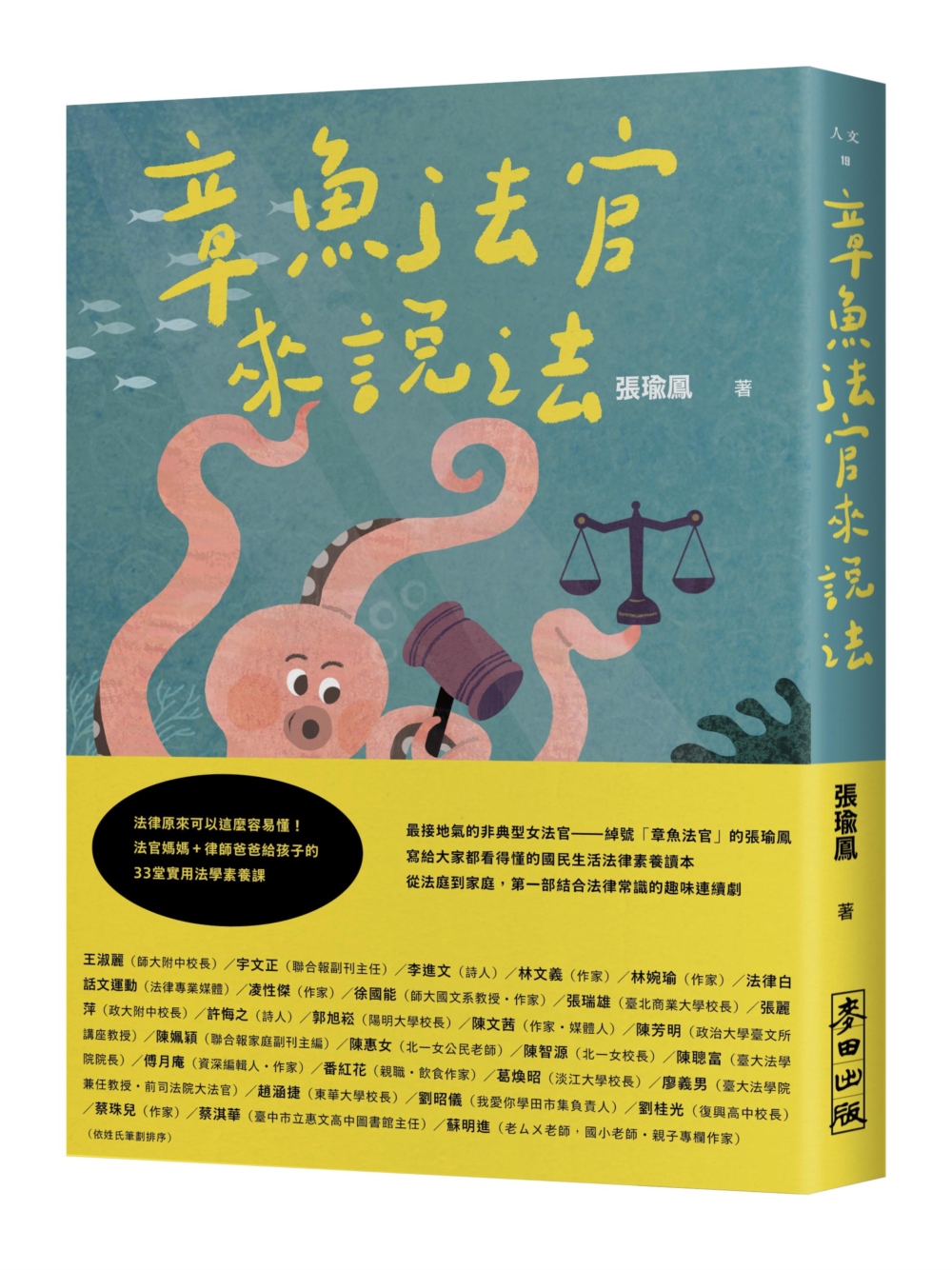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