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從一個文學創作者,改投身進工人運動的這幾年,時而想起,美國哲學家桑塔格曾經探問,如何「更有道德」地旁觀他人之痛苦,她將旁觀的情感分為兩種:憐憫和同情。前者是站在更高的位置俯瞰,疏離地停在「我知道你痛苦」。後者要投入更多想像力,將自身放在和他人平等的位置,感同身受他人之痛苦。兩種情感的道德價值或有高下,但都意味「責任的局限」,觀看者對事件當下無能為力,已經和被觀者拉開時空的距離。
但,如果越過旁觀的位置,嘗試以實際行動,改變他人之痛苦時,人應該為他人之痛苦負責到什麼程度,又應該抱以何種情感面對他人呢?這並不只是,文學和藝術如何介入社會的抽象辯證,對工人運動而言、對組織者如我而言,是實際鬥爭存亡的路線選擇,也是黛西.皮特金(Daisy Pitkin)《飛蛾撲火》欲探究而未竟的核心命題。
黛西25歲的時候,投身為美國紡織成衣工會的組織者,第一個協助的,是跨國集團索迪斯位在鳳凰城的洗滌工廠,並在其中結識了工會頭人阿爾瑪,兩人並肩作戰、組織工會,共同經歷各種困難,建立起無比深厚的革命情感。
從外觀來看,《飛蛾撲火》分成「蛾」和「火」兩條線交互敘事,前者是黛西和阿爾瑪的故事,後者則上溯美國女工抗爭的歷史傳統。寫作手法上,黛西採用書信體,承載她對阿爾瑪的叨叨絮語,然僅能為單向的通訊,因其敘事伊始,是黛西和阿爾瑪的組織關係已然裂解、個人關係隨之崩壞的其後。通書情感充滿對主體修復的深盼,想對阿爾瑪告解,昔日在鬥爭中,組織者「不能」或「不敢」讓工人知道的內面私我。
在 Instagram 查看這則貼文
究竟什麼是組織者呢?表面來看,工人理所當然是工人運動的抗爭主體,組織者多為知識分子,像是來自外部的「他者」。資本或社會大眾的模糊理解,組織者更像「滋事分子」,是在抗爭現場靠衝撞換取議題曝光之人。然而實際上,組織者真正的工作,或說更深層、更日常的工作,其實是「培力」,協助以為自己沒有條件反抗、只能安分認命的工人,去改變自己和資本的關係,轉化為工人運動的抗爭主體。也賴於此,組織者才能在工人運動中成為主體。
要將工人轉化為抗爭主體,是一件非常難的事情。
諸多以勞動為題材的文學作品,例如臺灣讀者熟悉的林立青《做工的人》,大多會描述工人在勞動現場經歷過的苦難,然其以為改變工人苦難的方式,是寄望社會大眾能有更多同情的理解,進而影響國家法制,而非工人團結起來抗爭。少部分意識形態偏左的作家,例如楊逵的〈送報伕〉、陳映真的〈雲〉等,描述工人在苦難中,體悟到社會結構或勞資關係的不平等,最終起身反抗,但這是種簡化的敘事方式,反抗的結果是成或敗,楊逵和陳映真都略過了中間的過程,也略過了抗爭主體內心的反覆和成長。《飛蛾撲火》誠是以非虛構寫作,去補足這個在文學中、在報導中都較少被再現的部分,其作為起點的提問是:為何承受同等苦難的工人,選擇會截然有別?
顯然,從痛苦到反抗,並非線性的過程。阿爾瑪問黛西,也問自己,我和其他工人為何不同,是因為有人比較憤怒、有人比較害怕嗎?黛西當下以為,戰鬥者和不戰鬥者的差別,不在憤怒或恐懼,而繫乎願景,繫乎人能否想像到「戰鬥的好處」。戰鬥的好處,就像懸在驢子眼前的一根蘿蔔,對大部分工人而言,指的是直接的經濟利益,吃到了,就可能停下來,一直吃不到,也很難撐下去。然而,戰鬥的好處難道只是存乎人外部的事物嗎?黛西在多年過後反思,戰鬥的意志,「可能是一種變態,一種極度渴望改變,以致自己被改變了的狀態。」黛西用一個唯美的譬喻來形容這種由內而生的改變:抗爭者就像毛蟲,要徹底溶解自己原有的身體,爆發成全新的存在,化作撲火的蛾。
「蛾」象徵抗爭主體,「火」象徵工人運動,兩者的對位關係,也是工人和組織者的關係。
在《飛蛾撲火》中,黛西屏棄在美國的工人抗爭傳統中常被放在歷史主線、以男性工人為主的鐵路工會,而以「國際女裝服飾工會」為起點,對阿爾瑪娓娓道來,1909年的紡織女工克拉拉 ( Clara Lemlich )在群眾大會公開反對男性頭人的妥協路線,發動史稱「兩萬人抗爭」的總罷工。但一場總罷工並不足以改變所有紡織工人惡劣的勞動條件,幾年後,不顧勞動現場安全的三角襯衫工廠發生一場導致上百人死亡的大火,成為美國社會深刻的集體記憶。
 克拉拉 ( Clara Lemlich, 1886-1982 )在1909年發動史稱「兩萬人抗爭」的罷工 。(圖/wiki)
克拉拉 ( Clara Lemlich, 1886-1982 )在1909年發動史稱「兩萬人抗爭」的罷工 。(圖/wiki)
 「兩萬人抗爭」(Uprising of the 20,000)現場。(圖/wiki)
「兩萬人抗爭」(Uprising of the 20,000)現場。(圖/wiki)
克拉拉的故事,代表工人運動中的性別不平等,女工想反抗資本,要先反抗滿足現況的男性頭人。且不只是工人的身分,克拉拉而後如黛西成為組織者,也要面對和其他男性組織者間的不平等。黛西的取捨,是藉性別位置,拉起她和阿爾瑪間更多的共同點,更是以自身選定的路徑,引領阿爾瑪從勞動現場的微觀鬥爭,往上走進更高維度的工人運動,這同時意味著思考座標和時間座標的新生。
然此際的新生,終究也存在著權力關係。明明阿爾瑪是在工廠內部更有影響力的頭人,何以傳道授業者,反而是年少資淺的黛西呢?工人通常是身體歷經痛苦,而後改變了思想,知識分子則反過來,是被思想感召,選擇成為組織者,組織者通常具備更好的論述能力、更高的文化資本,也更有條件占有工人運動的領導權。
工人真的都能信服組織者的領導嗎?在抗爭張力最強的時刻,阿爾瑪也會反問黛西:你和我們不同,你領著工會的薪水抗爭,你不會因為戰鬥而被解僱。
我作為空服員工會的主要組織者、長榮空服員罷工小組召集人,也時常被質疑:推空服員前進,是在推空服員去死。然而,我曾因對時機的判斷不同,幾度勸說她們不要罷工,我也曾在罷工只有部分成果、空服員想採取更激烈方式抗爭時,再度強烈反對。同一時間發生的故事是,在連日暴雨終於暫停後的罷工棚,某個空服員靠著我肩膀,用忍著淚和鼻涕的聲音說,「我不想放棄,我真的不想放棄。」我問,「為什麼?妳會這麼說,就是想放棄,那為什麼還不放棄呢?」她說,「因為我覺得不甘心,因為會員覺得不甘心。」
我擦乾自己的眼淚告訴她,「妳想哭、妳要覺得害怕都沒有關係,沒有人知道罷工最後會變成什麼樣子,但妳一定要答應我,去見董事長的時候,絕對不可以哭,因為妳是空服員工會的幹部,代表空服員工會的時候,就算全世界都不認同,也要相信自己是一個可以跟董事長平起平坐的人,妳的尊嚴,就是空服員工會的尊嚴,也是我的尊嚴,所以妳去見董事長的時候,絕對不可以哭。」
她說,「好。」然後,她直到現在都沒有放棄。
何時要繼續、何時要放棄,對單純的旁觀者而言,只是程度和策略不同的方法論,但對工人運動而言,是人如何決定自身的存有論。如果不選擇行動,工人可以繼續用抱怨作為抒解,知識分子也可以只是站在高位消費弱勢的政治正確,但這麼一來,現實永遠不會發生質性的改變。工人運動是動員工人以改造社會的過程,改造外部社會的前提,繫乎在每個行將爆破的時刻,組織者能否協助工人,工人能否起身完成自我的內部改造。
這個過程,或比單純被剝削更讓人難以忍受,是以許多的組織者、許多的工人,像黛西和阿爾瑪,培力有時,裂解更有時,畢竟進入他人之痛苦,也意味著自我被他人進入,要承受更多一分他人之痛苦、集體之痛苦。面對集體之痛苦,阿爾瑪是「毛蟲」,黛西也是「毛蟲」,都要溶解原有的身體,都可能在化蛾以前,中途被剖開繭,只餘下一團漿液。
《飛蛾撲火》羅列了美國女工抗爭的歷史傳統,也深描了組織者和工人相互面對痛苦的過程,像臺灣工人運動組織者吳永毅的《左工二流誌》,要解決的難題是「人如何繼續運動」,黛西所欲之路線,如其後記言,她主張工人運動應由下往上,以關懷取代憤怒來驅動人,想望一隻蛾不靠外部因子,自身就能飛行向光。這條路線是否能通過檢證尚未可知,或只是理想,或只是象徵,但應可作為你我進入他人之痛苦時,面對殘酷之餘,有份溫暖的私存。
《飛蛾撲火》是一部漿液之書,也是一部修復之書,黛西終能在多年過後返身工人運動的集體隊伍,漿液得以修復為毛蟲,或可期盼,黛西下一部真正的「蛾」和「火」之書。同為組織者,更盼,眾生作繭千百度,皆終能化蛾開翅,讓嚙咬葉子的聲音,於焉響滿人間的樹林。
作者簡介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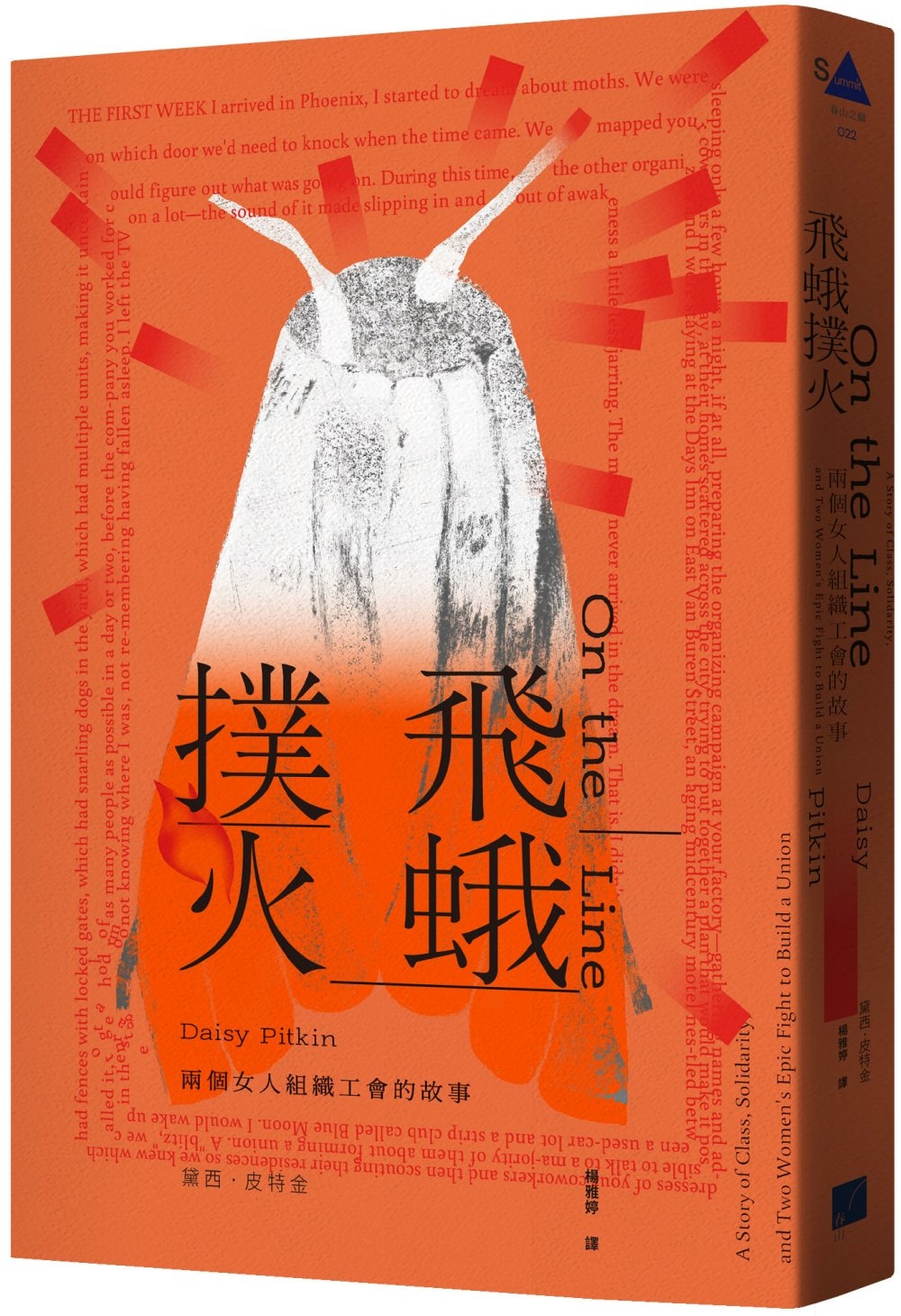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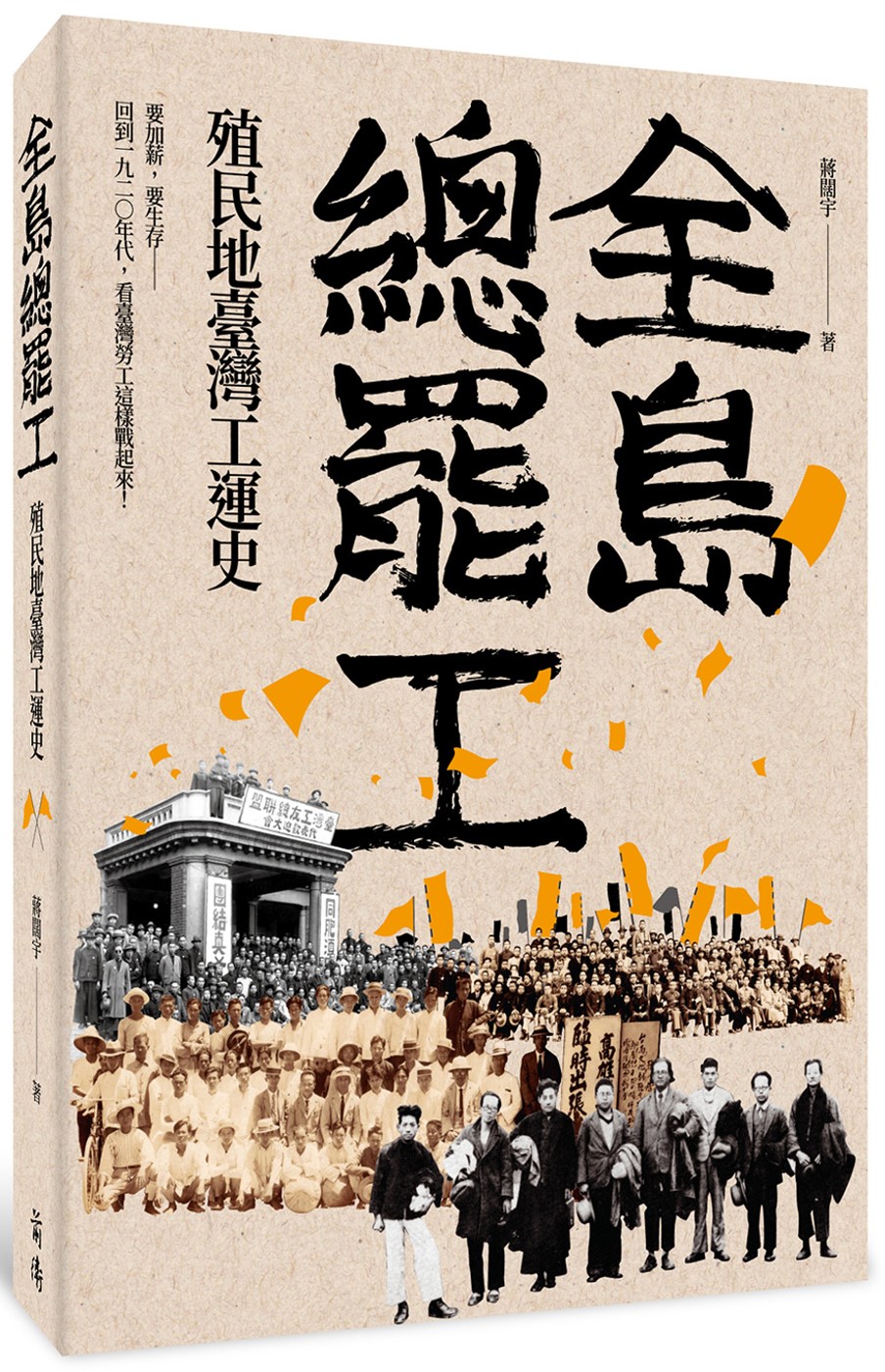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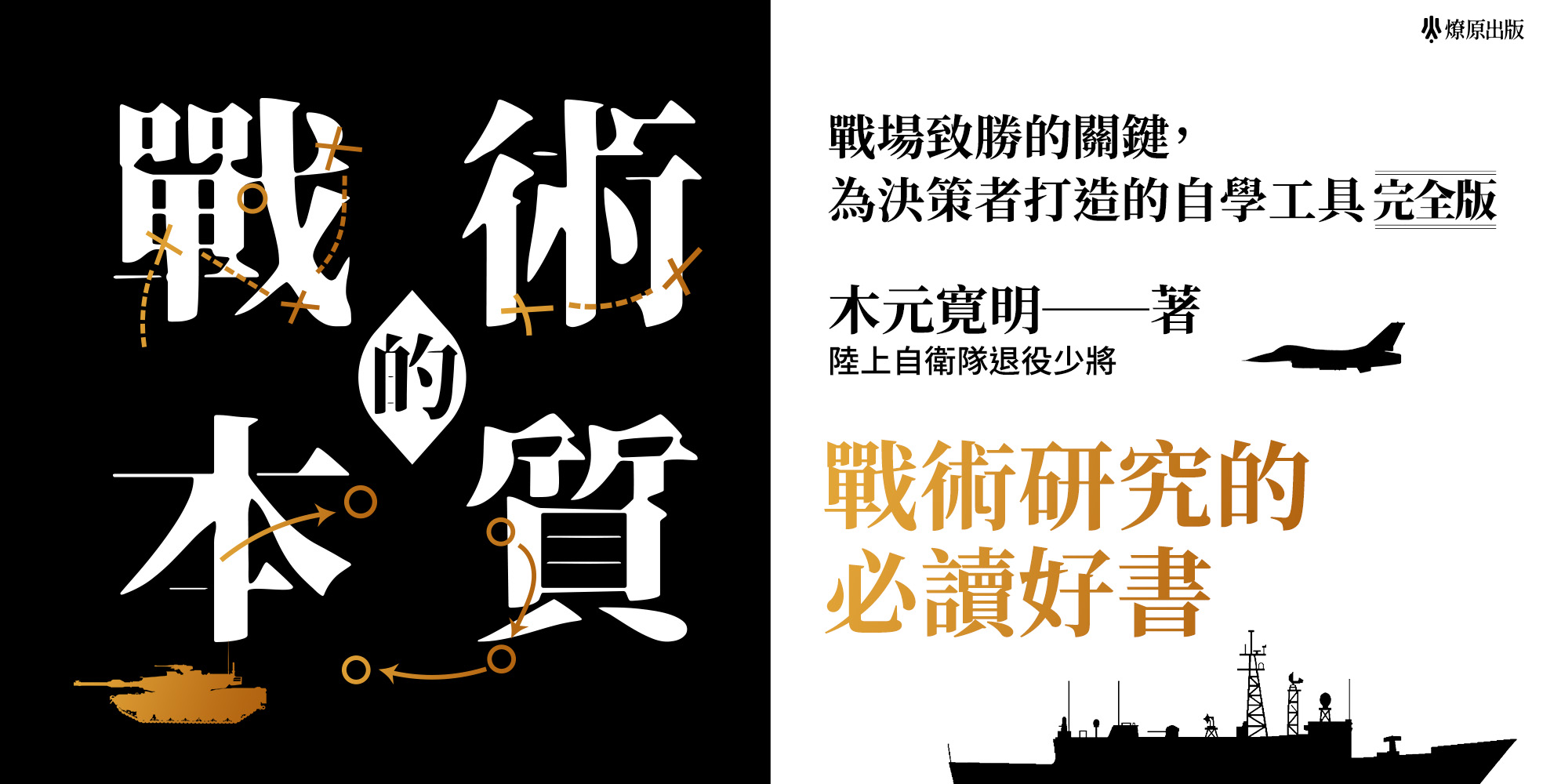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