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幽暗的地方燒出火花────
當代的美洲文學,怎麼發聲?
怎麼更新人類的表達?
我的簽證要我每三個月離開美國一次。去哪呢?鎖定中南美洲。哪一個國家呢?我打開瀏覽器,在搜尋欄位輸入「democratic school」,找到了祕魯高原上的一間民主學校。我寫信問他們,能讓我去當志工嗎?我好奇世界各地的民主學校怎麼運作?學校架構怎麼回應不同特質和學習節奏的孩子?學校怎麼落實民主和自由,遇到什麼困境?祕魯的文化底蘊是什麼?那裡的孩子做著什麼樣的夢?不久,我收到校長的回信,他簡介學校的第一段文字是這樣的:
一月中,暴雨到來,直到四月底才停。五月,雨水在枯萎,滿足的大地歡樂。植物在雨季默默伸展。田野迴盪綠意。六月,植物有些發黃。七月和八月,夏天已經滿了。天空由非常特殊的藍色和乾淨的雲層組成,很深。那時,風最淘氣,彎曲靜止的樹枝,撞到沉睡的牆壁上。九月中,浩瀚的雲層緩緩出現在東部山脈的上空,停在地球的上空互相擠壓,直到它們成為一體;它成熟了,它變暗了,墜落,一個又一個,形成第一場大雨,又一場猛烈大雨,然後另一場。閃電在黑暗中閃爍,夾雜雨水,雷聲在遙遠的地平線後面墜毀。雨一直下到十月。雨有點累了,停下來,十一月又繼續。十二月,雨再次暫停,一月中旬重新開始。
讀到這麼動人的描述,我立刻訂了秘魯的機票。
寫下這段文字的安利奎.加巴哈(Enrique Carbajal)不只是祕魯民主學校的校長,還是祕魯的小說家。常在學校看見他默默勞動的身影:洗校車、拿鏟子挖洞、鋸木頭做學生的大型溜滑梯、為學生手作的每一輛木製小卡車鑽出圓形的車輪。每天清晨他開校車去瓦馬丘科(Huamachuco)鎮上接一批學生到山上的學校,再開車下山接另一批學生上山。午後放學,也開兩趟校車送學生回家。忙碌了一整天,聽說,半夜他才走進自己的書房,靜靜看書、寫小說。
我沒有親眼見過他的書寫勞動,但我每天見到他揮汗而不停歇的身體勞動。尋常的一天,他鋸斷桉樹的樹幹,刨掉樹幹上突出的枝節,磨平表面的木刺。整個下午他帶著學生安靜而奮力地刨出六根長直的木條,鑽洞栓接,打造出兩座足球門框。框做好了,他們扛下草坡,來到一座廣大的平原。他趴在地上,向下鑽洞。臉貼著土地,把手臂放進洞裡丈量深度。不夠,就再向下挺進。
手臂發顫了,他仍舊不留一點餘地給輕忽和任意。勢必要把足球框牢牢紮進土地,一如那是從地心長上來的。持續開鑿,持續丈量。灰頭土臉也掩蓋不住他發亮的眼神。他全情投入去對峙的,不是地底的洞,而是他追求精確的深淵。抵達精確之前,他的氣力沒有耗盡的可能性。或是說,未知總在引逗他的氣力一點一點擴展開來。
 Enrique Carbajal 帶孩子自製足球門。(攝影 / 吳俞萱)
Enrique Carbajal 帶孩子自製足球門。(攝影 / 吳俞萱)
 在草地上挖洞,安插足球門。(攝影 / 吳俞萱)
在草地上挖洞,安插足球門。(攝影 / 吳俞萱)
 Enrique Carbajal 伸手丈量地洞的深度。(攝影 / 吳俞萱)
Enrique Carbajal 伸手丈量地洞的深度。(攝影 / 吳俞萱)
氣力沒有底的 Enrique,他創造的小說世界是什麼樣子?日光無盡的某個上午,我躺在學校草坡上讀他的小說《過去的故事》(Cuentos de tiempo viejo),我用翻譯機把他的西班牙原文翻譯成英文,好不容易讀完第一篇〈風〉,納悶自己是不是漏讀了什麼?肆虐的惡意,從何而來?小說中扯掉一切的男人也扯掉了我的閒散。我打直脊椎坐好,仔細重讀每一個字——
山下,寂靜的大地在溫暖的午後沉睡。山上,農舍傳來幾隻公雞褪色的歌聲。山腰,一處黃色的小山坡,農場的盡頭,一家人趕著為堆積成山的玉米剝殼。他們持續勞動,一堆彩色玉米露了出來。
驢子昏昏欲睡地在乾枯的蘆葦叢中咀嚼。午後在長大。那一刻,家中的某個人一語不發,睜著眼睛觀察陽光下的時間。其他人,家中的任何一個人都發現了一個心煩意亂的男人正輕輕地從稀疏的山丘往下爬。靠近的時候,他們看到一個醜陋的人。「我們的基督徒」,父親這樣告訴大家。下來的是一個矮人,臉色陰沉,裹著一件破舊的緊身斗篷。他全神貫注地向下走,時而穿過多石的群山,時而穿過寂靜的群山,沒有保護自己避免受傷的一雙農家涼鞋。斗篷末端的每一次移動,掀起一股可怕的風吹彎平靜的植物。他就這樣,一路下山。
當他從山谷的一個洞裡消失時,一陣惱怒的大風促使他吸一吸鼻子,他上山去扯掉了農舍的屋頂、動物、植物和更多的東西。
 《過去的故事》第一篇〈風〉。(攝影 / 吳俞萱)
《過去的故事》第一篇〈風〉。(攝影 / 吳俞萱)
Enrique 敘事的意識化為由遠而近的中性鏡頭,毫無偏愛地穿過沉睡的大地、山腰上的農場、勞動的一家人、去殼的玉米。中性,意味著目光停留的時間相近,景框內的物事擁有相等的分量,沒有誰是誰的背景。這樣的開頭,仰賴俐落分層的細節慢慢堆疊出整體的敘事筆法,快照出一個穩定的日常景象:巨大的靜態之中孕育著微細的動態生機。
「沉睡、褪色、昏昏欲睡、乾枯」做為此處生機的調性,構成一種靜滯悠緩的和諧。直到一個心煩意亂的男人現身,以他「全神貫注、掀起風暴」的行走姿態徹底改變了此地的安穩秩序。這個被辨識為「基督徒」的男人為何心煩意亂?為何臉色陰沉?為何專注而堅定地向下走?為何一陣風激起了他毀壞一切生機的行動力?
中性的鏡頭無心,它帶我平等地凝視「陽光下的時間」,無論是寧靜恆定的日常運轉、基督徒的容貌和穿越群山的態勢,或是突如其來的摧毀;唯獨陽光照不進的男人內心,Enrique 沒辦法凝視和揭露,僅僅勾勒出一個突兀而驚悚的場面:一個堅毅行路的基督徒,被風驅動而剝奪一個原始自足的生態系的平衡,吹彎了陽光下的時間。
為什麼 Enrique 以無法丈量的意念和無法抵禦的暴行,做為「過去的故事」的序幕?我繼續翻開名為〈風之母〉的第二篇小說,沒想到那個扯掉一切的基督徒從第一篇跑到了這裡——
孤獨的混蛋。加快腳步的一個男人,望著封閉的天空挾帶風暴的威脅。突然,一場雹暴接著一場又一場,冰雹在孤零零的上空歡快地散開。男人腳步匆匆,跑過一些灰色的大石頭;冰雹已經倒空自己,反彈回來。為了拯救人類,在灰色的石頭後面,一個隱藏的小屋出現了。
小屋中的老婦人,妥善藏起基督徒,哄騙她的四個孩子,避免他們吃掉基督徒。第三篇〈沖洗時間〉中沉睡的河水守候趕路的基督徒,等待把他淹死。在基督徒消失之後的每一個極短篇,Enrique描寫石頭、彩虹、狗、狐狸、妖精、魔鬼、女巫、靈魂……,人有非人的狀態,非人也有人的狀態,就像〈狗與人〉的一座山對另一座山說:「讓我們愛他吧。」另一座山回答:「我們不能,他帶著他的狗。」而〈精靈之夜〉寫道:「妖精睜開眼睛,看著男人,閃電般地沉入水底。男人瘋了。」
獨立的各個短篇之間沒有必然的因果呼應,然而,日常的險境、突發的異象、深不可測的自然力量和命運發展,那詭譎的神話氣息貫穿整本書,成為每一篇故事的心跳。而最後一個極短篇〈被追捕的Juido〉描寫一個被關在黑暗牢獄中的男子Juido成功反抗地主,小說的最後一句:「他還沒有穿衣服,就打開門,又開始無休止地逃離上帝。」
 《過去的故事》書封
《過去的故事》書封


 小說《過去的故事》內頁。(攝影 / 吳俞萱)
小說《過去的故事》內頁。(攝影 / 吳俞萱)
我忍不住跑去問 Enrique:宗教在你的創作中的位置是什麼?你為什麼以基督徒的故事做為整本小說的開場?又以逃離上帝為結尾?幾乎每一個極短篇都在描繪靜態的日常生活被突如其來的暴力闖入,卻不知道暴力所為何來、又指向什麼?為什麼你如此專注於刻劃這樣荒謬而無情的事態?對你來說,這是現實嗎?
Enrique說:「如果妳從學校往北邊看過去,妳會看到向北延伸的兩座巨大山丘和一個湖泊。在那裡,發生了〈狗與人〉的故事。我見過一個人穿過小鎮,他的狗跟在後面。這個人總是孤零零地在路邊,就在最後一縷陽光照亮山頂的那一刻,他不計晝夜地離開了。聽說,許多人在不同的地方見過他。我也見過一個男人突然瘋了,然後突然痊癒,不知道瘋狂和療癒從何而來?我的家人見過死者的靈魂在地球上流浪和哀嚎,見過烏鴉(名為 malagüera 的鳥)棲息在靈魂的肩上,唱著即將死去的人的名字。我認識一些人,他們在死前幾天見到自己。我聽說神話般的鳥生活在盛產黃金的地方。我親眼目睹蜂鳥做為一種神聖的動物而受到極大的尊重。現在,告訴我,這些經歷是真實的,還是想像的?」
他繼續說:「在我們的安地斯世界,人類與超自然元素混合共存是一個尋常的事實。人與風、人與水、人與精靈、人與神話生物的相遇,都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人類總是干擾超自然的活動、侵入它的空間。超自然就像一隻受到騷擾的野獸,牠在某些時候做出回應和反擊。我們相信,蛇從一片湖泊破出,在雲層的幫助下,在閃電的追趕下,從天而降,進入另一片湖泊。平靜的湖泊會肆虐變色,吸引孤獨的人或動物。最初,天主教來到我們的土地,在湖上撒鹽,用他們的宗教蓋住我們的宗教。比起天主教,我更喜歡秘魯的古老宗教;在我看來,它更接近男人,更活潑,令人眼花撩亂。我決定以〈被追捕的Juido〉結束這本書,我想為那些被壓迫了幾個世紀的人們伸張正義。Juido體現了農民階級、被壓迫者,他的名字就是西班牙文『huido逃離』的變體。」
如果,這些小說都是秘魯這座土地的傳說,Enrique 採集並改編這些過去的故事,那麽,他的難題也許不是起造魔幻,而是找到編織這些魔幻事件和現象的自然結構。荒謬而無情的事態於他,並不是刻劃出來的,而是被保留下來的。我想起他在〈河流〉寫道:「遠在下方和遠處,水留下了最小的一個麵包擱淺在沙子和石頭之間。最古老的從未被發現。」為什麼古老且深藏不露的事物吸引著他?為什麼他想寫下「過去的故事」?祕魯的土地和文學傳統給了他什麼樣的文學啟蒙嗎?
Enrique 說:「有兩位作家向我揭示了文學的世界,Ciro Alegría 所寫的世界是我的世界,出現在他書中的人物是我與之共處的人物。筆直的山脈、藍色的岩石、肥沃的土地,都是我踩過的。我從小就相信我是他書中的牧羊人。而 José María Arguedas 的書教我觀察遙遠的土地、寂靜的峽谷、城鎮、柳樹和飛行的鳥。他寫出了印地安人與大地相連的精神。我從他留給我的溫暖山谷展開了我第一部探索神話的小說。
我是一個對自己寫的東西非常不滿意的人,所以我不斷重寫,直到句子達到我的意圖我才會平靜下來。《過去的故事》是我的第二本小說,是我父親在簡陋的鄉村世界的房子裡講給我聽的故事。我不像父親擅於講故事,所以我沒有辦法將它們傳給後代,我保護它們的最好方法就是寫下來。在我看來,寫作永遠是在拯救和保護我所理解的一切。構成這一本書的故事現在是安全的,我已經為我的世界做出了貢獻。」
 左:西羅.阿雷格力亞(Ciro Alegria, 1909-1967),秘魯小說家。1934-46年因反政府活動兩次被捕,之後流亡國外。
左:西羅.阿雷格力亞(Ciro Alegria, 1909-1967),秘魯小說家。1934-46年因反政府活動兩次被捕,之後流亡國外。
右:荷西.瑪利亞.阿奎達斯(José María Arguedas, 1911-1969),以使用了蓋丘亞語(Quechua)的獨特風格描繪印地安人的世界,被譽為秘魯國民作家。
最初讀到 Enrique 介紹學校的文字,我深受感動的並非詩意的修辭,而是一種生命的定位。他不先說這是一所什麼樣的學校,而是描述籠罩和孕育這所學校的自然天地。他將自然的意志擺在前頭,擺在一所人造的理念學校的前頭。在談論民主和自由之前,他沒有忘掉他所身處的天地具有怎樣的自由,他的學校是被這樣的天地撐起來的,他的學校是跟隨這片土地的風雨一起變化和發展的。一所突破了維生技術層次思維的理念學校,他的框架不是理念,而是自然。將人擺回天地之間,再去談自由的格局,這樣的自我定位觸動了我。
而他做為一個小說家,也把自己擺回天地之間,再去發展創造格局。他試圖還原自然的無情,一種超脫情感層次的自然本性。於是他只能描繪外部現象和後果,無法描述內在動機。自然不一定具有那樣的東西,即使有,也超越了他的理解。他對精確的追求,就是不以自身的有限想像去圈圍自然的事態,不輕易詮釋自然的動機和奧祕,不尋求人性的解答,而是尊重自然的孕育,也接受自然的摧殘,將所有的神祕留存下來,反應人在自然中的被動性和依賴性。這是安地斯山脈的生命觀,還沒過去的故事。
 Enrique Carbajal帶學校的孩子們去拜訪部落的鄰居。(攝影 / 吳俞萱)
Enrique Carbajal帶學校的孩子們去拜訪部落的鄰居。(攝影 / 吳俞萱)
作者簡介
曾獲選東華大學「楊牧文學研究中心」青年駐校作家、原住民文創聚落駐村藝術家、紐約 Jane St. Art Center 駐村藝術家、挪威 Leveld Kunstnartun 駐村藝術家、美國聖塔菲藝術學院駐村作家。2022年夏天從花蓮的阿美族部落移居美國,就讀美國印地安藝術學院創意寫作研究所,持續追探情感的深淵、日常與神話的糾纏。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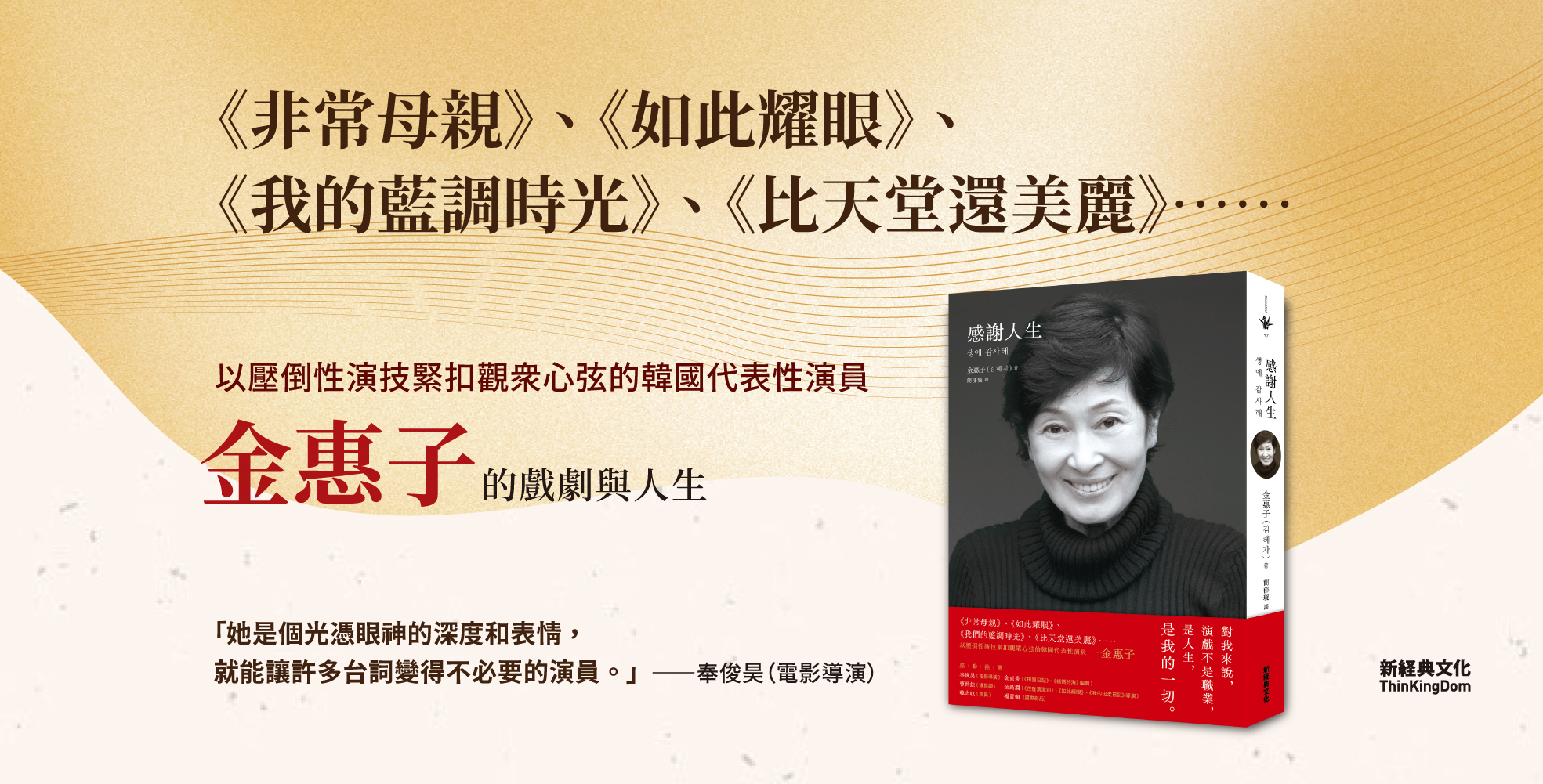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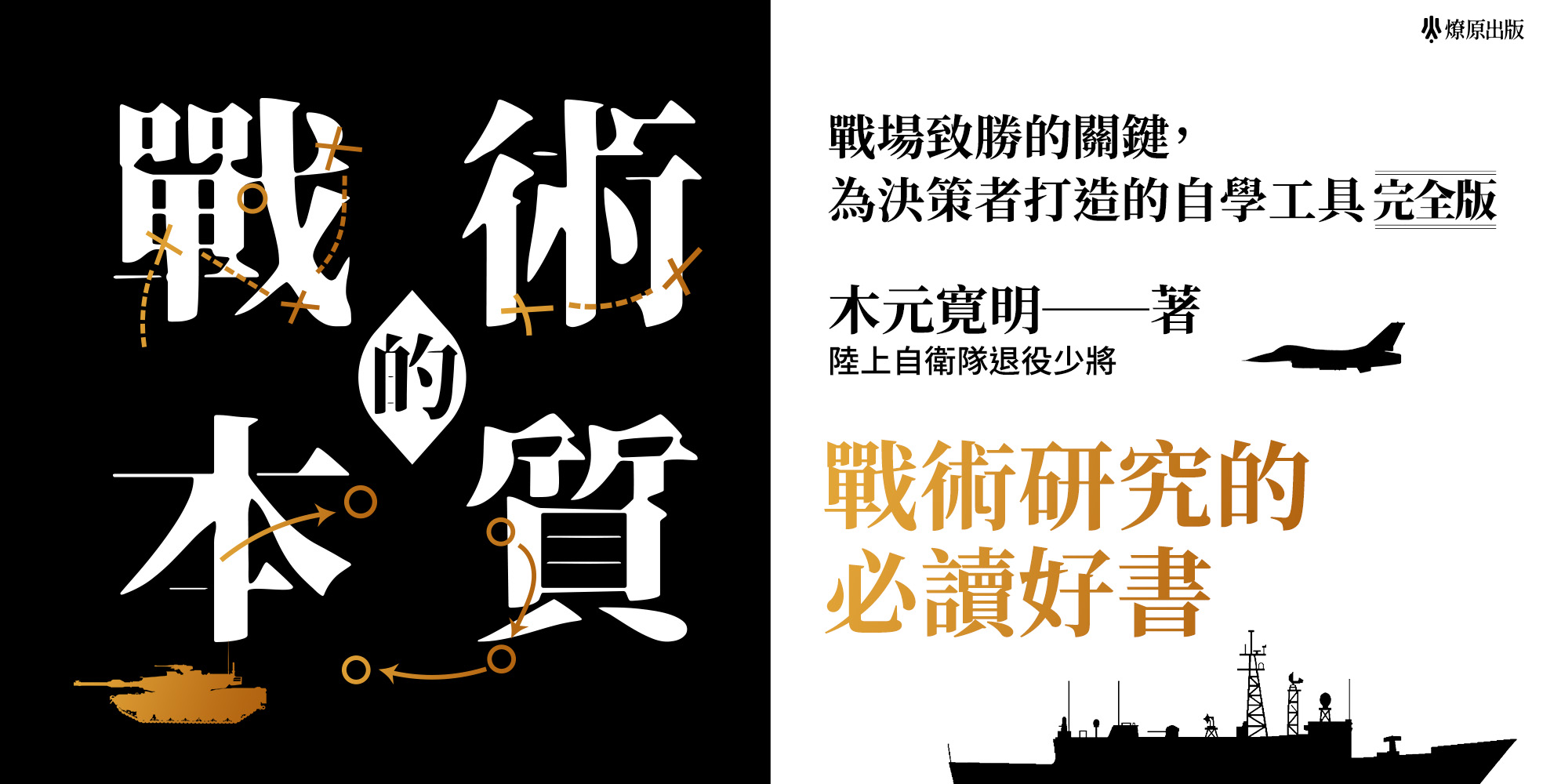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