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人文與民主》除了自序,收入的十一篇文章,七篇亦有收在台灣、香港的他種余英時文集,其餘四篇則是只此一家,別無分號。舊版沒有的〈從科學民主到人文民主〉,是我特別建議時報文化出版要在新版加入的。原因很簡單,這篇 2019年講詞算是2008年〈人文與民主〉講詞的延續。〈人文與民主〉又是1988年〈民主與文化重建〉一文的延續。再往上溯則是1984年〈文化重建私議〉。既然同一主題前面幾篇都已收進本書,新版當然應該加入最後這篇。
2010年舊版,出書用意顯然是為了把2008年訪台期間的三場演講整理付梓。三篇分別是發表於中研院的〈「國學」與中國人文研究〉,發表於政治大學的〈台灣人文研究之展望〉,還有中央大學的〈人文與民主〉。重複收入的七篇則是他本人挑選。原因,可不是他手邊沒別的文章可收。余英時最不缺的,就是未結集文章。即使今天,都過世一年了,那些文章只要有人出面蒐羅,編出個兩本絕不成問題的。因此,重複入選一定有余英時的道理。
「人文研究」與「民主」部分的四篇舊文,道理比較明顯,因為都跟2008年演講有明顯脈絡關係。「思想」部分的三篇,則較不明顯。
三篇裡的第一篇〈中國思想史研究綜述──中國思想史上四次突破〉是2007年在名古屋大學發表的演講,場合是日本中國學會59屆大會。在余英時的四篇學思歷程自述中,這篇是學術內容最紮實的,為他的思想史著述提供了一把最佳鑰匙。
但余英時把它選進本書,原因應該是它正好體現了〈台灣人文研究之展望〉中的呼籲,就是重建自身文化不該強套西方公式。另外,〈對塔說相輪〉兩篇則展現他一貫對西方思想動態的關注。三篇並陳,正好呼應〈「國學」與中國人文研究〉的主題,也就是他借用王國維的話所強調的,中學、西學應該「風氣既開,互相推助」。
對余英時來說,要避免蹈入「西方中心論」的陷阱,最好方式就是把西方理論讀通,讀活,讀到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
2008年是余英時獲得克魯格獎後第一次來台參加院士會議。對於演講,他一向是有被邀請,時間能夠配合就盡量配合的。這次,已經答應演講了,沒想到一下飛機,就身體出狀況,被送進醫院,要搭機返美才辦出院。整趟台灣行,每晚陳淑平(余夫人)也陪他睡醫院裡。已承諾的三場演講,每次都是主辦單位派車來接,演講完再把他倆送回醫院。期間余英時受到腎臟內科權威陳振文(後來的為恭醫院院長)、腫瘤醫學權威閻雲(後來的台北醫學大學校長)很好的照顧。陳淑平特別要我寫出他們名字,作為感念。
日後,陳淑平跟我說起這場病,總說:「幸好是在台灣發病,因禍得福!」原來,〈人文與民主〉那場,本來是要跟楊振寧對談的。一直到前一天,《中國時報》還在宣傳這場「大師對談」。問題是楊振寧不只親共,還崇拜毛澤東。余英時1992年〈「六四」過後的浮想〉一文就是不指名地譏刺他。這場對談的安排,我會說是強人所難,中時駐華府特派員傅建中則挖苦說是「頭腦不清或是不信邪」。但既然名目是「余紀忠講座」,余英時認為他根本無法拒絕。總算後來有了醫生認證,才變成他可以自己一人講,楊大師則改去跟其他人同台。「因禍得福」是這個意思。
三場演講的時間是2008年六月底、七月初,出書卻要等到2010年一月,可見回美國後,身體依然非常折騰。事實上,他根本沒想到自己過得了那關。所以舊版《人文與民主》已經算是他準備給台灣的最後建言。所幸吉人自有天相,他後來又寫出《論天人之際》,並在2014年再次來台,這次是領取唐獎,2018年發表《余英時回憶錄》,2019年則受邀用遠距錄影的方式,發表〈從科學民主到人文民主〉。這最後一次公開演講,就真的是最後建言了。
主題是他常關心的台灣民主品質。政治學者就同一題目,通常是建議要營造理性對話空間啦、增進選舉以外的公民參與等等。余英時給的建言卻是提升人文素養。
老實說,對於他這建言,我本來腦袋是一堆問號的。不是有許多人文學者,院士等級的,只會嫌台灣民粹,嫌美國撕裂嚴重,卻不懷疑中國今後只會越來越強?何況許多人文經典內容根本反民主,像柏拉圖《共和國》就是。
多虧新版加了最後演講,我才覺得我有搞清楚他的意思。首先,就這題目,他最常援引的,中國古書是《明夷待訪錄》形容理想學校那段,「漸摩濡染,莫不有詩書寬大之氣」,美國作者則有白璧德、羅爾斯、布魯姆、小施勒辛格。其中,羅爾斯與小施勒辛格是美國意識型態光譜的自由派(左派),白璧德與布魯姆則是保守派(右派)。
要從余英時引用的西方論著,去判斷他思想到底偏向美國左派還是右派,根本是不可能的。以本書為例,他雖引用羅爾斯《政治自由主義》一書,但只是取其「背景文化」概念,並沒為作者的大政府思想背書。他引用小施勒辛格《美國歷史的循環》,則只是以書中對白璧德的肯定為證據,說明人文崇尚在美國已經是左右共識,不再被貼上守舊標籤了。
至於布魯姆《美國心靈的封閉》一書,余英時也只是認同「大學是為民主社會樹立最高的精神標準的聖地」這個論點,並沒跟著附和作者對六○年代新思潮的譴責。至於布魯姆主張的,人文教育必須以經典為骨幹,而且必須是他最重視的那幾本西方經典,柏拉圖《共和國》之類的,這點余英時就連提都沒提了。
我發現,余英時「人文民主」一詞中的「人文」,定義比較接近「民主公民的基本素養」,這素養可以是道德的,例如多數為何應該尊重少數,也可以是技藝的,例如如何運用理性去說服觀點不同的人,或在無法取得共識時要怎麼妥協。
在知識層面,這種素養可以是人文,例如透過文學去培養同理心,也可以是社會科學,例如在相信候選人「拚經濟」的承諾之前,要先知道政府發展經濟可以使用哪些手段,不同手段各自又有哪些取捨。
內容當然因時因地而異,因此余英時在最後一篇演講,才特別強調台灣應該加強足以抵抗中共滲透的那種人文素養。
也就是說,余英時並沒單純到以為說,一個人只要飽讀詩書,選上院士,就不會為極權張目。他很清楚人文就跟科學一樣,既可為民主服務,也可成為極權工具。他重視的人文,是可以打造一種文化氛圍,讓民主越來越鞏固的。這是余英時認為台灣現在最需要的,所以才在人生最後,向台灣如此建言。

作者簡介
2014年金鼎獎雜誌專欄類、2018年九歌年度散文獎得主。
著有《愛還是錯愛》(親子天下,2015年)、《向康德學習請客吃飯》(印刻,2016年)、《最低的水果摘完之後》(天下雜誌,2018年)。譯有珍.奧斯汀《理性與感性》(印刻,2017年)。編有《余英時評政治現實》(印刻,2022年)。
2002年創辦雅言出版公司。
【OKAPI專訪】雅言文化發行人顏擇雅:我不跟著流行讀書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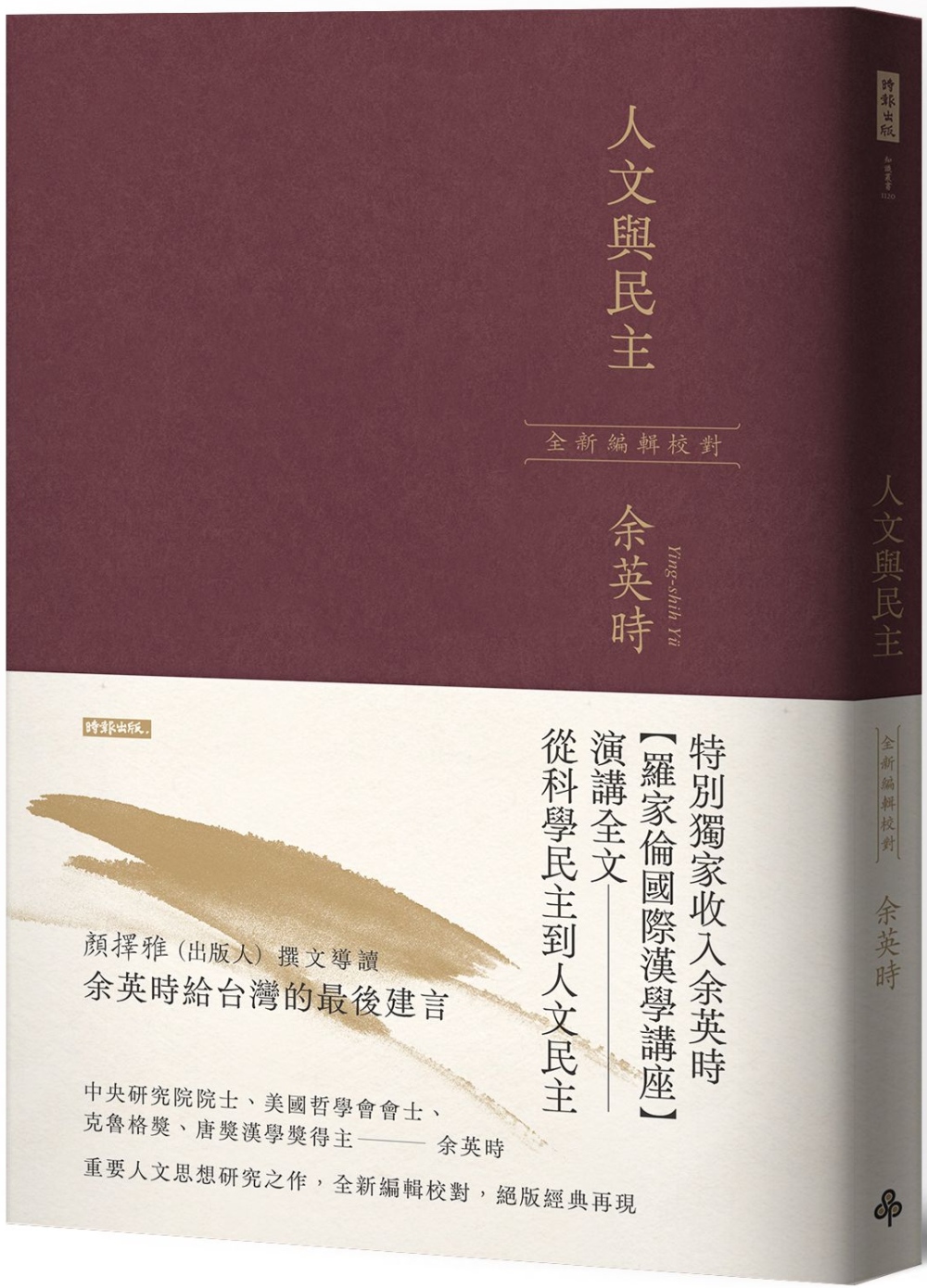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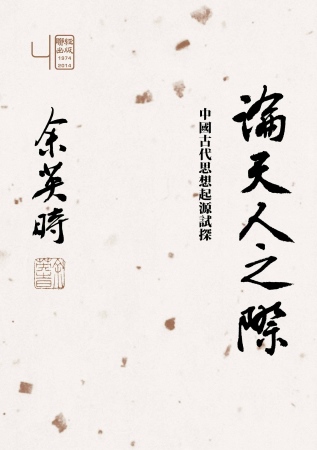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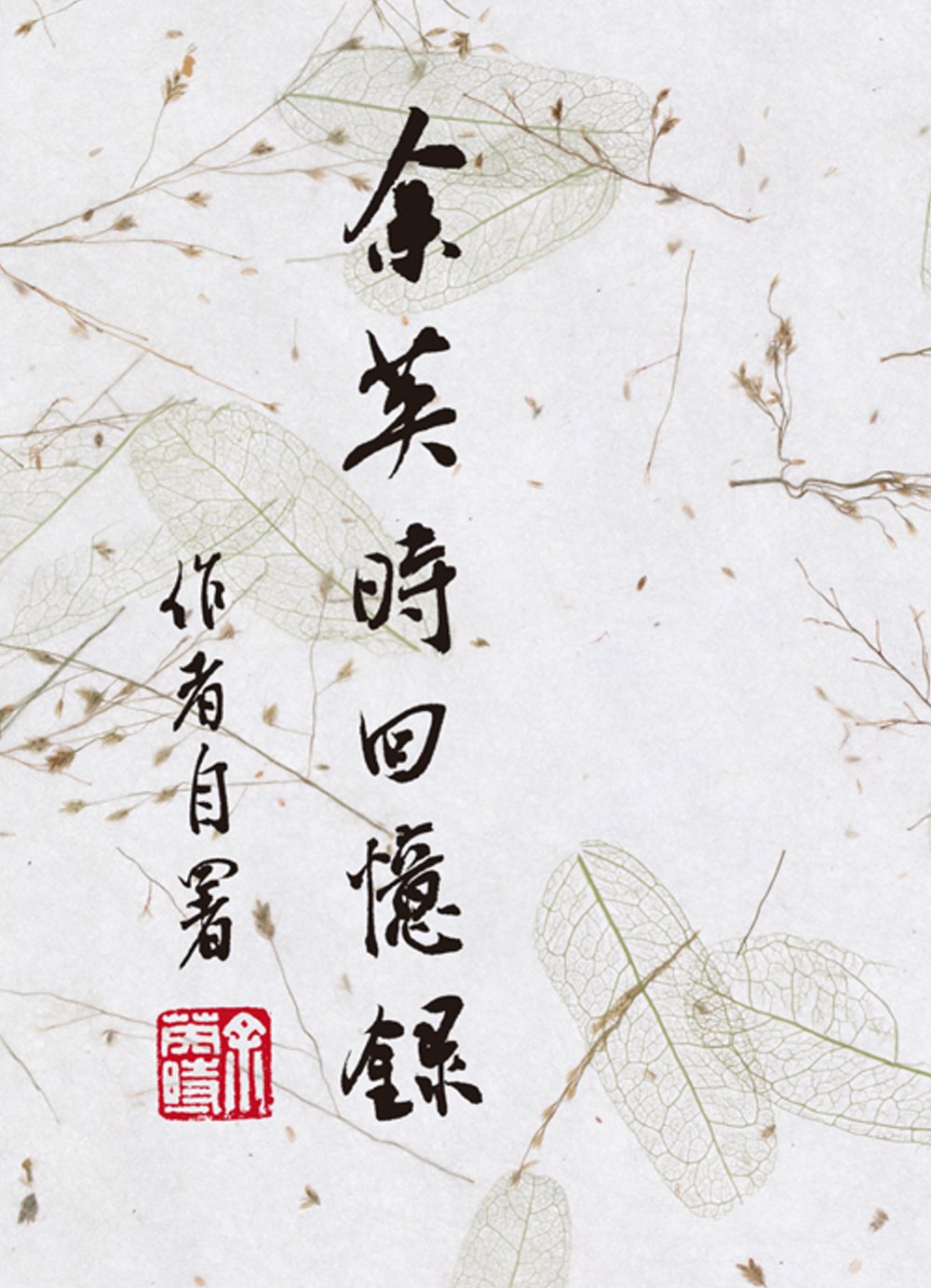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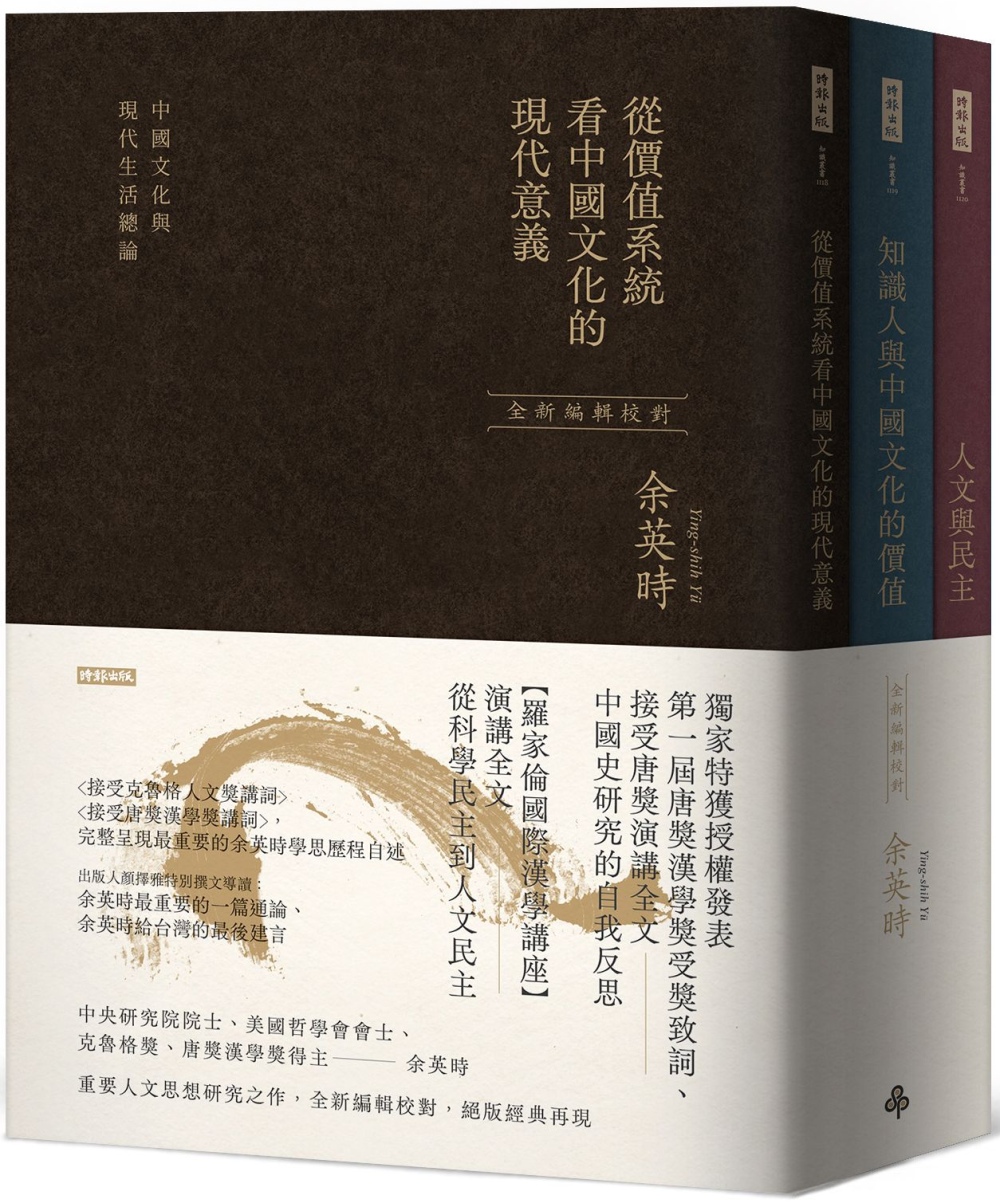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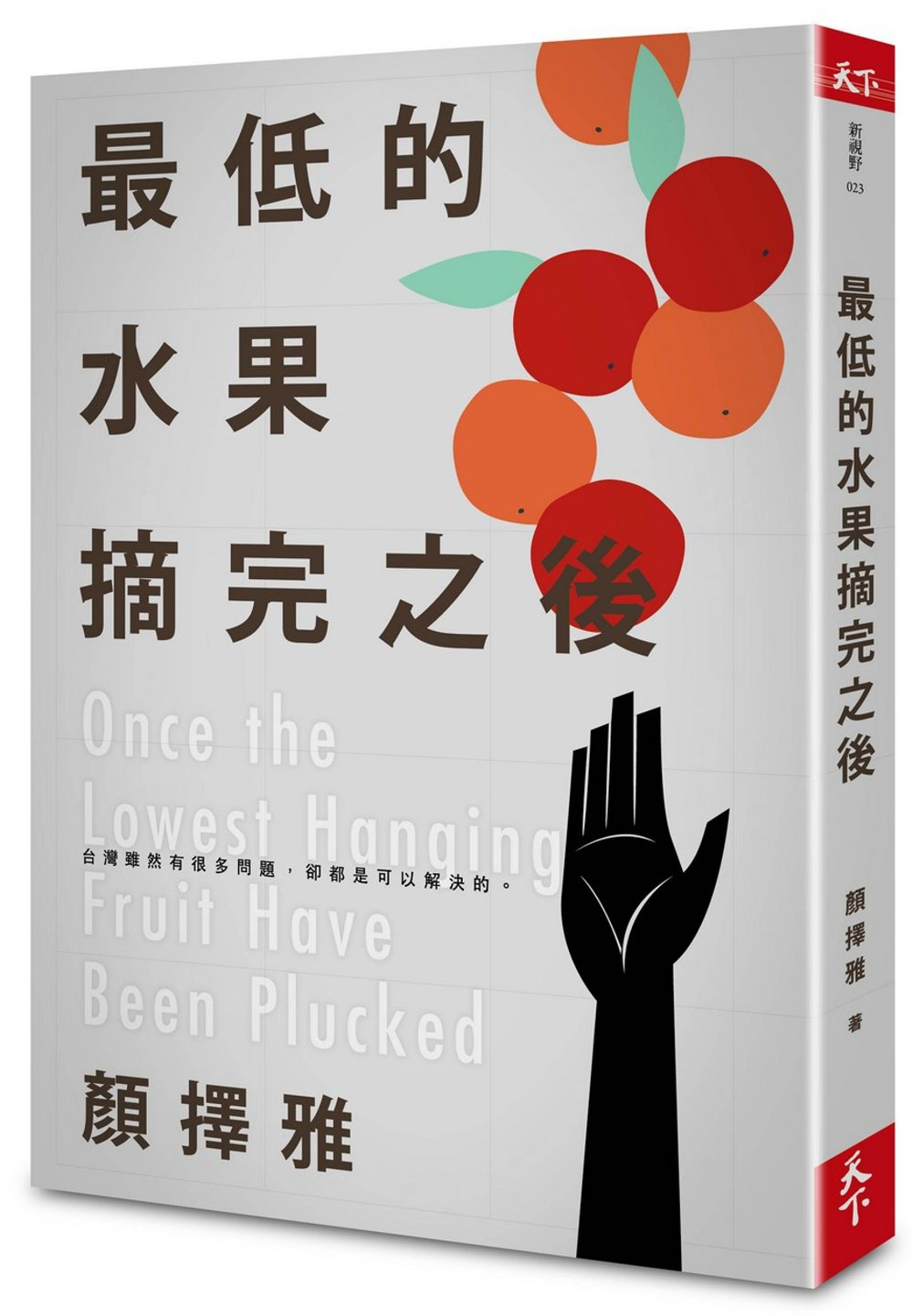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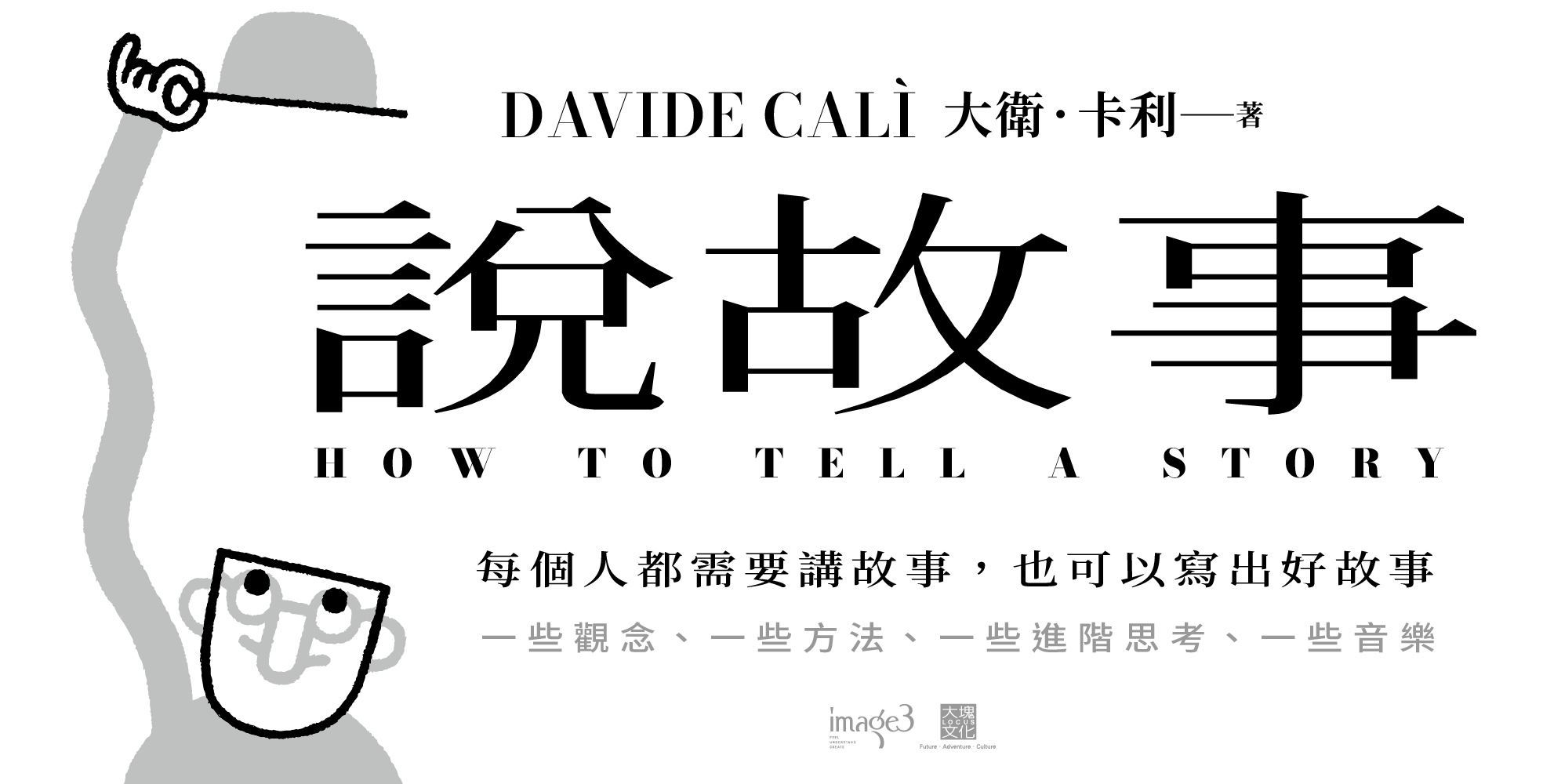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