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由值多少錢?「無價」是否也有它的底限與價碼,如果以四百萬美金換你一生不再開口唱歌,你願意?
哈金最新長篇小說《放歌》,以一個中國歌唱藝術家姚天為引線,將中國統治下的言論自由與人身自由,串起一系列的比對與思考,挑戰了高牆與強權、挑戰不可說也無人承認過的暴行,而它最挑戰的更是「自由的價值」。匈牙利詩人裴多菲(Petöfi Sándor,1823-1849)絕世金句中,遠遠凌駕生命與愛情之上的事物——「自由」,在一個半世紀以後的當代、看似有了許多和平開放的民主國家後,它似乎變得普遍與輕易,該如何重新衡量價值?
小說裡藉由一段中國官員勸說主角姚天不要背離國家、不必流落美國,只為了某種並不真實或實際的存在(自由),或許也完美解答了許多娛樂新聞、知名人物的選擇;當一個人對自由的價值有疑惑,多半是來自於不曾失去過:「自由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幻覺。最多是一種感覺,甚至不是健康的感覺。自由總是建立在沒有多大能力的基礎上。乞丐可能有自由,卻沒有尊嚴。又是他肚子餓得呱呱叫,自由還有什麼價值?」戰爭與死亡都在遠方,比鬼更可怕的是貧窮,即使如此,對那時(2009年)離開中國、第一次朦朧感受到自由形貌的姚天,卻在家庭需要更多金錢時,拒絕了四百萬美金的提議。對尚未真正感受過自由的人來說,姚天的堅硬,來自一種藝術家的自矜,如他所言:「他是個歌手,如果他不能出聲了,他還能是什麼?他將一無所有、誰也不是——再沒有什麼東西,它可以為之工作、為之奮鬥,安頓內心的信仰。」
姚天拒絕的不只是金錢,而是一個國家的特別部門,它們總一直拿金錢或房產收買批評國家政策的知識分子或不同政見者,條件是得對政府的任何作為保持沉默。出走到遠方,終於可以說出「國王的耳朵是驢耳朵」這一整個國家知而不宣的祕密,也終於敢在心裡對自己承認:「現在的中國,沒有不跪著生活的地方。」就像恐怖的前任情人,離開得拿代價來換,姚天在中國的家人也不得安寧,其妹之死揭露的另一個祕密是——法輪功學員在中國被政府販賣器官的可能,為此,他與他的家族遭受了思想審查、監視、封殺與打壓,這與過去號稱「中國歌王」的歌唱家關貴敏(法輪功學員),形成虛實對照。「有所本」的片段真實,也是一種虛構技,虛實之間,當然也藏有哈金自己。在美國的姚天無法換發新的中國護照,也正如哈金曾回憶自己在1997年的往事:「我的護照無法延期,所以我不能離開美國。後來我成為美國公民,然後就對想念中國感到疲勞了。」
在他鄉開始以另一種語言寫作,哈金所有的中文版作品都不是由母語書寫,而是經過再譯的。這或許也很接近哈金對祖國、對家鄉的曲折情感,想念疲勞的前身是「也曾想念」。經常有人將哈金與同樣放棄母語、以英語寫作的康拉德和納博科夫一起談論,但三人的選擇其實有本質上的不同,「避難所」之於納博科夫、「實驗場」之於康拉德,哈金則介於兩者之間,他總是選擇最合適體現「移民掙扎」的一種語言,畢竟語言本身也是一種掙扎。掙扎幾乎也像是一種自由,當你感受過自由,你會知道它並不溫柔,哈金在《自由生活》(2007)寫道:「如果你不知道如何運用自由,自由對你將毫無意義。」自由可能充滿未知與恐懼,一如《放歌》中姚天被國家表演團開除時,他忽然意識到:「從現在起,他徹底自由了。這也是一種讓人膽寒的感覺,因為自由意味著一切要靠自己,從肉體到靈魂,你就自己對自己負責了。對這種狀態,他既陌生又新奇。他敢肯定,在自由和安穩兩者中,大多數中國人會選擇後者。如果他還在國內,他的選擇可能也跟別人一樣。但自由最終還是落到他頭上,不管他有沒有準備好,他已經擁有了它。」
這一次看似「大型流亡」的最初,不過是姚天為了多賺四千美金,私自決定在美國多留幾天接一場表演⋯⋯然而他所在的「當下」,國家級的演出者也必屬於國家,他們必須團進團出、不提供私人選擇、事事都得回報;說來不可思議,卻發生在並不久遠的時空,姚天妻子舒娜感慨與擔憂:「現在已經是21世紀了。你們團的領導應該知道,你不是他們的所有物,他們不能夠為所欲為。」迎來的卻是壞消息,小說設定發生在天安門事件後近二十年,可惜從他們到我們所在的任一當下,相似的故事仍不斷發生。《放歌》當然是一本政治小說,所有的小說都關於政治,萬事萬物也難離開政治,只要事關權力與資源的分配,發散出的討論,就已經是政治了。即使姚天總說:「我對政治沒興趣,只想做一個自由藝術家。」他的好友則提醒:「你周圍沒人自由的時候,你可能嗎?自由不僅是一個個人的選擇,更是一個社會條件。」
自由當然更是政治,因為它是最簡單的以資源換取權力,或者相反,以權力換取資源。自由的所在,往往不會均富,甚至可能街頭滿是流浪漢,政府總在忙著處理治安與救助,就像美劇《女傭浮生錄》(Maid,原著《我只想讓我女兒有個家》)裡,有許多住在露營車、得靠社會補助與收容所活下去的人們。在《放歌》裡頭,也有如此典型的美國場景。姚天在凌晨1:50到了紐約港務局汽車總站,為了省錢得等到早班巴士時間,在一片赭色夜燈映著的天空底下,他聞到空氣中有一絲腐爛的味道,像是煎炸過很多遍的剩油和地下污水,「他看到大約二十個男人和女人,正貼著牆根睡覺,大多數是無家可歸的流浪漢,蓋著毯子,儘管有幾個人看起來像乘客,旁邊有行李和箱包,似乎在等早班巴士,車站裡也有一股霉溼的味道,他挑了一個地方,躺在一個老人旁邊,這個老人雙手放在肚子上拿著一個威士忌酒瓶。姚天把頭上的針織帽扯下來蓋住臉,打算打個盹。」
姚天加入他們,等待。一如姚天為了生計,成為工人、在車站賣唱、到大西洋城的場子唱歌⋯⋯或許有人會說,大藝術家淪落如此生活、如此貧窮,不如不要,「祖國」如此強大,沒有人要為美金以及最低生存線折腰。我忽然想起小說中一段插曲般的遊覽經歷,多年後,姚天終於等到妻子女兒來訪美國,他帶著妻女參訪了梭羅故居,三人談到梭羅幾乎是避居的生活史,他為何想要遠離世人?姚天像是能共感般地說了:「他對自由的概念是純粹和絕對的,孤獨的確是通往自由的道路,為此你必須接受發生在你身上的一切,包括飢餓、疾病,甚至死亡。你將對自己的一切,身體和靈魂,負責。」就像人為什麼要孤獨、為什麼不享福?往往不是沒選擇,恰好是出自於有選擇。以此解答了姚天為什麼不收下四百萬美金、為什麼跑來他鄉受苦的種種疑問,或許自由並不值錢,卻有價值。
就像選擇變老、選擇死於何方,小說中安排了一個有趣的角色,患了癌症的姚天一次遇見來美國治病的中國退休高官「包先生」。包先生已老,並且安然於老,甚至和他說起:「你看見我的頭髮嗎?花白了,這是我本來的樣子,在這裡我就不需要隱藏。以前因為沒有像上級同事那樣把頭髮染成烏黑,經常惹麻煩。隱瞞真相是那裡官場文化的精髓。老實說,我到這裡後,我覺得我終於可以做回自己。」在自由中,或許沒有人願意老;但在不自由中,總有人期待「選擇」老。越是集權的國家與領導人,似乎總在閃躲著老病死,不管是北韓、俄羅斯到近代中國,掌權者的模樣,從髮絲到服裝,最好恆常如雕像。
「只要沒有遺憾,就不應該怕死。」這是姚天在生與死的掙扎中領悟到的道理,一如他的好友亞斌談起遺憾,遠在故鄉的父親死前都未能見到面,遺憾裡有更多痛苦與憤怒,「有時我懷疑我們的生活不是對的,我們所有的犧牲不是必須的,合理的。為什麼我們中國人就得對付生活中這麼多坎坷啊?」「而且都是人為製造的。」在《放歌》中,每一個名詞,從「自由」到「遺憾」,都不僅有一種語境,《放歌》想說的,從來不是單一的;一如姚天不是哈金,哈金卻多少將自己放進了姚天裡頭。
這不是一個歌唱家的美國夢、也不是一個移民者的奮鬥史,或一個流亡人士的控訴。它是一首名為自由,歧義的歌,捨棄了遠方的青春與家鄉,才終於擁有了沒有限制的歌單。在哪裡都可以唱歌、在哪裡也都可以選擇不再唱,這才是真正的放歌。
作者簡介
1987年生,台灣台中人。 摩羯座,狗派女子。
無信仰但願意信仰文字。東海大學中文系、中興大學中文所畢, 目前就讀成功大學中文博士班。 曾獲台北文學獎、教育部文藝創作獎、文化部年度藝術新秀、國藝會創作補助等獎項。2015年出版首部散文《請登入遊戲》, 2017年出版《寫你》, 2020年出版第三號作品《我跟你說你不要跟別人說》。⠀⠀⠀⠀⠀⠀⠀⠀⠀⠀⠀⠀⠀⠀⠀⠀⠀⠀⠀⠀⠀⠀⠀⠀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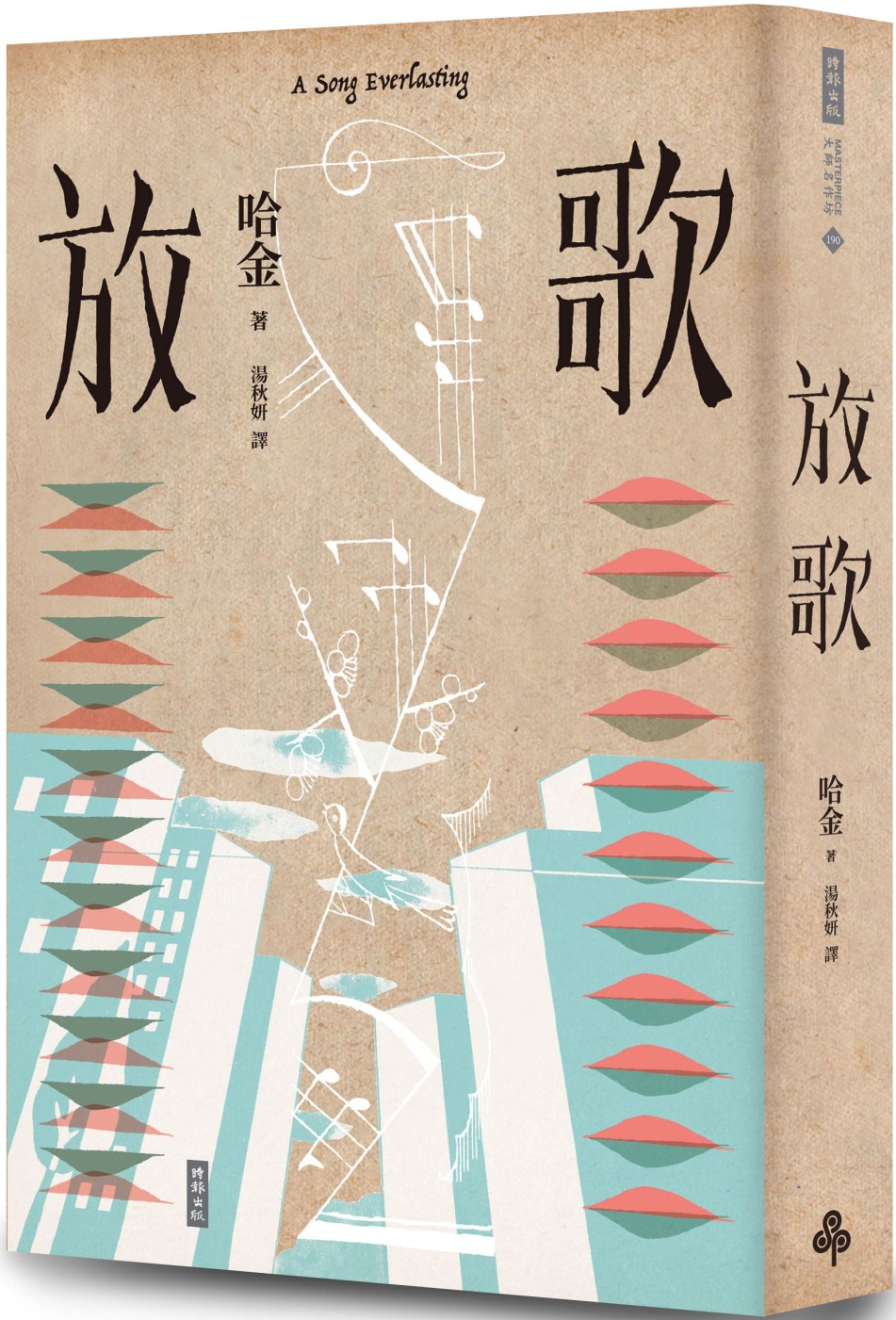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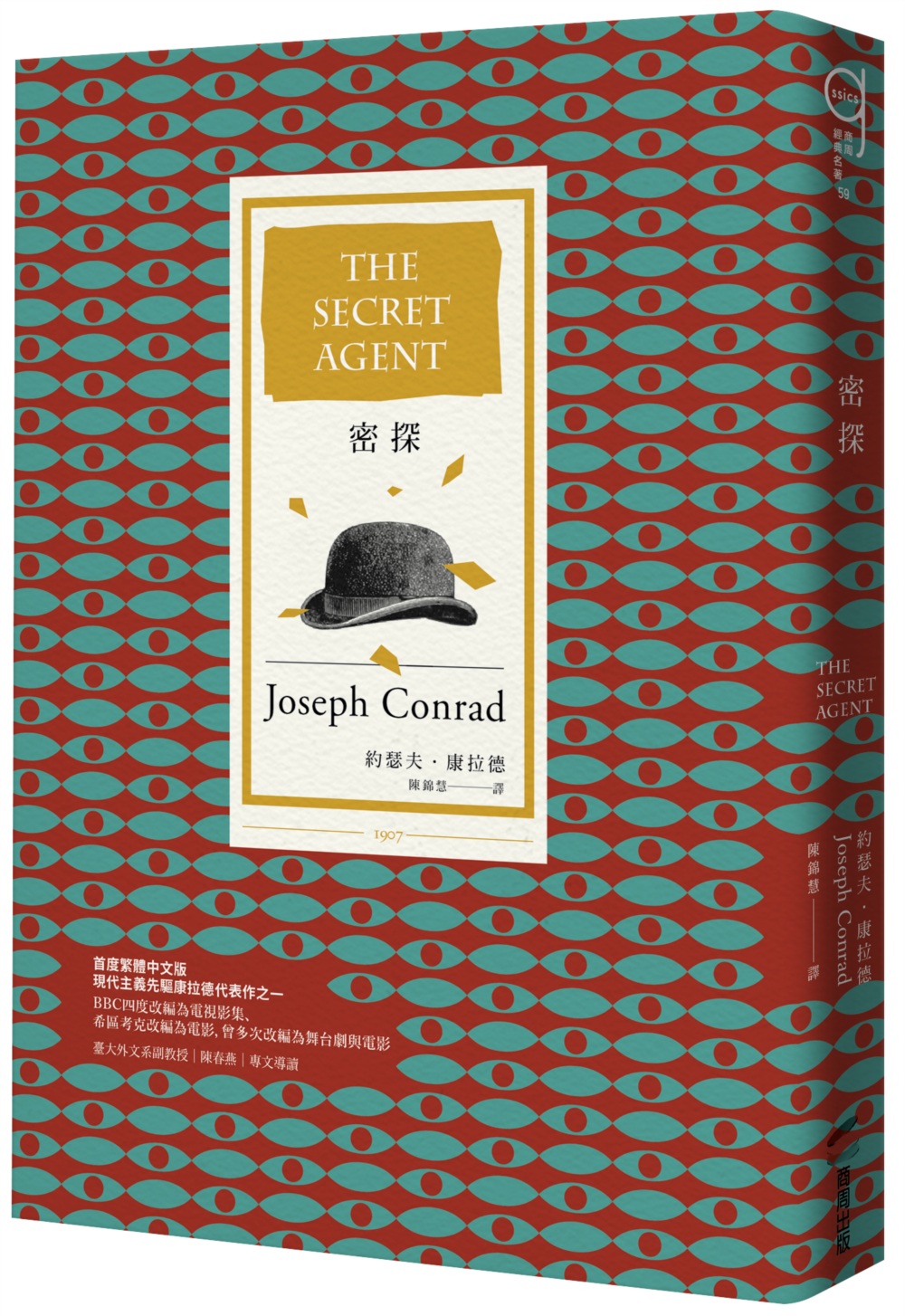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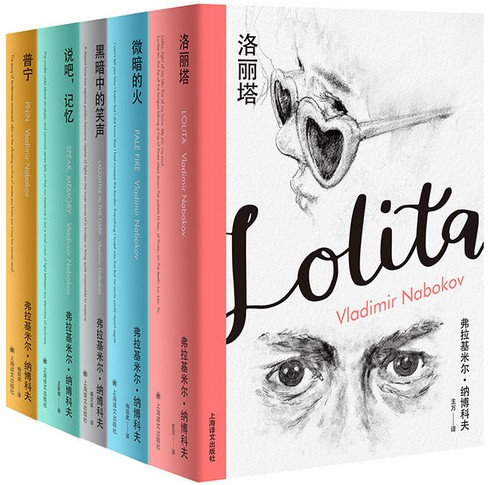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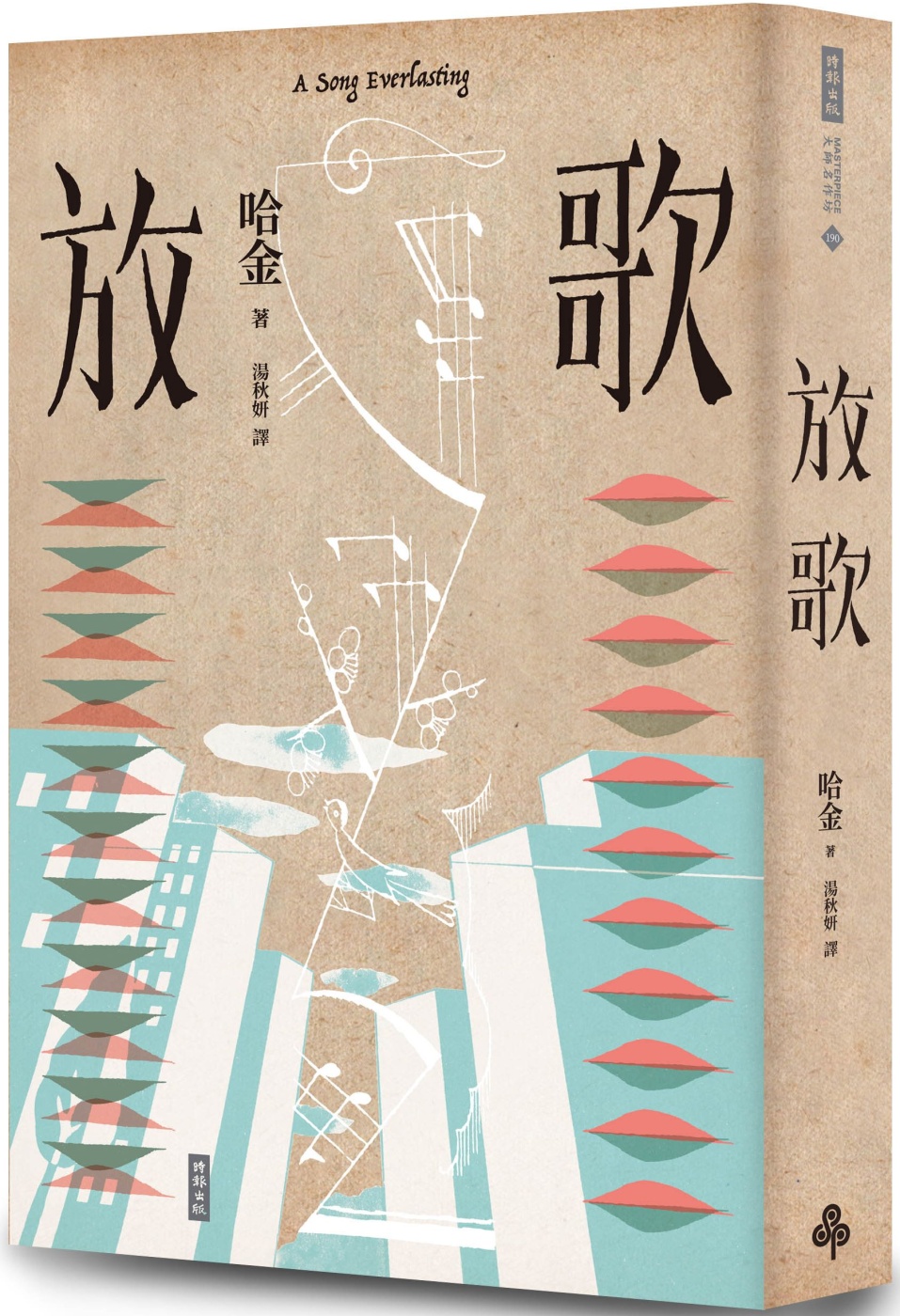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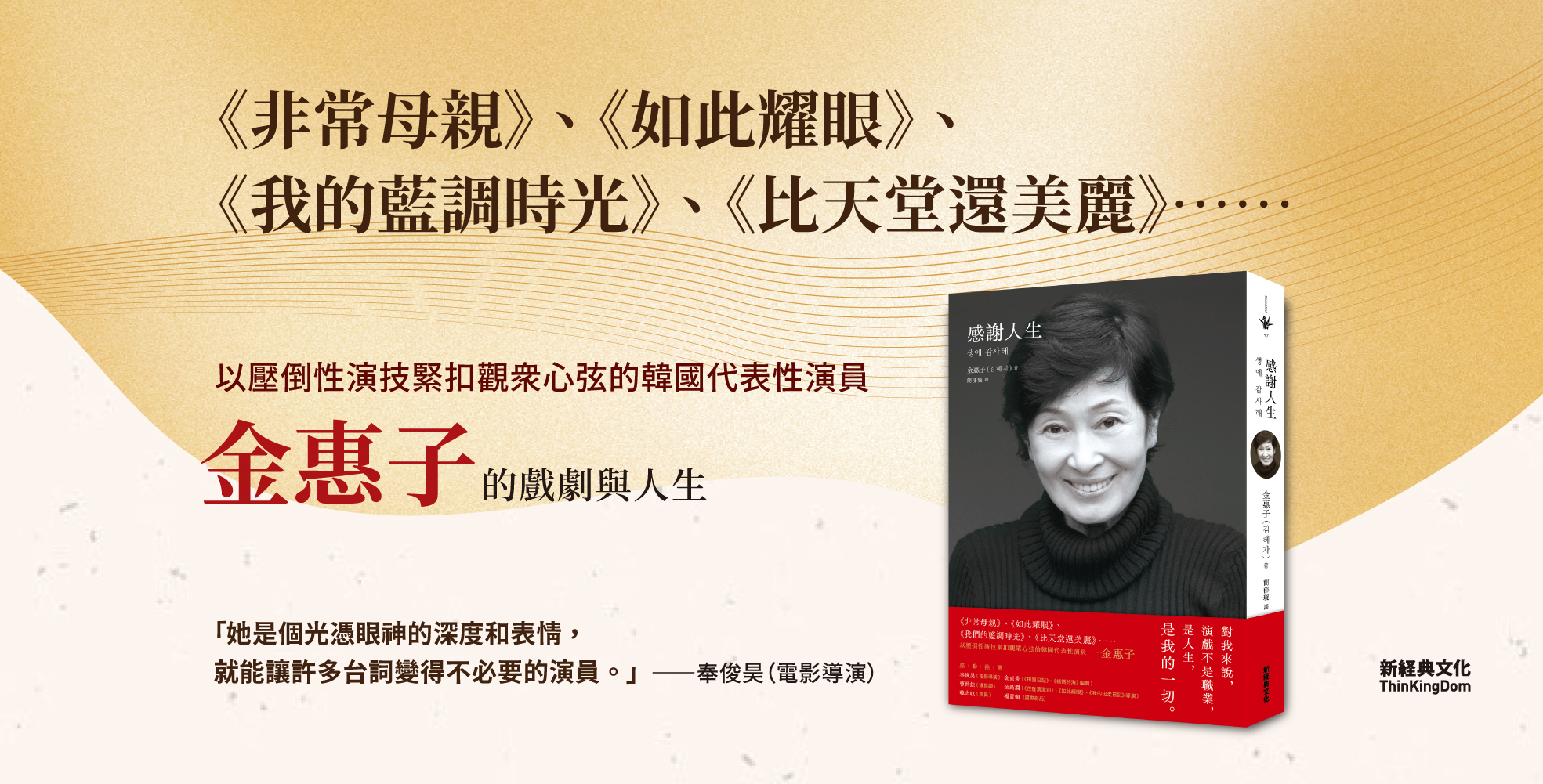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