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另一種語言寫作,象徵著動手拆毀一切,象徵著新的開始。」
──鍾芭.拉希莉
哈金最後一次申請回中國任教是2004年。那時他已經出版包含詩集、長短篇小說等多部英文作品,屢獲美國重要文學獎項。哈金以韓戰的中國士兵俘虜為背景的《戰廢品》在該年出版,隨即獲得不少好評。但哈金一直沒收到中國方面的回音。他知道這件事沒指望了。
2007年問世的《自由生活》,標誌著哈金從以往的中國,搬遷到如今安身立命的美國。這不僅是語言的,也是精神的漫長遷徙歷程。此後,哈金的小說作品幾乎都落在移居美國的華人故事。諸如短篇小說集《落地》寫紐約法拉盛華人社群;《背叛指南》以八○年代轟動一時的金無怠間諜案為原型,演繹個體與群體之間的拉扯;《折騰到底》以諷刺筆調從情感恩怨談後九一一的中美關係。其中,唯一例外的《南京安魂曲》,也主要從美國傳教士的視角來呈現南京大屠殺的歷史現場。新近的《放歌》則跨越2010年代前後,描寫名滿中國的歌唱家,如何觸犯政治禁忌,陰錯陽差在美國重新開始。

▌自由的代價是不自由
《放歌》的主軸是專唱紅色歌曲的歌唱家姚天隨團到美國巡演,為了賺外快,意外被逼到滯留美國,最終不得不成為美國公民。這是一種揭開「中國式自由」的過程:一直以為擁有自己人生、職涯決定權的歌唱家,原來不是他以為的那麼自由。於是姚天踏上追尋自由的旅程。他面臨的是這樣的處境:成為「遺民」,或「移民」。
「遺民」意味著他全部的思考重心仍在過去,依舊緬懷昔日榮光而想延續到另一個地方,實際卻是意圖看著後照鏡開車。「移民」則象徵重新開始,必須拋棄過往包袱,面對當下,學著獨立生活。也因此,小說描述姚天如何學會開車的段落充滿隱喻:這表示他終於把視線從後照鏡移開,看著前方,邁向未知。
小說中,演出機會日漸減少的姚天迫於生計,從紐約移居波士頓,從一個自己的房間到另一個分租房,他甚至放下身段去當建築工人,某程度就像是在尋找自己的歸屬,試圖答覆他自身的「抵達之謎」。姚天在美國一面領受自由的同時也一面遭受困頓:他失去了歌唱家最重要的聽眾,尤其是同一種語言的受眾。他必須學習以英語歌唱,重新摸索聽眾的喜好。這也是隱喻:彷彿被拔除了聲音,而得從另一種語言學會說話、唱歌。
姚天與妻女睽別六年終於在美國重逢,卻與他的想像不同。在北京清華大學任教的妻子舒娜,學術生涯穩步向上,那是姚天原本生活的模樣:如果他繼續留在中國,他能有不錯的收入和聲名,或許也能擁有私下批評時事的空間,前提是他必須聽黨的話,服從黨的安排。也於是,夫妻關於自由、未來生活的藍圖逐漸分歧、漸行漸遠。偌大的「國家」幽靈橫亙在姚天與舒娜之間,一如哈金上部小說《折騰到底》那位異議記者馮丹林的描述:「看來中國就像個第三者擋在我們中間了。想必我就算成功把你弄上床,一個冷酷的國家橫亙在我們中間,我也硬不起來。我拚了老命也辦不到──幹一個國家太難了,簡直做不到,除非是這個國家的總統或者總理。」這部小說中的姚天確實面對舒娜硬不太起來,也草草結束。這更令人想起馮丹林的尖刻質問:「我就是不懂,為什麼一個國家想幹一個公民就幹一個公民,但一個公民卻無法幹回去。為什麼?這個問題真叫我絞盡腦汁。」
姚天對這個問題大約也沒有解答。被注銷中國護照的他,只能繼續留在美國,承受自由生活帶來的種種不自由,甚且面臨病痛的試煉。或許有些讀者敏銳察覺姚天來自中國歌唱家朱明瑛、關貴敏的身影(尤其是關貴敏與法輪功的連結),我聯想更多的卻是《自由生活》的主角武男,以及哈金自己。
\關貴敏的〈浪花裡飛出歡樂的歌〉是小說主角姚天的拿手歌曲 /
▌哈金的宇宙搖
今年廣受好評的電影《媽的多重宇宙》,從艱苦經營洗衣店的老闆娘秀蓮身上,映照出美國華裔族群的生存處境:外有種種刻板印象的角色束縛,內有諸多親子關係與傳統包袱的掙扎,他們得埋葬掉所有不切實際的夢想,才能繼續生活。電影以諧謔角度呈現移民第一代雖然日子困頓,仍心心念念期盼子女成材,過更好的生活,結果總是落空。兩代人永遠處於難以理解彼此的狀態,有如兩種語言的雞同鴨講。電影以絢麗、迷眩的視覺特效,注入多重宇宙的爆炸想像,讓原本困在國稅局辦公室的秀蓮,穿梭各種不同版本的自己、丈夫、女兒與其他人。
直到讀完《放歌》,我才約略明白,也許哈金一直在演算的,就是他腦中的多重宇宙。在《媽的多重宇宙》,主角需要透過「宇宙搖」(verse-jumping)徵用另一個平行宇宙的技能或意識,而哈金則是透過作為「宇宙搖」的書寫,通往不同版本(version)的自我。
比方說,《自由生活》時常被視為哈金的半自傳小說,也是他自認的代表作。而他也總要不厭其煩聲明,許多描述細節確實來自他的生活經歷,但他從未在中餐館工作,也沒有眷戀不忘的初戀情人。但讀者如果細心核對,會發現,主角武男的年紀、就讀博士班的大學、寄居波士頓地區的經驗,乃至於曾在南方的亞特蘭大一帶待過八年等,皆與作者相仿。這正展示出小說家以假亂真的虛構實力。在新版《自由生活》序文中,哈金自承「我比武男幸運得多」──這句話的反面就是,萬一不走運,他也許就要過那樣勞碌奔波的生活:日復一日守著餐館長時間勞動,時時擔憂著債務、健康,偷偷想像著其他可能的生活,懷著祕密似的寫英文詩,「不斷承受孤獨和失敗,渴望走完兩三代移民才能走完的路程」。(一個對照:繼哈金之後,以小說《內景唐人街》拿下美國國家書卷獎的游朝凱是台裔美國人第二代。)
又比如,《瘋狂》的主角萬堅與天安門事件之間的聯繫,某程度折射出,如果當年哈金並未出國留學,可能遭遇的情境。《瘋狂》從個人的瘋狂、群體的瘋狂,寫到國家的瘋狂,是以主角最終決心改名換姓,選擇出走,而目的地也可能就是美國。現實世界中的哈金,受到天安門事件的震撼,決定留在美國謀生。從這裡接往《自由生活》,書中還在波士頓讀政治學博士的武男,就因六四屠殺的緣故,放棄學位,打算去過自己選擇的生活。儘管那些選擇都只是底層的勞力工作,武男也只能且戰且走。整部《自由生活》刻劃的盡是不自由的生活,最後作者以武男的詩歌、詩話收尾,暗示著經過五、六百頁的磨難,武男總算獲得了一絲創作的自由。
以此對照,《放歌》有如《自由生活》的變奏,只是這次的主角擁有比較輝煌的過去,可以讓他在美國耗用紅利。然而紅利花完之時,也不得不腳踏實地,從頭累積。觀諸《自由生活》、《背叛指南》、《折騰到底》、《放歌》,皆以移民為題,同時在這跨國移動中遭遇「國家」與「自我」的矛盾夾擊,最終這四部小說的主人翁大多都選擇「自我」(儘管《背叛指南》抉擇是「自我了結」),憑靠自己的雙手在美國重新找到定位。這是痛苦的重組,也是哈金自身以英文寫作,寫成一個跨語寫作典範的真實經歷。
▌華文文學的美國叔叔
關於跨語書寫,哈金曾引用詩人約瑟夫.布羅斯基:「當一個作家訴諸一種有別於母語的語言時,他要麼出於必要,像康拉德;要麼出於熾烈的野心,像納博科夫;或為了獲得更大的疏離感,像貝克特。」這段話不禁讓我想到,二戰前後的台灣文學處境。戰前,出於必要,出現許多日文寫作者;戰後,同樣出於必要,一眾熟稔日文書寫的寫作者,不得不改以中文寫作。其中僅有的異數是黃靈芝。二戰後才開始以日文寫作的黃靈芝,原以為命不久長,無法投注時間給中文,就這麼一路寫下來,成就自身獨特的日文創作。其間,他也曾懷有「熾烈的野心」投稿日本的小說文學獎,卻始終未獲青睞。直到暮年,他才以俳句獲獎。黃靈芝沒能完成的心願,在數十年後由另一位跨語書寫的李琴峰開花結果。
哈金當年在波士頓大學寫作班的同學鍾芭.拉希莉,據說是少數能理解他之所以寫那些中國故事的朋友。他們後來分別斬獲大獎,成為2000年代美國移民文學的代表作家。哈金在英文安家落戶之時,拉希莉卻在2012年移居羅馬,希望自己能精通義大利文。她在幾年後出版以義大利文寫成的散文集《另一種語言》,甚至出版第一本以義大利文創作的小說,隨後由她自己再翻譯成英文版。對拉希莉來說,她原有的母語孟加拉語以及後來的「繼母」英語,充滿太多個人生命與文化的撕裂衝突,她總得在兩個語言間來回拉鋸,「直到二十五歲左右時,我發現了義大利文。我不需要學那語言。沒有家庭、文化、社會壓力。沒有必要。」正因為沒有必要,她熱烈擁抱義大利語文。儘管另一種語言意味著另一道需要跨越的高牆。我猜,或許拉希莉現在更能體會哈金以英文寫作的甘苦。但同時,他們也都在另一種語言抵達了自己。
我時常覺得,哈金是華文文學的美國叔叔。如果文學寫作是一個巨大社群,那麼在當前台灣,我們透過翻譯接引或汲取來自各方的文學資源,正持續影響或滲透在地的寫作構成。例如,對一個小說初學者來說,太宰治、村上春樹、瑞蒙.卡佛或艾莉絲.孟若等人,可能比任何一個華文作者影響更多書寫的視野。哈金打開了另一種影響方向:從英文的邊緣空間(既是語言的也是內容的)書寫,抵達英文文學的中心地帶。哈金拓展英文文學的書寫邊界,也透過翻譯成華文,反過來形成另一種略帶距離、帶著翻譯腔的寫實文體。大多華文讀者恐怕都是透過台灣中文版來閱讀哈金,並以這些作品來理解現代中國、當代美國的內在景觀。
老派的哈金二十多年來,始終堅守寫實路線,穩定產出,即使放諸美國文壇也是少有的多產。他說:「英文寫作最困難的地方是怎樣在『成功』之後仍能不斷地寫下去。當你問美國作家為什麼又寫了一本新書時,他們常會說,『我想繼續做為作家存在下去。』這種低微的動機其實也是才能的根本,表達了不斷創造的欲望。」
這是生存之必要,也是寫作之必要。
作者簡介
1981年生,雲林人。臺大歷史所畢業。曾任耕莘青年寫作會總幹事。做過雜誌及出版編輯。著有《字母會A~Z》(合著)、《文藝春秋》、《黃色小說》、《壞掉的人》、《比冥王星更遠的地方》、《靴子腿》。最新作品為長篇小說《新寶島》。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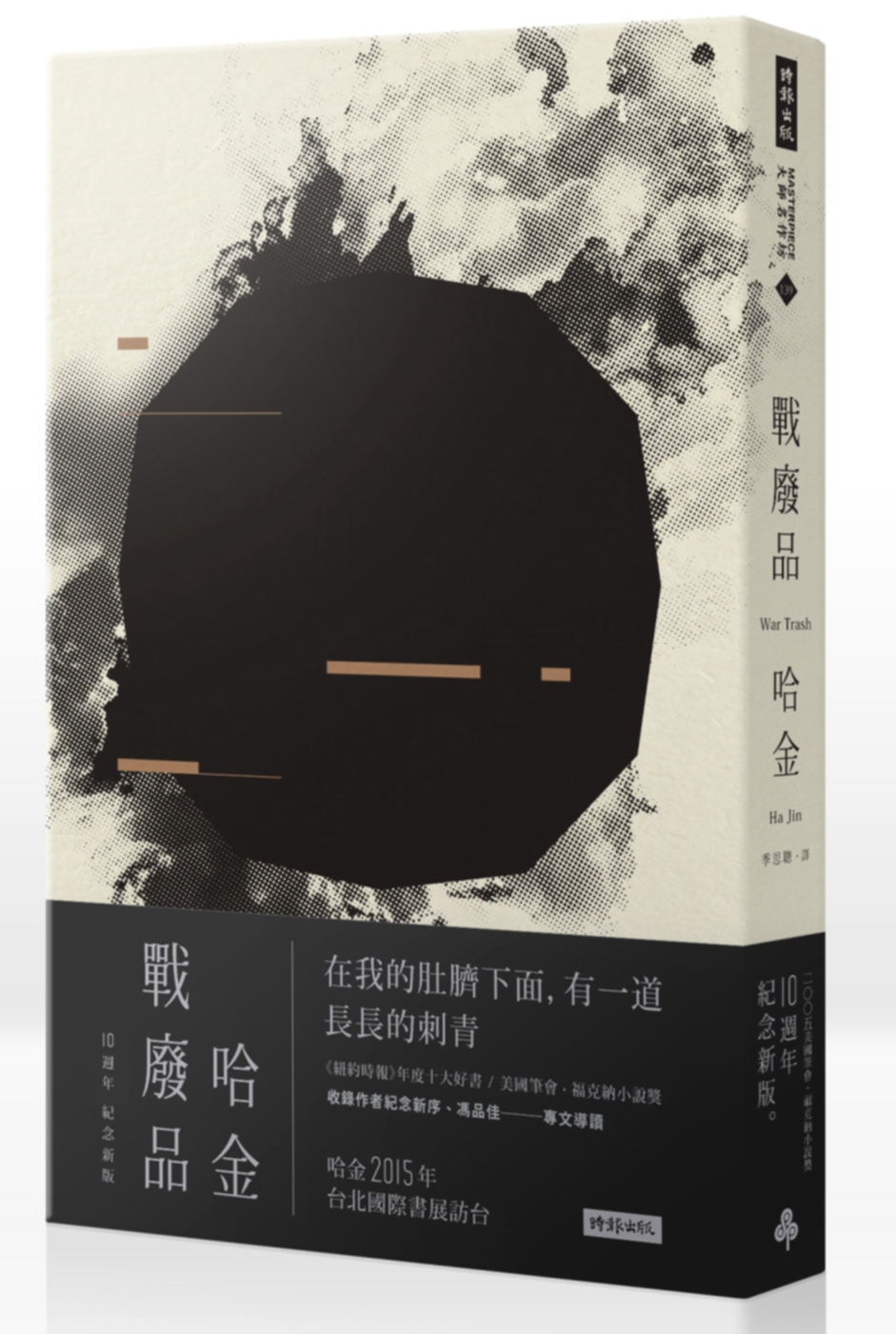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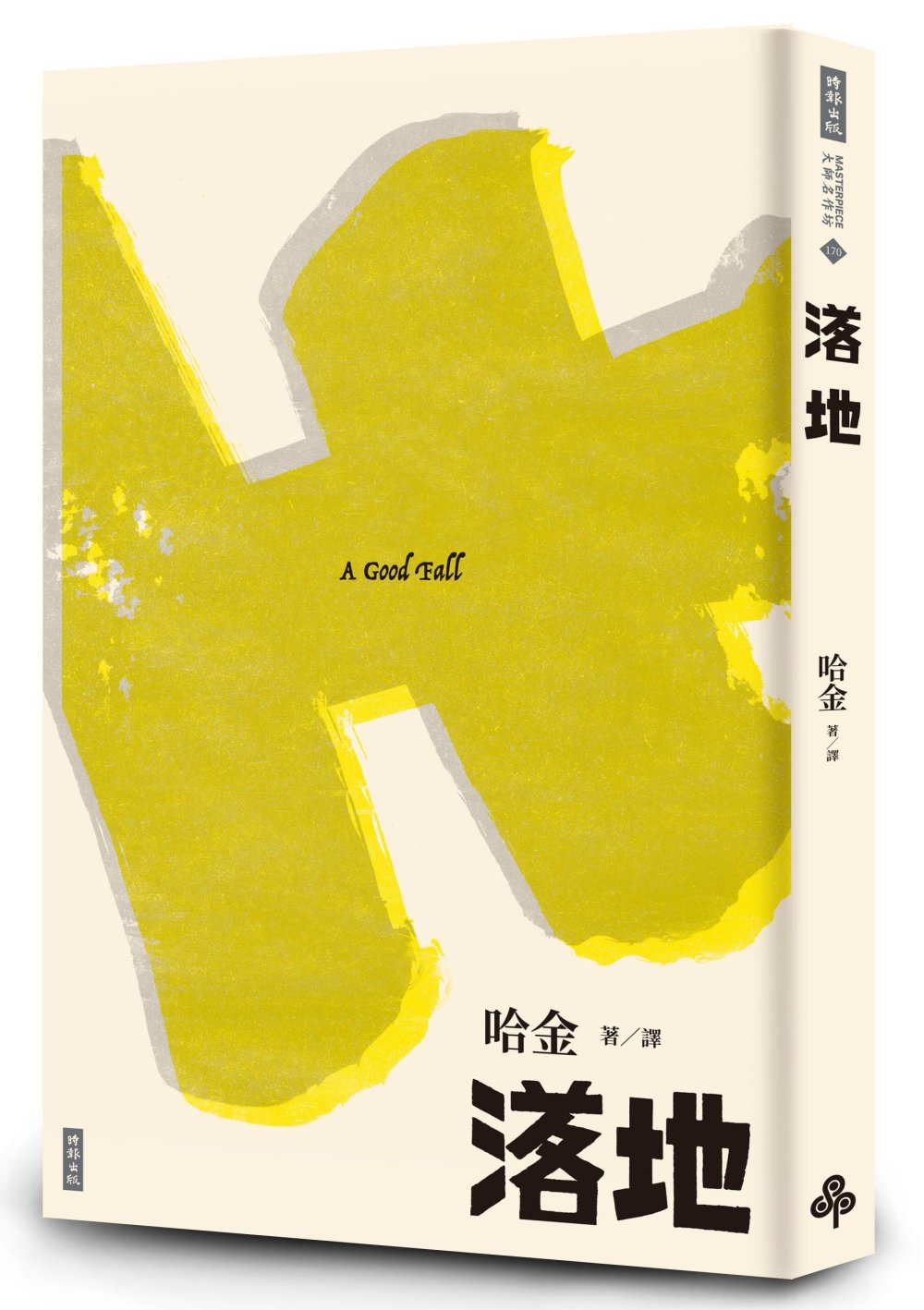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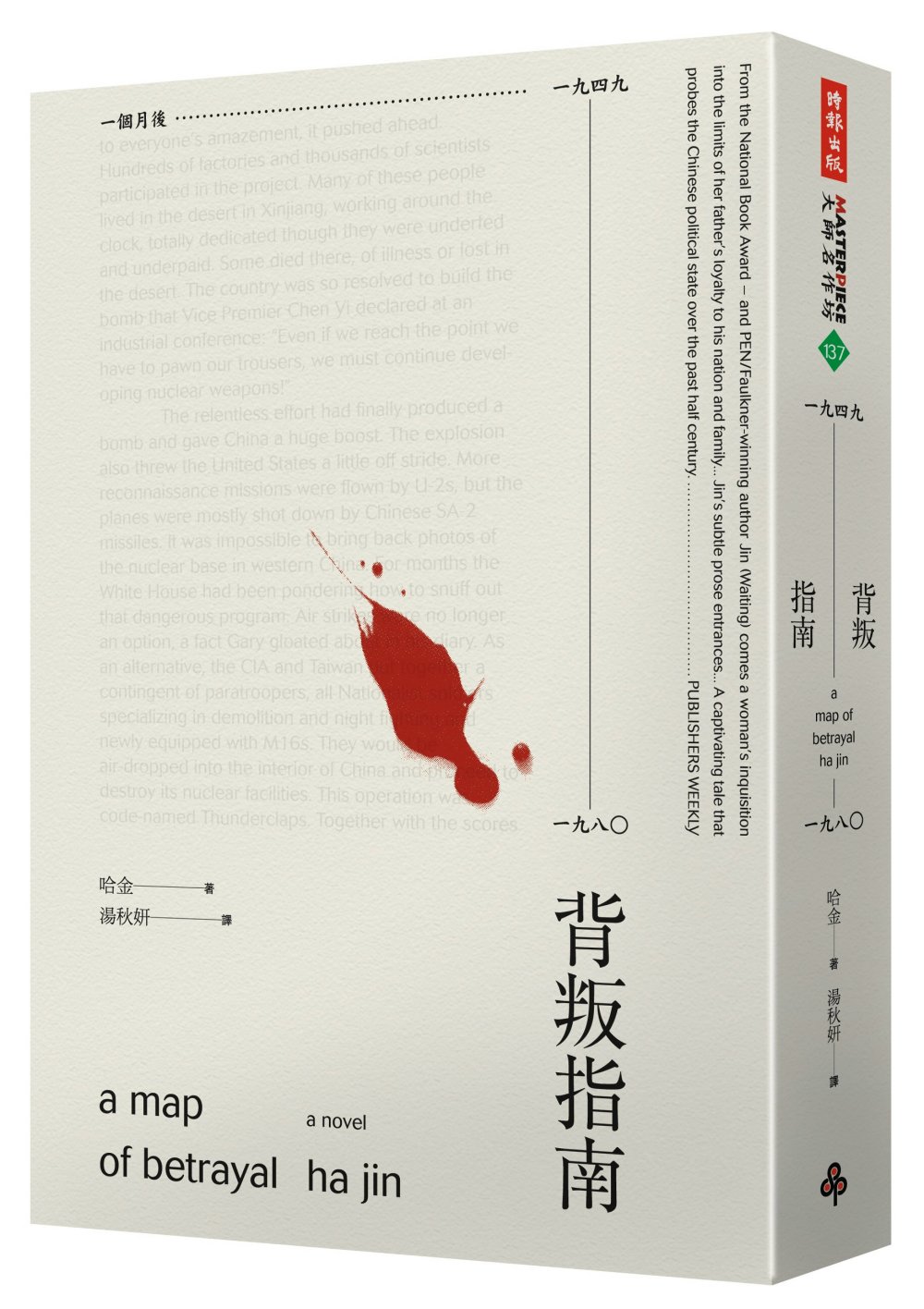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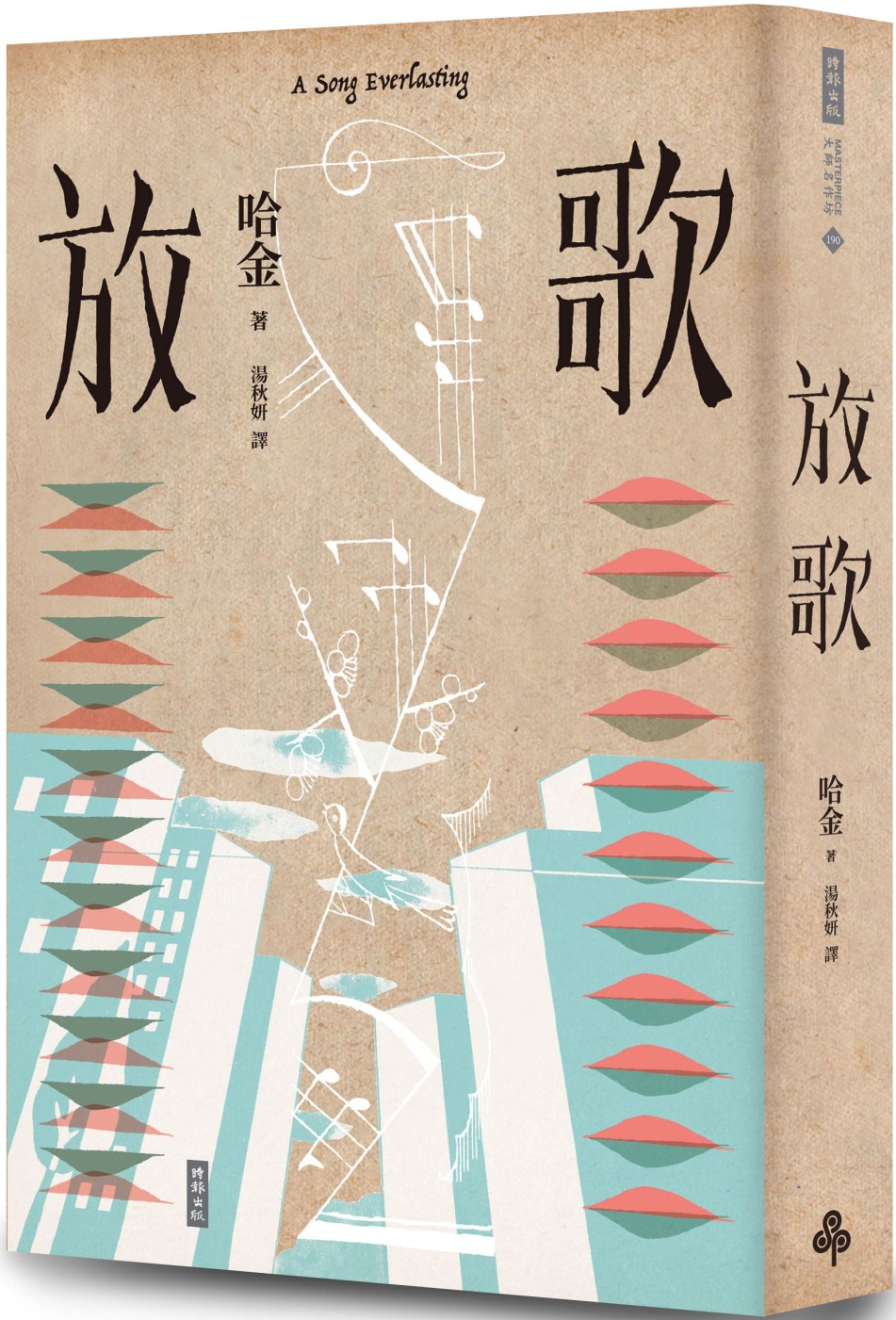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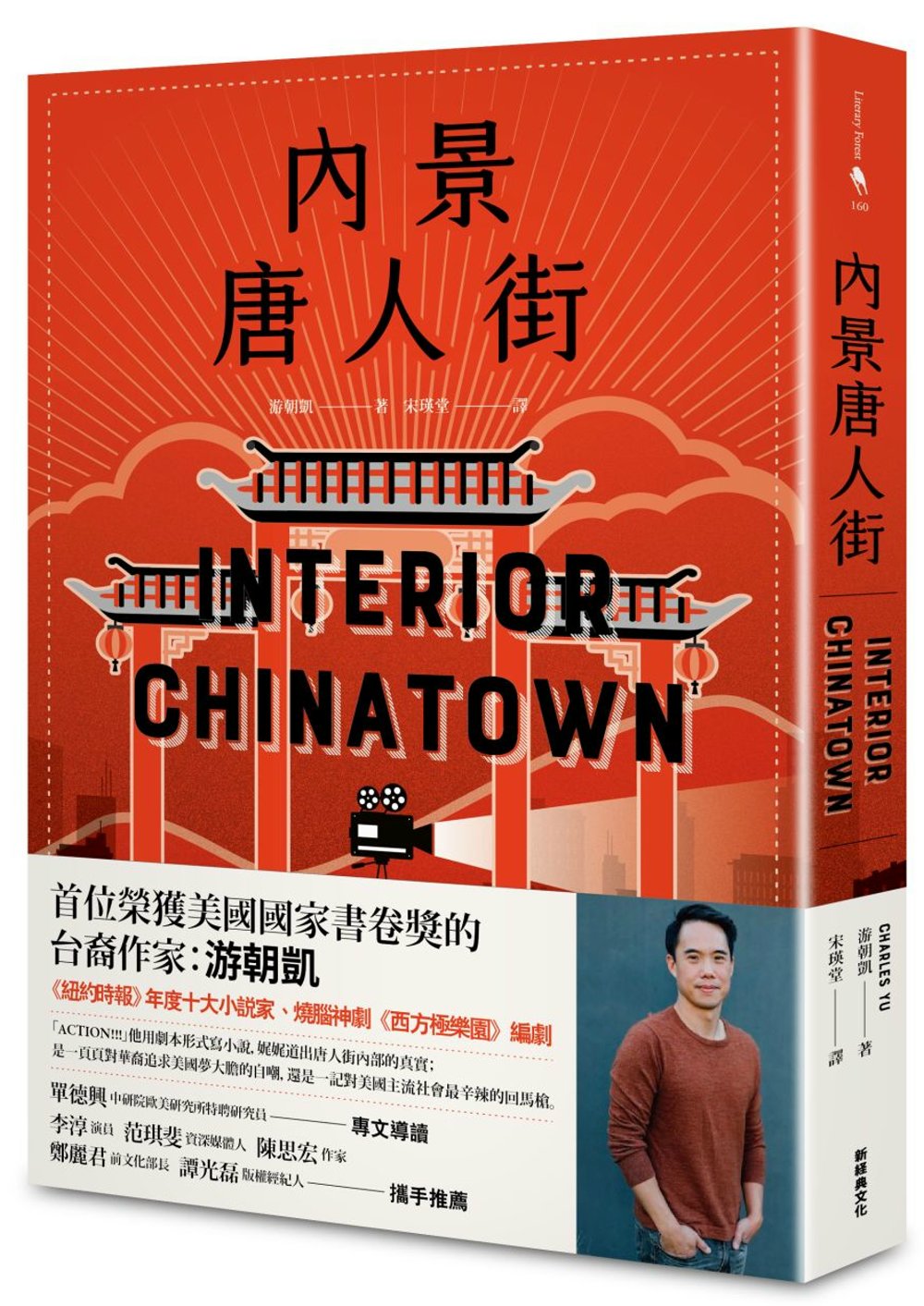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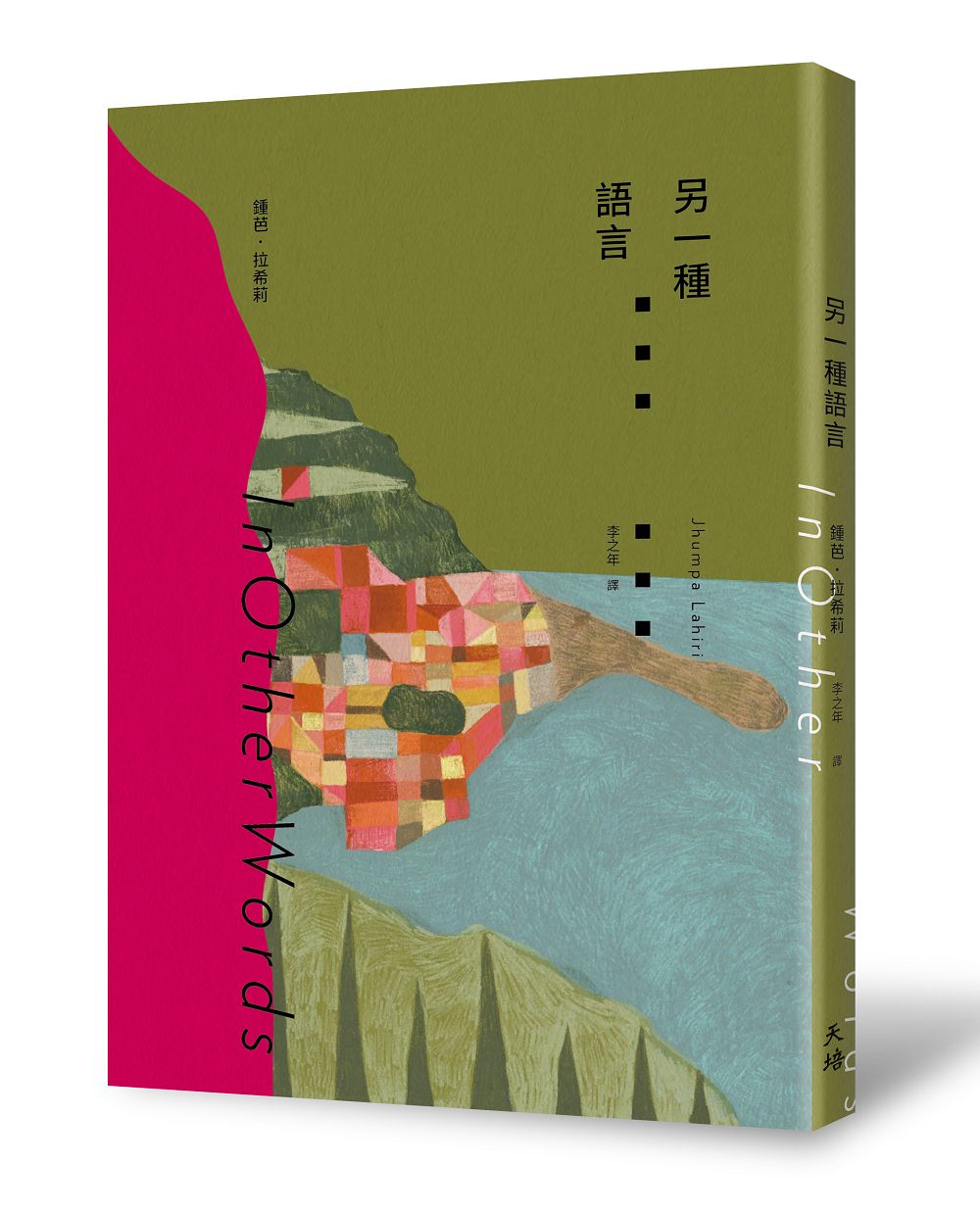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