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超過二十年歷史的馭墨三城文學獎,由雄女、雄中、道明、中山大學附中、三民等高中共同舉辦,是高雄區指標性校園文學獎,運作皆由學生發起,顧問也是文學獎創辦人之一為作家林達陽。
青春大作家 ╳ 第24屆高雄馭墨三城文學獎╳ 小說首獎

被凝視的無能女體
文/曾家茗|高雄女中
她突然有一個衝動,想要在旅館裡待上好一陣子。一切都是那麼地臨時,卻像是有個人早已在旅館那等待她的到來。
入住前的那天早上,她接到情人L的電話,問她家可不可以讓他借住幾晚,她連原因都懶得問便拒絕了。然後L沉默了很久,久到她以為他是打來沉默的,她聽見爐子上燒開的熱水發出高頻的尖叫,她不耐煩地說去泡你的咖啡吧,這欲言又止的不快才被他勉強收結。
掛了電話,她突然感到一陣不可控的飢餓,從內部勃發壯大,像是熬過夜晚的棄雛,在清晨的亮光中瀕死。但她沒有任何一點食的貪慾,只好逼迫自己喝杯熱水、吃點隔夜的淡粥。她後悔剛剛這麼快就拒絕L,也許她可以用自己喝不了的清水替他泡杯咖啡,在早飯桌上看著他修長的指節與濕潤的嘴唇,一口一口喝下苦澀的液體,像是自己在進食一般,內臟與脾胃感到溫暖。
但她拉不下臉回頭去求L,於是她打電話給另一位情人R,問他家可不可以讓她借住幾晚,R連原因都沒問便答應了。然後她沉默了很久,久到她以為自己是打去沉默的,但她確實在開口後就反悔了,她並沒有任何一點想要見到R的慾望。她忘記這通電話是怎麼結束的,好像是R熱情地說他會期待她的到來,也好像是她騙R說她愛他。掛上電話後,她感到羞愧,卻沒有一絲的歉意,即使她後來真的失了約,並且開始對R感到厭倦。
她入住的旅館不新,允許旅客們抽菸,令她滿意的是只要多付一點小費,餐點便可按時送至門口。她點了一支菸,坐在床頭上抽,並隨手把房裡的燈關上(床頭有一個可以控制各燈的面板),但午後的光仍從窗簾上方的縫隙透了進來。
頭頂的光線忽明忽暗地灑在白色斑駁的天花板上,就好像在水族館裡的大缸,看著水帶動四面八方的光,在透明壓克力板上穿梭、游離:偶爾閃避水母的冒失,偶爾纏繞魚群的鰭邊。她覺得自己是鮮明的海底世界中,唯一一株趨近於白化的珊瑚,盲而且脆弱。她突兀地生長在細沙裡,任觀魚者一再對上又撇過目光。
她想起16歲那年的初夏,陽光一如今日無可避免地爬進房間,她沒有慾望,但出於好奇她還是把手指頭含進了自己的陰道。她尊崇儀式感,在骨盆下鋪了張乾淨的小墊子,剪齊指甲,洗手三次,深吸一口氣,再緩緩地前進、前進、前進至底,但她感覺不到歡愉,只是靜默地豎著中指,躺著。她不知道接下來該怎麼辦,拔出來嗎?還是轉動?或者指尖發力?空調在吹,光線在動,一切靜默無聲。那時的感覺跟現在一樣:水族館的大缸、白色的珊瑚,沒有人想要在她身上逗留太久。直到房門外傳來某人的腳步聲,她才感受到些許的擁塞,也許是因為緊張的關係,她的甬道被迫地將她的手指吐了出來……
好燙。她的思緒被迫停止,菸已經見底了,她不自覺地丟下菸蒂,飯店的地毯被她的恍神燒出痕跡。她拿鞋熄滅了星火,並去浴室沖洗紅腫的指頭。她下意識地關門、反鎖,豎起中指沖洗,恍神地看著水在指尖化開,並在接觸到洗手台的那一剎那一致地往排水孔湧去。
然後她又坐回床頭,開啟所有的燈。
每次在燈光下,她總覺得有人正看著自己,於是她乾脆什麼也不做,頂多安靜地坐著,抽菸。像天花板上那兩台速度不一的舊式風扇(左邊轉得比右邊慢許多),週而復始的循環,並且百無聊賴。她的每一日,在吃飯、在行走、在夜晚、在清晨、在超市、在酒吧,她停留原地,耐心地迎接那些目光。有時,幾個目光會成為她玩弄的情人,但大部分的凝視只會出現一次。
床頭櫃的手機響了,是R打來的。她知道R平時不會輕易地打電話過來,除了一種原因——這是交往前的約定,她要求她的情人們必須被她注視——她接起電話,聽見R與另一個人的喘氣聲,她開啟擴音,放置手機,並輕輕地摩擦右手中指指尖凸起的小水泡。每次在這種時刻,她總會注意一些不重要的小細節,像是背景的白噪音、另一個人的用詞、R的回應,她可以想像他們正在充滿濕氣的房裡,也許是被大樓陰影遮擋的平房,又或者是老舊的小公寓,除濕機開著固定的頻率,低平地貫穿整場歡愉。她清楚R的習慣,當R的聲音迴盪在空蕩蕩的旅館房間時,她的腦中浮現了R身體赤裸的顫慄,像是落雷從頭頂降下,她感到久違的興奮。
當電話那頭只剩下R與另一人粗重的呼吸聲時,R一如往常地開口喊她的名,輕柔地像貼著她的耳廓,她可以感受到R吐出的濕氣與熱度。那樣的真誠和溺愛,迫使她想起自己對R如同報復的凝視,她突然感到一陣反胃,抓起床頭的垃圾桶就吐。
她吐得很厲害,但除了早餐的一些湯汁水液,大多都是乾嘔。等到她平復了情緒,R也剛穿好衣、走到大街上,他像個交往不久的情人,捧起電話就問,我今天做的好嗎有讓妳開心嗎妳什麼時候要來我家呢我一直都等不到妳,她平淡地說我們以後不要再見面了,R慌了,他問我做錯了什麼嗎還是我之後不要再這種時候打電話給妳了妳不喜歡的話沒關係啊,她說沒事,只是真的不能再聯絡了。
R當了她目前最久的情人,她以為這次會跟以往有什麼不同。掛了電話,她把所有關於R的紀錄刪去,並順手把其他守約的情人A、K、W的號碼也一併刪除。她有一種鬆了口氣的感覺。
房門外傳來晚餐送達的敲門聲,但她沒有食慾。
那天晚上她早早就去睡了,旅館的床上僅有一條絲質的薄棉被,也許是因為冷,但也可能是因為飢餓,她翻來覆去了好幾個鐘頭。直到她不情願地張開眼睛,看見窗外的燈光灑進房內,她才突然意識到有人在外頭等她。她拉開窗簾,眼前是另一棟一模一樣的旅館,對窗有個女孩也醒著,不,應該說她看不出他的性別,只是直覺地認定他有著某一種女孩的氣質。
她知道自己遲到了很久,於是報以羞赧的微笑,他看起來並不介意等待,只是用優美的手勢比劃著重複的語句。她不懂手語,卻毫不猶豫地點了頭,他給她的感覺並不可怕,反而有種讓她願意獻身的親暱感。他再次揮動指節,動作飛快,從鼻樑落至下巴再舉到臉旁停滯數秒,在唇上劃三個大圓再滑到胸前,輕點雙手再推往額頭,她被迷住了,目光聚焦在他的指尖上,想記住,卻依然漏掉了好幾個步驟,等到他停止了動作,她才發現他一絲不掛地站在窗前。白赤的身軀在她眼前展開,像是一卷乾淨的畫布。然後他就這麼站著,等待,她漲紅了臉,意識到自己渴望些什麼。她往下觀察深夜裡的柏油路:微起伏、無人、呼吸輕淺、路樹昏暗,她把目光重新投射到他的身上,深吸了一口氣……突然間,左手邊隔著兩間房間的燈亮了起來,她嚇了一大跳並下意識地伸出手把窗簾拉上,她不知道自己在害怕些什麼,但等她回過神並把窗簾再次拉開時,他已經不在窗邊了。
她很後悔。那是她第一次那麼想要展示自己的身體,也許那也是最後一次遇見他了。她失落地走回床上,躺著,想要回味他剛剛的手勢,卻什麼也想不起來。
隔天下午,飢餓叫醒了她,她探出房門想要拿取午餐,卻發現未領的食物全部都被收走了。她無事可做,於是決定先去洗澡。
即使不可能有人進門,她還是依照慣例關門、反鎖。面對前方一大片光亮的鏡子,她突然感到不知所措,要快速解決嗎?還是去關燈會比較好?或者直接背對?想到要看見自己完整的裸身,就覺得害羞彆扭。但她想到他,想到他優美的指節,想到昨夜未實現的膨脹慾望。於是她開始脫衣。
她解開襯衫的釦子,一顆、一顆,從靠近鎖骨的開始,每把一顆鈕扣從洞口推出,她的緊張便加地無所適從。解到第二顆時,她已經可以看見自己微起伏的胸部與貼身的胸衣,到第四顆時,她的手開始顫抖,肚臍露了出來,扣子多次從雙指間滑走。第六顆扣子她解了四次。到第七顆扣子時,襯衫才從她的身上滑落。她看著鏡中半裸的上身,並且用力地捶了一下鏡面。好蠢。在害怕什麼啊。
她接下來的動作便俐落許多,解開內衣釦環、鬆開褲頭、脫下內褲,一切都按照平常的方式進行著。她並未正視鏡中全裸的自己,只是拿起沐浴乳與洗髮精,進到淋浴間沖澡,並同時打開浴缸的熱水。
一進到淋浴間,她又開始害怕。僅容一人的空間是矩形,兩塊長玻璃與角落的牆秩序地排列,沒有浴簾遮掩。她感覺有個人坐在浴缸的邊緣,也有個人站在洗手台前,另一個人則是靠在浴室的門把上,看她。她的菸癮又犯了,但她只能把自己蜷縮在角落,打開蓮蓬頭,等待,些許的熱氣像煙,毫無顏色與形體,他們濕潤地包覆著她,從冰冷的磁磚地板向上舞蹈,輕盈地滾起波浪與漩渦,溢出玻璃簾幕,最後緊貼在微膨脹的透明牆上,使它成為一座多霧的城墎。現在這裡只有她了,她緩緩地從角落站起,像一株從原古沉睡至今的鐵線蕨,舒展幼葉與孢,感受潮濕的暖意。
水氣隔絕了大部分的雜音,她重新回到了水底,一個人的水底。
她在這個時候想起他,昨夜那位性別不明的人。那具身子很美,充滿了祕密,他沒有生殖器,彷彿不是為了繁衍而出生的。他俐落的曲線沿著頭頂往下延伸,繞過腰部後緩行於腿骨,肩膀突出而下身精瘦。他很乾淨,還不懂的羞恥,兩隻瘦長的手輕輕地掛在兩側並不定時地揮舞,那些優美的手語對他來說不像是一種溝通,而像是對自己的撫摸。昨夜,那短短的幾分鐘裡,不只是她入了迷,他也進入了瘋狂的狀態。他的身體像是被神經叢包圍,到哪裡都是刺激,她忘不了他顫抖的身體與失焦的眼神,他清楚地知道她在,卻完全不理會她。她渴望變得跟他一樣。
出了淋浴間,她掛著水珠,又踏進了浴缸。她仰坐,缸的長度剛好容許她把腳伸直,水清澈見底,她清楚地看見自己的裸身。她小心翼翼地伸手去摸,摸得很輕,近乎於點,在碰觸到胸脯之前她就停止了動作。她無法像昨夜的那人一樣,她太害怕這具身體了,像是一塊所有人都覬覦的未知大陸,而她被排除在這場殖民遊戲之外。
這樣的念頭成為具體,是在16歲的夏末,在E的宿舍裡。學生宿舍的冷氣壞掉未修,立扇嗡嗡作響,生鏽的擺頭不時發出尖銳的噪音。她把燈關上,房內的斜陽在微塵中顯得魔幻,E額頭的汗珠滴落在自己的臉上,緊張的呼吸清楚可辨,她撫摸他的觀骨,沿著臉龐將他的長髮順至耳後,並且要求他停止他的遲疑,E答應了,她閉上眼睛,感受到自己正緩慢地包覆住他,像一張有著細小礫石的岸,擁抱一波又一波的浪潮,但這片海實在是太安靜了,無人、無蟹、無褐藻,不過她並不介意,只是專心地享受在漲退潮之間的海聲。沒過多久,E卻慌張地打斷她的想像,妳怎麼了沒有任何感覺嗎是不是我還不夠熟練……E說話急促,聲音越來越小聲,她疑惑地看著他,他形容她麻木的身軀與沉靜的眼神,不像那些女孩啊他說,妳剛剛就像一根擱淺的浮木。
她意識到那片海岸,其實是末日後被遺留下來的。那片無人可以行至的彼方。
在E之後,她的床伴一個換過一個,她期待有人可以走到那無足跡的灘頭,沿著海線激起碎裂的浪花,或者在沙灘上蓋下鮮明的手印。但不管是誰,他們總是會在這片海域中死去,化成細小的泡沫,隨著潮流往海洋的方向流浪。後來E向她坦承,自從那次以後,他就很少做愛。每次看到他們閉上眼睛,我就會想起妳靜默無聲的臉龐,像是要把我吞噬一樣,他說。
她感到羞愧,卻沒有一絲的歉意,她繼續與那些目光上床,並在過程中保持一貫地冷靜。
怎麼做才能跟那具身體一樣呢?那麼美麗的身體、那麼美麗的歡愉……她把一半的頭埋進浴缸裡吐泡泡,看著熱氣鑽入毛孔,皮膚漸漸發紅。她想起E當時說過的話:我並不感謝妳把無能的美麗給了我。無能的……美麗嗎?她從浴缸站了起來,想要冷卻皮膚的悶熱,目光卻對到了鏡中的自己。
這時晚餐送達的敲門聲響起。
她的目光離不開自己的身體,在煙霧的層層包圍下,她終於能理解E說的,她其實很美,跟那具不存在性別的身子一樣美。那近乎平貼、大小不一的胸脯、微凸現的鎖骨、肋骨、髖骨、堆積些許脂肪的腹部下緣(裡頭藏著子宮)、被毛髮覆蓋的陰部……跟她看過的所有女體一樣,但也不全然,她現在擁有了自己的飢餓。
她走向鏡子一步,只要她感受到自己比上一刻加地飢餓。
一步、一步、再一步,她最後跪到了洗手台上,撫摸鏡中的女體。她的手指剝離了霧氣,越來越多的光出現在鏡子裡,但她並不害怕,她知道那是自己的目光。直到女體清晰可見,她吻了她。她緊緊地含住那對嘴唇,焦急地尋找尚未溫熱柔軟的部分,女體冰冷的體溫被她漸漸填滿,那狂烈的靜止畫面,迫使她近乎窒息。空氣被吸光的寧靜像海,而她是僅存的末日後人,獨自站上靜僻地沙灘,踏浪。
她踏著踏著便跑了起來,像是回到年少時期,那充滿精力的青年,依序地退去胸罩與短衣,任鹽粒刮傷赤裸的半身,她越跑越快,追逐著無止境的海岸線,狂風打起高浪,濺濕了她的短髮,她越跑越快,她的赤腳踢起泥沙,印下深淺不一的坑洞,冷風灌進她的五孔,她就快要喘不過氣……
要斷氣之前她驚醒了過來。嘴裡發出嗚咽的喊叫,那似乎不是來自她的身體,而是某種神秘的語言。她喘著氣,蹲坐了下來,浴室的霧氣早已散去,她感到一陣疲累的暢快。然後她穿衣,但又退去,一股腦地把內衣丟進了垃圾桶,走出浴室。
接下來的連續幾天,她足不出戶地生活著,披著同一件袍子,不再打電話給誰,也把剩餘的情人L的號碼刪去。她一貫地吃著旅館配送的三餐,但也不定時地為自己停掉餐點。
在幾個禮拜後的某個晚上,她見到了熟悉的燈光,她跑到窗邊拉開窗簾,他已經在等了,一如那天的凌晨,他赤裸著性別未明的身子。她愉快極了,呵著白氣,在窗上寫字,但她沒有想要讓他看懂的意思,正如同他優美而不具溝通性的手語。今天是微雨的日子,天冷,她的字一剛寫上去就被冷意吃去,什麼也沒有留下。
她有很多話想說,她一直寫、一直寫,他也耐心地看著,有時也用手語做為回應。那些像密碼的話語,之於她,是一種迷人的召喚。她盡情地書寫,他熱情地揮舞,像是彼此不滿足於可預期的飢餓,於是各自在11樓的高空挑逗對方。後來她迫切地解開遮掩曲線的寬鬆袍子,袒露陰阜,感受空氣的冷刺進她的皮膚,那樣的微刺痛感使她狂顫,小腿不由自主地收縮,整副身體超出了她的控制。她必須專心在自己的書寫上,無法分心去留意他的手指。
深夜的道路是熟睡的山脈,吞吐著安詳的呼吸,蚊蚋躲在路邊的凹洞,路樹被黑暗包圍,一切安靜無聲。她享受在這樣安靜的時刻裡,並沉醉於自己的美麗。但她的暢快突然地被其他房間打開的燈打斷,她抬頭,是隔著他三間房的房間。但仔細一看,她驚訝地發現還有兩間房的窗簾未掩,住的人正趴在窗上,看她。有那麼一刻,她很想逃跑,很想轉過身拉起窗簾躲進房間蓋棉被,但她沒有那麼做。相反地,她讓她的袍子滑落身軀,並對他們豎起中指,一種極為厭惡卻善意的表態。
現在,這裡終於只剩下她跟他了。

作者簡介
曾家茗│高雄女中
高雄人。喜歡蜥蜴,有紅色的水壺帽子,之後會有âng-âng ê kng-thâu!→☆°×♪♪♯
看更多得獎作品
1.【青春大作家X第23屆馭墨三城文學獎】新詩首獎:明天將會是頭七
2.【青春大作家X第23屆馭墨三城文學獎】散文首獎:我們17歲,在高雄
3.【青春大作家X第23屆馭墨三城文學獎】小說首獎:我們不能只是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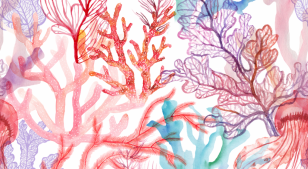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