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讀到沐羽的小說,我並不知道作者是誰。那是2020年夏天的事。我為香港一個文學創作雙年獎擔任小說組評審,連續許多天,審閱百多份小說作品。作品上只有編號,沒有作者名字。某個夜裡,讀到〈在裡面〉,甚覺驚艷,在文字之間有一種沉潛的力量,指出了生活裡幽微的磨人、青春的呆板和想逃也逃不出的空洞,以及人性裡不易衝破的軟弱。這篇小說在當時給我的震憾,我卻無法在評審會議上,翻譯成有利於作品名次的理據。我費盡了力氣,但這篇小說只得到優異獎的名次,即使在我心中,它其實是第一名。之後,我一直有點耿耿於懷,即使我從來都知道,得獎和好作品之間,不一定存在等號。
事隔一年半,《煙街》出版,〈在裡面〉成為書中的第一篇小說。作品會有自己的命運,它最後會長成什麼樣子,或會到達什麼地方,其實跟它表面上的經歷無關,因為某種深沉的變化,總是發生在一切的底部,肉眼無法辨識的所在。
讀畢全書,掩卷之際,我想到「逃亡」和「逃逸」的分別。在我所居住的城巿,曾有很長的一段日子,都是逃亡者的定居地,以及逃逸者的天堂。直至2019年出現了變化,有人說那是黎明前的黑暗,有人指出像地殻重整時長久的地震,也有人說是世界末日的景像,超越想像的例外狀況。在我看來,城巿成了一個被發展商強收用作重建,人們紛紛主動撤離,或被迫遷,而剩下來的殘破不全的房子。
每個留守的人都在想,如何留下來,或,如何走出去。
逃亡或逃逸,並不全憑主觀意志的選擇,多半仰仗命運的安排。有些人原來打算靜悄悄地逃逸,但到了機場才發現自己的名字在某張名單上而被拘捕;有些人原本決定受難,卻因為某種原因而不得不逃亡。
逃亡的意思就是,將永遠無法回到出生和長大的原居地。逃逸者則是遊蕩於黑和白之間,那灰色的地帶,閃避了各種可能出現的後果,無處惹塵埃地來去自如,只是心裡保留著祕密。逃逸幾乎是一種非常時期的處世之道。地獄的某一層,試煉人性的所在,則留給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甘於受難的人。〈永遠與一天〉裡的李浩賢,原本並沒有成為受難者的決心和準備。當他和同伴第一次在學校附近打遊擊時,被自己設下的樹枝路障絆倒後,僥倖被友人拖離現場,糊裡糊塗,就成了逃逸者;一起打遊擊的陳子朗,逃脫了警方拘捕後,不得不離開香港,成為一名逃亡者。他後來成為了受難者,卻不是因為參與任何行動,只是因為在街上無辜地被截查,而惹來殺機。
《煙街》裡的受難者,多半沉默寡言,或,只是被敘述和描述的人,無法言說。李浩賢暗戀張佩珊多年,卻始終找不到合適的言詞表達心聲,直至終於儲存了足夠的對白和勇氣,卻因為一念之差而沒有付諸行動,他就永遠失去了機會,甚至被奪去性命。在〈亂流〉裡,被控「違反國安法及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的議員朋友,幾乎是慷慨就義的,一直都是,被監禁、被剥奪自由、被敘事者「我」探望,被敘述,但,沒有說過一句話。至於失去生命,再也沒有回家的林廷鋒,一直只是哥哥林廷璋的聆聽者。他死後,當林廷璋試圖回想他的話,卻只想到一片虛空。
逃亡者則深陷如濃霧的憂鬱之中,久久無法走出來。〈為什麼靠那麼近〉中的阿嵐,從香港到台灣後,把自己埋進很長的昏睡之中,什麼也不想做。他對任何事情也提不起興趣。身體啟動了防衛機制,把意識從帶有危險的外界隔絕。到了〈製圖〉,阿嵐不再躲在屋子和睡眠裡,他開始每天到街上蒐集別人的生命故事,像昆蟲用觸鬚碰觸前方。這是他修復和外界關係的階段。畢竟,憂鬱往往源於人無法把能量在某方面充分地發揮。阿嵐找到自己的方法,在一本又一本的筆記上畫下折線,直至完成了一百本,他的憂鬱就過去,順利踏進了只有房子、妻子和大海的平庸生活,而平庸是大部分的人所嚮往的幸福和穩定。如果阿嵐是一個有圓滿結局的逃亡者,則張子朗是無法善終的那一個。他在〈永遠與一天〉裡逃脫警方追捕,卻在〈為什麼靠那麼近〉中成了有輕微創傷後遺症的手足。讀者無從得知張子朗成為成人後的生活如何,只知道他再也沒有踏足香港。
逃逸者會否是一個較輕鬆的角色?在〈亂流〉中,弟弟失蹤後,林廷璋患上了「壓力性旅行上癮症」。當他還是空中服務員,一旦想到弟弟,就去旅行;當他在疫情下失業,則在回憶中旅行。表面上在逃離弟弟失蹤和死亡帶來的衝擊,其實,他在逃逸中不斷往自己想要逃避的方向前進,不斷鑽進和弟弟共有的記憶之中。愧疚和失落或許是逃逸者的普遍症狀。或許,〈亂流〉裡的敘事者「我」也是其中一個逃逸者,只是以某種看來機智而戲謔的語調,把某種不知所措製作成語言的衣服。
在受難者、逃亡者和逃逸者之間,並沒有哪一個比另一個更正義勇敢或高尚,他們全是在歷史和命運的擺布之下,各安其分地盡力演出屬於自己的人生藍圖。
在這三種角色之間,逃亡者苦苦掙扎,奮力從身心受創努力活得正常和平常;受難者不是死去就是被囚禁,都失去了言說的能力或權力。或許,仍能握著筆或筆電侃侃而談的就只有逃逸者,他們仍有尚算健康的身體和心靈,可以犬儒,可以幽默,可以內疚,也可以想像。
我們其實都知道,2019 年的香港,像歷史上無數不知名的已無人能記起的人道災難,根本無法跟納綷種族清洗猶太人比擬,因為,後者是所有殘忍中最幸運的一樁,它被發現被保留,成為了受壓迫者的標誌和代表。同時,無數慘絕人寰深埋遺忘的泥土下。
小說可以看,也可以聽,文字也是一種呼喊。《煙街》的呼喊,關於密碼,只有共同經歷過的人,才能聽到某種意義。就像〈製圖〉中的馬哥經營的香港冰室,香港人在那裡圍作一團,說出只有他們之間才能明白的言外之音。「手足不是Condom」、「懷疑人生就去散步」、「插水」、「呢度我地頭」、「多個人多雙筷」。在方言以外,也是某個時間點的記憶和密號。只有共同的經歷才可以獲得解讀的密碼。語言充滿邊界,而回憶是屬於內向者的。
作者簡介
延伸閱讀
- 我希望讓香港人和世界看見勇氣──《時代革命》紀錄片導演周冠威訪談
- 活著的心願僅僅是「挺直腰桿做人」:香港作家韓麗珠談《半蝕》
- 「只要你的文字好,官府是禁不了的!」──專訪章詒和《往事並不如煙續篇》
- 超級歪/危險之所在,亦是救贖之所生:社會運動先鋒的教戰手冊《我們為什麼要上街頭?》
- 馬欣/在人力末世,能避開「消失」的只剩逃亡了──讀吉田修一《逃亡小說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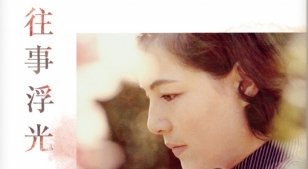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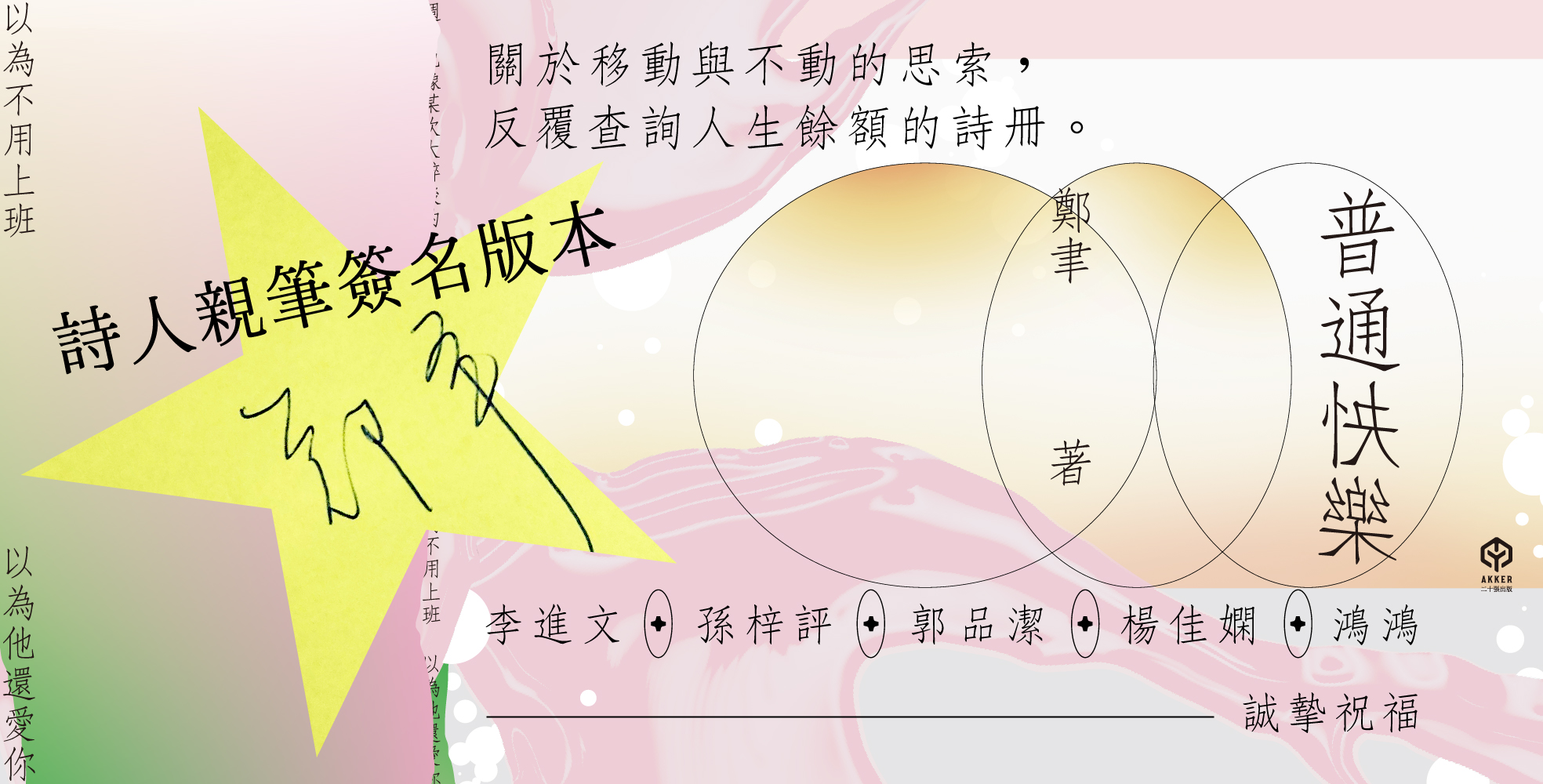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