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攝影/施尼娜,提供 / 章詒和)
2004年,章詒和以被視為中國建國以來的頭號大右派——政治家章伯鈞之女的記憶與視角,寫出了一段歷史,或是說時光間隙的歌:《往事並不如煙》。相隔十七年,當煙更散、曲更淡時,有些人事依然值得念念不忘。章詒和從來沒有忘記,還調度了更多人物與故事,《往事並不如煙續篇》是續寫,也是新憶。如她在其中寫的:「時間是風,能平復很多的往事與傷痛。」
這一回她所書寫的人物,像是:青年便與毛澤東熟稔,最終病逝台灣的左舜生;文采過人,18歲便如預言般寫出「第一傷心民族恥,神舟學界盡奴風」的柳亞子;還有思想右傾,卻未真正走向右派,最早投入中國共產黨,直到去世前仍無法回歸正式黨員的沈雁冰(他以筆名「茅盾」更為世所知)。以及,書中最特別的出場人物,是章詒和「往事」系列中第一位並非親身認識,而是因緣看到其獄中手稿,有當時「中國頭號影星」的趙丹⋯⋯等等。
在章詒和筆下,名字不只是名詞,這些人也不只是風,更是樹。那些被縫進歷史夾層的故事,被她一一拆現內裡,只因這些人事:「枝枝節節都在述說著前朝與當今」。
Q:在您的《往事並不如煙續篇》裡, 續寫了更多於「五七時期」被打入右派的中國文藝人士,從沈雁冰(茅盾)、沈鈞儒、葉恭綽、洪深、左舜生到趙丹。其中您在〈另一個趙丹—「獄中文檔」讀後〉寫道:「政治在中國是一種疾病。」令人不禁想到,在另篇談沈鈞儒文章裡,憶及父親的唏噓與提醒:「小愚,你不要學爸爸,不要搞政治。一個人生活裡真正重要的東西,不過兩三種,這裡沒有政治。」這與您2017年接受香港媒體「端傳媒」採訪時提及的「文人與統治者,歷來都是彼此仇恨又相互需要」觀點,兩相對應,心驚而沉重。「政治」如此危險與絕望,您認為是什麼讓「文人」與它牽扯不休,自封建中國,直至您的父輩?再到如今,您怎麼看自己與政治的關係?
A:中國古代文人多有仕途情懷。他們不是社會統治者,但都有強烈的使命感,也就是人們常說的「兼濟天下」。他們總懷著一種社會責任,力圖幫助統治者管理好社會以拯救天下蒼生。哪怕自己受到威脅和迫害,也不會放棄。這是什麼?這就是文人的一顆嚮往「入世」之心,他們也覺得自己是「濟世」之才——就是自古延續下來的「文人從政」傳統,它也是文人實現人生價值的重要途徑。於是,就有了文人們與政治「糾纏不休」。古代去考科舉,現在爭當公務員。進入現代社會,知識分子實現自己價值的途徑多得很,自然與政治就疏遠了,也拉開了距離。這是個巨大的進步!
父親搞政治,我絕不搞政治,經歷和經驗告訴我:「政治從來骯髒。」
Q:1957年始,中國政府開始了一連串的「反右運動」,但在您的記憶裡,早在1945年延安召開「七大」時(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毛澤東發表的口頭報告中已見端倪;同年十月,毛澤東給周恩來起草的《關於反對劉航琛一類反動計劃的指示》加寫的第五條,更直指:「等蔣介石及其反動集團一經打倒,我們打擊的基本方向就應轉到自由資產階級,明確了下一個,要把它的右翼孤立起來,爾後一步一步地拋棄他們。」
從「反右」的醞釀到1966年開始的「文革」,您在端傳媒的採訪裡也憶道:「文革前,父親看了報紙,跟妳說:『小愚啊,中國近代史上最黑暗的一頁就要開始了。』」回首過往,這一長段延續數十年的歲月,哪一時期或事件,您認為最是黑暗無光?今時今日,又是如何天光?
A:無論章伯鈞,還是羅隆基,他們都有天生的政治敏感。1957年看到〈這是為什麼〉社論,立刻感到中共的整風運動轉向了。1966年看到「516」通知,就預感到一場最暴烈的政治運動即將來臨。當然,章伯鈞沒有料到毛澤東會弄個「紅衛兵」出來,也沒有想到搞抄家、遊街一套。但是他告訴我們說:「這些就是當年湖南農民運動的那一套。」說到「暗無天日」,當然是文革。遊街、揪鬥、死亡,無論是被專政對象,還是造反派,其內心都是恐懼的!今天的中國大陸和國際環境有了極大的改變,但還是一黨專政,人們手裡沒有選票,因此,黑暗還是存在著。怎樣改變?只有靠全民族的覺醒。
Q:《往事並不如煙續篇》裡,談趙丹的獄中生活,更像反照自己生命經歷。其中有段談獄中飲食是「不求珠玉,但求米粟。犯人時時處在食物短缺的飢渴之中,最想吃的是肉和糖。」尤為深刻處,是寫自己:「我獄中十年,夜裡做夢幾乎都與吃有關,寫給母親每一封信的末尾都是要吃的!⋯⋯犯人肚子裡實在沒有油水。母親寄來的豬油,令所有的獄友羨慕不已。每隔幾天,我就用小勺挖一點豬油攪拌到菜裡。豬油攪拌過的菜頓時成了大菜,特別香!我總是有意延長咀嚼的時間,捨不得嚥下。出獄後回到北京,我曾在一盤素燒圓白菜裡拌上一勺豬油。夾一筷子送進嘴,咋這麼難吃?」從年少時的餐桌(康同璧母女作東的西餐、父輩相請的宴席到家宴)裡轉身,經過獄中十年,再到如今,過往經歷是否在您身上留下什麼飲食喜好或習慣?
A:經過十年大牢,最大的飲食改變是喜歡吃大米飯!因為無論監獄,還是勞改隊,基本主食都是粗糧。
Q:針對「中國未來想要走得更好」,您當年在香港的採訪裡回應:「必須清算與『去毛化』。」如此才能走到真正的百花齊放。在《往事並不如煙續篇》的書序裡,您更憶細節:「(1949年後)留在大陸的知識分子滿心以為未來的道路通向天堂,大家邁著歡快的步伐,一齊走進了地獄。希望而來,絕望而去,原來人家許諾的民主、自由和幸福原本就不存在。」這裡談及「更好的未來」,或是真正的民主、自由和幸福,您認為還能如何達成?
A:中國大陸走向民主自由,要靠我們每一個人。而我們一些人總期待出現一個大人物,帶領我們走向民主自由。想當初,鄧小平帶頭搞改革開放,希望以此解決中國集權,封閉、落後、貧窮⋯⋯搞了近三十年,現在可又都回來了:還是集權嘛,還有全面腐敗,還有權貴資本。所以,靠好領袖好班子好政黨是不行的。
Q:自散文起,您也創作了「女囚系列」四本小說,再到寫民國伶人、男旦的《伸出蘭花指》(2019),如今《往事並不如煙續篇》又再重返散文。書中您如此定義左舜生的散文回憶錄:「大人物的回憶錄往往是政治失意後的精神補償,但左舜生的書,不是。」更直言,他的回憶錄《近三十年見聞雜記》是研究近代中國的重要史料。然而,您對書寫自傳式回憶錄,卻在接受台灣記者陳宛茜專訪時說到:「我的一生太痛苦了,現在還沒有勇氣提筆。」想請問您,從書寫他人到自己,兩者間付出的心魂與跨越的勇敢度,有什麼差異?小說與散文,對您想說的故事,又各自起到什麼作用?
A:寫他人易,寫自己難。特別需要面對自己的勇氣。我個人認為,小說和散文都不難,一個是虛構,一個是非虛構,但前提只有一個:「你要有故事!」其次才是你會不會寫,寫得好不好。
Q:自當年您寫《往事並不如煙》以來,「最後的貴族」一詞,已為不同媒體與領域所用。但曾經,「右派」也好、「貴族」也好,它們全被視為禁忌與羞恥的名詞;同樣地,從側目到打擊某種權貴階級的現象,在台灣也不曾停止(只是程度不同),許多文學作品裡都可見到如您曾寫的:「被收回的舊宅、司機與廚師」等等現象。然而,當中國最後一代的貴族們,一一消失,缺失的不只是生活方式與器物制度,那被中斷的某種風骨與意志,該怎麼傳承、該怎麼召喚?
A:某種人物只出現在某個社會階段和某個特定的環境。如康同璧、張伯駒、聶紺弩。某個社會階段過去,某個特定環境消失,再想出現這類人和這類事,幾乎沒有可能性。當下大陸的收藏家極多,沒有一個像張伯駒;如今的作家多如牛毛,沒有一個像聶紺弩。風骨與意志,你有就有,他沒有就沒有。沒有風骨的人、意志薄弱的人大多生活得很好。所以,討論「傳承」與「召喚」在當下大陸似乎沒什麼意義。
Q:在您的心中,如果「往事並不如煙」,它更可能是什麼呢?對於記憶,您曾經說自己並非從小記性好,而是因為「一個人孤獨到極點,孤獨就成為力量,支持你去記憶。」在您的散文裡,經常使用的詞也是「我記得」與「還記得」,對您來說,「記得」這件事,它帶來什麼好與不好?
A:記得就好!可寫,可說,可畫⋯⋯就怕你什麼都不記得。我沒聽說記憶還有壞處。
Q:自《往事並不如煙》等書的簡體版出版被禁,近十多年來,網路成為重要的傳播媒體,查封的除了書籍,更多了網頁(如討論區「貼吧」被關閉)。請問您,直至2018年都還能夠在「微博」上看您分享生活或是手稿,這幾年您不再使用的原因?以及,身處今日中國,您怎麼看待網路的力量與使用它呢?
A:我的文字被查禁,微博被封,微信是「限群限圈」。但網絡是不可能完全封死我。比如前不久,我寫了一篇題為〈我本來就不漂亮〉的敘事散文,朋友發到網上,三天之內有二十萬人瀏覽。他們不用章詒和三字落款,用「張一合」之類,但人家一看文字,就知道是我寫的。所以我常說:「只要你的文字好,官府是禁不了的!」
章詒和在2019年出版了小說集《伸出蘭花指:對一個男旦的陳述》後,曾在受訪時說這是她的最後一部小說,幸而又補充:「告別文學,但還沒有告別寫作,還是會繼續寫。」這一本《往事並不如煙續篇》就是她的「繼續」。經過寫小說多年的淬煉濃縮,她的字語愈發簡凝,就如同這本延續近二十年的書名,以及她與父輩一生的故事——往事並不如煙,那是因為往事本不該遺忘。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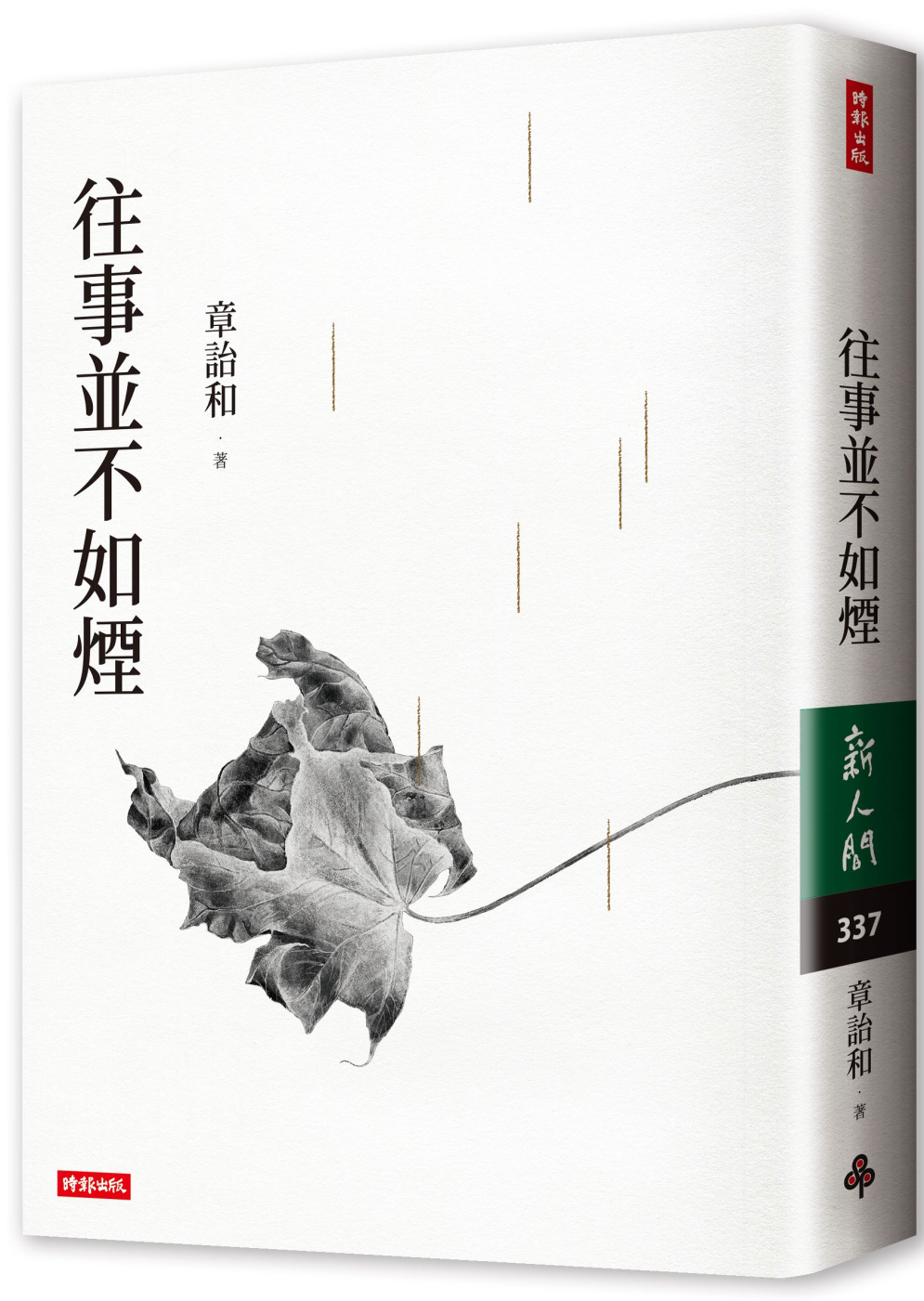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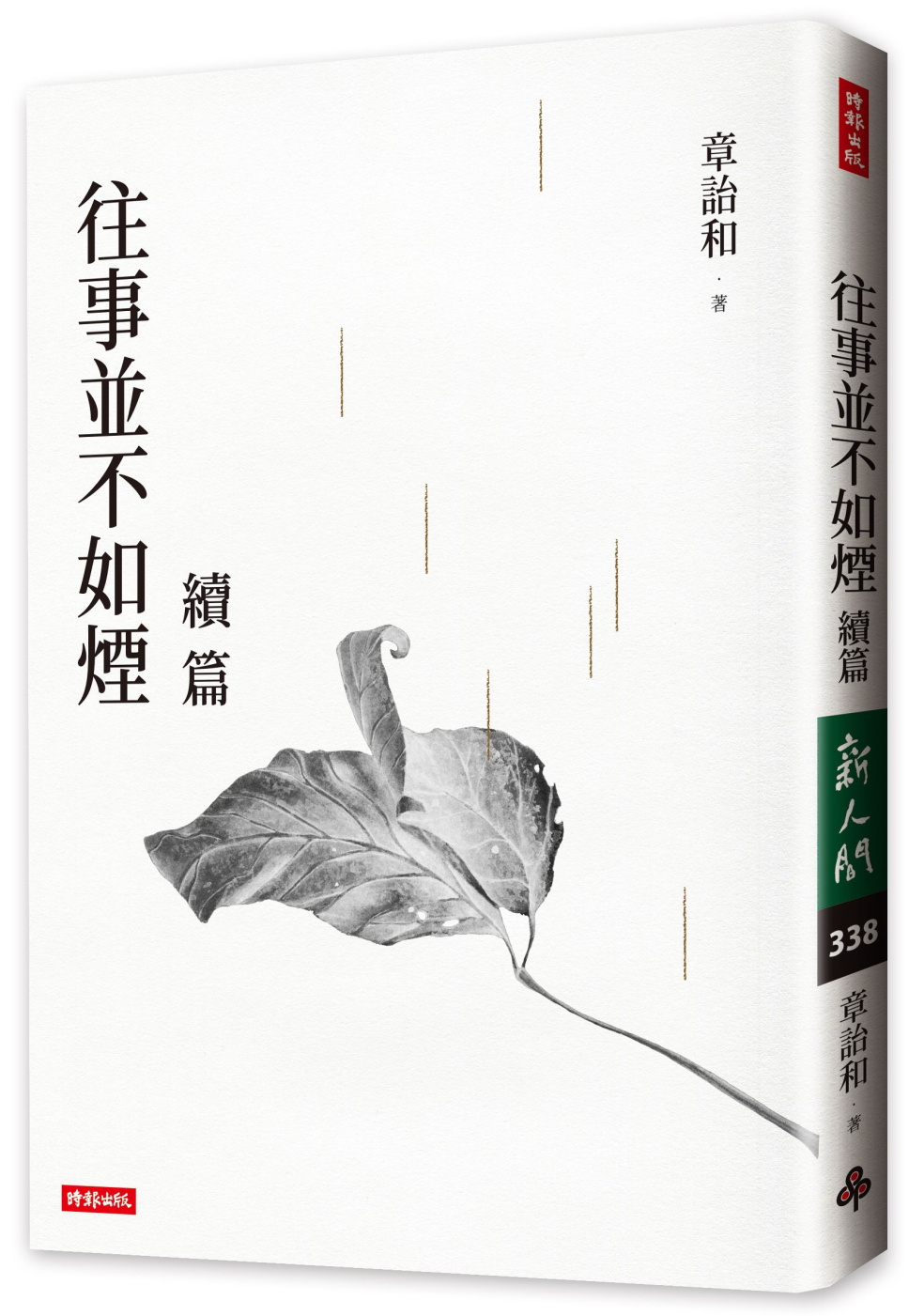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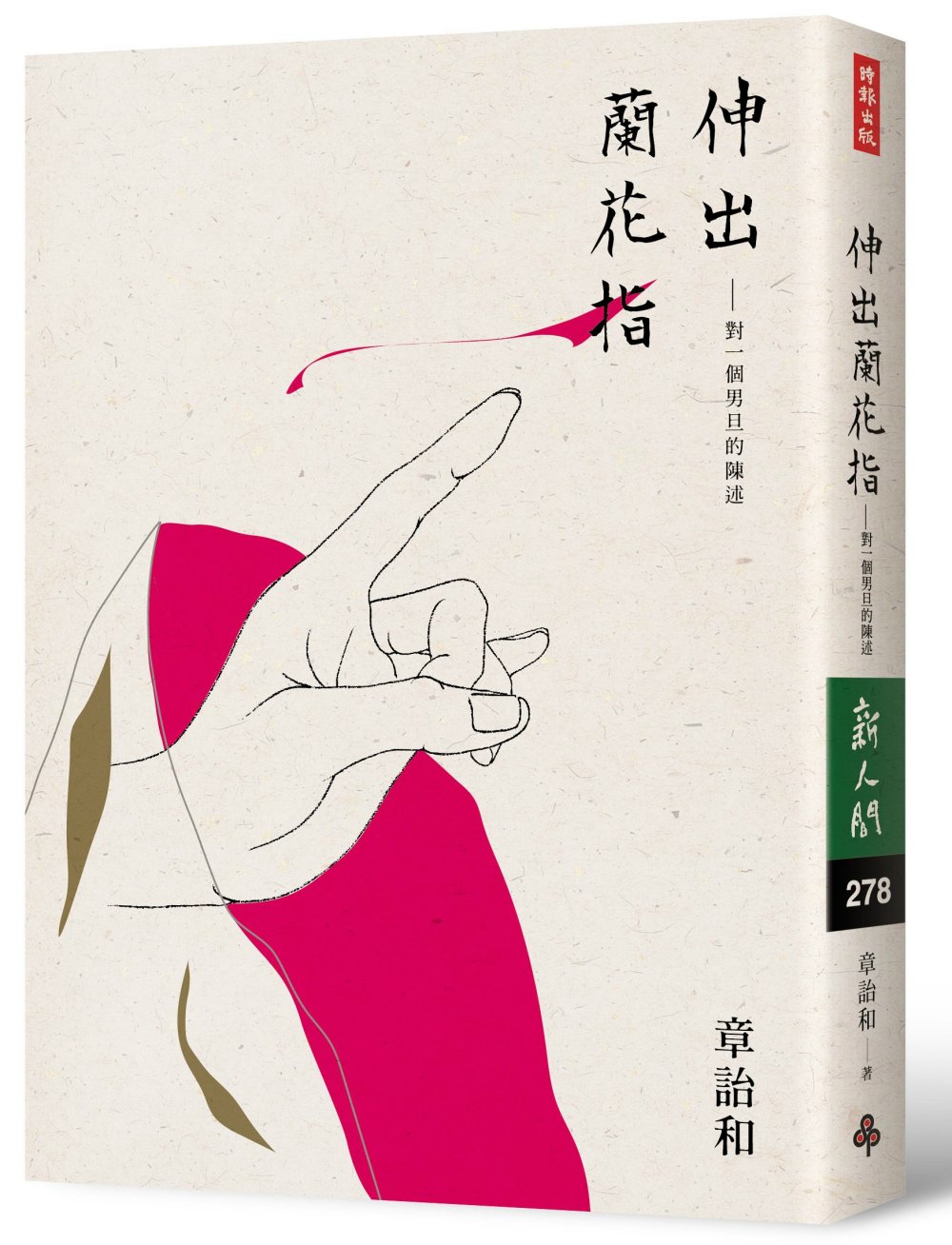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