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的人,活著活著,恐就成為自己欣賞的演員,只是碰巧的,真正的觀眾就只是自己一個。他們如此入戲,深怕自己的人物設定不夠連戲,最後他們不計真假,因戲假只能情真,別像書中的庸介提早出戲就好。
自己都搞不清楚真假的社群人格
人如今不僅有社會性格,也有網路性格,為確保連戲,有時連自己都騙。「無盡的耳語」就是「噓」一聲閉嘴警告詞的迴盪。
人心迴盪的常是自己的耳語,有不能講的、再三斟酌的、與自己人設不合的。我們都收得嚴實。而那些不能宣之於口的,經年累月下來竟比說出口的,更能形塑我們。
這本《無盡的耳語》比起桐野夏生以往的作品,有了更多的對白。但埋伏的也是在對白下的暗流。
那些暗流甚至比他們說出來的話還更有清楚的輪廓。有趣的是,書中這些角色從小就習慣活在謊言裡,無論是哪一個世代,為了要讓自己的社會人格搭建得穩當,往往連自己都搞不清楚真假。
需要女配角的主角癮
女主角真樹就是這樣寧可半夢半醒的人。對於謊言從善如流,對於拆穿他人騙局總輕言放棄。有時懷疑念頭會一閃而逝,但隨即就為方便行事而掩蓋掉了。隨時都以一種下雪似的漫不經心,讓其掩蓋掉歲月的煞車痕。
真樹雖然是以採訪維生,但多半為企業主做訪問,讓那些需要遮掩或美化的,不至於走漏風聲。於是真樹視若無睹的,反而挑起讀者抓蟲打怪的癮。真樹對好友美波有著情感上的依賴,她似乎也沒有很多朋友,儘管美波對她的態度反覆不定,但她總像抓住唯一的稻草般,不捨放手。
她的婆婆,真樹雖真心不喜歡婆婆自私的性格,受不了她的挖苦,但總是不斷退讓底線,就算已經再婚也是如此。彼此都需要對方比自己更慘。
真樹不想讓人討厭,好像讓人討厭會很麻煩般的應付著。所以她下意識總是感覺累,只是不想當一個壞人一樣敷衍。於是她在第二段婚姻裡,即使不習慣,她也從不畫出自己的底線,也鮮少與丈夫克典溝通什麼,如此在安靜豪宅過著做客般的日子。
中年人多少想逃離自己人生的一線戰場
若說有什麼傷痕,自然是有的。她心上的口子,是她第一任丈夫庸介的失蹤。從第一年的擔心到第二年懷疑丈夫是自殺而自責。這分懷疑才勾出了她對周遭騙局的警覺心。你才發現她對自己人生也是個僅止於出席的逃兵。
與其說這本書有什麼犀利的案件觀察,桐野這次比較像挖人心裡的井,看那些書中的中年人有多少是自己人生的逃兵。真樹不想面對自己的逃避現實,她躲進另一個婚姻裡。即便那戶人家女主人的痕跡仍在,其中的家人鮮少與她交流,而她的丈夫近乎霸占她所有時間的待在身邊,彼此間相伴大於相愛。
她與她的兩任丈夫都是人生的逃兵。有的是直接人間蒸發;庸介在青春期就慣性失蹤,之後也沒真的活進現實裡,懷抱著從高二開始的大秘密,他與他的社會性格全然相反地活著。終於,神經線崩掉。
而真樹與她的第二任丈夫面對人生問題,就懸在那裡。如他們聽說庭院裡有蛇窩一樣的反應,雖然感到討厭或不適,但都假裝房間裡沒有大象似的活著。
這群大人都是善於騙自己的高手,謊話講多了變成真的以後,不僅傷害到他人,也像一個活火山一般活著。真樹與丈夫克典平靜像死火山,默默地譴責自己,總習慣虛應故事。
不靠假面就有消失的恐懼感
他們總有別的事要忙,光是維持自己的人設,真的讓書裡的老老小小都累透了。包括克典的小女兒,為了發洩對父親失責的怒氣,於是開部落格為自己的悲劇加蔥加蒜的搞了個重鹹悲劇。人們愛沾悲劇的光,群舞出仇恨的大會操,讓克典的女兒真矢帶風向玩上了癮,索性將悲劇人設的油門踩到底,如煙花一樣盛大地放大自己的謊言。
這次桐野夏生用她比針還銳利的筆,以社會當成主角,玩起了人性戳戳樂,裡面有多少個角色,就有多少個謊言。沒有什麼好人或壞人,每個人都有無盡的後台與小小舞台,死守著那點光源與安全感而庸碌著。
桐野藉由配角的真實,來反串主角的正當性。這是時下社會化後又加了社群人格,如無法無天地加蓋了房間,最後如大型違建與繁衍體,讓人懶得拆穿他們的謊言。
如我們按下的義理讚,只是方便看著他人的套路,彼此不下戲、彼此留一線。
女人的主戰場仍是彼此
桐野夏生可貴在她對自己的主角並不寬容。從成名作《異常》開始,她就讓筆下的主角逐漸扭曲的性格,與周遭人的扭曲交纏在一起。讓「他人如地獄」的呈現不只是鏡像呼應,而是像水草一樣糾纏。儘管覺得對方可鄙,如真樹對菊美與美波,有著自認寬容的天真。
而那種「天真」更激怒了對方,彼此卻都捨不得離開對方,她們需要彼此來較勁。其中女性之間的關係,不乏以男人為獎盃,無論是婆媳拉扯,還是同愛上一男的好友。如百年宮鬥劇,有時丈夫與兒子的位置形同虛設,但在這社會設定下,她們仍需要一個假想敵,讓自己繼續假寐,但多是耳語的獨腳戲居多。
故事前半出現的蛇,彷彿沒人看見過,只是個隱喻,他們每個人都有不能觸碰的真相的隱喻。
桐野夏生向來對於日本人表面上禮貌周到戳得毫不留情。他們像忘了自己一樣,有的就此崩解,有的演到底。如同最後真樹的內心戲:「石堆裡冬眠的蛇會不會知道自己的害怕。」如此悲涼,彷彿真的是個戲精。
作者簡介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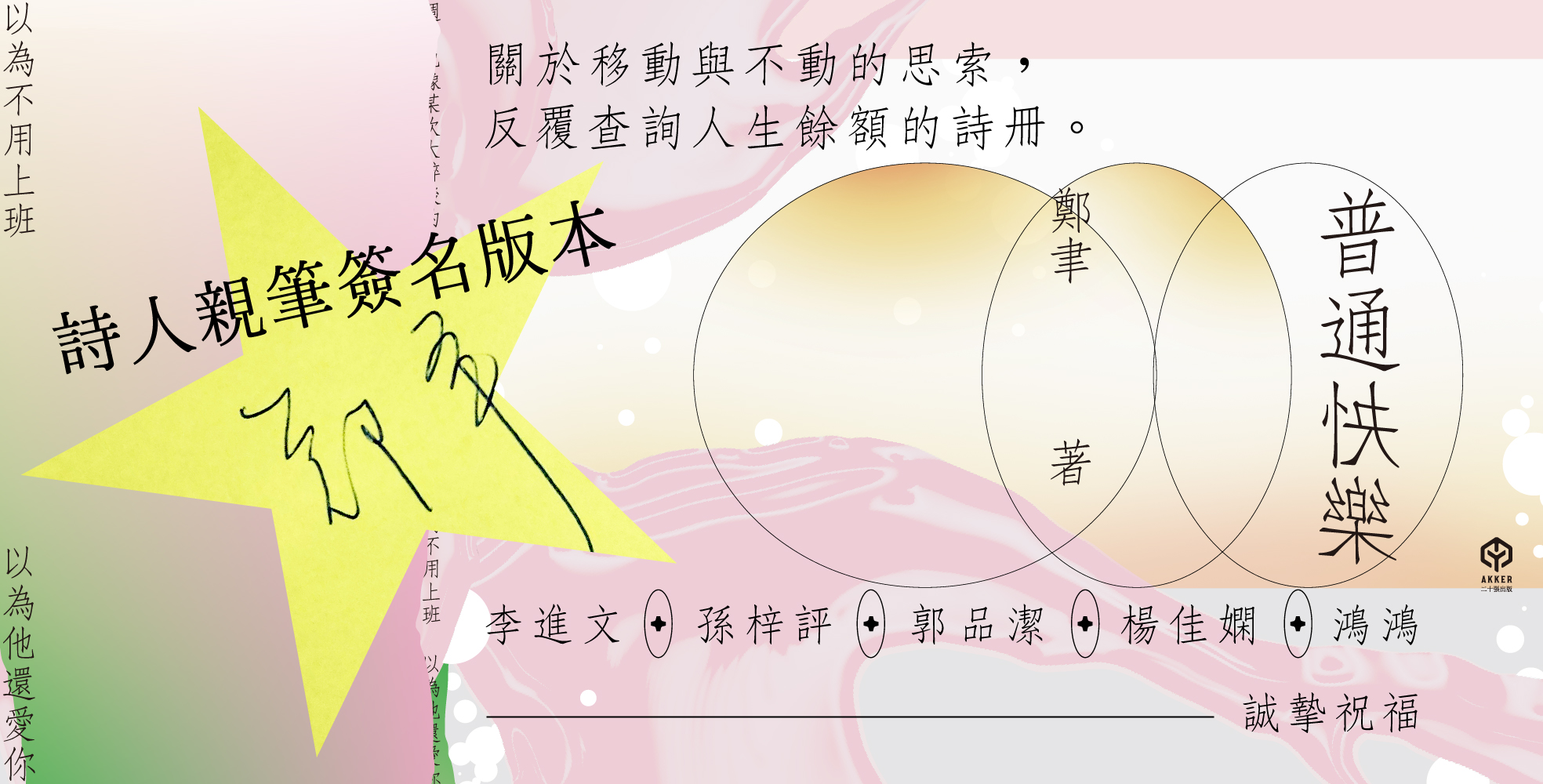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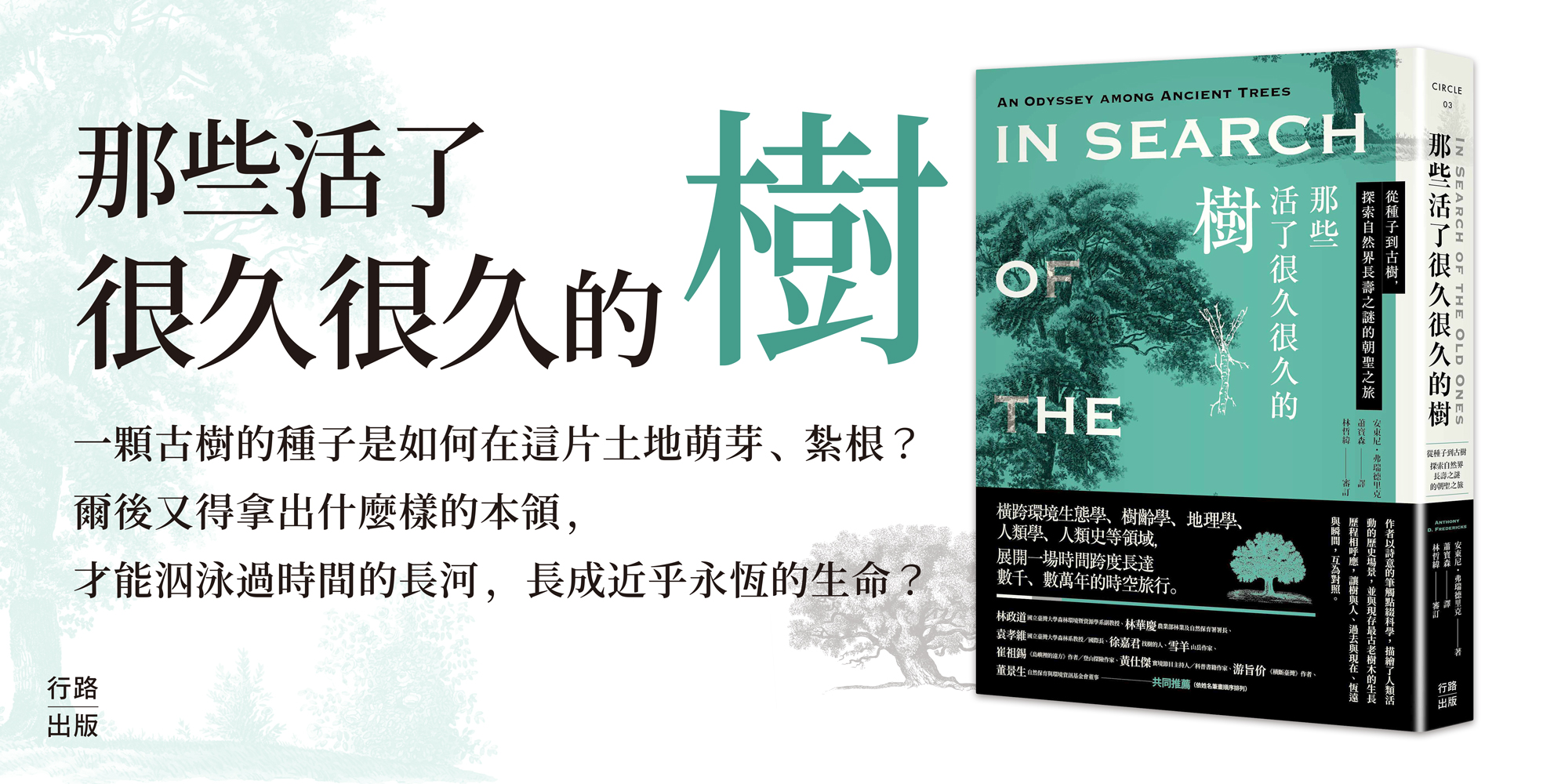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