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天紀錄》有個有趣的疾病隱喻,主角法蘭希絲在遭遇一段混亂的情愛時,發現自己得了子宮內膜異位症,子宮膜細胞逃逸出子宮,在體內遊盪,沾粘其他器官,造成嚴重經痛,可能造成卵巢功能失常。
這讓人想起,過去西方認為女性如患有歇斯底里(Hysteria)的精神病,乃是起因於子宮在體內遊盪,暗喻少女法蘭希絲浮動的情感漫遊。法蘭希絲初戀對象是中學女校同學玻碧,兩人分手後仍是好友。在都柏林念大學時,她們搭檔表演朗誦詩歌,認識了作家梅麗莎。玻碧傾心於梅麗莎,而法蘭希絲則與梅麗莎的演員丈夫尼克意外發展出婚外情,新世代的危險關係於焉開始。她愛她,她愛她,她愛他,他愛她,作者莎莉.魯尼(Sally Rooney)處理四角關係題材,顯現出近年歐美千禧世代愛情觀的趨勢,性傾向已經不是重點,人物個性與意識形態對戀愛的權力糾葛更為重要。
四人之中,個性塑造最立體的是玻碧與法蘭希絲這對前情侶。玻碧凌厲明媚,智識過人,自詡為女性主義者,喜愛一腳踩住他人痛處,製造混亂,憑藉尖銳的言語武裝自己,做為對自身富裕家庭背景的反叛。法蘭希絲低調內斂,信仰共產主義,卻暗地羞於面對中下階層的父親,彆扭的個性使她一再踏進泥濘,沾得一身煩憂。男主角尼克則不同於傳統文本壓迫女性的陽剛男性,他性格優柔,溫和而善於聆聽,深受憂鬱症所苦。作家筆下的人物對自我與他人的認知充滿猶疑,不知彼此的閒談、試探、質疑、託詞拼湊起來,究竟該定義為愛情,還是友情。小說裡對話一來一往,拉鋸戰般想瓦解僵持的局面,四重奏各拉各的旋律,心懷鬼胎,盤算誰和誰的節奏合拍,誰又和誰同步呼吸。
如此複雜的心理活動,本可大筆一揮,砍鑿得火星四濺,但莎莉.魯尼捨棄戲劇化的結構,以細密文字描述法蘭希絲的生活,如洗石子般鑲嵌諸多細節,要一路讀下來,才逐漸浮現當代愛爾蘭年輕女性輪廓。法蘭希絲和玻碧、尼克的羈絆,其實都帶有被宰制的SM(性虐─受虐)意味,她甘於被玻碧嘲弄,願意屈就於較為黯淡的位置,旁觀玻碧在人群中閃耀光芒,獲得男男女女的愛慕。另一方面她與尼克交往時,既在性愛中獲得快感,卻又焦慮被性所操控,墜入嫉妒梅麗莎的深淵,使她對自己深陷外遇的陳腐套式感到絕望。為什麼她無法愛完之後灑脫地抽身就走,像個堂堂正正的女性主義者?為什麼她無法像玻碧,無懼他人眼光,脫衣下水游泳?
法蘭希絲憎惡自身常處於被動無力的狀態,讓人想起美國詩人希維亞.普拉絲(Sylvia Plath)的小說《瓶中美人》(The Bell Jar)。法蘭希絲如普拉絲小說女主角艾瑟(Esther),彷彿隨著子宮內膜細胞漂浪,在性與羞恥中浮沉,因著無法將自己填入社會任何角色而深深沮喪。與艾瑟不同的是,法蘭希絲沒有因嚴重憂鬱,試圖攀越死亡的稜線,而是在頻頻自殘中,逐漸改變了自我的認知。
四角戀曾經一度看起來有實踐多元情慾的可能性,但其後法蘭希絲自省,所有情感都有權力位階的落差。她愛的不只是尼克,還包括他與梅麗莎潔淨的家、中產階級的舒適生活,以及梅麗莎的作家身分;愛上尼克象徵著倘若她能夠活成梅麗莎,或許就能成為出色的作家,而非一文不名的大學生。就如同後來法蘭希絲挪用玻碧的身分和經驗書寫小說,下意識用文字打造另一個玻碧,因為她仍然愛她,所以當她聽聞玻碧企圖接近梅麗莎時,她無法不感到嫉妒。嫉妒是愛的負片,需要一番沖洗,愛才能顯影。少女可以是共產主義者,少女堅持政治與美學的原則,但愛憎比智識藏匿得更深,總是背叛表面的矜持,滲進文字,洩漏出真實的液漬。至此莎莉.魯尼的洗石子工法才展現全貌:真正的動機往往埋藏在言語與動作底下,當文字將角色的模樣雕琢成形,內在的迂迴心思也才溢出痕跡。這是最基本的寫實技巧,卻很少人不賣弄花俏手法,一點一點積砌。魯尼相信她可以讓讀者沿著碎礫泥砂讀下去,直到穿拂過層層事實,呈現出別樣風光。
末了的轉折既在意料之外,也在情理之內。法蘭希絲沒有和任何人定下來,她仍在躑躅,但相較於之前的天真畏怯,法蘭希絲對成人世界少了豔羨,多了點寬容。梅麗莎不是她想像中成熟優雅的女作家,梅麗莎需要倚賴人脈才得以出書,也曾多次出軌,卻仍困守婚姻。維繫婚姻關係的是愛或友誼?是國家體制或人的慣性?法蘭希絲得知玻碧不願兩人回歸「女朋友」關係後,又盪回尼克那一端。「人和物在我周圍轉動,以一種模糊不清的階級系統各安其位,這是個我現在不懂,也永遠不會懂的體系。一個由物體和概念構成的複雜網絡。人生的某些事物,是你必須先經歷,才有辦法真正理解的。」法蘭希絲如是說,她不再張望未來,遐想前景有多美好。人與人透過對話簇生的金色絲線,如畫糖般勾勒出少女面貌,而法蘭希絲在經歷這一切之後,終於看清了自己,不多不少。
在這準則融解,人際關係液化的時代,一切都在輕輕晃盪,莎莉.魯尼在重疊殘影中,準確捕捉到了當代年輕女性的面貌,有點倔強,有點迷茫,明知成長的痛楚就在那裡,前人都經歷過了,還是不死心地再走一趟,如耶穌行過水上,危顫顫地,從與人的交接中,目睹世界開天闢地的晨光。
作者簡介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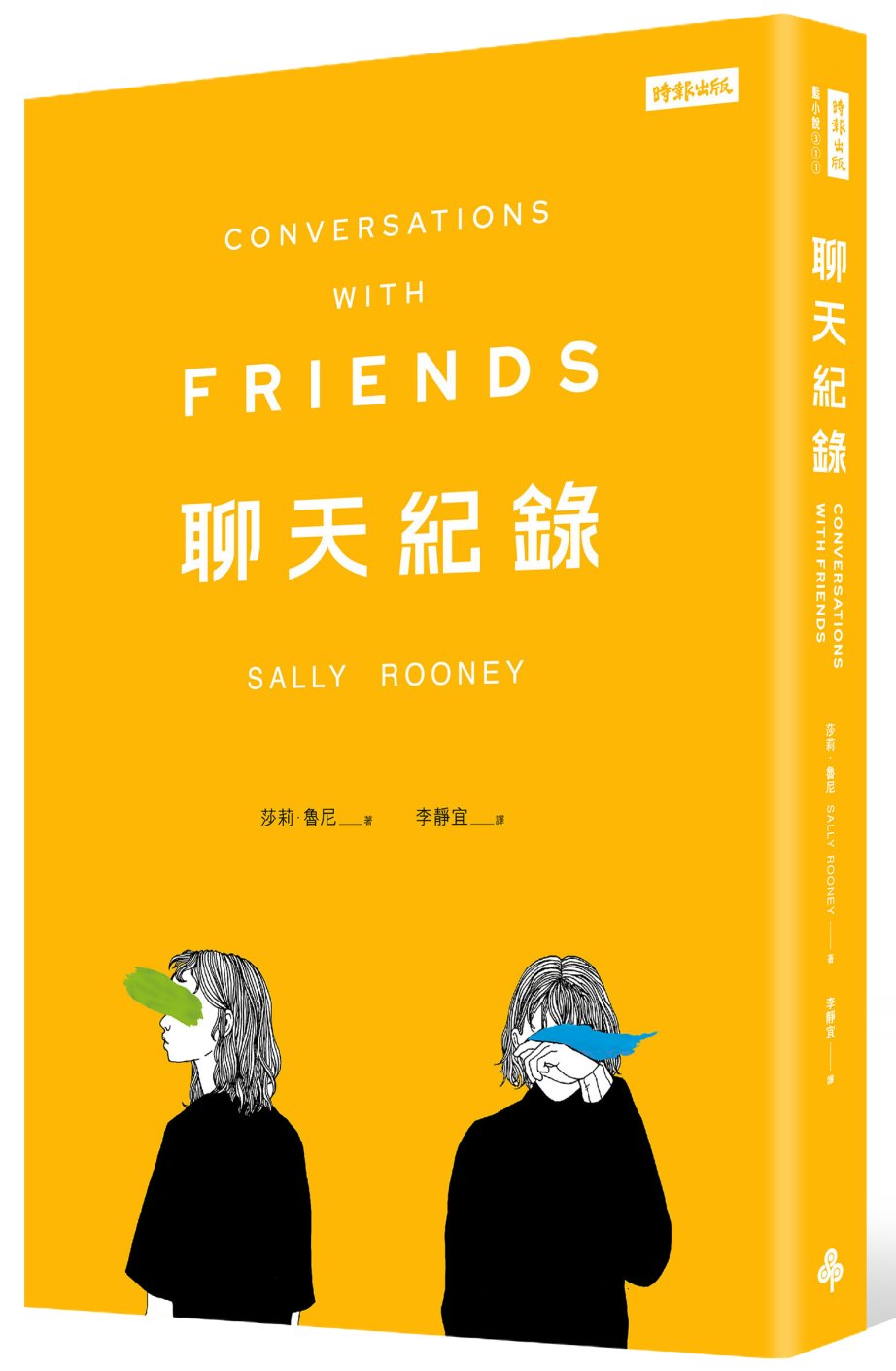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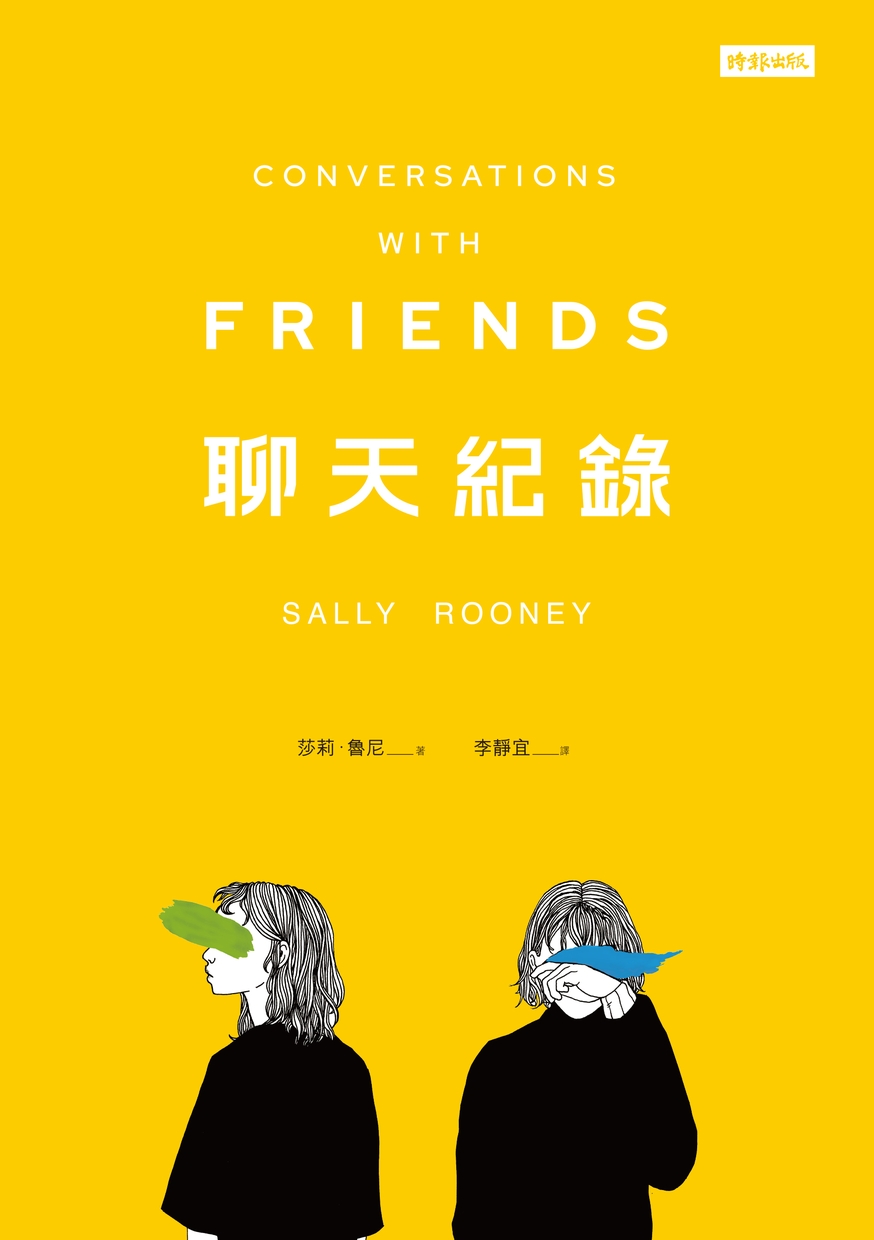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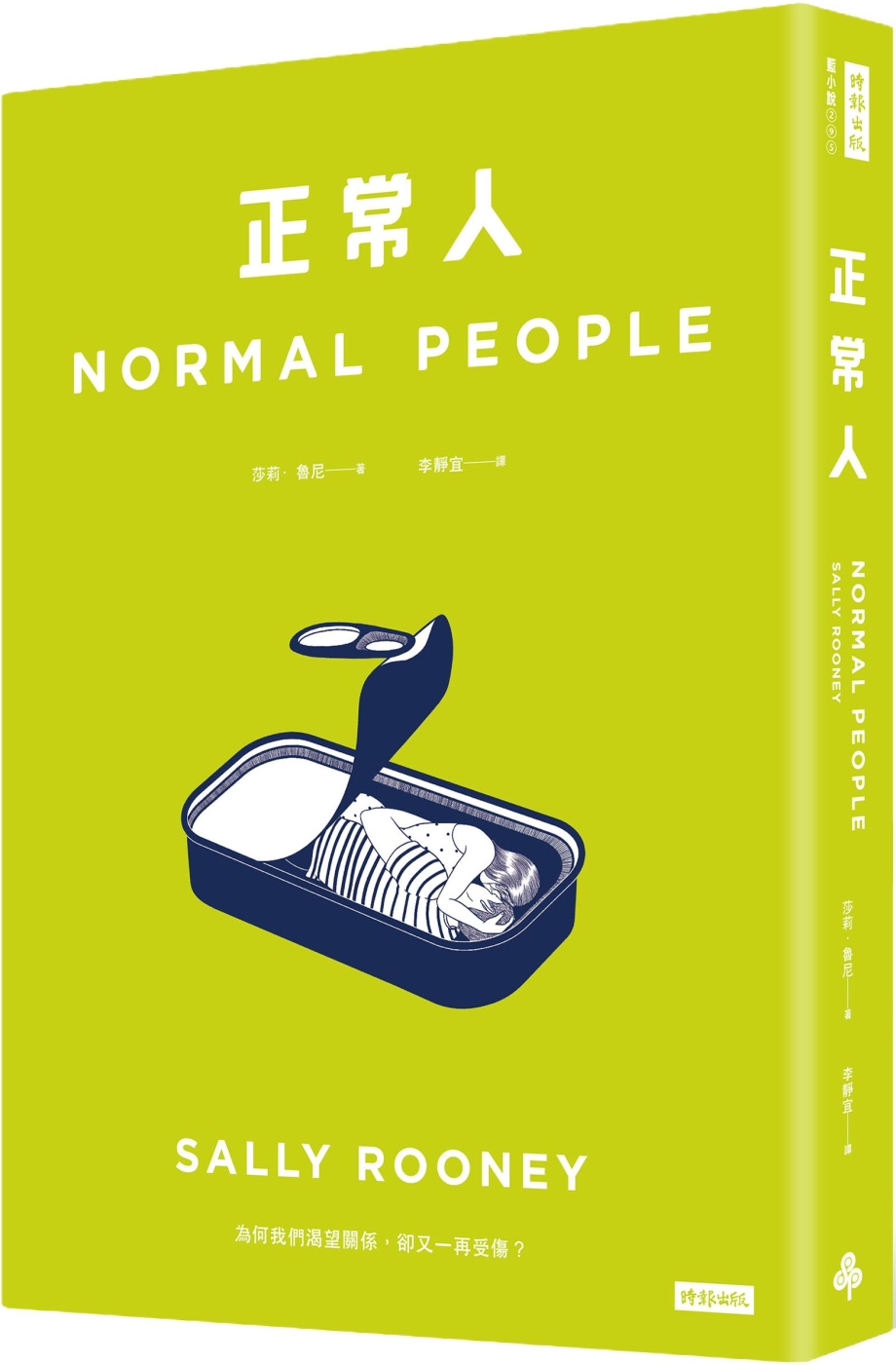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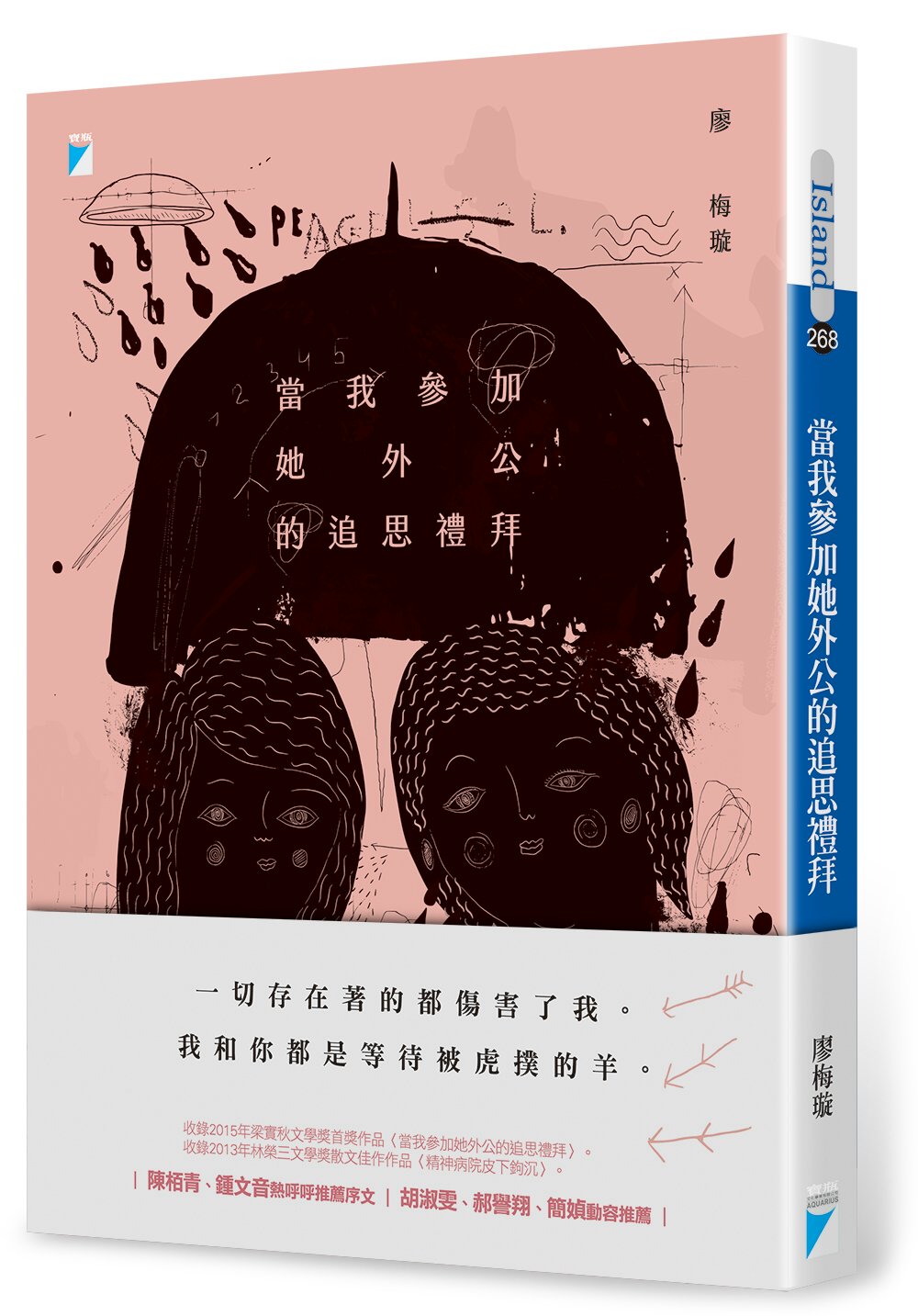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