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什麼故事,會比誠實的人生更精彩?讀《我的奮鬥2:戀愛中的男人》到一半,我就忍不住想起電影《楚門的世界》:由企業收養的孩子,自誕生起就被迫當實境秀明星,攝影機不間斷即時播放,收視率長年不衰,無數觀眾看著他長大,陪他戀愛、結婚。楚門之真實,在於對比人性虛假,他的一舉一動無所遁形,甜祕密與壞心機全數公開,其滿足的窺探欲,正是《我的奮鬥》系列作裡,最外顯的特質之一。
唯一疑問是,當楚門陷入某生活迴圈,如開啟自動飛航模式,所有戲劇成分皆停滯時,觀眾會多無聊?我何必打開電視去看一個和自己一樣無趣的人?看他無表情上下班,吃飯睡覺機械般活著,微笑有時苦悶有時,一顆真心炙熱,也只是個凡人體溫。若不能鑽入他腦中,我們看到的終究只是鏡相的自己。
想像楚門在三級警戒時無法出門,花去整個假日窩在房間裡看一本六百多頁的書稿,字排得麻麻密密,簡直有相互對峙之勢。他的母親經過時瞥見,說,「那麼小的字你也讀得進去?」楚門說,可以啊,然後繼續翻讀兩個小時。
我為什麼要看這樣的節目?除非我能聽到他不間斷的牢騷,如溫泉不斷湧出無休無止的潛台詞。
而這就是《我的奮鬥2:戀愛中的男人》基本上的文字內容。故事一開始,作者本人就說自己正寫完這部小說的第一冊,後設般將自己人生揉進作品裡,全書細密之無遮蔽全曝光的程度,幾乎像作者本人脫光衣服拍寫真,而且各種局部放大到,你能看見他指紋隨時光演變,一根頭髮因思考過度落下的程度。
但也不是一本和情人上傳私密照的相本。閱讀此書,我首先充滿疑惑的,在於它不是一個戀愛故事,而是一個男人婚後與妻生養三個孩子,帶女兒去上課時看見美麗的老師就想跟人家睡,偶爾與惡鄰交手,並指控岳母邊帶孩子邊酗酒的故事。
叨絮之不可免,因為其正是小說的魅力來源。我想起二十歲時看《愛在黎明破曉時》,男女主角浮生相遇,共度一日,期間幾無情節進展,只是不斷交談,分享著身而為人會有的一切觀察和見解。二十歲的我無法看穿其迷人之處,就在於真實和虛掩不斷交手,散文式的透露、詩的意境。
但如今的我早不是當時的青年。二十歲的夏天,作家的母親打電話告訴他,肚子長了個大腫瘤。年輕的作家那時關心的,是自己的愛情和未來。他想像葬禮的場面,想到媽媽的遺產,「接著我又想到,我終於有件有意義的事可寫了。」其冷酷、殘忍,卻如實以告最黑暗的念頭,光是這段就令我不禁寒慄。身為一個寫作者(或記者),我何嘗不曾在家國不幸時,興奮自己或能有所為?
然而我敢這樣坦白嗎?作家且寫出自己那年曾動過自殺念頭,「我從小就有這種想法,因此看不起自己,這根本不可能發生,我有太多事要報復,太多人去恨,太多東西糾纏不清。」他寫記得一年冬天,下了兩公尺雪,某週末,「我們挖了好幾個雪洞,中間有坑道相連,從花園一直通到鄰居家的院子。我們就像著了魔,全然沉醉於這一天的成果,當夜幕降臨,我們就能坐在深深的雪層底下聊天。」
我們讀書,就像鑽進那潔白又無光的雪洞坑道裡,在深深的雪底下聽他和浮生裡相遇的所有人,無止境私聊。他和友人蓋爾談文學,談自己的書,談人生,所有事都像作家寫過一封沒寄出給蓋爾的長信,是「一片凍結的時光」,慢慢融化,流進讀者眼睛。作家被蓋爾逼視自己或有似無,曾使一名十三歲的少女懷孕——還(走得太遠)把這事寫進書裡。作者在對話中否認,轉頭又將轉播鏡頭照進自己腦中:
「我的記憶裡確實有個相當大的黑洞。我住在北方時常常喝得爛醉,像那些年輕的漁民一樣,週末出門閒蕩,一瓶烈酒一晚就喝個精光,最少一瓶。整夜整夜的記憶消失了,好像在我心裡留下一條條坑道,滿是黑暗、陰風和情感漩渦。我做了什麼?我都做了些什麼?我在卑爾根讀書時狀態依舊,整夜整夜的記憶消失不見,我在城裡放浪形骸,就是那種感覺,我回家時夾克的胸前可能沾滿了血。」
二十歲的男人,走過惶惶不可終日的少年青春期,繼之以荒唐而噴發情感接近暴力的成人歲月。戀愛中的男人,有過一段婚姻,在(類似)逃亡的過程中進入更茫然的人生,在此時遇見女人,形容其為「那個春天,世界突然打開了……」男人與女人非初識,也曾有過他愛她,而她愛另一個他的經歷,告白失敗後打破鏡子自殘的男人,和住過一陣子精神病院的女人,他們的戀愛豈可能是童話?
但打敗幸福的,終究是日常。三個孩子相繼出生,作家已能寫出「兒童像狗,總是湊在一起想看熱鬧」這樣精闢的句子,或推著嬰兒車走在路上忽然對自己的男子氣慨產生強烈懷疑,自憐又可悲。作家擁有詮釋權,詮釋自己也詮釋身邊人,一日作家開車在路上,轉頭看見一家子熟睡模樣,「幸福在心裡奔湧而出。」但只維持了也許三秒,「隨之而至的陰影便出現了,這是幸福的黑暗伴侶。」
他且感嘆自己「不僅僅是機會變少了,我體驗到的情感也在變弱。人生不再那麼熱烈。我知道我到了中途,也許行程已經過半。」這一切,是對自己殘忍的誠實,寫成書就轉嫁到他人身上。當他終於發出那驚悚的詰問:「那個二十歲的青年現在在我身上還剩下多少呢?」我終於理解何以書出版後,妻子將再度躁鬱症發作?
更可怖的是,也轉嫁到讀者身上,讓我也問了自己同個問題,陷入巨大不可捉摸的惶惑之中,而這恐怕已是二十歲的青年現在還留在我身上的唯一遺產。
戀愛中的男人,讓自己成為戀愛中的楚門,讓全部人生成為一場轉播表演,讀者不知真假比例,不知何真何假。當他「開始寫自己的生活,就按照現在的樣子來寫,像日記,對未來開放,記錄近年來像黑流一樣發生過的一切。」讀者被暗湧滅頂,也只是剛好而已。
唯有忽然出現的二十歲的夏天,提供了救贖。母親的病與重生,母親在最後仍說出的那句「我的確愛他」,那個被作家視為爛渣的父親。那一天,作家的父母相遇,即將戀愛的男人和女人,「真是美好的回憶。陽光,公園的草地,樹,陰涼,那裡的人……我們那麼年輕,你知道的……是的,那是一次奇遇。一次奇遇的開始。就是那種感覺。」
男人拋妻拋子,多年後,卻仍是女人最美好的回憶。所有的回憶都是美好的,雪洞、坑道,烈酒與消失的記憶,消磨掉的愛情。戀愛中的男人頓悟不假外求,或許也無須頓悟,像「寫作唯一的意義就在於寫作。」戀愛唯一的意義就在於戀愛,生活唯一的意義就在於生活。
如實記載下來,就成了一片凍結的時光,看似厚重,其實輕盈。
作者簡介
1981年生,台北人。淡水商工資處科、樹德科技大學企管系畢業。得過一些文學獎,入選過一些選集。著有散文集《小朋友》《昨天是世界末日》、詩集《一起移動》《最靠近黑洞的星星》。經營個人新聞台「頹廢的下午」。
延伸閱讀






 楚門的世界
楚門的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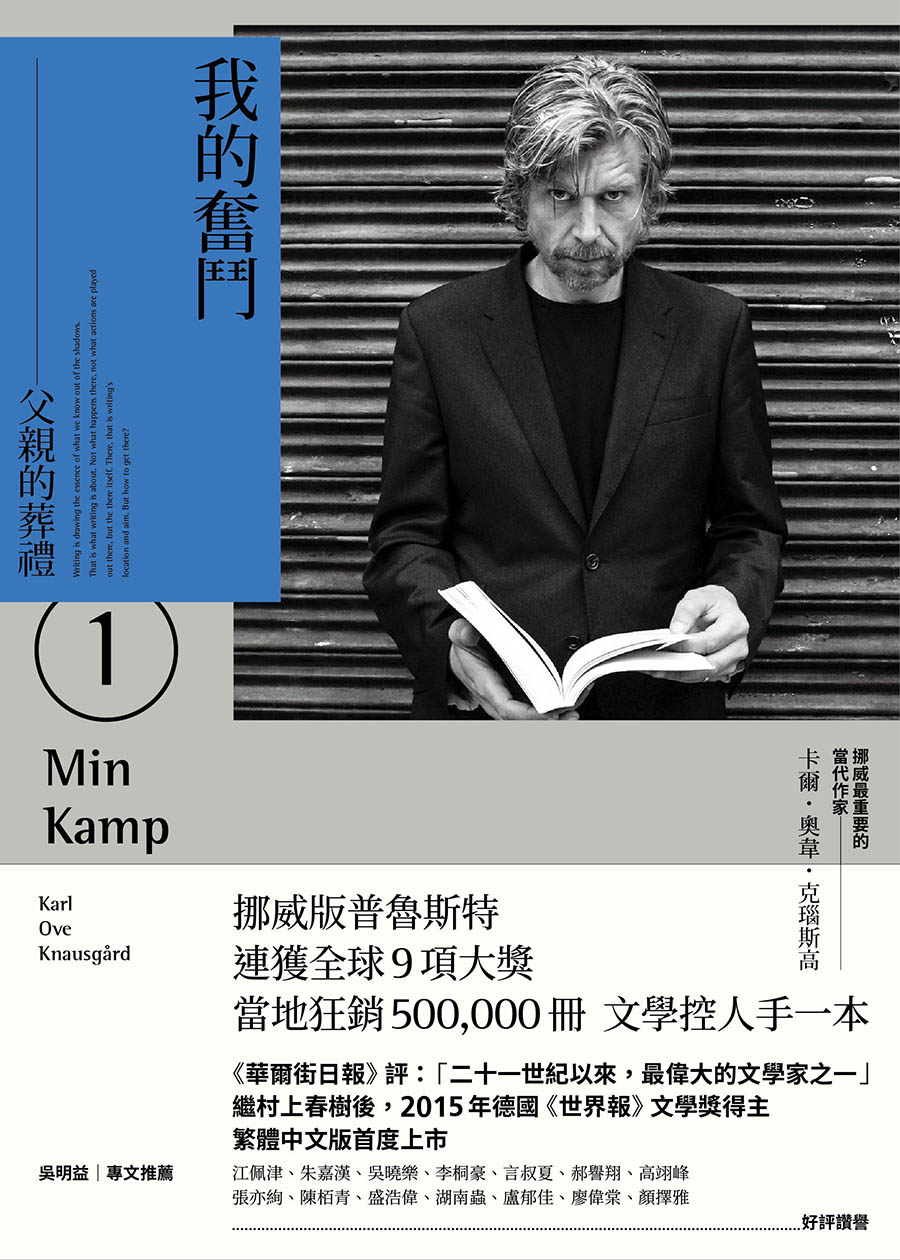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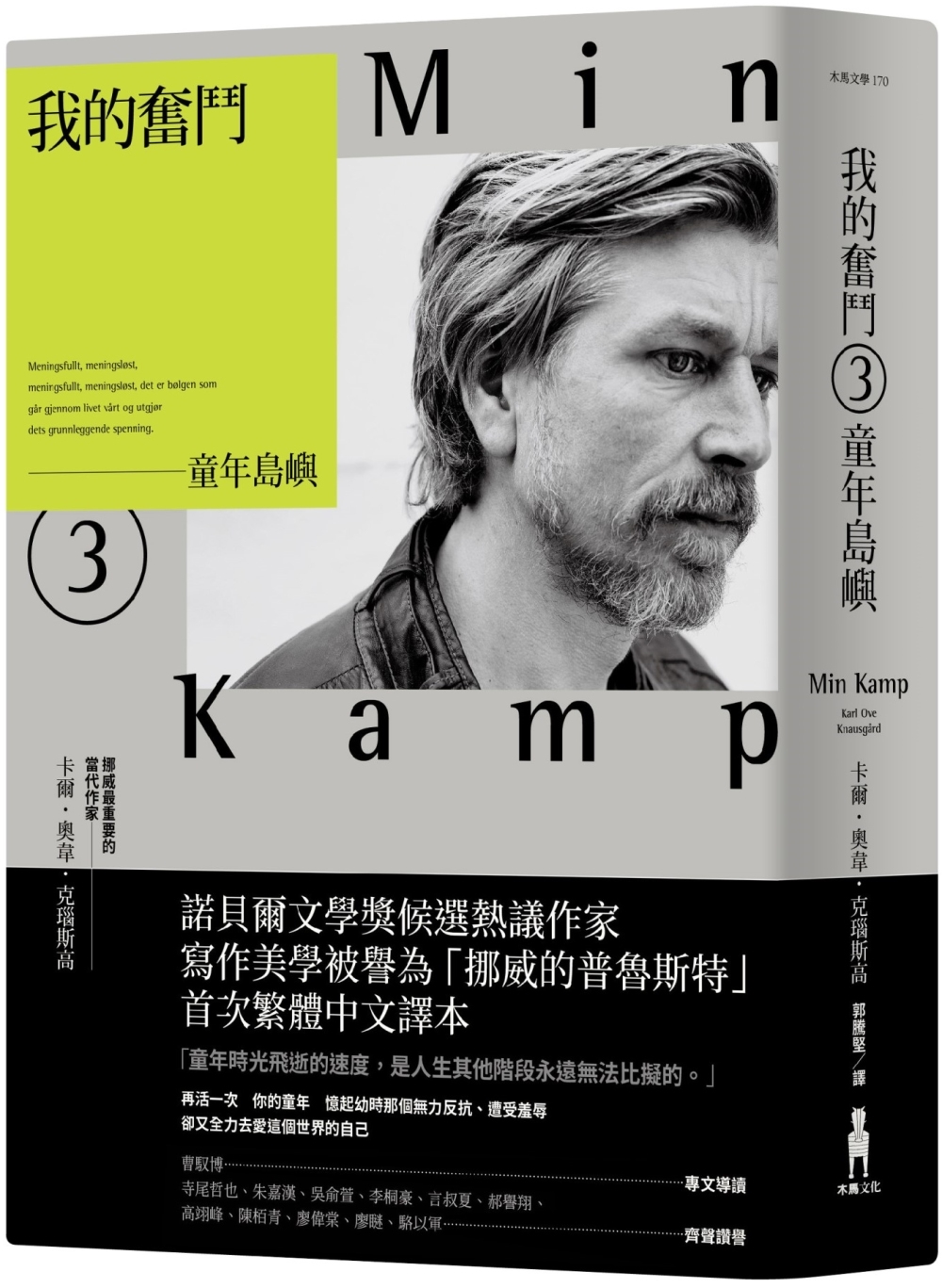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