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以來最偉大的發明,具體顯現在「三分鐘帶你看完紅樓夢」、「十分鐘讀懂尼采」、「高能。七分鐘通透漫威宇宙」等影片裡。這類「X分鐘帶你看完」系列的流行反映出一種工具性的追求,其性價比直逼武俠小說裡的山崖,跌落山崖撿到武學祕笈、摔進山坳遇見快掛點的武學高手。山崖的高度反應奇遇的強度,下墜就是飛昇,曠世奇功幾百年功力一個墜落就搞定。如今Youtube和Facebook上有無數知識與資訊的山崖任君挑選了。點開發燒影片,一鍵擁有,高速抵達。
你可以讓Siri小姐用它典型毫無抑揚頓挫的聲音念出下列文字,我將用三分鐘帶你讀完奧根.海瑞格的著作《箭藝與禪心》,這本書說的是:
德國學者奧根.海瑞格(Eugen Herrigel, 1884-1955)在日本學習弓道。拜師阿波研造學藝多年,連箭靶都射不太中。老師說你成功了。
甚至不用三分鐘。全書閱畢。打完收工。灑花。萌萌噠。小夥伴別忘了幫我點讚按關注,並開啟小鈴鐺。
這就是「X分鐘帶你讀完」系列展示給我們看的。你知道發生了什麼,你只是不知道,知道這些有什麼意義。你以為擁有,但你擁有的,只有「我擁有」的這份感覺。越充實,越空虛。
事實是,《箭藝與禪心》所講述的,正站在「X分鐘帶你看完」系列的反面。它的內容和我們這世代試圖以短時間吸納全部的形式相反。
台灣人追求高CP,更少付出,更多獲得。「X分鐘帶你看完」系列詮釋了現代意義上我們以為的成功。那一種捷徑。避開錯誤,節省時間。但《箭藝與禪心》是過程之書,它不避諱多餘,願談失敗,反覆試錯。這裡頭點出的困惑遠比答案清晰,過程比結論更詳細。如果快速抵達終點意味某種成功,那《箭藝與禪心》甚至是一本失敗之書。
連作者奧根.海瑞格自己都質疑了。拉弓挫敗幾千次,連基礎呼吸都學不會,結果老師一點就通,他老兄在書中自問:「為什麼師父要看我花那麼多冤枉力氣去試圖心靈拉弓,卻不在一開始就教導正確的呼吸方式?」
用現代人的眼光看,為什麼老師不像「X分鐘帶你看完」系列一樣,一口氣指出終點在哪呢?
當然,書中師父沒有回答他。但用奧根.海瑞格自己的話說,答案可能是:有些事是「只能從經驗中學會的東西」。
經驗必須從過程中獲得。《箭藝與禪心》重新校準了「過程」與「終點」的觀念,其實也反轉了現代人之於成功與失敗的概念。終究,抵達終點並不代表你完成旅程。我們所渴求的,反而萌芽於所經歷的過程之中。而失敗,則是我們的導師。
所以,學習弓道到底想要的是什麼?是讓箭命中靶心?是快狠準殺死一個人?那看看《飢餓遊戲》就好了。那裡頭女主角箭無虛發,還能推翻一個國家呢。
但奧根.海瑞格所需要的是,殺死自己。他想透過拉弓接近的,是道。是禪。
那是只有在過程中才習得的。當箭的抵達不是最終目的,途徑反而成為終點。過去,不只是過去而已。《箭藝與禪心》的好看,在於他把學習弓道過程中種種矛盾、扞格鉅細靡遺記錄下來:
「如果我捏緊手指,那鬆開手指時弓就會震動。如果我輕鬆拉弓,那箭還沒到張力頂點就飛射而出。」
那不只牽涉物理學和身體慣性,更事關思考「我」的本質:什麼時候「掌控」,什麼時候「放棄」?為何全然的控制卻導致偏離,而某一刻福至心靈的撤手卻反而成全一切?
為了掌握弓弦,他必須控制身體,調整呼吸,和自己身心重新締結關係。人因此重新發明(或發現)自己,於是,在弦的漲滿與弓身的震盪之間,箭尚未發,一個完整的我正如圓月,充盈天地之間。
 在弦的漲滿與弓身的震盪之間,箭尚未發,一個完整的我正如圓月,充盈天地之間。
在弦的漲滿與弓身的震盪之間,箭尚未發,一個完整的我正如圓月,充盈天地之間。
瞧我把《箭藝與禪心》說得多神。我倒也想分享我私密的體驗。做為一名台灣讀者,許多人認識《箭藝與禪心》可能是因為攝影家布列松的傳記,《卡提耶-布列松:二十世紀的眼睛》中描述《箭藝與禪心》是畫家布拉克送給布列松的一本小書,就此開啟他的心靈之眼。「這本書是波楊送給布拉克的,而波楊也是從別人那裡得到的,這本書有一種魔力,讓人必須把它像接力棒一樣傳遞下去。」一代西方大攝影家重疊上東方弓箭手身影,快門按下的那一刻,是眼快還是箭快,「現代新聞攝影之父」想命中的到底是什麼?
35歲的布列松因為這本書改變了創作觀。那時猶是少年的我則想,如果能搞到《箭藝與禪心》這本書,是否就能窺見創作的奧祕呢?在那個「X分鐘帶你看完」系列還沒流行的年代,《箭藝與禪心》在台灣被翻譯成《箭術與禪心》(2004),在該書絕版的數十年間,台北市立圖書館數量有限的這本小書始終處在預約中狀態,過手在許多如我般想要跌落山崖撿到絕世祕笈的小夥子之間。
而我發生了什麼?箭已射出,這些年間,我終究成為一名寫作者。多數時刻,我只有在截稿期之前(不,我說謊了,經常都是截稿期之後)才開始創作。這些年來的創作時光,完全可以用《卜洛克的小說學堂》裡一段話表示:「我認識的作家,每個人都會混到不能再混,這才心不甘、情不願的回到自己的房間,面對那部打字機。」
後來我才發現,我活成「X分鐘帶你看完」系列的影片本身。我知道終點在哪──如果那就是指交出作品。我混到不能再混,好不容易提起筆。我抵達終點。我交稿了。我一次又一次交稿。我有驚無險過關。我可以在每個待辦事項框框前打勾。但只有我知道,我做了,卻不代表做到。我完成了,但也僅僅是完成而已。
這些作品,是我真正喜歡的嗎?每一次作品的完成都只是讓我更不確定。創造反而成為我的枷鎖。我覺得我把自己寫薄了。
我時不時問自已,如果只是完成,卻沒有效果,那我渴求完成的目的何在?
我追求效果,但效果意味什麼?又是什麼的效果?
終極的提問:我嚮往的創作是什麼樣子呢?
後來,我在朱天文《巫言》的訪談裡讀到,小說家有段時間練習早起後「不看報紙,到書桌前面,清晨這段時間大概還是你精神最集中的時候,非常理智清明。即便是寫少少一點,過午就覺得差不多了,總是覺得今天是做了事情了,也有了一點成績在那邊,那種感覺是蠻輕鬆的。」
所以這就是讓我舒服的方法嗎?祕訣便是,早上起床就開始創作?「覺得今天是做了事情了?」
於是有陣子我的床頭書都是「早上三小時完成最重要的事情」、「晨型人成功術」一類。它們成為我神龕上奉請的新神。
如今,《箭術與禪心》再版,時移事往,連祕笈本身都改了名字,而我活到跟當年初讀這本書的布列松一樣大了,當我再翻開書,裡頭句子像箭矢一樣射來:
「他只能像個早上醒來的人考慮一天的計畫,而不是一個得到開悟的人在本然狀態中生存與行動……他所進行的一切,在他還不知道之前,便已經完成了。」
「正確的一擊會讓射手感覺一天好像才剛開始。他覺得他可以做好一切事,或者更重要的是,可以做好一切的不做。這種狀態真是愉快極了。」
那一刻,有什麼正中靶心,我忽然明白一件事情。我關注的重點並非是在「早上就去做」,甚至不在於,完成。
我真正嚮往的,其實是一種「完成感」的獲得,在創作的那刻感受到自己的心靈一如手腳能得到充足伸展,像倒空。又像完滿。有完全的自己。又不能自己。
我真正想要的,不是真的開始在一個早上。而是讓自己像一個清晨。那時天光尚亮,空氣中無數微塵漂浮。一切還有可能。
那是創作最好的狀態。也是生活的。
我也該搞清楚了,《箭藝與禪心》不是祕笈,但它也不需要是。創作哪有什麼祕笈。反正你也已經有「X分鐘帶你看完」系列了。你已經能快速抵達萬事萬物的終點了。但正是這個時候,更需要《箭藝與禪心》。它是一個提醒,把你推出去,看世界之外有一個更大的什麼,又時時把你拉回去。在每一個當下,每一個動作之中。察覺。察覺其不察覺。乃至彷彿不覺。像書中反覆提及「當下的真心」。中文翻譯得真好,他還用「真心」二字呢,傻乎乎的,像是告白。但唯有讓我們在那個更大的「它」──無論你怎麼解讀這個「它」,大道、禪、心流──之中。那個更大的,也會在我之中。
作者簡介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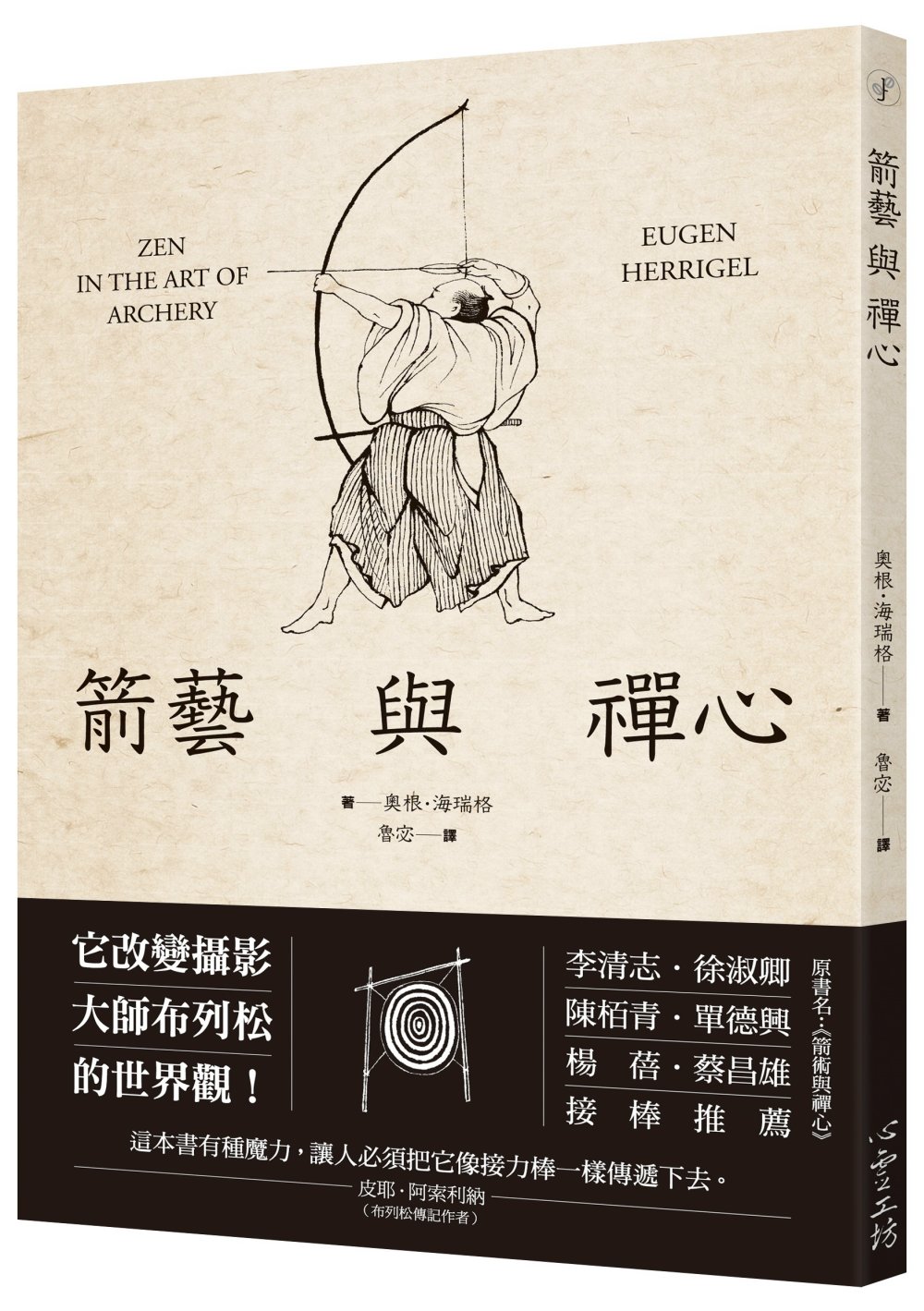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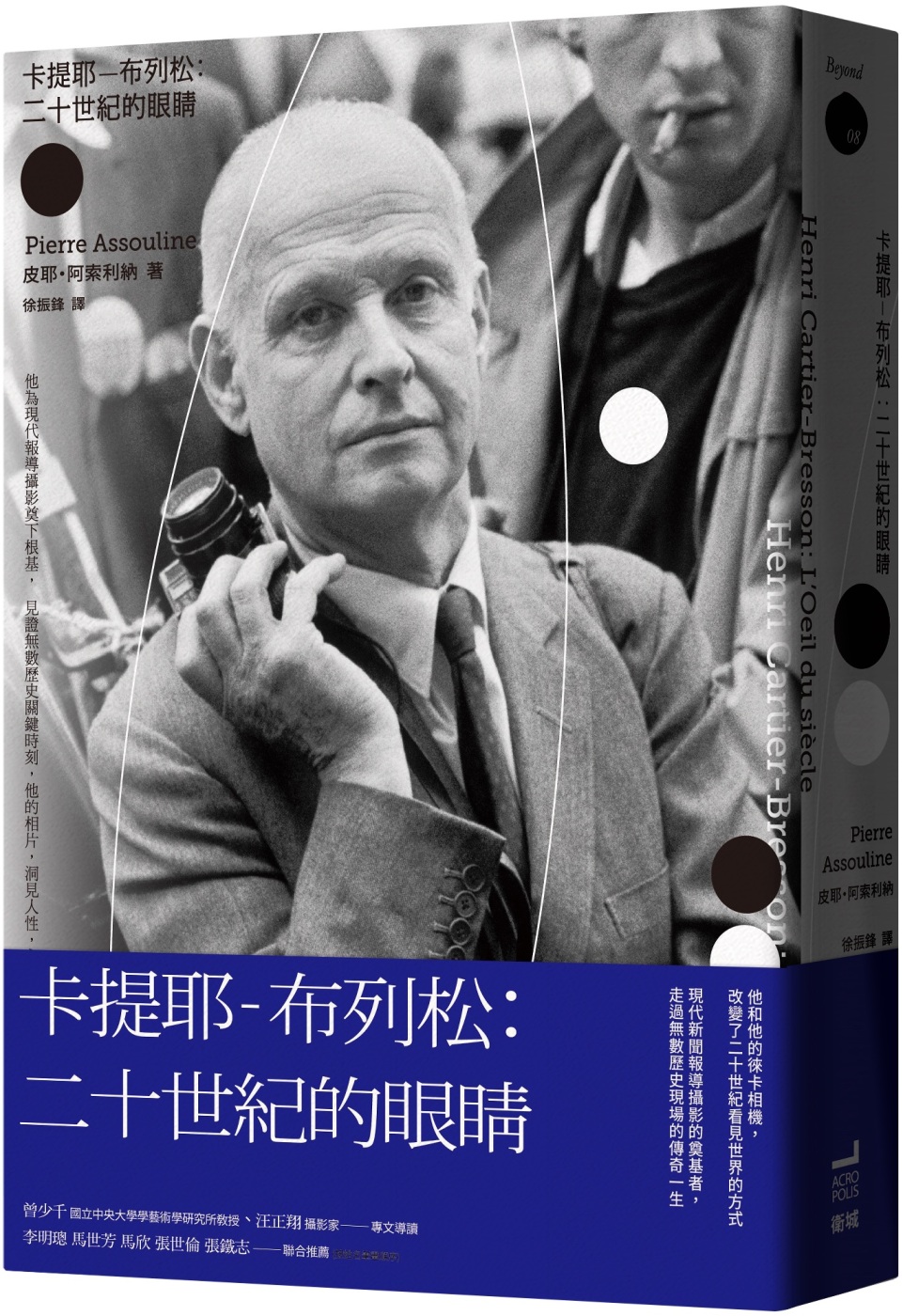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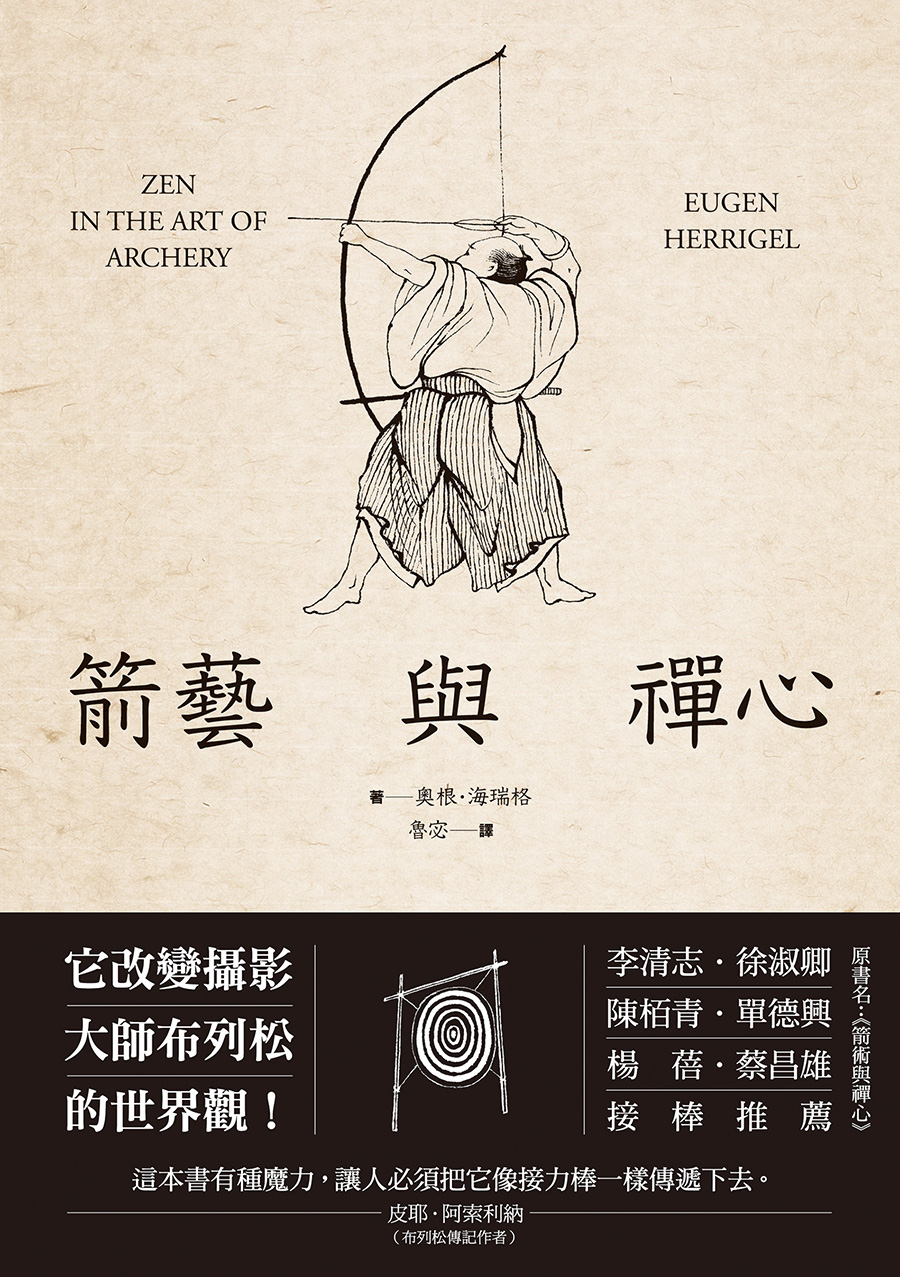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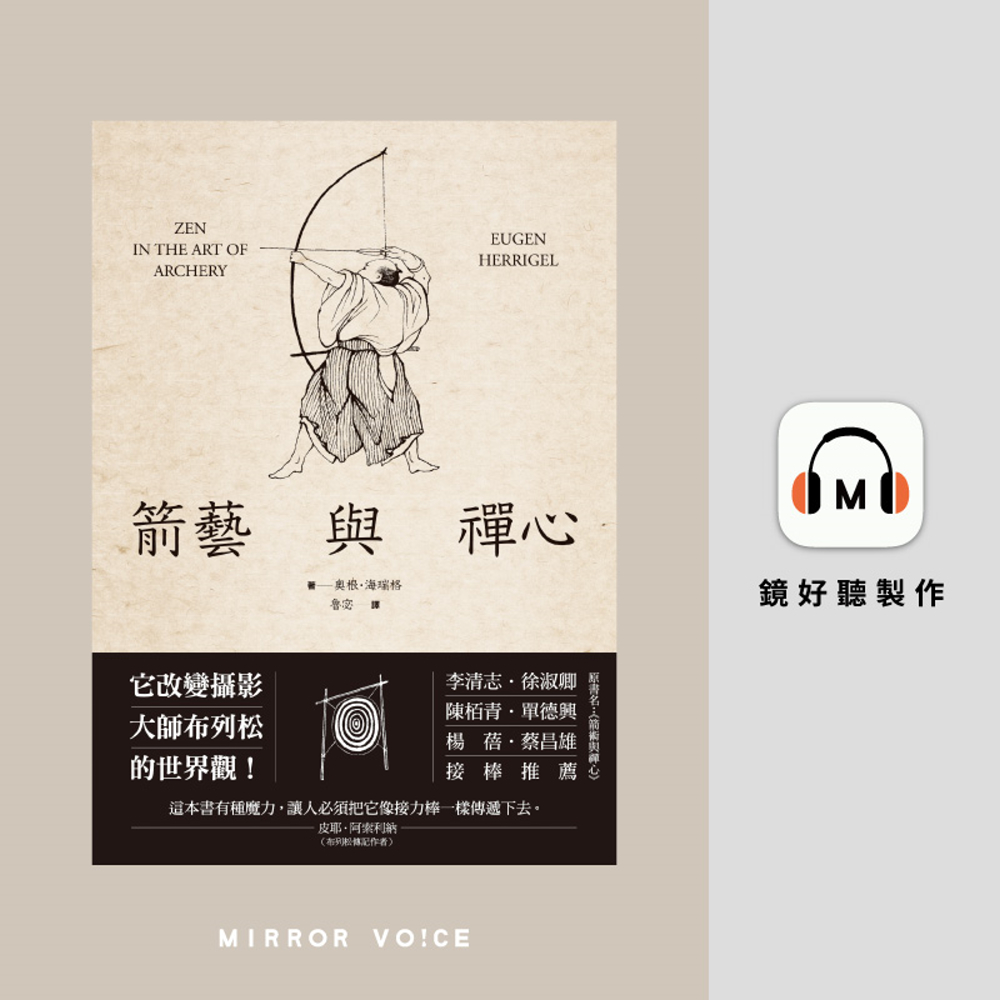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