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立場的差異並不是來自道德立場的高下,韓粉很多都是我們日常所見、努力生活的好人,造成這些歧異是來自對歷史記憶的不同詮釋。在台灣社會裡,政治對立陣營中,統獨立場不見得完全相異,其中一項核心差異是不常被拿出來討論的:蔣經國是民主化的推手嗎?台灣社會有一群人懷念舊時代,這個舊時光正是以蔣經國治理為中心:經濟起飛,民主化開端,舊時代的偉人像慈愛的父親把亂世裡的子民,一個一個打撈上岸。
學者吳乃德新書《台灣最好的時刻》以美麗島事件為主題,梳理在歷史時空下,這個事件何以重要?如何影響日後台灣民主化的過程。書裡也回應了這個提問:蔣經國是民主化的推手嗎?如果是,何以在解嚴前幾年的美麗島事件大舉逮捕黨外人士,企圖肅清民主運動?在蔣經國的最後時光,他何以做出解嚴的決定?
作者以「台灣最好的時刻」形容美麗島事件的那段時光,書中寫:「在那個最好的時刻中,台灣人集體展現人類心中『善良天使』的那一面…因為許多人有著共同的價值,也願意為這些價值付出。」在1979年美麗島事件之前,先有《自由中國》雷震組黨遭整肅入獄(1960),之後有許信良、康寧祥等黨外人士開始參政之路(1973)以及中壢事件(1977),島內社會開始追求民主自由。
直至美麗島事件爆發,原本的警民衝突被誣為叛亂,軍事大審引起從知識分子到社會大眾的集體關切,包括像是政治立場與黨外不盡相同的作家陳若曦,她求見蔣經國,並為美麗島事件參與者求情。這股風潮不僅在知識界,書中提到一名不知名的商人,每個月定期從台北開車到受難者家中,留下五千元贊助。
不同於之前「雷震案」逮捕範圍有限,事件後社會沉寂。美麗島事件的軍事大審是當年少見的開放現場媒體報導,吳乃德認為,這很可能是留俄背景的蔣經國從史達林的經驗判斷「民意站在他這邊」(當時的台北市長李登輝也呼籲全體市民共同聲討、制裁暴力分子)。
1937年,史達林整肅政敵,許多入獄的開國元勳為了保命,配合史達林的劇本,在法庭上認罪,承認自己反革命、是資本主義的走狗。1980年,蔣經國原以為這場大審也會有類似的效果,不料,美麗島這群被告在法庭上宣揚民主理念,把法庭變成一堂盛大的「民主課」,為日後的民主運動留下火苗。軍事大審之後,黨外雜誌與運動更加蓬勃發展,社會追求自由多元的聲音並沒有因此沉寂。
吳乃德惴想1980年代的蔣經國,面對將美麗島的「叛亂分子」關進牢裡,問題沒有解決,黨外民主運動卻更活躍;國內治理不斷出現危機,有陳文成案、十信案、煤礦爆炸案;對外則有來自美國國會要求台灣提升人權的壓力。蔣經國的快速民主妥協,是不得不然的選擇,這個決定也保障了國民黨在民主時代的競爭力。在第三波民主化國家裡,國民黨是唯一在民主化仍穩定執政的政黨。
此外,蔣經國不像他的父親蔣介石:「他父親的天下雖然只剩孤島台灣,畢竟是自己打來的。蔣經國的天下卻是繼承而來,所以他必需創造民眾的普遍支持。」這是蔣經國時代的合法性危機,就算選制內涵有多少不公,但對他來說,民主選舉形式是一塊必備的遮羞布。
吳乃德在書中還有一個有趣的「回顧」,我們現在視為理所當然的民主,在1980年代的台灣媒體與知識圈裡,「民主」並非普世價值,而是充滿各種「先決條件」的概念。例如,當時出現這樣的說法:經濟發展必須到一個程度才能擁有民主(所以,執政者獨裁是因為經濟發展不夠)、政治民主必需在一個有建全「民主文化」的社會才能發生(所以,獨裁不是因為執政者想獨裁,而是因為人民沒有民主文化)。
1983年,美國眾議員索拉茲(Stephen Solarz)訪台,談及民主價值並不會與任何宗教、傳統價值不合。此番言論,立刻得到當時《中國時報》發行人余紀忠的反駁,他認為台灣處於戰爭威脅下,民主易造成中共分裂台灣的手段、過分民主易導致極權、政治參與必需先要有堅強的共識。
除了媒體輿論之外,當時的中研院院士金耀基甚至還說:「不必在乎民主的形式,只要有權力者的意志和主觀意願就可以創造民主了。」、「一黨政治中民主的可能是存在的…這些黨…包含了不同的利益和階層…亦即黨內結構是多元的。」這些人主張,民主不必複製西方的體制,禁止人民成立政黨的一黨獨大也可以是民主。所以,台灣式的權威體制也是中國民主的一種了。
這些在解嚴前嚴厲批評民主運動的言論,在蔣經國決定解嚴後,又開始頌揚他,例如金耀基寫道:「我相信,他自己一定是以無限關懷的心情離開人世的…在民主政治發展方面,他更為中國現代化最難的一關做出了突破性的建設。」
頌揚蔣經國的風潮也延續到他死後多年,2003年中研究的一項調查卻發現,有46%的受訪者同意「像解嚴之前蔣經國時代那樣的政治,對台灣比較好」。然而,對獨裁舊時光的嚮往並不是台灣獨有,史達林統治期間死亡近2千萬人,但俄國一份2015年的調查,有52%的俄國人認為史達林「可能有貢獻」和「極有貢獻」。
俄國記者亞歷塞維奇訪談共產時代的遺老寫成了《二手時代》,在巨大的苦難之後,並沒有換來自由,她下了這樣的註腳:1917年革命之前,有人說「未來沒有站在自己的位子」,一百年過去了,未來還是沒有到,換來了一個二手時代。
台灣何嘗不也是如此?蔣經國的民主妥協,換來國民黨在新時代的有利位子,李登輝成為第一個台灣人的國民黨領導者,推動民主化成為「民主先生」,於是蔣經國被理所當然視為「民主推手」。
在二手時代裡,各種政治「錯覺」交織而成現代政治衝突的樣貌。那些政治立場相異的人,不論哪一方都是台灣社會的一部分,因為都是來自不同的歷史詮釋經驗。
正因為這些歧異,吳乃德在書裡最末提及:「遺忘可以帶來和解…但遺忘與記憶同樣重要…我們不能全然遺忘過去…而是記憶什麼?遺忘什麼?以及如何記憶,如何遺忘?」在2020年,台灣內部民族意識形成的時刻重提美麗島事件,他替自己的書下了這樣的註解:「民族是基於自由意志的結合,為共同的歷史記憶所凝固。而記憶的內涵是,民族的成員如何為社群的共同利益而犧牲和付出。」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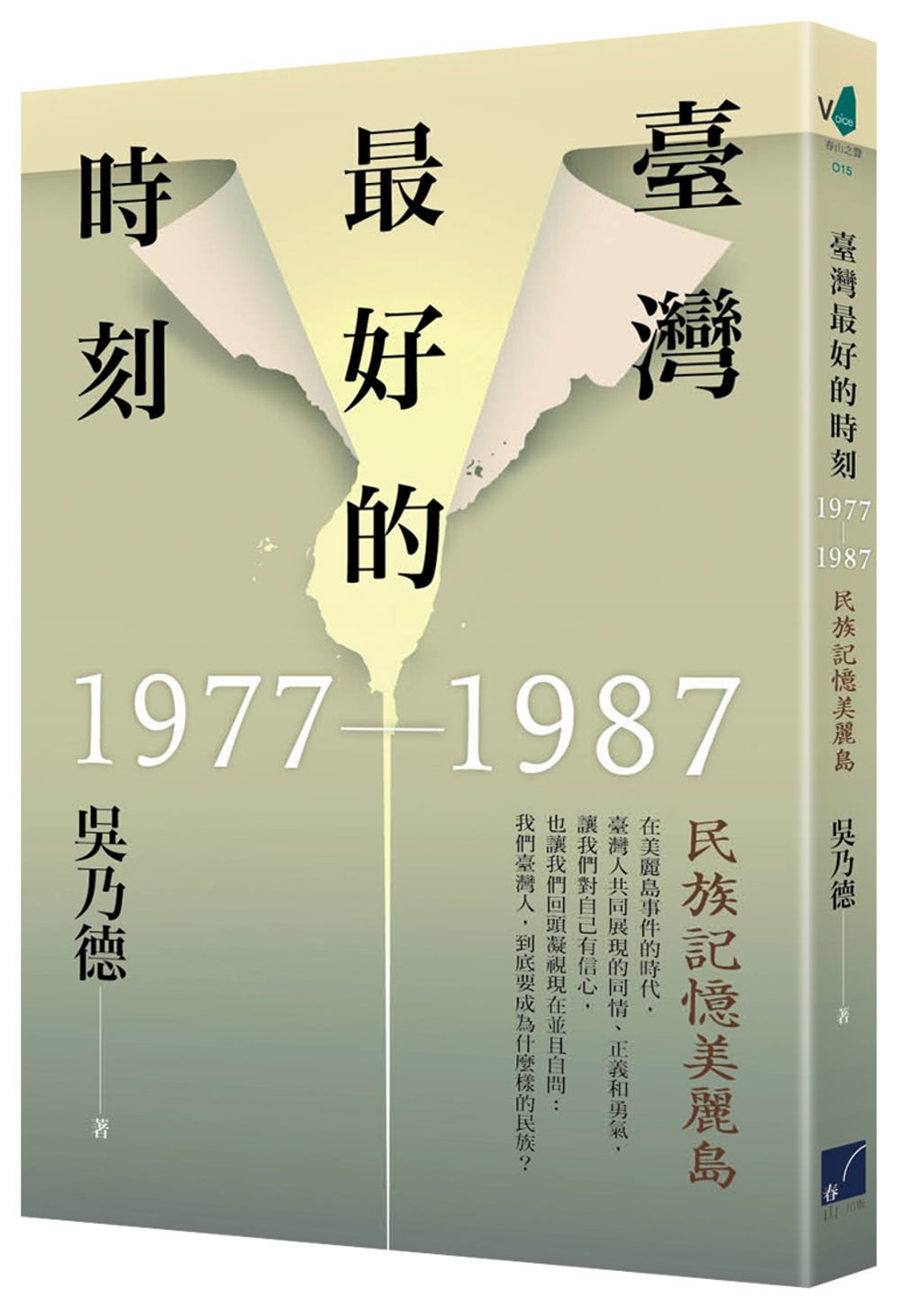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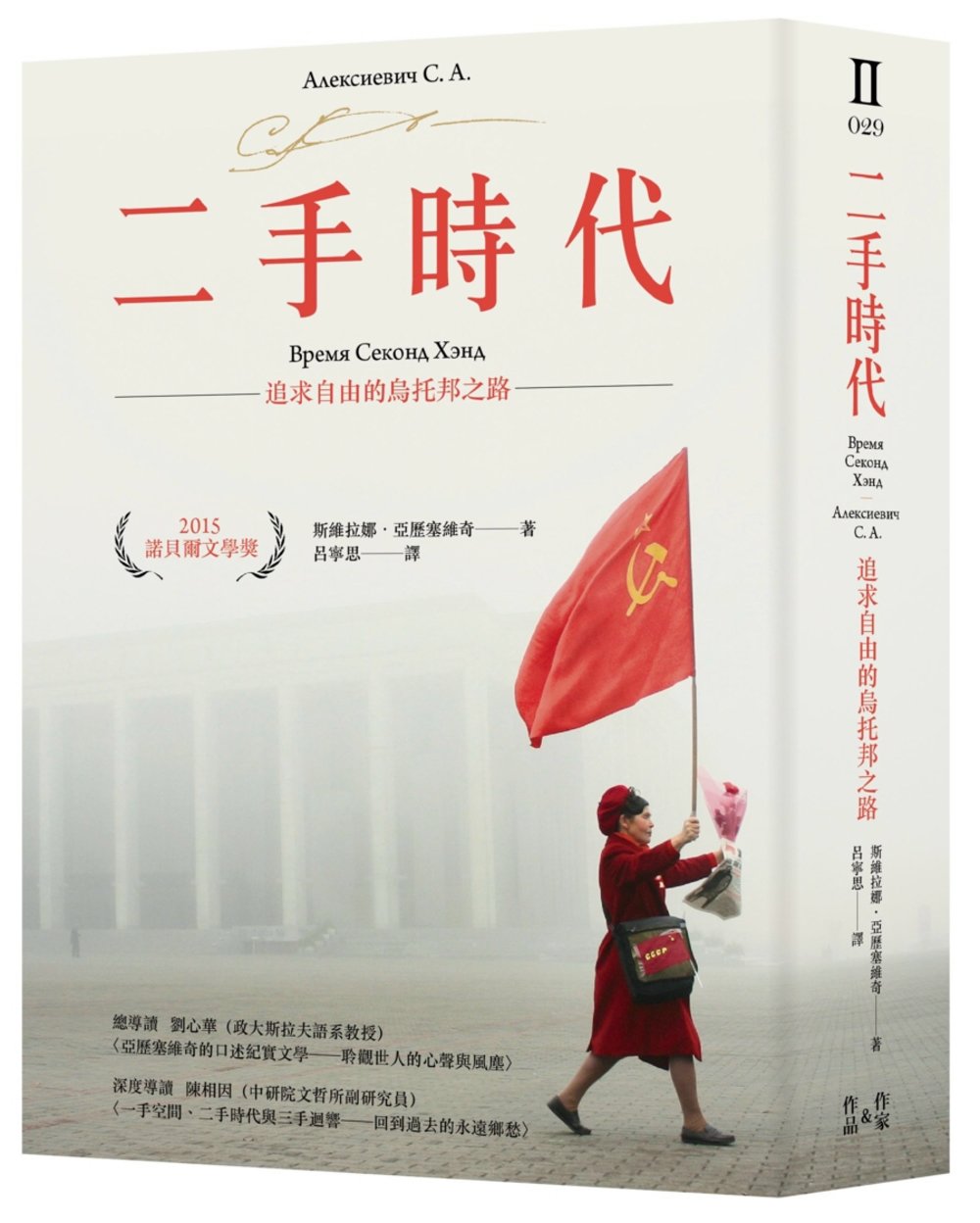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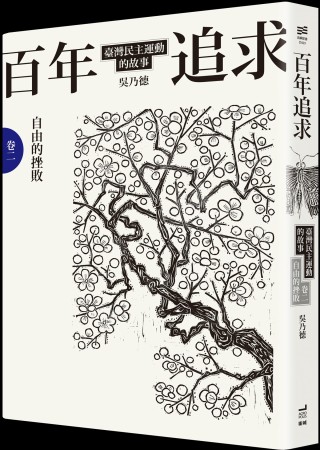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