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巫維珍踩進出版這一行,是誤打誤撞的緣分。念中文系的她當年很喜歡滾石文化發行的《廣告》雜誌,一志想進入雜誌社或傳播媒體,為了鋪路,還先去念傳媒相關研究所。結果論文寫完,就速速得到二魚文化的工作機會,成為一名初出茅廬的菜鳥編輯。
她回想二魚文化草創時期,雖久遠仍如數家珍,新鮮人遇上新公司,人少什麼位置都要會打,從新書提報到記者會都自己來,「很多事我是在什麼都不知道的狀況下就開始做,大概就是有一種憨膽吧。」她曾經手吳明益《蝶道》、王盛弘《慢慢走》、《臺灣同志小說選》、《臺灣成長小說選》……等書,累積了編輯功夫,也結識眾多作家,「尤其是做選集,我很感謝這個磨練的機會,你要一一找到作者授權,他們在哪個單位、怎麼聯絡,其實是十分瑣碎的行政工作,但那時我也不覺得是苦差事,很多累積就是這樣來的。」

隨緣隨時勢,順水逐流積成了她生命的河道:從二魚經手多本文學選輯,後來到馬可孛羅嘗試設計類書籍與小說,再到麥田擔任副總編輯經營翻譯文學,甚至成立子品牌「小麥田」進軍兒童文學,次次於她是嶄新試煉。她提及2014年成立小麥田,初推出的《格林姊妹大冒險》《祕密之屋》就挑戰了兒童文學常規,整套書多達10-20萬字,從通路報品到邀請推薦人,一路磕磕絆絆,「台灣童書市場習慣把童書分齡,一開始我有點抗拒。讀書就是讀書嘛,我們小時候也沒人規定這是幾歲以上讀的、或幾歲適合多少字數。」
發現人們對童書的認知總是固定在「繪本」或「某種樣子」,巫維珍屢屢有股不服氣:為什麼「某類書」才叫童書呢?有限制的是大人的想像力,還是小孩的理解力?但她明白,生態自有形成的來龍去脈,必須理解與尊重,「有次想在讀書會分享《彼得與他的寶貝》,那是關於『離別』的故事,我們提出跟寵物分離的失落,延伸到跟親人分離或單親家庭;不過有些家長認為孩子聽完可能會哭,但你講完就走,可能沒辦法對後續的情緒問題負責……」慢慢摸索、慢慢靠近,她用最直接的打法,拿失敗換經驗值。講起挫折,巫維珍都當作練功,「現場有很多實務的考量,當你從企劃、業務各環節都去多瞭解,做書時就會想到各種層面,不是自己高興就好。」

問她,從只需對一本書負責,到對一個書系、一個品牌負責,如何沉穩以對?她聽了一逕苦笑,「我每天都很焦慮耶,半夜起床上廁所就想到那個誰還沒交稿、誰還沒聯絡。」出版從來就很難是一個人的事,剛開始當編輯,你倚賴作者、譯者、設計、排版、印刷廠的協力;職涯規格升高,你得顧及業績目標,或擔憂同事無法準時出書,或怎樣說服性格迥異的人一起合作,偏偏出版市場緊縮……「畢竟你希望人人有年終,考量就不得不務實。」
掛著資深副總編頭銜,她弱弱地表達肺腑心聲,「我以前從沒想過要考慮這麼多人,我一直覺得自己只是個擔心社團不能好好發展的學姐啊!」

聽來宛如漫畫的青春煩惱,巫維珍的應對方式也非常青春:下班去游泳。在澄澈波光中載浮載沉,起初諸事纏擾心緒,煩久了倒成參悟契機,「你就是要沉住氣,在換氣過程中找到自己的節奏。」約莫心有所感,她補充,「我覺得有些編輯是天才型選手,光跳水就抵達泳池的一半,一出手驚豔四方,也有些博學型編輯才華洋溢;我只是很規律地從這頭游到另一頭,但游泳教練告訴我,節奏抓對了,只要不停下,紀律會帶你到達終點,慢一點也沒關係。」
做出版是想要讓世界更好,不是更快,專注在自己的水道修行,就不會為了鄰道的超前急躁不安。
編輯兩大生死索,一繫於時程表,另一繫於業績報表。牽引一本昨天還不存在於世界上的書降生是編輯的天命,但書自帶八字,有些功成名就,更多費盡心力只換得戰敗沙場。「但能做一分是一分,我愈來愈學到如何去為一本書加分。」比如,《丹麥女孩》找「台灣TG蝶園」撰文補充在地的性別觀點;菲力普.普曼《黑暗元素三部曲》加入上一版沒有的作者插圖,前傳《塵之書》同時收入英美兩國的插圖版本,同事還費心溝通作者燙金簽名(作者說從來沒在其他版本做過這件事),並加入越洋訪談文章。「如果引用普曼訪談裡的一句話:『我是故事的僕人』──大概編輯也是如此的感覺吧,做完這些再送小孩出門(上市),我會覺得對這本書有交待,沒愧對它。」
重出絕版已久的朵貝.楊笙經典童話《姆米系列全集》也是一例,該系列大多數已曾有中文譯本,巫維珍思考良久,心一橫同時推出八本,直到上市前團隊都戰戰兢兢:重新思考封面、不停估價書盒成本,想怎麼說服國外授權首刷的贈品(又擔心送審過不了)……,「雖然別人總是說,你們要出姆米了好棒喔,但我的內心很悲觀,總擔心著,不確定這條路的終點會有什麼在等我們。沒想到反應出乎意外的好。」在導讀手冊中,編輯部認真寫作的角色介紹與作者生平,為讀者仔細介紹了姆米谷的一切,「好好詮釋作品,讓它比『可愛』有更多的意義,我想是成功的原因。」


數算種種籌劃與過程時,她難得地從嚴肅中浮現笑意,「其實做書的時候滿快樂的,我的心態一直是完成任務,想把一本書做到好的心情,像李宗盛〈山丘〉說的,『不自量力地還手,直至死方休』,你想努力試試看自己能做到什麼程度。」
市場日益艱難,文學編輯們都在跟Netflix、社群網路、電玩等感官刺激更強的對手競爭消費者的時間。巫維珍倒也不是沒想過離開這行,她笑說,「但也不知道能去哪。」她低頭翻開周夢蝶當年所贈詩集《十三朵白菊花》,語氣有一種柔軟,「當時我只是個小朋友,但前輩的善意讓人永遠難忘。」詩人用心找到與她同名之人嵌入題字,時光已在紙側燒出斑點;她對自己編過的書豁達,但遇過的人總放在心上,「劉德華有唱過:『感激你不放低我更維護我』,我常想到『出版業』就是那個『你』,我算幸運,一路上有很多人照顧。每當回想起跟合作對象相處的快樂(或憤怒),就是往前看的養分。」

周夢蝶題字:「據我看,所謂現代詩,不過是一種東一句西一句的東西而已!女鋼琴家蕭維珍如是說」。

她形容自己是「一點小事就很開心」的體質,「我常逛獨立書店,看到有賣自己編的書就好高興喔!路上見到有人看書也很感動,即使是圖書館借的也很好。」這行業雖然挫折指數偏高,巫維珍卻也做過多本暢銷書(《三杯茶》《熔爐》《丹麥女孩》《以你的名字呼喚我》),近年也多次入圍開卷好書(《強尼上戰場》《復仇與求生》)、鏡週刊年度好書(《追逐尖叫》),這都為她帶來鼓舞。「這一行很多人沒留下來是因為缺少成就感,我現在能做的,也許是協助同事做出一本受到肯定的書,他就有信心繼續待。我一直希望能讓同事覺得,在這裡工作是件值得驕傲的事。」
啊,這果然是希望社團(和社員)好好發展的認真學姐會想的事吶。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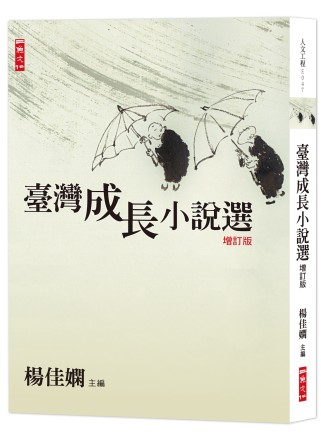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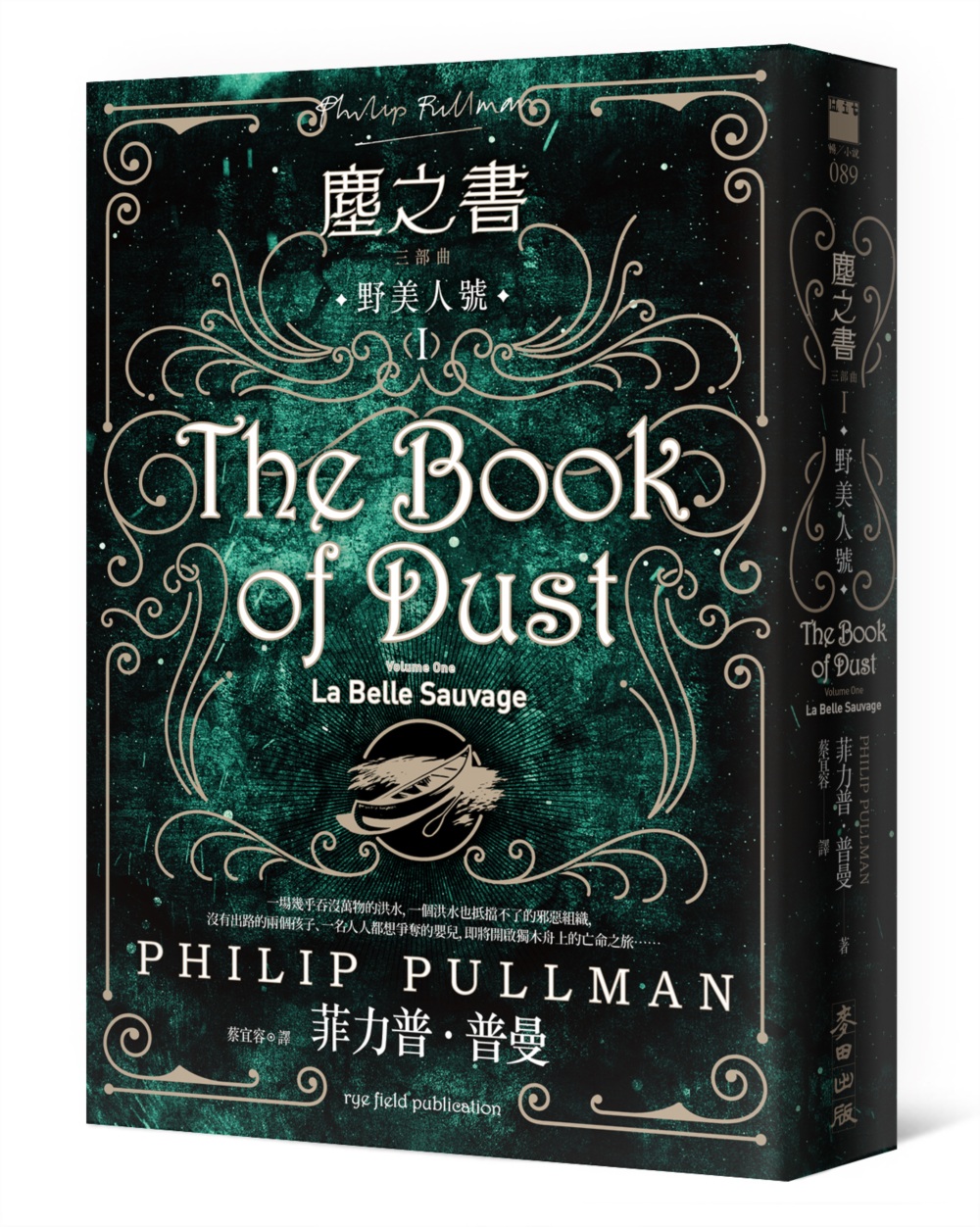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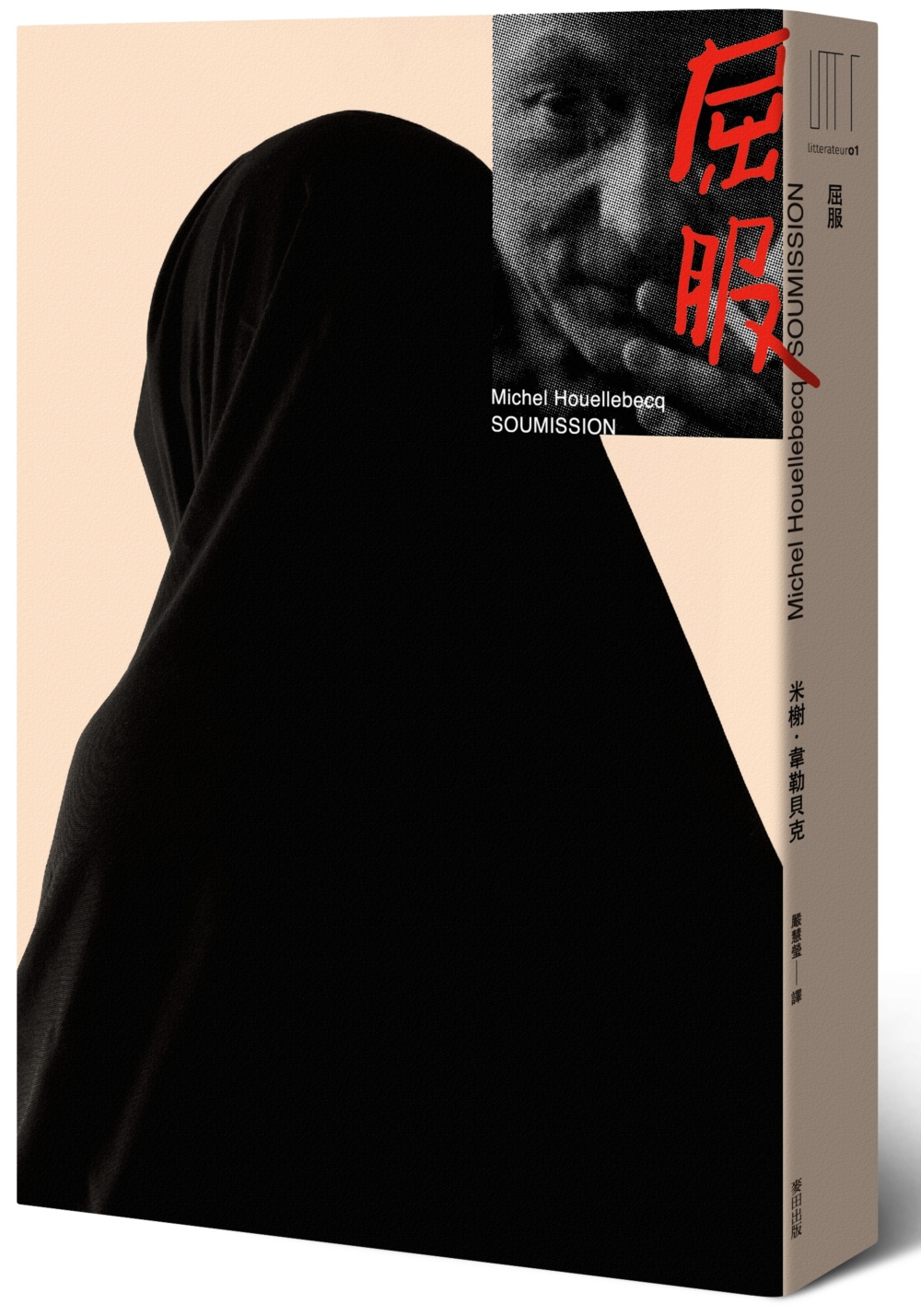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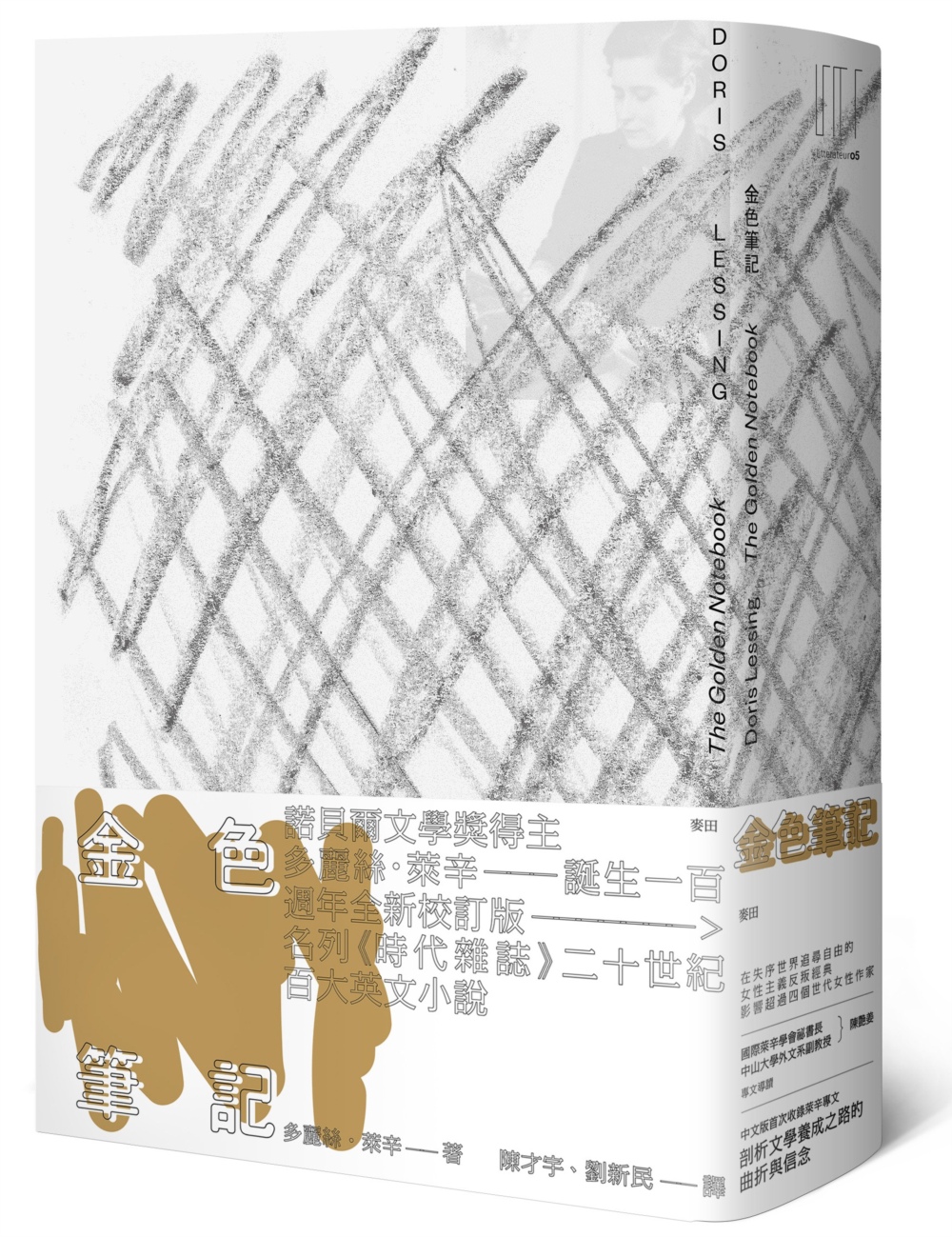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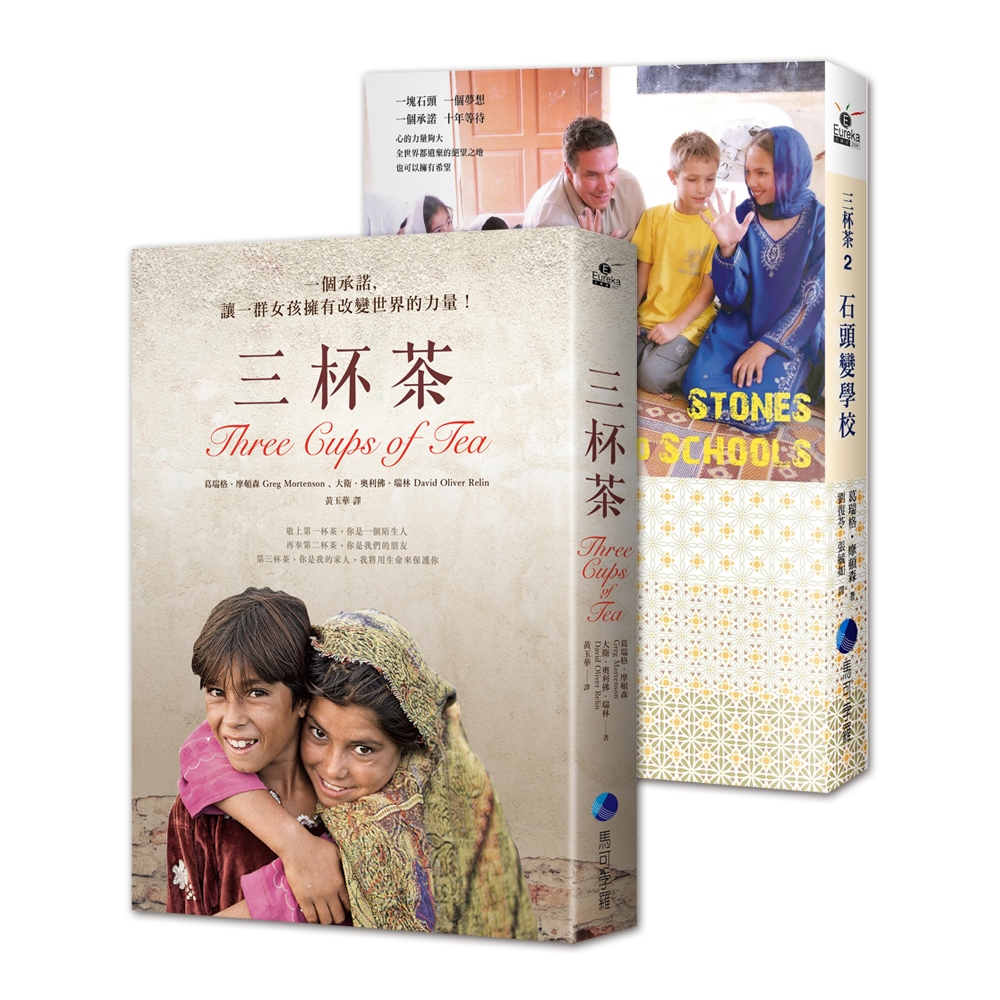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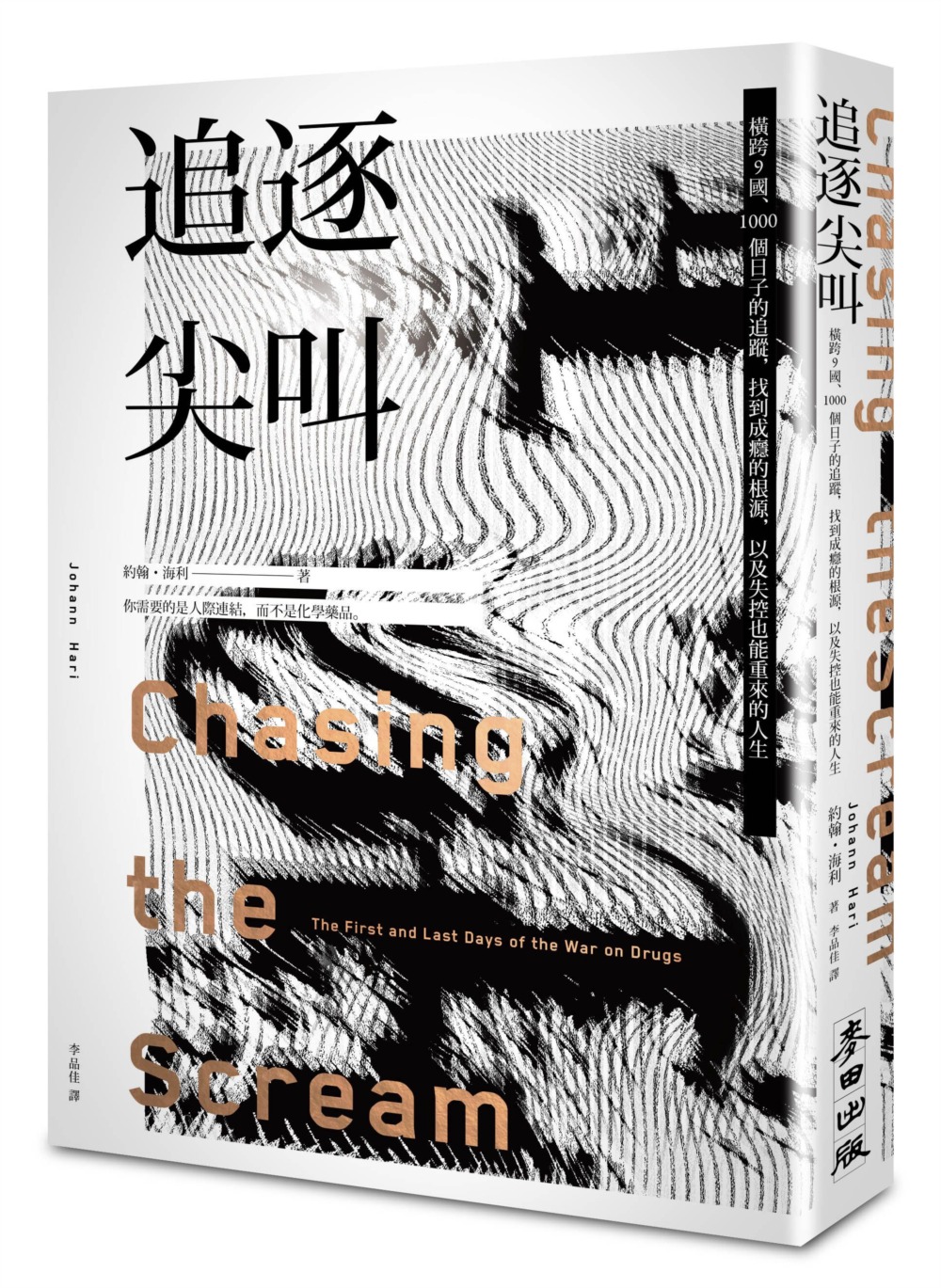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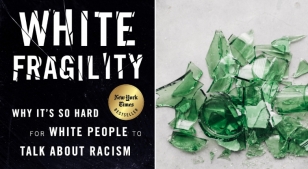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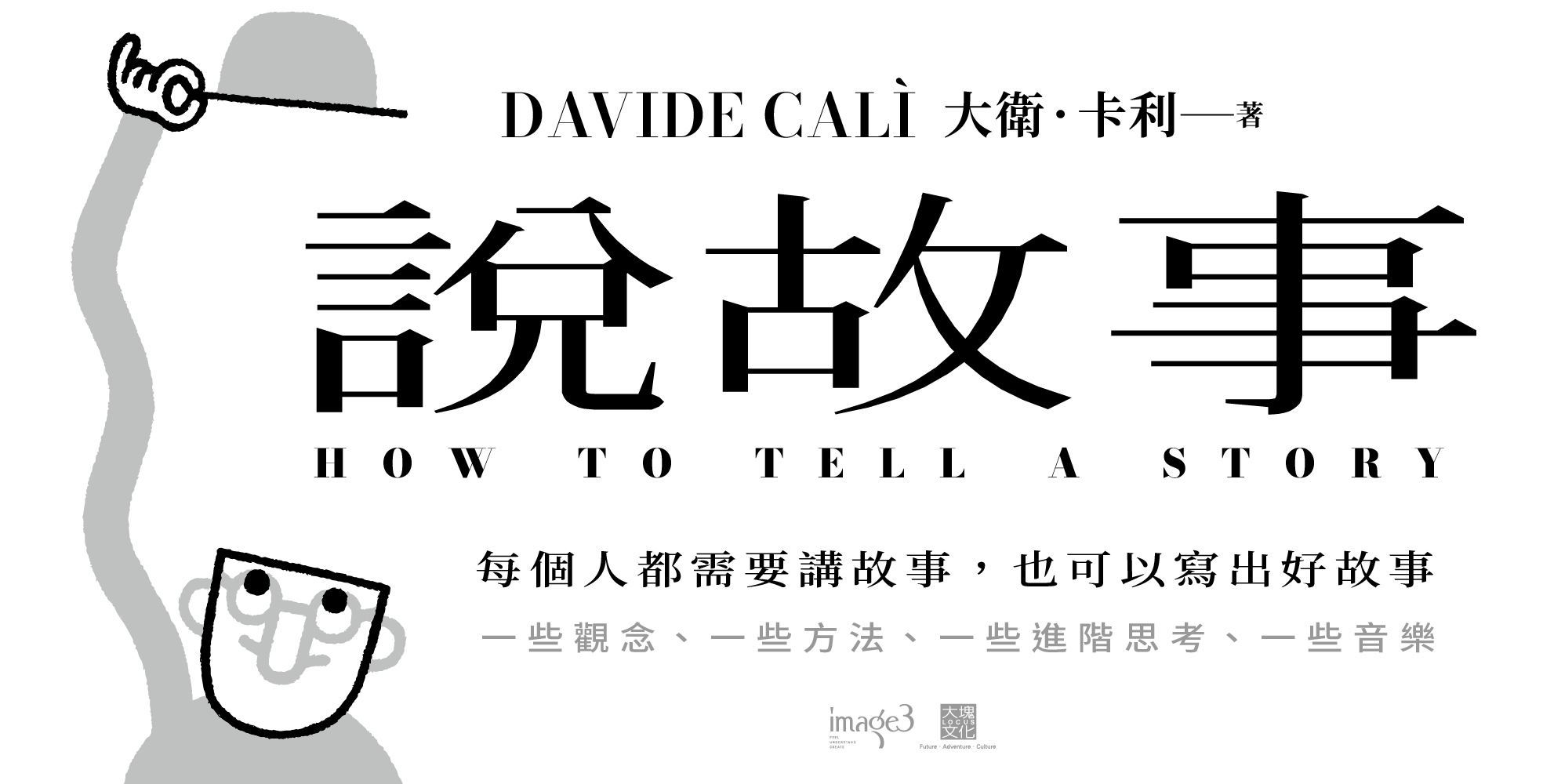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