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是先發現悲傷很美,才知道原來它是叫「憂憂」的。目前憂憂其實仍沒有像電影中回來了,它還持續被人們醜化中,於是心理醫生也阻擋不了現代憂鬱症,因為人類喜憂的程式,被商業生物的設定取代,強制改寫了憂憂,迷信快樂是主秀、讓樂樂過勞的我們,還能找回憂憂嗎?
我是先發現悲傷很美,才知道原來它是叫「憂憂」的。目前憂憂其實仍沒有像電影中回來了,它還持續被人們醜化中,於是心理醫生也阻擋不了現代憂鬱症,因為人類喜憂的程式,被商業生物的設定取代,強制改寫了憂憂,迷信快樂是主秀、讓樂樂過勞的我們,還能找回憂憂嗎? 
不知道別人是怎麼長大的,但我是先發現悲傷很美,才知道原來那是「悲傷」的。
所以憂憂,我不知道你為何會在電影裡被畫成胖胖的、總抿嘴自艾的小孩,是因為「悲傷」會給人很重的感覺嗎?所以「樂樂」就相對會被畫成很輕盈的嗎?就是討喜與否吧,但我對他們在銀幕上被畫出的體態形貌都很陌生。
悲傷其實不重,命運對悲傷的出手很輕,懸浮著、漫遊著,且無所不在的落腳,為很多事情做了花開過的註解,似乎在自然生態裡,「悲傷」是種必然的循環,花果謝了就變成別的。我還記得我認識「憂憂」的第一眼,它如白駒過隙,匆匆掠過我的眼前,有點像是我小時候幼稚園的校工,我一直記得他的背影,他一笑總缺幾顆牙,沒有要補的樣子,腿有點不便,於是他從我身邊走到遠處時,拿著那些鍋桶瓢盆,總會發出叮叮咚噹的聲音,愈遠愈清楚,我側耳聆聽,就知道時間是怎麼來的,又是怎麼走的,日頭下的人又是怎麼愈走愈駝的,聽看得我入神,直到他人被巷道吸走了一般。那巷道是歲月嗎?看似循環其實只是一瞬。
我幼年讀書時,座位有時會幸運地靠窗,我會為此雀躍不已。那勁風入冬後,對樹木可不留情,枝枒有時會激狂地舞動著,什麼也留不住似地掙扎著,相映天空,就像幅水墨畫,樹木厚實著所有的輕盈,於是有葉子與枝枒無時無刻不伸手向白雲,幾分像人類渴求自由的姿態,呼喊著、翻騰著、一輩子做足姿態的,根基在於哪裡也去不了,於是換得有幾十片葉子可以選擇飛走與墜下的自由。人都如此吧。
在校園漫步時,有時會撇見幾個孩子拿水沖螞蟻,那些筆直的頓時變七歪八扭的行進路線,即使碰到了人降「洪水」,那些小蟲子們仍企圖排隊,那算是有點「悲傷」的畫面嗎?不知道,我都還來不及下定論,它們就停格在我腦海裡,一幕接一幕的,並且在日後衍生出不同的故事發展,我跟著「憂憂」輕盈小巧地留下的註腳走,總會發現轉角後突然廣闊的人山人海,以及土地與天空的形貌,又讓我想到家附近畫舖師父們繪畫時著迷著的那一筆墨,他們喜歡在畫舖裡,畫著竹葉,末尾總留下一筆蒼勁的力道,看著看著,才發現「憂憂」是有強大韌度的,每片葉都有很不一樣的力道,那在「頑抗」什麼嗎?還是在「順應」著什麼?
看了幾次幾位老人畫水墨畫,才知快樂是我們找來存糧的,而「憂憂」才是形塑我們的,那些突然的、意想不到的際遇,給人一道刀工,讓你心頭有了山壁,而一旁才得以有了傍山的江河與野草,「憂憂」在素描與國畫筆觸中,都必須是「毫不延遲」的,那出手之精準,不知道是慈悲還是殘忍的鋒利,像神的刀功一樣,所以憂憂不可能是胖的,憂憂只是因為我們內心的排他與害怕,用快樂與憤怒占滿前廳,讓它始終擁擠堆積在角落而已。
快樂大抵上是相同的,因為我們刻意地集體追求,但悲傷,每個人的都不同,也使每個人都不同。
憂憂本質像《刺客聶隱娘》的美,「他只有一個人,沒有同類」,時時都具有存在感地被隱藏著,每個人其實都是「聶隱娘」,並沒有同類,如今的我們只是把與他人的雷同處放大化而已,那類不同於群體的,都放在「憂憂」那裡囤積,深怕拿出來,於是憂憂是我們怕不「合群」的情況下,不斷餵養大的,我們把異質之處藏起來,一直到好像門都快關不起來的地步,於是憂憂才會被我們想像得拙重,就像伊藤潤二畫的《人頭氣球》,人不斷「斷尾求生」地融合社會,那些不想分辨、無以名狀的就大到冉冉升空,自己是什麼,搞不清楚像裝了氦氣一樣,就虛大到飄走了,漸漸地,在上面飄的,會比落實在下面行走的還多。
 憂憂是我們怕不「合群」的情況下,不斷餵養大的
憂憂是我們怕不「合群」的情況下,不斷餵養大的
因為我們沒有悲傷那根線啊。我們從小非常害怕悲傷,因為那似乎很「不討喜」,於是我們人人抱一本阿德勒的《被討厭的勇氣》,像廟裡求來的護身符一樣,心裡還是怕得要死,但如此這般,就如人怕自己影子一樣乖謬,每個人都是自己的「怪談」,怕那些暗處的蟲魚鳥獸,那些進犯的心頭魍魎,於是我們日光與藍光並用,沒有哪一代像我們這一代這麼怕在人群中「不討喜」,怕自己的「本象」。「憂憂」被我們搞醜了,「樂樂」也被我們搞成整型紙片人,每季在伸展台秀身材放閃兼打卡,憂憂則變成包圍我們四周的狼群,我們以3C藍光抵抗他們的進逼。
我們想像的憂憂,根本不是憂憂本身,憂憂如今出走了或反撲,人們憤怒的腹地擴大(因為快樂過度提領,變成如鋰電池總充不飽),我們留下的憂憂變人質,只是一個空殼,很像村上春樹《世界末日與冷酷異境》書中,主角被抵押居留的影子,那時空,人們以為它是不需要的,可以割捨的,是啊,我們要拿憂憂來做什麼呢?就跟電影一開始演的,我們要拿「你」怎麼辦呢?
我記得我小時候,家對面是木造的廢棄官舍,有很久沒修剪的庭院,樹都長出來張牙舞爪,晚上看起來煞是恐怖,白天時我們這幾個小孩卻愛從殘破木門裡鑽進去探險,地上滿是枯枝落葉,官舍早晚暮色都深,幾乎跟包圍它的樹連成一體,在都市裡成為一種孤單的異境。我們這群潛入者與它自己都知道遲早會拆遷成大樓,任何我現下目睹的這一刻,隔日都可能變成永恆,這時「憂憂」在我眼前心底,清楚地現形了。我們看著它在太陽下,在水泥叢林裡,這屋體是溫柔的,有點懷舊的倦態,像個猶有媚態女人老來盤坐在市區,花果爛泥成異香,樹的呼氣有點野蠻,有點像身處在林中,跟行道樹不同,你知道這深處是它們的腹地,它們大口呼吸著、伸展著,這巨大而野生的存在,如此活生生,相對自己倒像個有程式制約的人,卻也知道它們這樣的棲息遲早會被連根拔除。那時自己似乎體會到「憂憂」是什麼,也知道自己已被改造了,情感洪流硬被改道、整建成水壩渠道,憂憂也變成是不受歡迎的「闌尾」裝置,但它原是這樣的美,像盤結到地心的樹根,像連結到天空的呼喊張揚,是我們被綁住的「野性」,像那傑克‧倫敦筆下的「白狼」卻被圈養在後院裡,一直問你,它何時會被放出來?沒有逃遁地圖,我頓時跟那廢墟的樹一樣無助。
於是我懷抱著那廢墟樹呼喚林地的憂憂印象,揣在懷中讓它溫暖著,從小到大一直一直把它寫出來,我幼年看到的憂憂百百種樣貌,個個都很美,如今它們共同被圈養管理在邊陲地帶,我們每個城市人都只能分配到固定憂憂配額,多了就被排擠,視為異類,這城市與那城市,天地萬物的「憂憂」們都被控制住,於是我們需要這麼多物質給我們類「快樂丸」的效果控制,但如果還聽得到「憂憂」,感受到它們野生初生的模樣,就會想把它寫出來、畫出來,如魔戒遠征軍始終在路上,企欲找憂憂回到它的崗位上。目前憂憂仍沒有像電影中回到操作台,它還在持續被醜化中,於是心理醫生也阻擋不了現代的憂鬱症,因為人喜憂的程式,被商業生物取代,被改寫了,我們所謂的正面力量矯枉過正,連快樂都不純粹。
你曾經看過原始的「憂憂」嗎?如果沒有,請試著從他者的生活裡看進去吧,或從山跟樹跟天空那裡出神地看,如電影中的隱喻,樂樂有多瘦,它根生雙胞的影子憂憂就有多大,不把憂憂寫出來,原始的樂樂也將會失蹤了,或被整型,成為想一昧迎合社會期待的人(於是怒怒就會隱隱坐大)。這不只是部電影的劇情,而是被控制的大人們是否還有能力找出憂憂的線索?從林布蘭特或巴哈裡?或者是你的初始記憶裡?你的「憂憂」或許還在那裡等你。
 樂樂有多瘦,它根生雙胞的影子憂憂就有多大
樂樂有多瘦,它根生雙胞的影子憂憂就有多大
《腦筋急轉彎》(Inside Out),為2015年皮克斯3D動畫片。由《怪獸電力公司》《天外奇蹟》等片的導演彼特‧達克特執導,導演與製片指出創作靈感部份來自《Herman's Head》。故事描述主角萊莉因為父親工作的因素搬家至舊金山,要準備適應新環境,萊莉腦中控制歡樂與憂傷的樂樂與憂憂迷失在茫茫腦海中,大腦總部只剩下掌管憤怒、恐懼和厭惡的怒怒、驚驚與厭厭的三位情緒,導致萊莉變得憤世嫉俗,而樂樂與憂憂則找尋回到大腦總部的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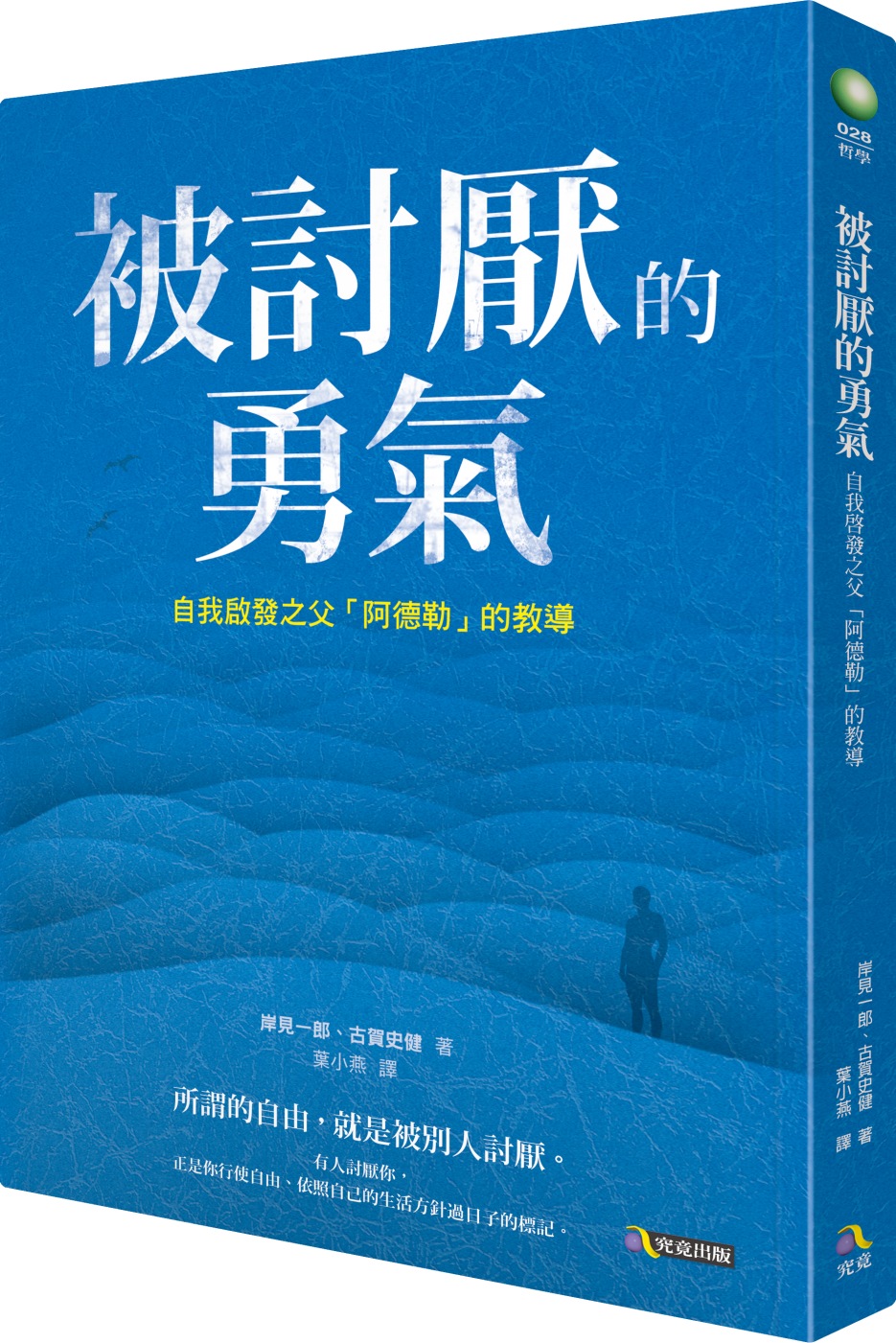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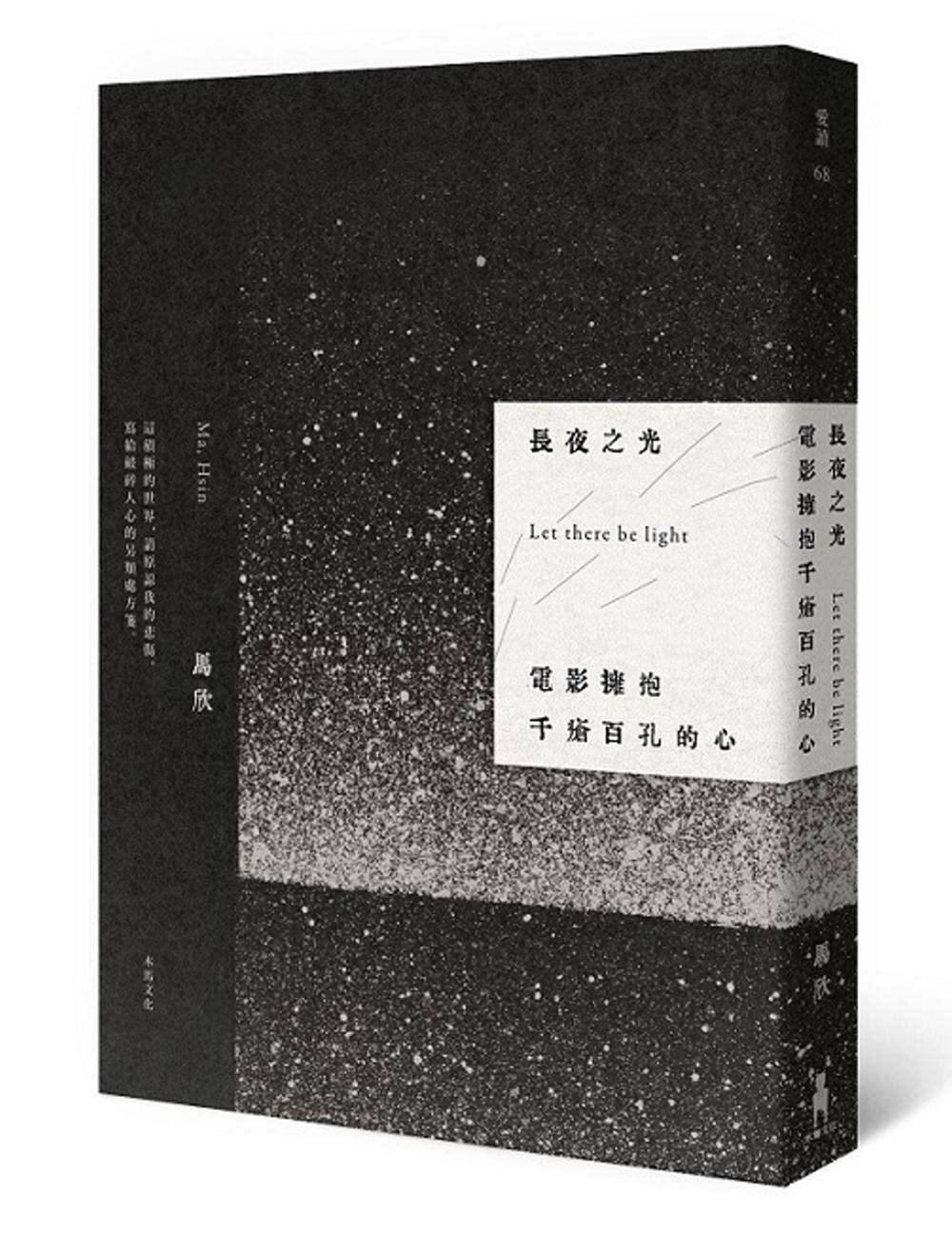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