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攝影/陳藝堂 圖片提供/伊格言)
(攝影/陳藝堂 圖片提供/伊格言)
和伊格言約在一個星期五下午。結束採訪之後,他要轉往自由廣場去參加「不要核四、五六運動」。那天他要登上野台進行演說,與現場反核的民眾一同探討核電與文明災難等議題,並分享他寫作以核災為主題的最新小說《零地點GroundZero》的心路歷程。
「以前就有參加過幾次『不要核四、五六運動』,但在這場合上台還是第一次。而且以往演講都是在室內,沒有講過野台,所以有點緊張。」他略顯靦腆地笑著坦言,「寫完《零地點》,我不小心真的變成一個核電專家了。」對這個議題有多了解呢?伊格言想了想,補充道,「可能有到可以上電視與人家辯論的程度吧。」
今年(2013)四月才剛以《拜訪糖果阿姨》與讀者再見面,不出數月,《零地點》便又面世,表面上看,伊格言的寫作速率似乎相當驚人,然《零地點》並非急就章,當中有著他自己的層層考量,與一次濃縮的爆發。當初出版社與伊格言討論,是否有可能撰寫一部以台灣核能議題為內容的小說,無巧不巧,他的腦海裡,始終轉著一個與「原爆」有關的寫作計劃,「剛好核電這個題目來了,我考慮了一下,覺得這些題目可以寫成一個系列,因為它們都互有關連──到底文明該如何利用能源?文明可以接受什麼樣的事情?」於是他決定承擔這個任務,以《零地點》做為整個系列的開端。
於此同時,伊格言考量的是,上一部長篇小說《噬夢人》用科幻手法敘寫,是以純文學來隱喻現實狀態的作品。多變的他,在面對《零地點》時,決定進行一次「貼地飛行」的寫作,「我覺得我可以寫一本直接跟現實對撞的書。」他大量蒐集、閱讀核能相關資料、採訪關鍵祕密消息來源、實地走勘小說中提到的重要地點,以期寫出最真實的情節。為了這部小說,伊格言半玩笑半認真地說自己「累得要命」,但一切都是必須。「我希望《零地點》與台灣的現實產生極大的互動,我也把這部小說視為一種行動藝術。既然有這樣的希望、還用了『對撞』這麼極端的詞,我就要更直接面對社會,必須用真實的材料來構築這本小說,不能隱喻,才能和現實結合得更緊密。」
於是我們在《零地點》可以讀到台灣現時現地的種種情境,以及政府官員與媒體紅人在面對核電、甚或核災發生後的應變,更有著許多台電處理核電事件的態度與方式──草率、隱瞞、掩蓋、謊言──比對自今年開始風起雲湧的核電新聞,虛虛實實,看得人心驚膽顫。這真的只是一部小說嗎?「是小說啊,是以貼地飛行的現實材料寫的小說。」伊格言神祕地笑了一下,旋即又轉為嚴肅,「在《零地點》裡的事件,只要發生的時間點是現在,我必須強調的是:我有充足理由確信其為真。」在閱讀與消化過大量資訊之後,他坦承,不只讀者可能會對書裡種種台灣核能與核變的「近預言式描述」感到不安,連他自己一路寫來,也因為這些他所探知的真實狀況,覺得很是驚恐。
「這雖然是一部以『反核失敗』為主軸的小說,但我更想講的,是關於『文明』。」回顧核能歷史,最初是一種善惡兼有的新能源,「核能既是殺人武器,也是人類的美好夢想,科學家期望把核能拿來和平利用,以非常少的原料製造出極多的能源。」伊格言說,假若他是生在那個時代的科學家,可能會很興奮地支持核能,「本來拿來殺人的東西,竟然可以發展人類的文明,不是很好嗎?」
然而,時至今日,核能的影響早已遠遠超乎人類所能控制的範圍,「人類的科技對核能的掌握與對輻射的理解並不清楚,對於核災只能講機率,對任何災變彌補卻束手無策,這很荒謬。」不清楚、不了解、卻還堅持要使用,無非將自己推上毀滅之路。「核能是文明產生出來的需求,我們覺得它可以發展人類文明,可是文明有沒有可能走錯路?答案是可能的。」就像諸多國家引以為傲的自由民主,難道得到之後就不會再失去嗎?並不見得。「文明也有可能退步的。同樣地,人類的文明有沒有可能犯錯?你要先承認有可能犯錯,才有可能認錯,然後去改正你的錯誤。」伊格言說。
撰寫《零地點》,伊格言最大的壓力來自於時間。「我在跟台電拚進度,必須趕在台電裝填核四燃料棒,讓生米煮成熟飯之前完成這本書,才來得及喊停。」雖以小說手法包裝,但諸多真實人事物的敘述,也不得不讓人擔心伊格言會否因此惹上麻煩。「確實有可能惹上法律方面的麻煩,尤其是台電可能會找上我吧。」但伊格言不甚在意這件事,也不去評估這個可能。「既然我把這部作品,以及作品出版後的變化,都當成一整個行動藝術,萬一真的發生什麼,我就接受,然後處理它。那都是我要承擔的,同樣也是我的作品。」
回到作家身分,伊格言自己又怎麼看待《零地點》可能為他帶來的影響?面對這個問題,伊格言搖搖頭,「無法預期。我也沒有希望得到什麼,我只希望反核成功。」
伊格言作品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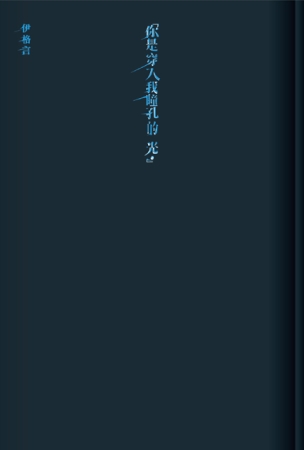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