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彭仁郁由長廊盡頭現身,粉紅色短髮在燈光下夢幻又張揚,像動畫裡的戰鬥少女走進現實,身上攜帶著無數戰場。
確實剛從「戰場」回來。2025年9月,花蓮光復鄉堰塞湖溢流釀災,彭仁郁也參與了救難隊。長年關注政治暴力、災難創傷與家內性侵等議題,難以想像她看過多少苦難現場,又如何反覆靠近那些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
在中研院民族所擔任副研究員的彭仁郁,也是長期活躍於社會事件前線的理論實踐者,多數人是因為促轉會、慰安婦、政治暴力受害者家屬等議題而認識她。新作《家的蜃樓》由兩位受訪者的訪談與故事輻射出亂倫創傷的各種探討向度,彭仁郁以民族誌方式進行書寫,這不是她初次踏足的田野,在法國攻讀心理病理暨精神分析學博士時,研究的就是家內性侵。「這個主題即使在法國也很禁忌,很多人以為家內性侵只在高風險家庭發生……事實上,無論法國或台灣,我訪問的案例多是中產階級,甚至很多經濟優沃的家庭。」
台灣社會對議題的關注討論,總是要用生命獻祭換取。鄧如雯事件後有了《家庭暴力防治法》,彭婉如事件之後立了《性侵害防治法》。但家內性侵的困境又更上一層樓,問題從來不只在於性暴力或亂倫本身,而在於整個社會結構如何讓暴力隱形?
《家的蜃樓》兩位主角:大榮與小汐,正是這結構下的生還者。
彭仁郁說,「家內性侵的倖存者,往往在日常的每分每刻重覆經歷著心理上的潰堤。而會有自殺衝動、成癮,各種常被判斷成精神病理的現象,是因為他的身心仍深陷在地獄裡……」
地獄是「人活著卻無法前進」的狀態,是混合依戀、羞愧、渴求與絕望的蠟像館。彭仁郁描述,「我在跟他們互動時,感受到他們隨時在預備——預備親愛的人下一秒會變成怪獸撕裂他,預備下一刻會被打。他們甚至不打算逃跑,因為太明白逃也逃不了。我曾經問大榮,小時候是不是其實知道爸爸要做什麼?他坦承即使知道,還是會配合,因為他太害怕爸爸丟下他。」
小汐亦然。相較於他人記憶中甜蜜的童年,她的成長經驗充斥著拳腳、鍋鏟、擀麵棍與皮帶;性侵與性剝削,只是眾多暴力與心理操控的形式之一。從小到大,小汐心中的父親宛如神般宰制一切,即便已成年,每每遇到父親,聰穎的她就退化成孱弱無力的孩子。家族對父親的經濟依賴羅織成鍊條,將她綁在牢籠之中。《家的蜃樓》刻意保留一段驚悚紀實:小汐父親遍尋不著女兒,循線找上當時與小汐斷續晤談的彭仁郁,哀求、恐嚇輪番上場。小汐因此被壓倒性的驚慌淹沒:彭仁郁會不會倒戈?自己會不會再次被逼到死角圍捕?那樣的恐懼其來有自,彭仁郁說,「我們的醫療與社福體系至今仍是家庭至上,出事時,頭一件事是連繫家人。萬一家人就是加害者呢?某種程度上,系統是在強化這個蜃樓。」

家是煉獄嗎?親愛的家人是怪獸嗎?家是避風港還是被神聖化的蜘蛛網?
真正可怕的不是恐怖故事或驚悚電影,而是醒來後發現惡夢是真的。「大家都說家是避風港,但我們應該去分辨,我們究竟是在守護家的真實意義,還是在維持一種被神聖化的『家的蜃樓』?」彭仁郁一度猶豫是否以薛西弗斯為書名,因為家內性侵的倖存者就像反覆推石上山的人,徒勞守護著「家」的幻影。「同時,他們會自責為什麼不離開?為什麼自己沒做好,害家人變成這樣?」
受創者會把憤怒藏起來,把傷口和哭嚎藏起來,把血腥和獻祭的屍骨藏起來。彭仁郁藉用考古學為喻,「沒人知道凝固的岩漿裡會挖出什麼殘骸,助人工作者必須不斷清理,還原現場,辨識哪些是添加上去的遮蔽物。同時,我必須透過想像沉入地獄,找到需要被找出來的人。如果沒有足夠訓練,你在地獄裡是待不住的,你只會看到眼前這個人有多難搞,不斷試探、挑釁你們的關係,最後你會萬分委屈,轉身離開。然而我們需要追問的是:眼前這個人何以總是過度警覺、如坐針氈?他發生過什麼事?」
比離開地獄更困難的,是陪伴受創者重返地獄,赤足踏過曾發生的一切。彭仁郁描述,起初大榮和小汐來到研究室如驚弓之鳥,眼神飄移、默不作聲,不知眼前的晤談者值不值得信任、哪些話能安心表露。「要能『說』沒有那麼容易。創傷之所以是創傷,很多時候是因為連當事人都無法理解,連自己都弄不懂的事要怎麼訴說?那些經驗可能沒有相對應的語言。」緘默,不只是因為失去語言或風聲鶴唳的危險,也因為他們以為這樣才能保住、守護這個「家」。
因此對助人工作者來說,難就難在,要如何拒絕快速方便的解答、抵抗被簡化的理解。彭仁郁有些激動,「我們現在說的跨領域專業都是紙上談兵!不光是性暴力,政治暴力或災難創傷都是一樣邏輯,你問我什麼是深水區?就是切割式的看待助人專業,自殺歸自殺單位,成癮歸成癮單位,但『創傷知情』是不把創傷者切割拆分,放進十個抽屜,政府再用十倍成本維繫所謂的成效。」
發願真正的跨領域系統整合的團隊,是否痴人說夢?無論哪個領域的創傷,都在問同一件事:我們或社會願不願意付出足夠長的時間,付出不可理喻的代價去看見這一切?彭仁郁指出,「大眾常見的反應是群情激憤,一窩蜂去譴責加害者——這正是受創者最深的恐懼。會有憤怒或害怕的情緒很自然,可是直接發洩,人不就跟海參一樣嗎……」她解釋,「義憤是最無濟於事的。把痛苦原封不動嘔吐奉還,不過是用自己對世界的美好想像,把受創者推得更遠更孤獨。」

那能怎麼做呢?彭仁郁認為要從海參進化成人,得練習容納、消化痛苦,一起創造新的關係經驗,才能找到出路。「每個人都有他的龐貝城,所以我們需要跟著他一起回去,在不斷訴說的過程中,重新辨識那些經驗。有時候,光是讓他不再獨自待在祕密裡,就很有價值了,因為祕密是有腐蝕性的。」
跟他的痛苦在一起,在場,並成為見證者。或許可以藉用卡爾維諾《看不見的城市》所言,每天生活其間的地獄已然存在,我們可以走方便且容易的路徑,接受、融入地獄,成為它的一部分,或者也可以選擇第二條路,在地獄裡尋找並學習辨認什麼人、什麼東西不是地獄,然後,讓它們繼續存活,給它們空間。
彭仁郁強調,「你想想,一個人要怎麼長期在地獄裡撐住自己?如果不是他擁有強大的內在韌性,不可能活下來。」
與體制戰鬥,陪伴受創者跟虛幻的怪物戰鬥,同樣需要撐住自己。長年的臨床訓練和接受分折的經驗,護持著彭仁郁,「所以很需要自我照顧啊,我會做瑜伽、彈琴、跳舞,以前還組過阿卡貝拉團。」彭仁郁爽朗大笑,「有人形容唱歌是有控制的尖叫。」

距離2016年初想像《家的蜃樓》這本創傷書寫的草圖,如今抵達了第十個春天。這趟拆解又重描「家為何物」的紀實錄,承載了上千個小時的談話、無數支離破碎的夢境、在警局、病房及法院的穿梭……至今,小汐和大榮在就醫時填的緊急連絡人甚至是彭仁郁。某日編輯隨意問起,大榮現在幾歲?看顧著這本書成長過程的人,忽忽意識到原來故事走了這麼多年——這條路,大榮、小汐還有彭仁郁,都邁入中年。
「小汐曾經形容,打開創傷像是潛入深海,晤談就像回來換裝氧氣瓶。」彭仁郁說,「或許在大家想像中,這些關係會讓我受束縛,我並不覺得,他們對我來說是美好的存在,但我期待他們靠自己補充氧氣瓶的那天到來。」
隨著《家的蜃樓》付梓,那一天似乎不再遙不可及。
這些旅程帶來什麼改變呢?彭仁郁毫不猶豫地回答,「讓我有更強大的信心吧!單向看會以為是我耗費十年陪伴他們,其實他們也投注十年光陰在我身上。若非這十年走過的路,我相信我對創傷理論的批判、對體制理想的藍圖,不會有現在這麼具體的想像。」
考古是漫長而節制的工作,創傷能被看見也是,讓湮沒在熔岩中的龐貝城出土,不過是第一步;活下來的人還在戰鬥,還在對抗,還在感受。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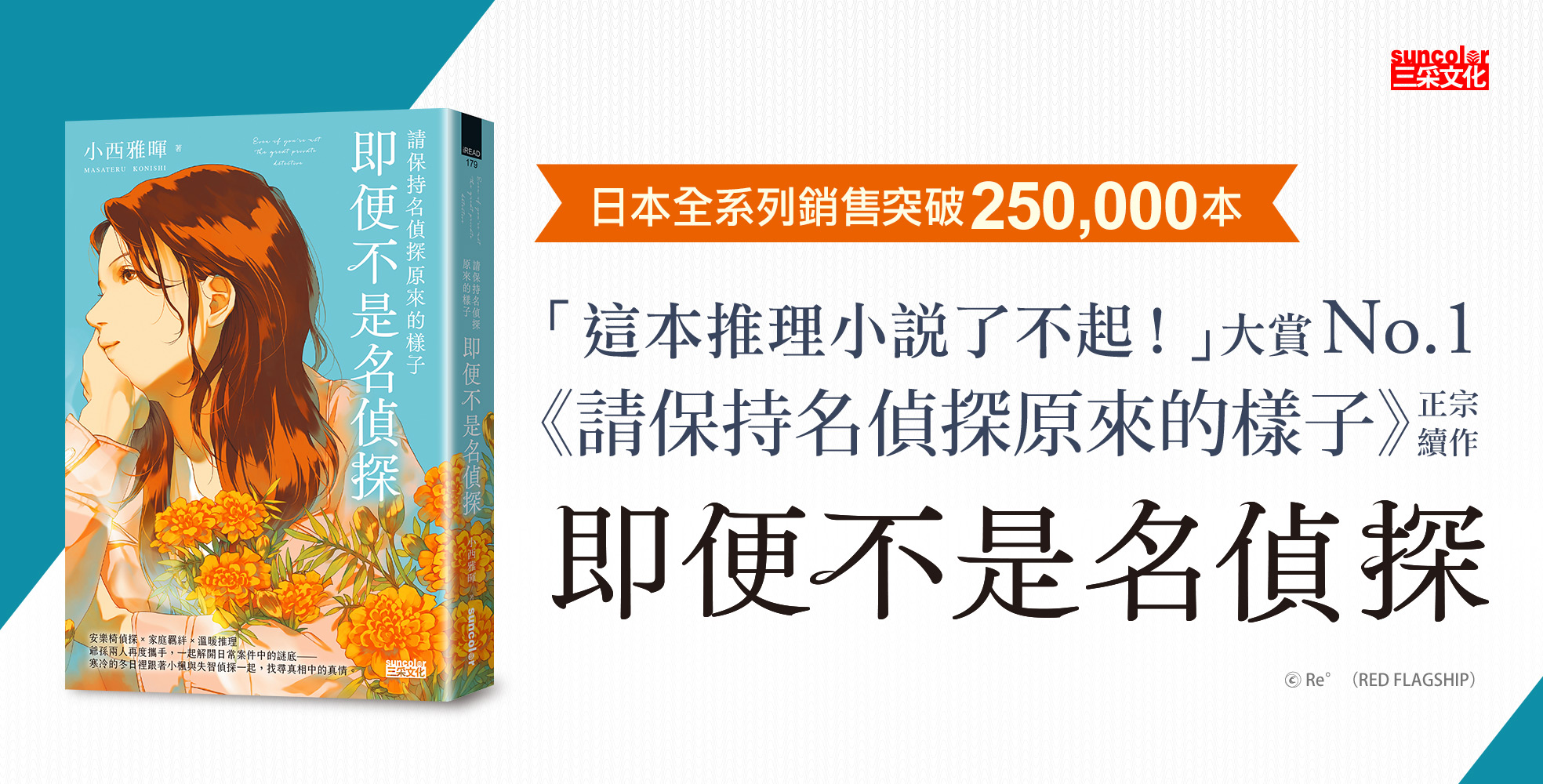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