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尚緯的《我還在這裡》散文集,我認為無法被單純歸類為創傷文學或者懺情文體,高度更觸及創作倫理,而且是當代讀者必讀的寫作倫理(aka遇到爛人爛事的保命錦囊)入門書。
宋尚緯本身是跨文類的作家,他以詩人的身分出道,出了六本詩集,三本散文集,同時是近四萬追蹤人次的臉書KOL—大多數時候頁面發的都是他所謂的「廢文」,不時佐以銳利度極高的時事評論,和網民吵架時強得嚇嚇叫。在網路流量至上的寫作時代,宋尚緯允稱當代的成功作家。但《我還在這裡》不是寫自己如何成功的散文,是徹頭徹尾地書寫人生的失敗,以毫不自溺的冷靜筆調,剖析人生中發生的慘案啟示。「賣慘」原是社群時代博取專注的手法之一,然而,這本散文的高度正在於—(作家不得不)以「賣慘」為主題,不卑不亢更不賣慘地,確實傳遞出「文學」的價值。
從大乘走回小乘的文學價值,救己還是救世?
宋尚緯上一本散文集,叫做《我真的不知道自己怎麼會變擲筊怪的》—寫他從一個絕對不信鬼神的鐵齒人類因緣際會變成了擲筊界的傳奇、無形界的小網紅,從無信到有信的理由是因為生病—身體長期累積的種種病痛加上中風(還加上罕病與洗腎),宋尚緯開啟了中醫調養加上神明調養的神奇之旅。而作家自承一開始不是去求神治病,是去跟神明聊天的。聊著聊著就得了各種氣味的符水,聊著就被神抓起來排除穢氣打嗝治病。敘說自己過往的所有執著都被擲茭所改變,讀來趣味橫生,但裡面寫的病痛,尚屬外部症狀,《我還在這裡》卻是心底的病根真正鬆動起來,看清楚自己過往因為外力傷害而用力到扭曲的肌肉,應該如何被善待:「我們總會以為自己和世界戰鬥,但我最近會想,其實多數時候,我們其實是在和以為那是整個世界的自己在戰鬥著。每個人都有在意的事情與自己生命的課題,也許我們都應該先瞭解自己到底在和什麼對抗會好一些。有時候會看到許多人像我以前一樣,會說有些人無法理解什麼是因為不夠聰明,可能是因為我本來就不夠聰明,所以我現在偶爾會想,人其實也不用那麼聰明,我們只要知道自己為什麼,以及和什麼在戰鬥著就好了。」
作家在書寫中不諱言自己的原生家庭經驗是不快樂的,種種情緒勒索也沒少過,禪宗有偈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但是,要得到本來無一物的頓悟,得先看清菩提樹的萌發與凋零,看清楚明鏡顛倒的本相,如果傷痕沒有被敘事,沉痾的污血持續在底下發臭,那就沒有癒合的可能。而在敘事傷痕時,作家很節制地「幾乎不寫出小時候發生的具體事情」,這種理性自省的姿態,使得宋尚緯的傷痕書寫偏向超然的分析,因為天性太過自覺,簡直就擁有自己可以幫自己做諮商治療的天分。
這種自覺特性,使得宋尚緯的傷痕書寫不耽溺於賣慘,而能專注於看清自身的侷限。同時展現出悲憫,因為知道文學的侷限只是「尚未被處理好的創傷」:「有些人認為,文學是全然藝術的,我不否認這種想法,但我也不能苟同這種想法。因為我所閱讀過、學習過的文學,從來不只是完全關乎藝術的,更多時候,我們閱讀所看到的感動,是關於內心的。我能看到偉大的文學作品中有內心的糾葛與思想的碰撞,也能看到那些深刻的作品裡,充滿內心糾結的痕跡。有些人會說,那些痕跡正是文學偉大的地方,但我有時候卻會覺得,那些痕跡,其實就是作者們沒有處理好的內心創傷。作者將其書寫出來,找到這個創傷,試著使他們癒合。指認出傷口的時候,我們的痛苦才有被處理的可能。……我們得先處理好自己,才能處理文學的事情。」
人文藝術,絕大部分是為了服務這樣的自憫而生的
宋尚緯不僅解釋了文字敘事治療之用,同時也全觀地指出假以「藝術創作」之名傷害他人的「倫理」,根本就不存在。我翻成白話再說一次:「你創作是因為你有病,你有病再可憐也不代表你就有特權去佔人便宜。」無法不想起劇作家黃郁晴的作品《藝術之子》,想起電影《TÁR》,想起《房思琪的初戀樂園》,藝術家多半有病有創傷,若非如此,怎會有心思去對生命發起大哉問?但,創傷是自己的事,因為表達得漂亮高超變成文學藝術的光環,那仍然是自己的事。最恐怖的是:當光環帶來過分權力,附加價值變成主要價值時,就會形成災難性的誤解—引用《房思琪的初戀樂園》作者林奕含的話來說—文學藝術,真的不該是巧言令色而已。
作家寫下了創傷的共感,下一步則是闡述界線的迷思。
由於網路社群的興起,當代作家幾乎是無法遵循「作者已死」的論調來生活。因為宋尚緯早期詩集多觸及創傷的爬梳,作家不諱言,自己在詩集出版後,收過非常多來自網路的求救訊息,各式各樣的深淵創傷向作家揭露,而作家也確實曾經試圖伸手去救援其中一些人,給予無論是金錢或是情緒上的支持,而後,作家殘酷地體認到了—絕大多數的人,他救不起來。「我像是在三途川堆石頭塔一樣,看著這座塔要完成了,接著就坍塌了。」
我想起《魔法公主》裡,黑帽子大人說過最殘酷也最誠實的一句話:「自己的命,只有自己能救。」因為多數的求救訊息都是將自身的創傷投射在作家的文字之上,某種程度上,活著的作家以文字成為了創傷者的「明鏡」,越是誠實赤裸的文字,越容易成為被投射的著力點,但,明鏡之相,終究是顛倒的。
創傷者必須要體認,只有自己說出故事,才能掌握改變故事與癒合的權力。伸出援手的人也必須體認,自己不是他唯一的支持,否則,善意就會通往地獄。
在當代網路世界,作家對讀者的「權力與責任」都被高度擴張了,當紅作家幾乎不可能躲起來不與讀者互動,而互動的過程中,被陌生人哀哀求助,往往會給軟心腸的人一種錯覺:自己還能安然在這邊寫點文字,或許是因為自己已修練得道,是能在深淵之上的神?我是否有責任垂下那條救命之索?

然後,宋尚緯經過沉澱之後,寫出善意必須被有所節制:「有時候慈悲心是蜘蛛絲,但是我們分不清楚自己究竟是垂絲的神佛,還是抓蛛絲的惡鬼。我們多以為自己是神佛,但多數時候,我們與惡鬼之間的分別只在於站的位置不同。我們以為自己的行為是善舉,但其實我們在推壞一堵一堵的牆。後來我才理解,有的時候站在旁邊看,也是一種善意,但這種善意要成立的要素實在太多,我個人還是認為與其之後後悔沒有伸出援手,不如伸出援手之後再來後悔。」
作家說他花了很長時間才將自己與他人切割開來,不僅談健康的界線,更談在界線成立前的種種思索,思索以後,原來是看不過眼就會發聲、就會就出手救援的宋尚緯,越來越採取後退、聆聽的姿態來應對求救的訊息。而這樣自覺節制的後退,在任何時代都是無上珍貴的。因為脆弱的讀者是最容易被操控的人—而成功的意見領袖,很難拒絕權力的引誘—話語如風,卻是無形且至上的權力。多少作者無法拒絕這樣的誘惑—畢竟手握權力的創作者完全有機會任意掠奪那些迷人的故事,甚至,掠奪更多,比如說身體的權力。
這本書幾無文采,卻處處光彩流動,作家從漫畫與戲劇的文本來談善與惡,又透過自己的無能與失敗,談文學的價值究竟是什麼?年少時,談到文學成就往往會有某種幻覺,以為好的文學能夠救世,說出正確的話語的詩人,就帶來春天、能夠號召群眾走上正確的路:「以前的我認為文字有極大的力量,認為文字就等同於思想,有極大的能量在。近年有些反思,大家都在說文學是民眾的武器,但事實上並不是,文學握在民眾的手中其實是貧弱的,當大家面對的是不平等的暴力,文學是無用的,文學沒有立即性拯救他人的用處。文學被當權者掌握是極有殺傷力的思想武器,但在此之前,我們應該了解的是,文學是如何去貼近常人……我認為文學其實是一個契機,令我們能夠理解自己過往曾做過的錯事……給我們一個使自己從過往的傷害解脫的可能。」文學之大用似乎本來就是KOL任務—帶領群眾思考與行動。但這也恰恰是文學之無用—宋尚緯在這本書中,對自己的審查更為嚴苛了—自己何德何能,有何等力量號召群眾?比起過往作品,宋尚緯在這一本書中,更加強調文字「安放傷口」的分量,毅然決然將癒合的權力和責任,歸還給未知的讀者。
有才德的人,沉迷於自身的美德之中,並擅自干預他人,這樣的人我稱之為鄉愿者,為了自己的感覺想當好人,乃是最大的罪惡。而知曉並且謹守界線,則是做一個好作家的開始。自省、後退,是否為當代作家尚待磨練的復古之倫理?
宋尚緯的後退,我認為是對於鄉愿的明確拒絕,拒絕鄉愿與自溺,這姿態既是自重重人,也是潔淨的偈了—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
最後想逆風的說:這本書,或許和我們過往認識的作家人設有所不同。過往宋尚緯是網路筆戰無役不與的熱血作家,看不過眼的事就說出來,但,無視於所謂「賣錢的」人設、忠於自我、誠懇順服蛻變,這一點也很宋尚緯。之前的多部作品雖然文風犀利,但我個人更加欣賞敢於打掉重練的真心話。誠摯推薦喜歡或不喜歡宋尚緯的讀者,都可以讀一讀這本《我還在這裡》。
作者簡介
1984年生,台灣師範大學美術系畢業。曾獲楊牧詩獎、府城文學獎新詩獎等。著有散文集《玩物誌》;詩集《如蜜帖》、《如廁帖》、《妖獸》、《失語獸》、《負子獸》、《雞卵糕仔雲》等八冊;主編詩選《媽媽+1》;藝術文集《藝術家的一日廚房》;插畫作品有《暗夜的螃蟹》、《虎姑婆》等。
延伸閱讀
- 諶淑婷/為何家長在現實世界過度保護孩子,卻在虛擬世界放任孩子?──讀《失控的焦慮世代》
- 個人即群體──革命家與劇場工作者的靈魂探問
- 【OKAPI編輯室選讀】為何資訊科技業高層不讓孩子使用智慧型手機?──《拯救手機腦》
- 諶淑婷/看似擁有一切的孩子,其實承受著永無休止的壓力──讀《懸崖邊的學霸》
- 羅怡君/只用道歉處理霸凌,是大人想逃跑的表現──讀《我的孩子是霸凌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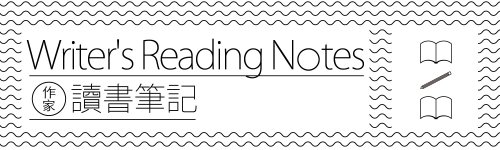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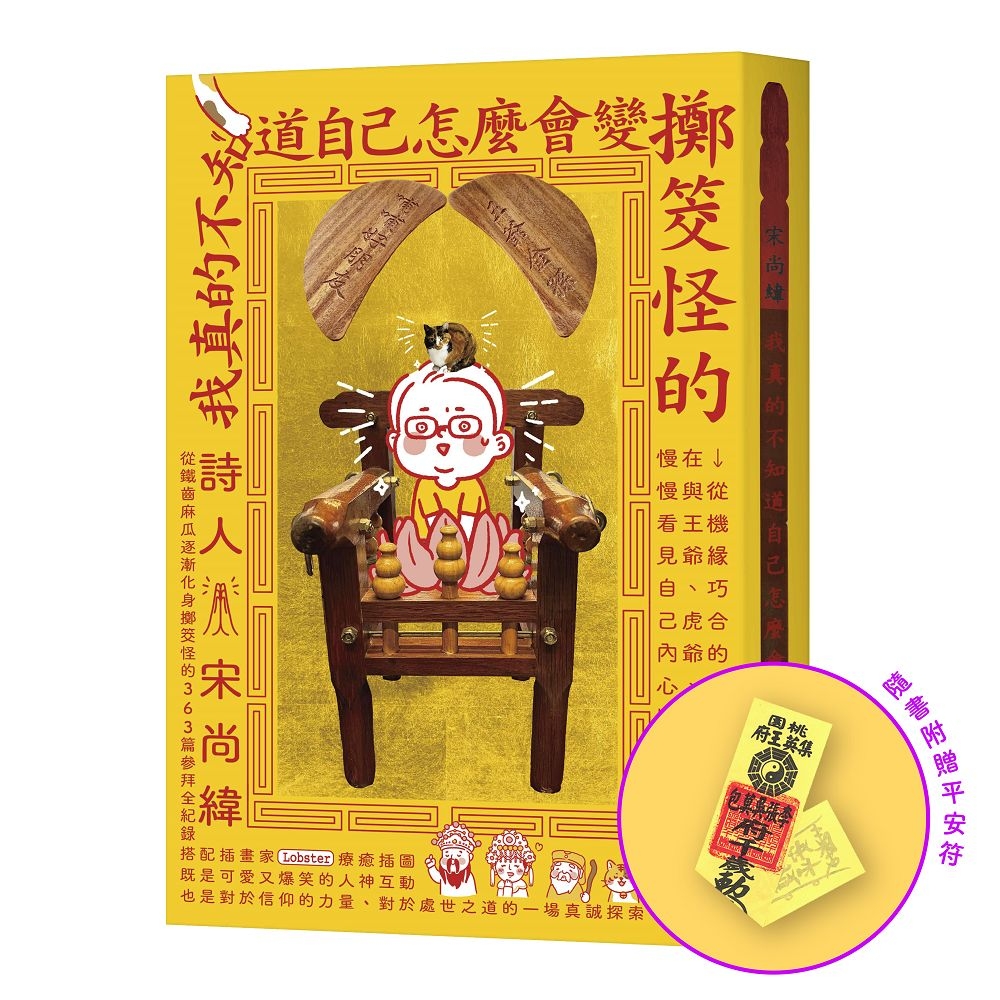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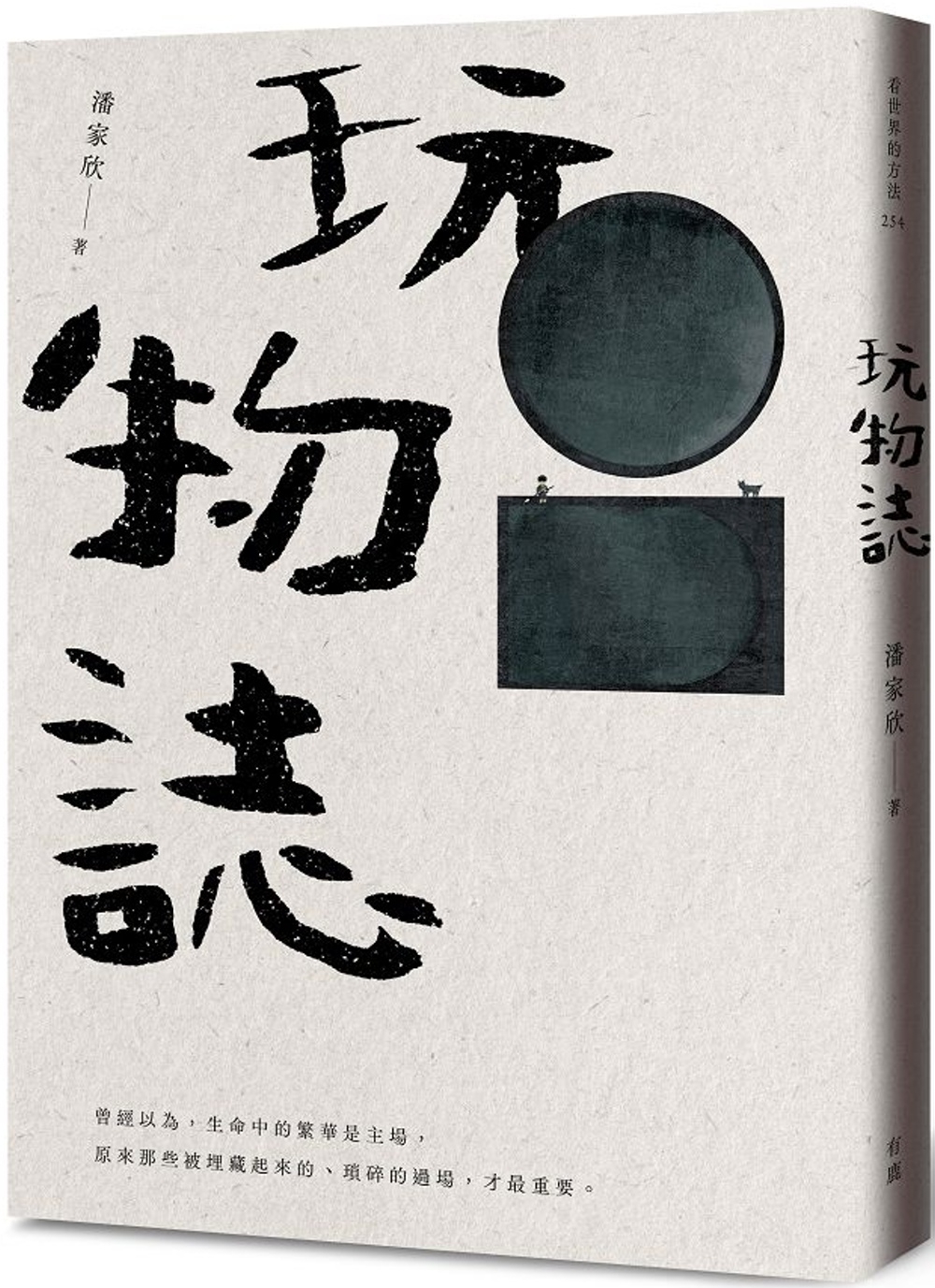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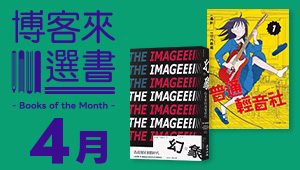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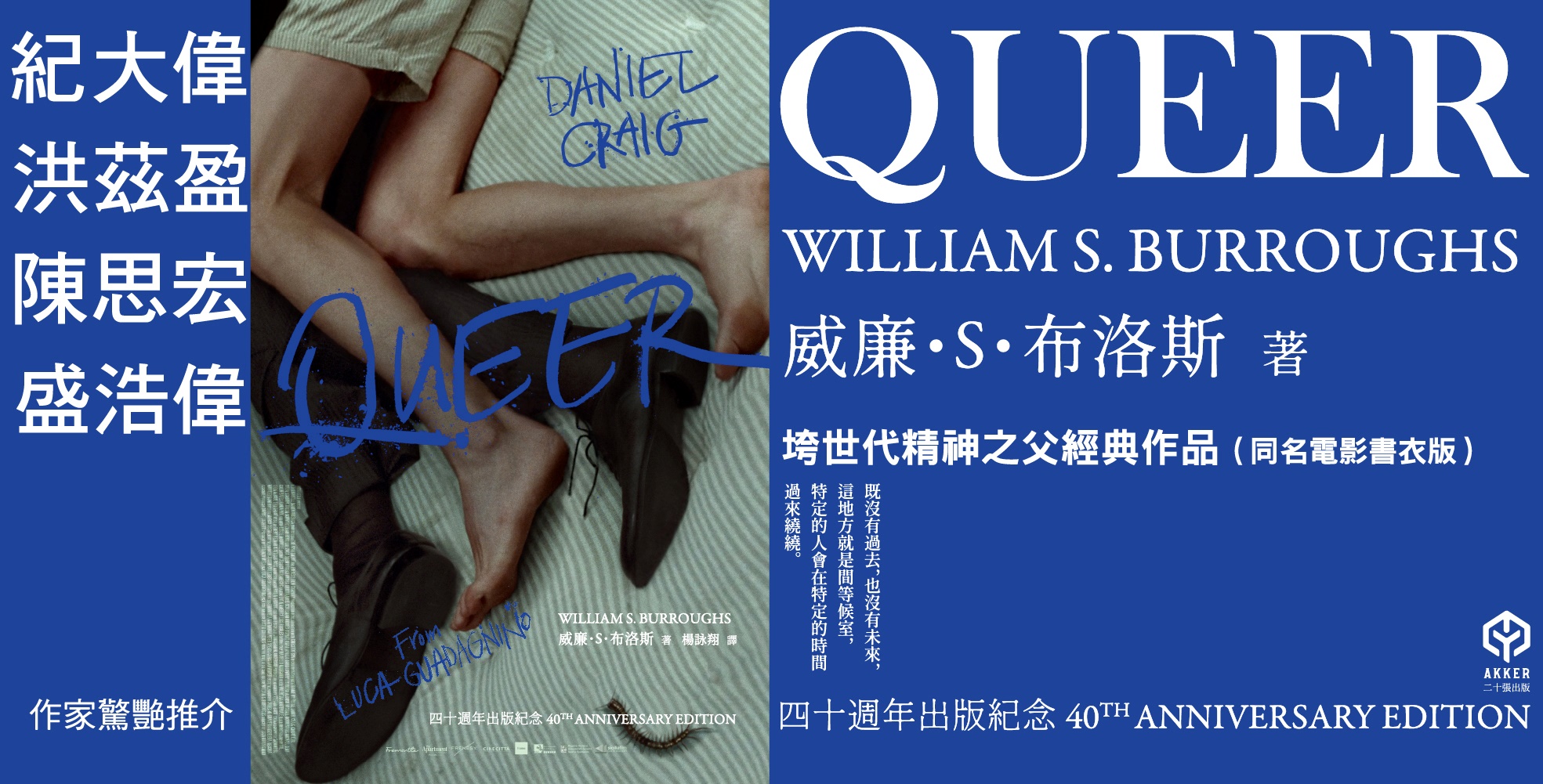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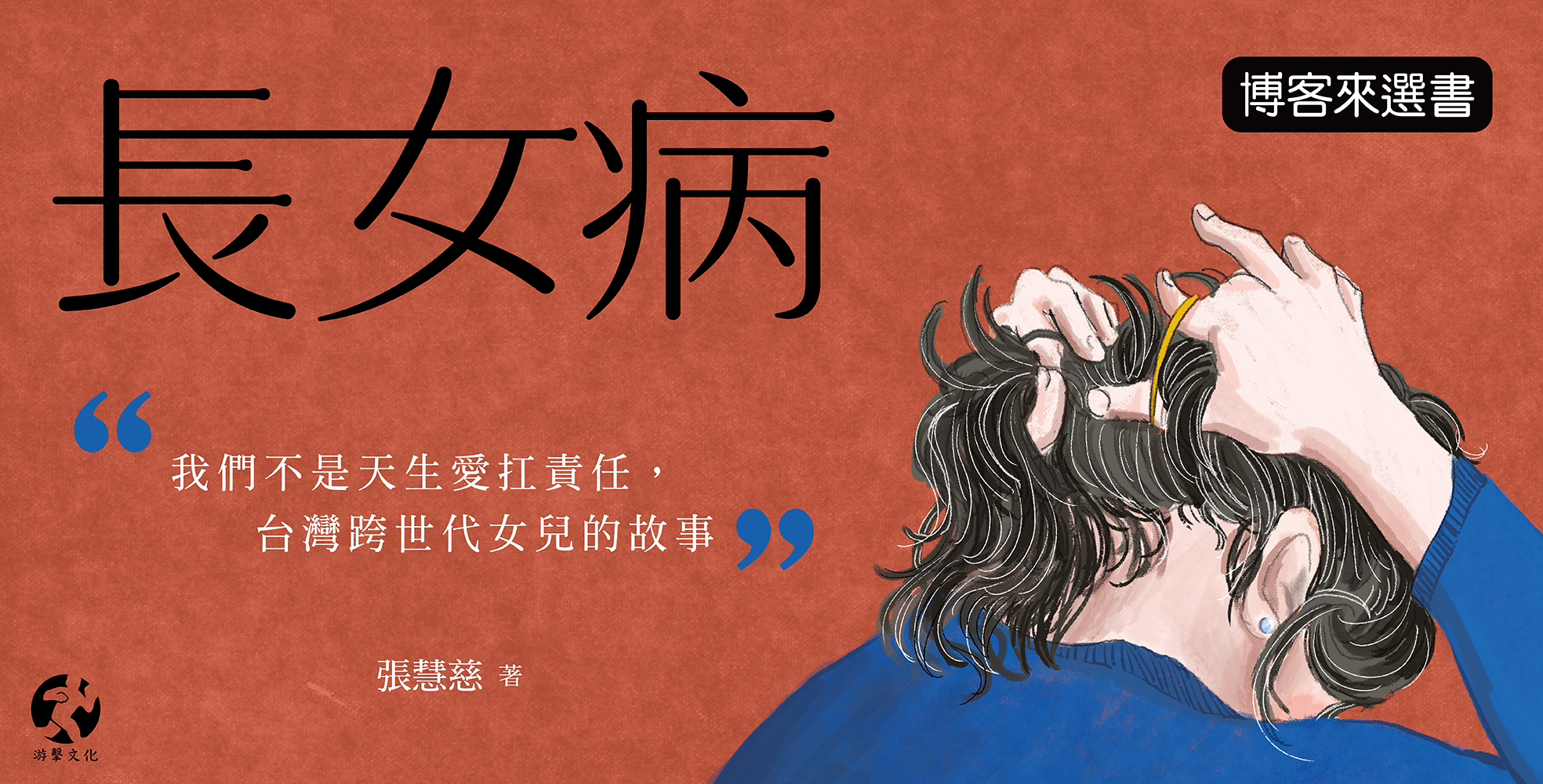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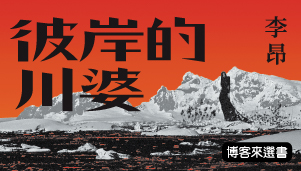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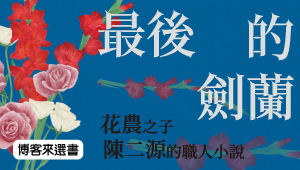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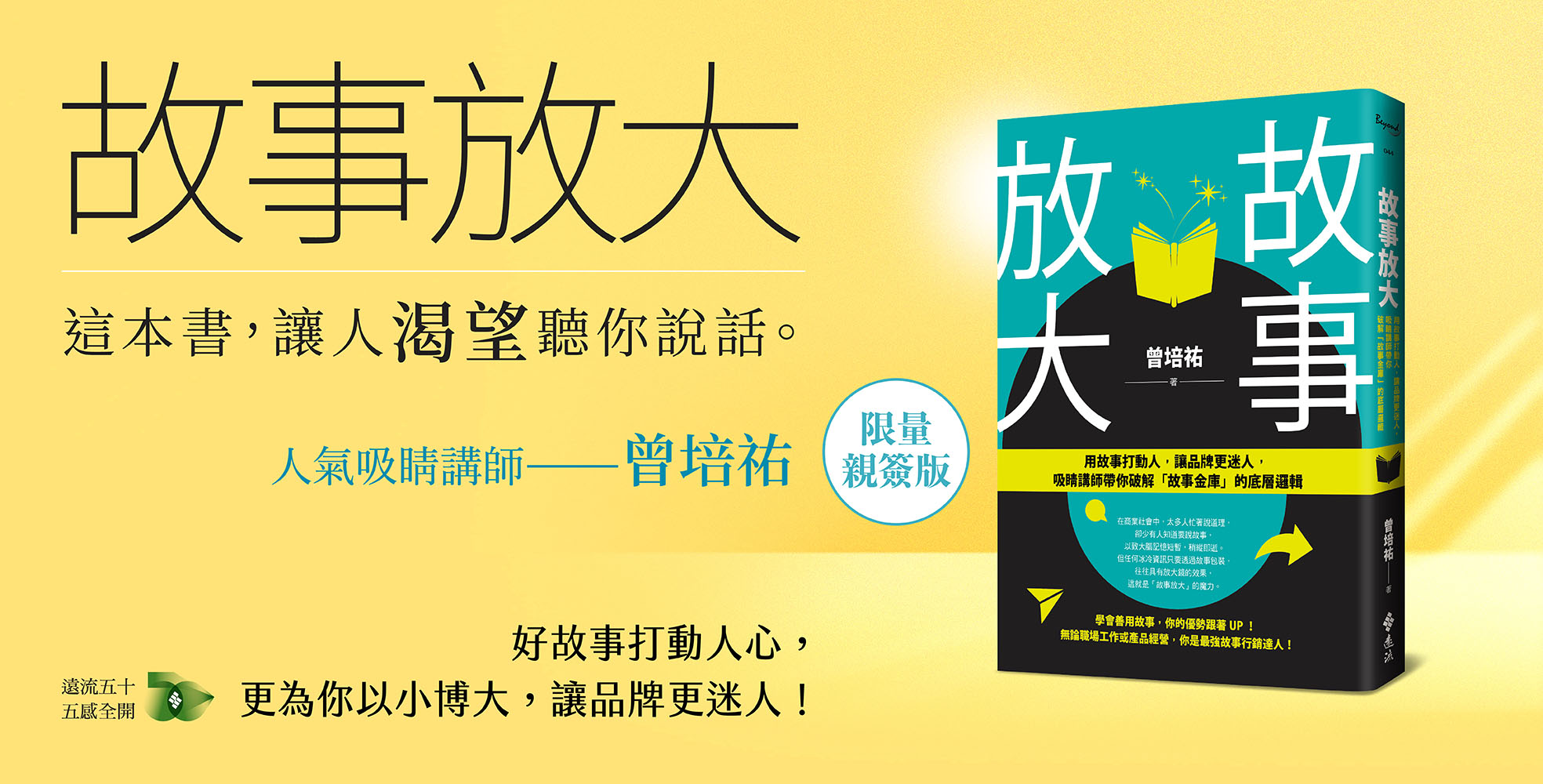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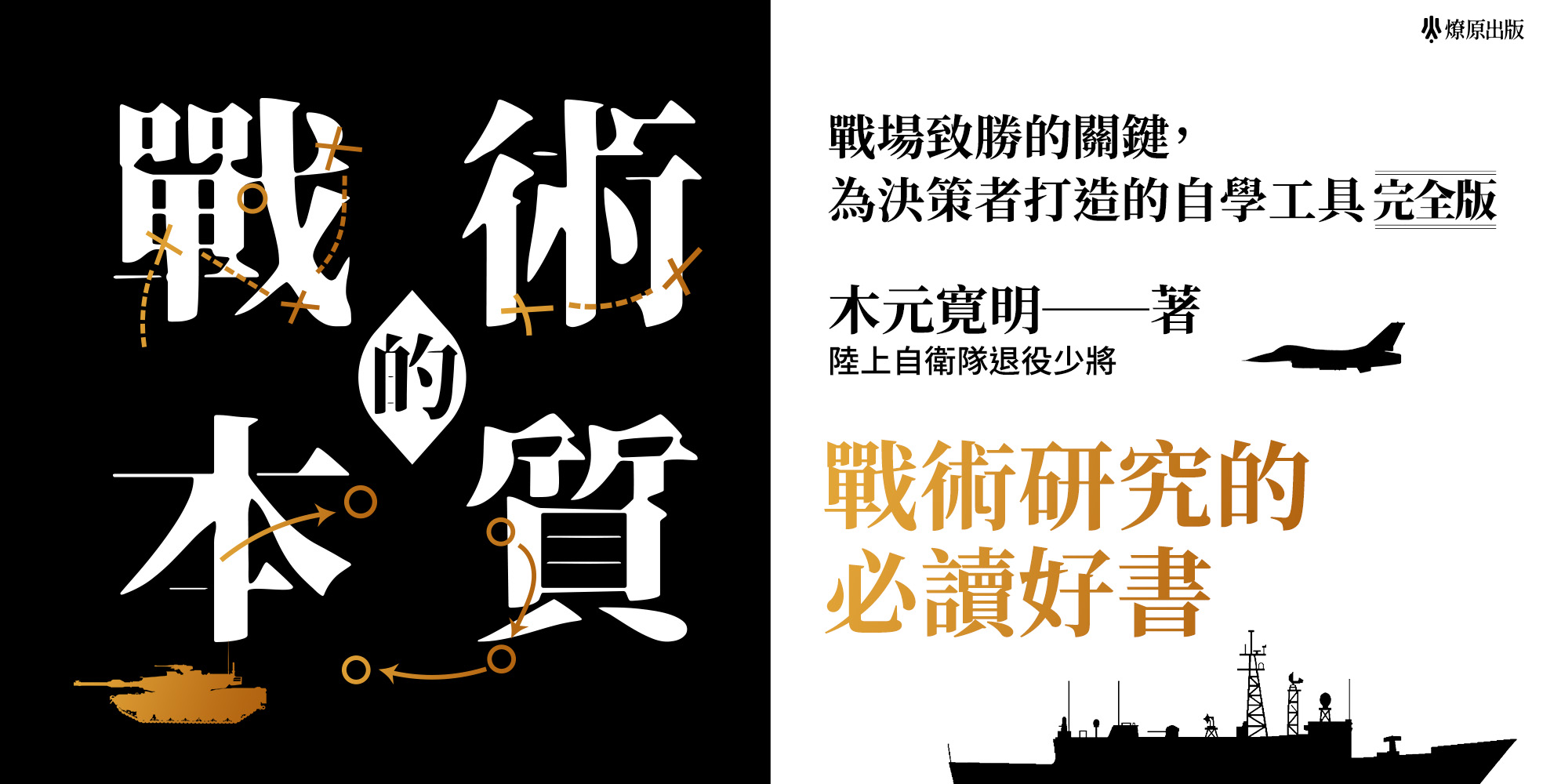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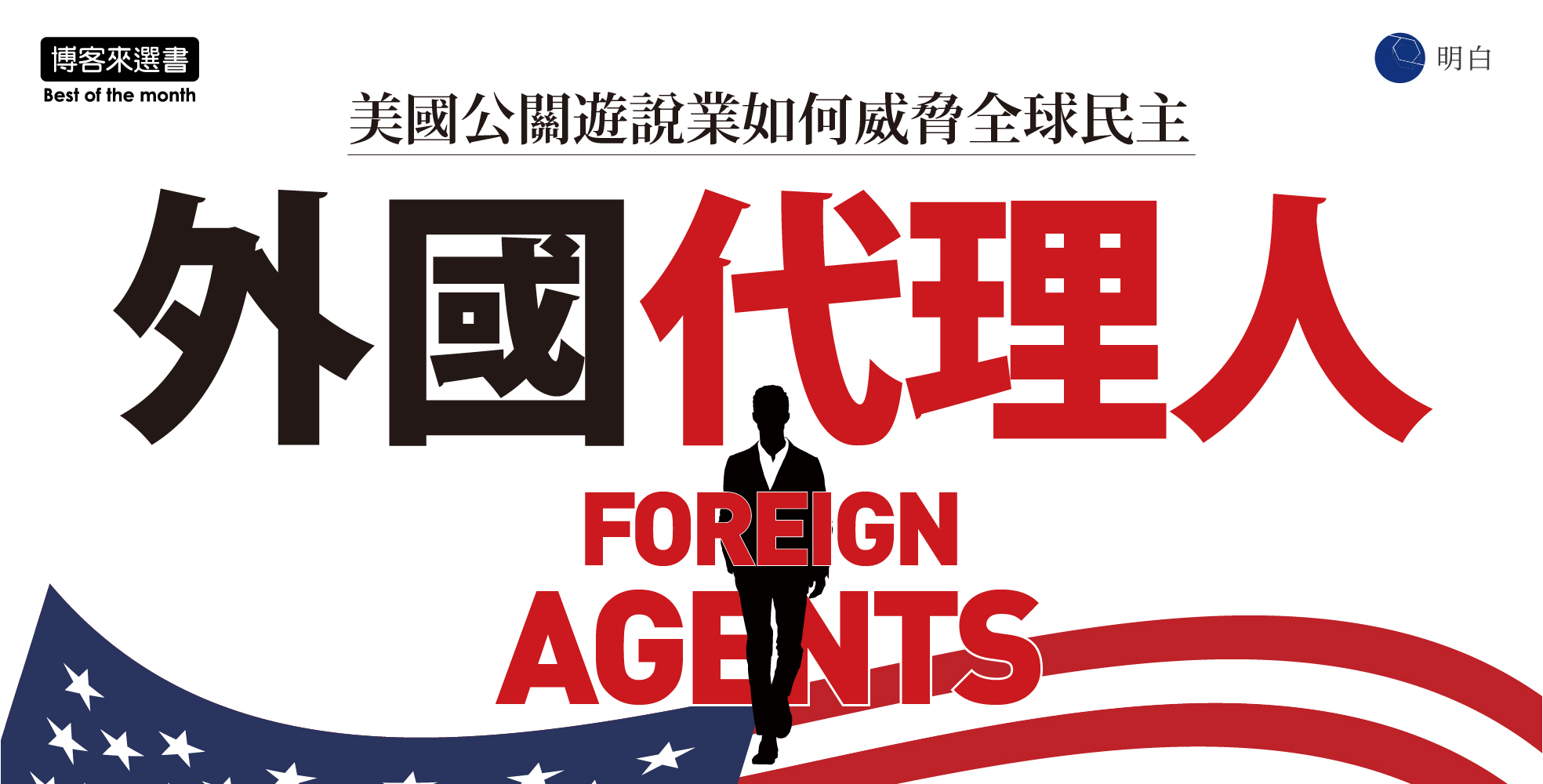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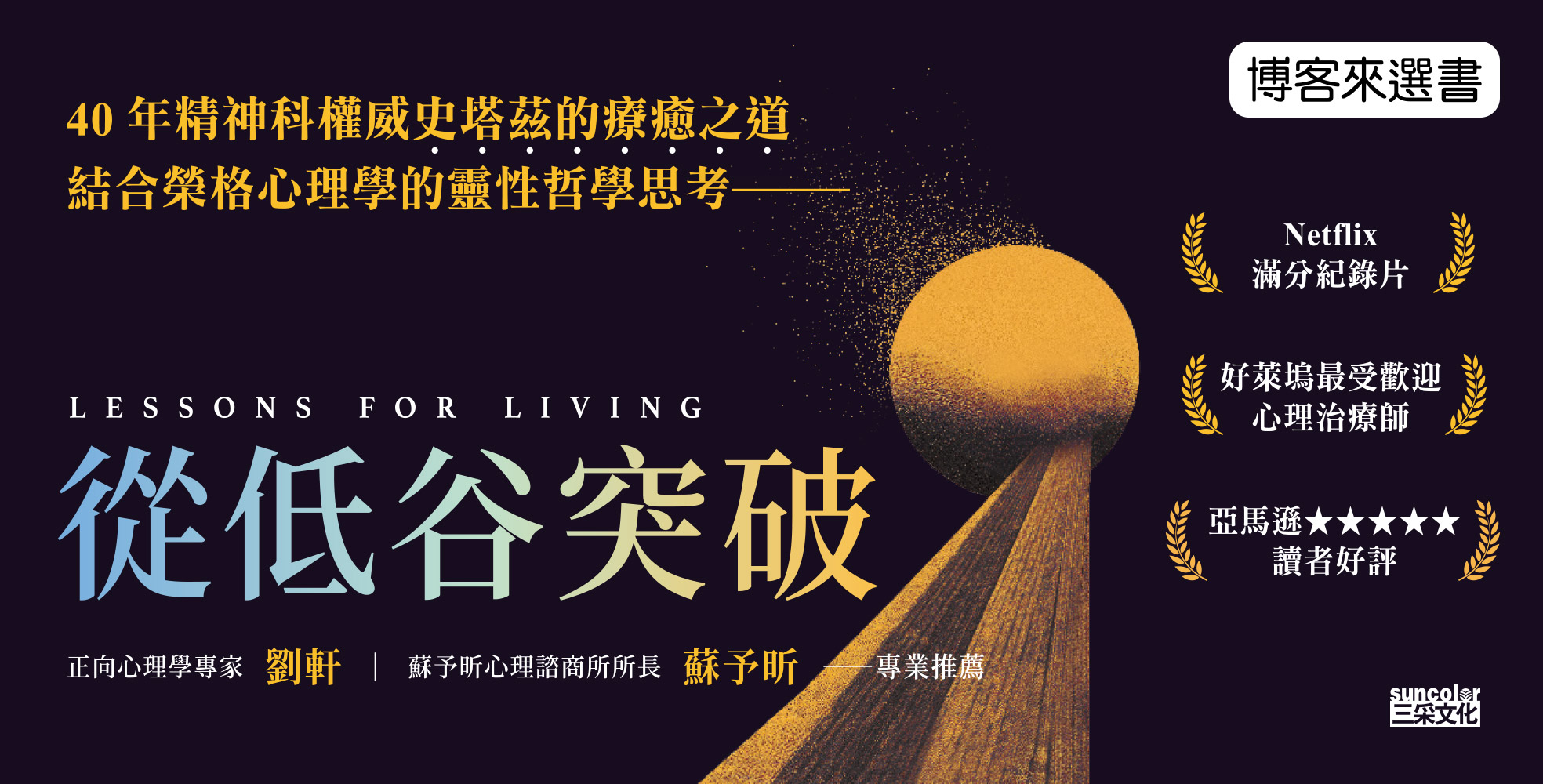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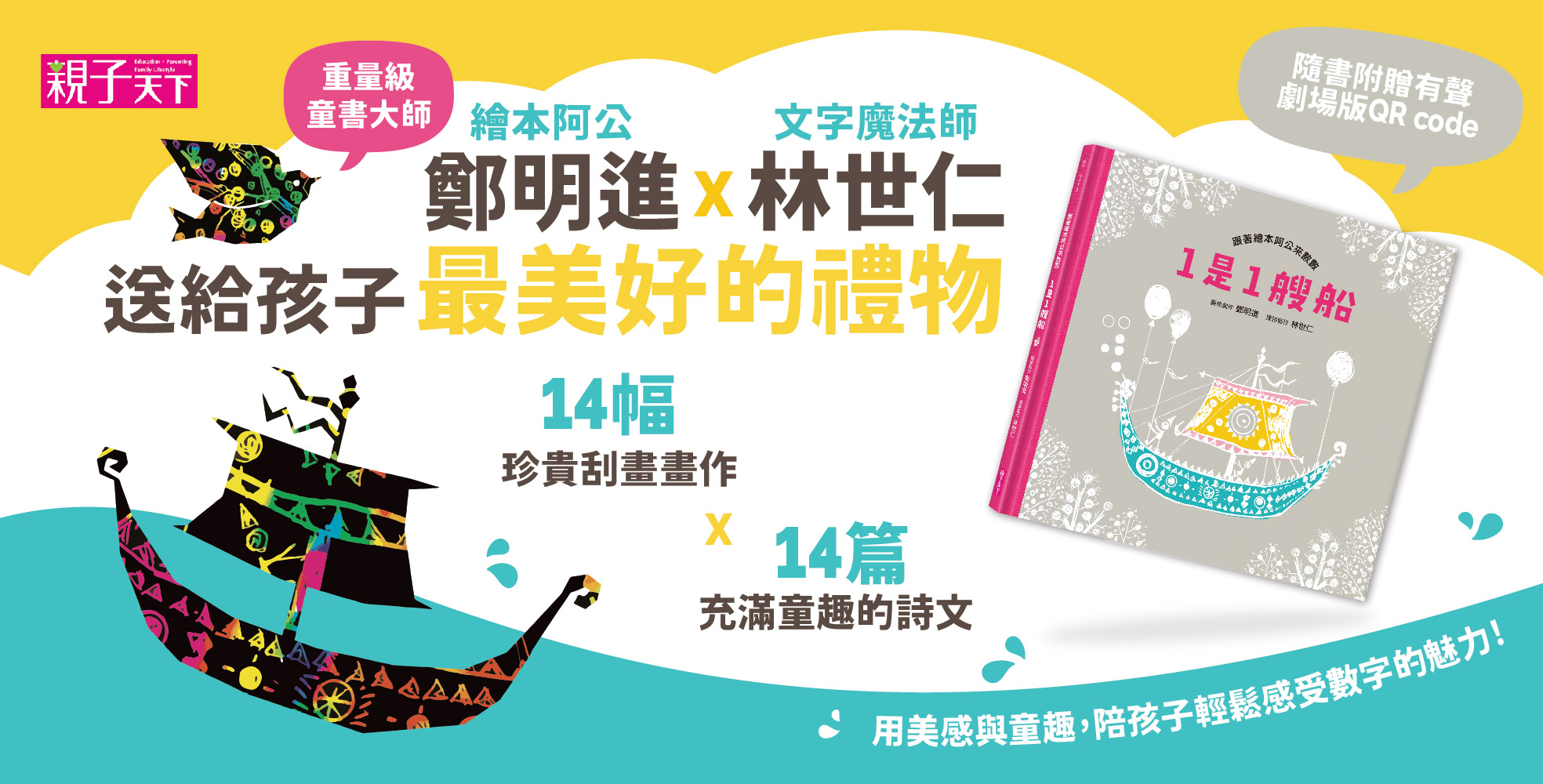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