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黃郁晴(左)、翁稷安(右)談最新的作品與創作背後的故事。(攝影:楊詠裕|場地協力:暗.敞 clair-obscur)
我們如何記憶一個人,或是一段歷史?有時,是透過一個小小的物品追溯而上;有時,則是在劇場的燈光之下,讓故事透過演員的台詞去轉生、去辯論、去映照過往生命的創傷。
通過《革命家的生活寶物》這本書,讀者以史明生命中的種種物件作為錨點,草蛇灰線地追尋革命家在時代中的種種思索;而《藝術之子》則藉由戲劇表演,探究劇場工作環境中的權力共犯結構、創傷與療癒的艱難議題。對於這兩本書的訪談,分別觸及了「物品」與「戲劇」,如何承載歷史記憶與個人生命經驗的重量?在找尋過去的過程中,映照今日的課題,轉化為對於未來的省思。
對 談 人

Q1:以四十件生活小物來開箱史明的人生,設定非常鮮活有趣,請問寫書的靈感怎麼來的?為何會決定從「小物」來寫?
翁稷安(以下簡稱翁):雖然掛名作者,但這本書對我來說,一直是本集體創作,是史明基金會的藍士博、逗點文創的陳夏民、編輯沈如瑩,再加上阿諾和我,大夥一起合作一本打破同溫層,讓更多人認識史明的書。為了讓一般讀者對歐吉桑的人生經產生共鳴和連結,士博和夏民在一開始就意識到史明留下的大量物品是不錯的切入,我則被他們的提議吸引,一來以「物」出發,呼應著史學研究近期的潮流;二來是我自己也始終對「物」有著深深的迷戀,很多寫作的想法也都圍繞在「物」上面,但因為各種原因(=藉口)始終拖延,所以雙方可以說是一拍即合。寫作時,我參考了松浦彌太郎的《日日100》、高橋大輔的《救命工具》、張亦絢的《感情百物》,以及陳柔縉老師的著作,快要完成時讀到了《她物誌》。這些作品成為了我的「顧問團」,給予很多支持。所以這本書雖然沒有靈光一閃的瞬間,卻有著集思廣益的共識與沈澱。
「小物」的魅力,除了能串起不同世代的生活經驗,也體現著人的有限與無限。人生在世,使用或擁有各種物品,這些物品都將留下使用者一小部分的生命故事,傳遞給日後的人們,這不只是趣味,也是一種浪漫,說到底,這也正是「歷史」肩負的任務。
Q2:寫這本書時最卡關的地方是哪裡?
翁:卡關的地方在於述說故事。史明的人生實在太戲劇化了,困難點在於怎麼樣挖掘物品的故事,描述背後有關的歷史,並且運用這些故事,串聯起史明和讀者的生活經驗。
Q3:全書裡你最喜歡的史明小物是哪一件?
翁:我最喜歡唱盤,我在學生時期瘋狂收集CD,也是用各種方法湊錢,所以對史明收集唱盤的經歷很容易共鳴。尤其看到他八十多歲時,還能對年輕時候的收藏如數家珍,那是真正樂迷才能了解的愛。

Q4:有沒有到最後沒有收進書裡,覺得有點遺憾的小物?
翁:書出版之後,遇到很多接觸過史明的前輩或朋友,每個人都補充了很多書中沒提到的小物。大部分其實都曾考慮過,但要成為故事,還需要再醞釀吧。我自己最遺憾的是已經有腹稿的〈結紮〉,但考量內容有點薄弱,嚴格說來不算小物,就放棄了。
Q5:你覺得出版這本書的時代意義是什麼?
翁:認識史明這樣一位主張臺灣獨立的思想者和行動者,不再於歌頌他的偉大,而是意識到他的平凡。一位和你我一樣的凡人,為了這片土地的未來,堅持做他覺得正確的事。他做得到,你和我也一樣可以。

Q6:請問你覺得史明歐吉桑本人看到本書,他會說什麼?
翁:聽說歐吉桑很不喜歡談自己,所以應該會把我們罵一頓(笑)。在我的幻想裡,我們會和他認真說明為何從小物出發,他可能由此為起點,和我們講述馬克思的歷史解釋之類的,無論如何,我想我會很享受那樣的對話。
Q7:如果只能用一句話來向年輕人介紹這本書,請問會用什麼話來描述?
翁:這本書的四十個小物,紀錄了一個凡人,努力成為好人,希望這片土地能有更好的未來,這也是生為臺灣人,每個人該有的自我期許:一起成為更好的人,一起護臺灣。
過去、現在與未來的凝視之問—訪談《藝術之子》作者黃郁晴
Q1:這部劇本含有劇中劇的設定,請問劇中劇為什麼是《海鷗》?契訶夫《海鷗》原劇中的什麼精神或元素,是妳想在《藝術之子》中闡釋或質疑的?
黃郁晴(以下簡稱黃):俄羅斯劇作家契訶夫的作品是戲劇系的必讀必演經典,因此本來就在我「學院血液」中自然地流淌著。而《藝術之子》原先是我在國家兩廳院的駐館創作,近三年的歷程當中要先經過兩次「開放工作室」的展覽與試演。
在第一年籌備期間,當時我與團隊聚焦的不完全是權勢性侵,還包括女性藝術家的生存狀態,某天我腦中突然閃過《海鷗》最後一幕妮娜的獨白,那是戲劇系的人幾乎都會背的一段:「我不知道雙手要往哪兒擺,不知道怎樣在舞台上站,不能控制自己的聲音。你不了解這種情況,當你意識到自己演得實在糟透了,那是怎樣一種感覺。」
此刻的妮娜描述的並非只是演員在舞台上的怯場經驗,更是她從鄉間到大城市闖蕩後徹底被擊潰的無力感。那時的我將這段台詞印在展場最深處的秘密房間入口,我所連結的是女性在日常生活中動輒得咎的處境,像是在扮演一個永遠演得不夠好的角色。
直到後來進入了劇本創作與實際排練,我漸漸用一種完全不同的目光去看原先《海鷗》劇中的三角關係——知名資深女演員阿爾卡吉娜、當紅作家特里果林本是一對,後來特里果林與一心想奉獻給表演的少女妮娜相戀,但作家與成功女演員也沒有斷了關係,妮娜的身心卻幾乎給毀滅了——通常分析不外乎針對他們三者的年齡落差、藝術成就去談,然而當我以權力及性別的角度重新看待之後,這個故事變得截然不同。
在#MeToo運動的脈絡中我們一再被提醒的是:熟人性暴力、情感關係的剝削、被對方以PUA方式操控……這樣的受害狀態往往難以言說,一段「羅曼史」被摘掉「愛情」濾鏡後極可能充滿赤裸裸的控制與界線的破壞。妮娜,真的只是「愛上一個不該愛的人」如此而已嗎?
《海鷗》結尾最動人的是,妮娜真正體會到必須為自己而演,或許在世俗定義中她失敗了,但那也是她最逼近藝術的一刻。至此我才發現當時想到契訶夫的直覺是為什麼:「我由衷希望妮娜不再只是被視為一個不得志的『女演員』,她就是一位藝術家,她為自己心中的藝術奮力向前。」

Q2:《藝術之子》劇場中,討論的不只有加害人與被害人,更大篇幅在談權勢性侵的「在場者」、「旁觀者」,也就是明知道事件發生卻眼睜睜在一邊觀看默許之人,妳讓其中一名旁觀者在多年後回來贖罪,關於這個安排,作者想說什麼?
黃:這應該是劇場與戲劇最有趣的地方,當我們看到角色實際在台上互動,觀眾也跟著不斷轉換視角以及立場,畢竟現實生活中從來都沒有單一觀點這一回事。
在這裡我想挑戰的應該就是題目中的這個「明知道」——我們真正知道什麼?多年前曾有一樁校園性侵事件影響我很深,有句被廣為流傳的話是這麼說的:「不要輕易踩上受害者的位置。」
但我還想更進一步指出:從事件發生當下,直到意識到自己受害,這過程絕不輕易。如果連受害者都不清楚發生了什麼事,需要花數年時間釐清;那麼其他在場的旁觀者真的是「明知道」有事發生卻「選擇」默不作聲嗎?他們是不是也困在當時自身的某種狀態裡呢?
指出這點並不是要為袖手旁觀的人說話,而是想要把性暴力現場每個人的「孤島」狀態顯露出來,如果能更理解性暴力的真實樣貌,才有機會在事件衝擊時為自己或他人及時醒覺。

Q3:《藝術之子》在劇中有一重雙關,作為加害人的「藝術之子」,以及之後真正出生的「藝術之子」,妳想談談這個雙關嗎?對靜芳/淑芬而言,藝術之子又是什麼呢?
黃:之所以設計「藝術之子」這個稱號的轉換,意義在於,從一個對他者的崇拜,轉移到對自身的關注。這是條受創心靈重建自我的必經之路,也是我的祝福。
Q4:劇中的靜芳影子,不斷在試圖回去彌補、阻止過去的「錯誤」發生。而「複雜性創傷後壓力症候群(CPTSD)」的患者,常見的反應就是解離失憶、大腦會不可控制地反覆重回創傷發生的現場。而在劇中重生活下來的淑芬,則建立了自己的新的人際系統與提供安全依附關係的庇護所,這邊的分離與重生設定是否有參考心理治療的實務理論或書籍呢?可以跟讀者分享嗎?
黃:駐館創作第一年(2021),我在兩廳院主持了一整年的讀書會,因此閱讀了大量文獻,在劇本的附錄都有不藏私地大力推薦!除了《海鷗》外,赫曼的《創傷與復原》是另一部有被直接引用進劇中台詞的心理學重量鉅作。不過並不是讀了這本書才發展相應的劇情,反而是故事全都確定下來之後,翻閱這本書才發現彼此驚人的相似處!這大概只能這麼解讀:我並不是用理論去理解創傷,而是通過自身經驗、他人的真實故事切身體會,才從論述之中獲得了某種驗證以及寬慰吧。

Q5:後記你寫了一封信給書中的角色,探討十二年來的心境轉折,十二年的時光,如果劇本是個孩子也上國中了。請問未來作者對於這上國中的《藝術之子》有什麼期望?會期待《藝術之子》的劇有十二周年的演出嗎?你對做為劇本肉身生產的自己,是否有想說但還沒說完的話?
黃:《藝術之子》原於2023台灣國際藝術節在兩廳院實驗劇場演出,而劇中的時間設定是上、下半場,一共過了十二年;對我個人的某些經歷來說,從記憶走到創作,也是十二年。對現在的我來說,這齣戲真的無法再演了。不只是我自己,或許整個劇組都像是生命中某個部分被耗盡一般。不過我很期待演出化為劇本書之後,有哪位勇者與他的團隊接下再度搬演的挑戰。
熱愛藝術的我們,如何面對藝術中的傷?藝術並不虛無縹緲啊,它是真真切切透過肉身來實踐的,是我們身心靈的一部分不可分割。弔詭的是,我們也只能在藝術中復原,不過不再僅是殿堂中被燈具打亮的藝術,但凡好好下廚、好好走路、好好休息、好好種花,生活中點點滴滴露出的光芒也都正閃耀著。
Q6:關於剛入行的劇場工作者(或任何藝術產業工作者),妳願意分享一句話,來做為安全守則/保命錦囊嗎?
黃:不管對方帶著多少頭銜、經驗、光環與魅力翩翩來到你面前,可以欣賞、可以借鏡,但不要膜拜——既然劇場藝術工作者鑽研的是人性,造神?就免了吧!
個人即群體,兩篇訪談都看似書寫個人私密的生命經驗,背後卻乘載了一代又一代的「人」掙扎發聲的故事;我們如何讓那些被隱藏、被忽視的疼痛不被忘記,又如何從過往的歷史中汲取力量,得以用明晰的眼光探問當代,乃至創造未來?
無論是物品還是劇場,作為載體,創作本身證明了人如何在歷史與現實的夾縫中留下痕跡,促使閱讀的人持續思索:我們如何能讓過去的故事,繼續發聲?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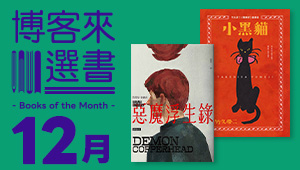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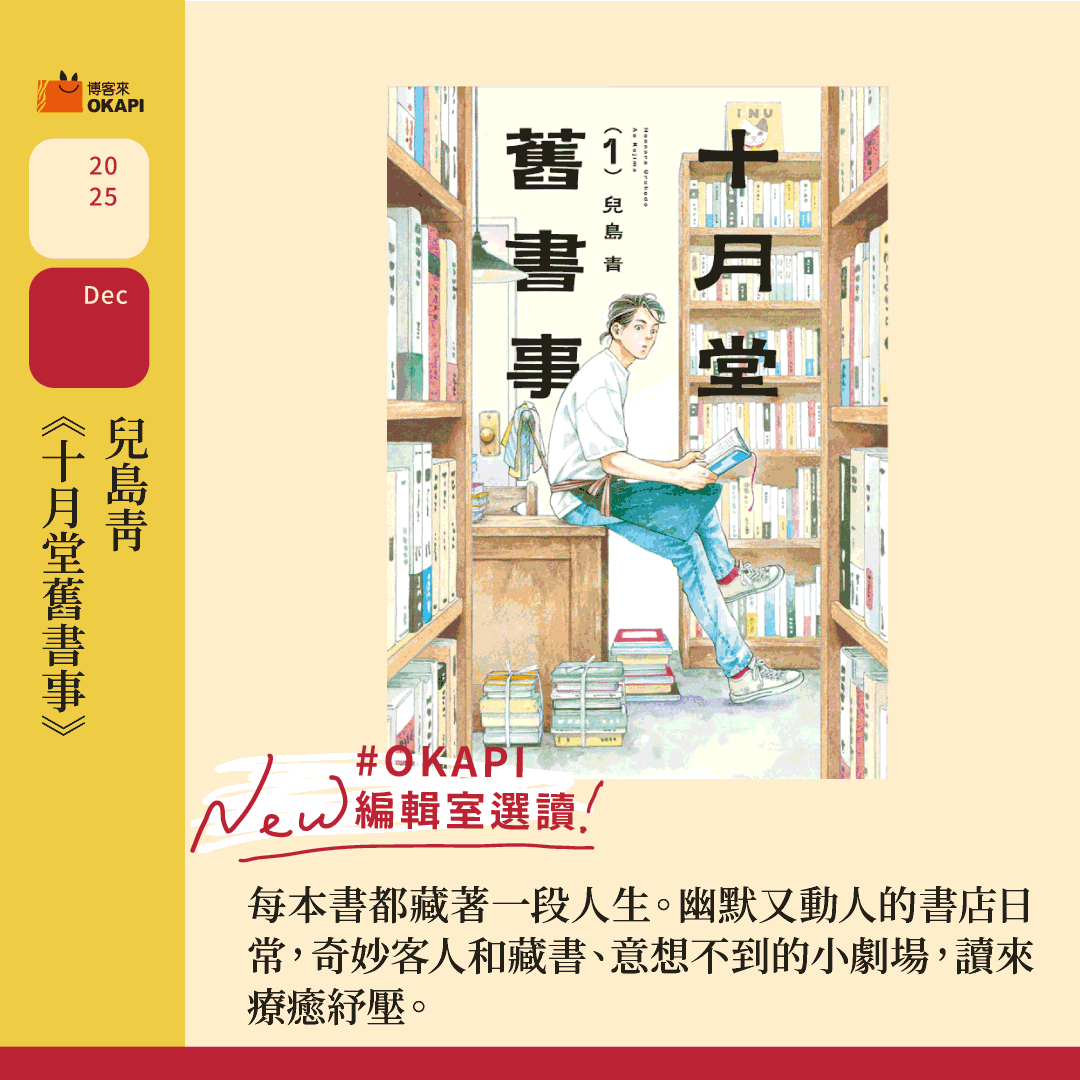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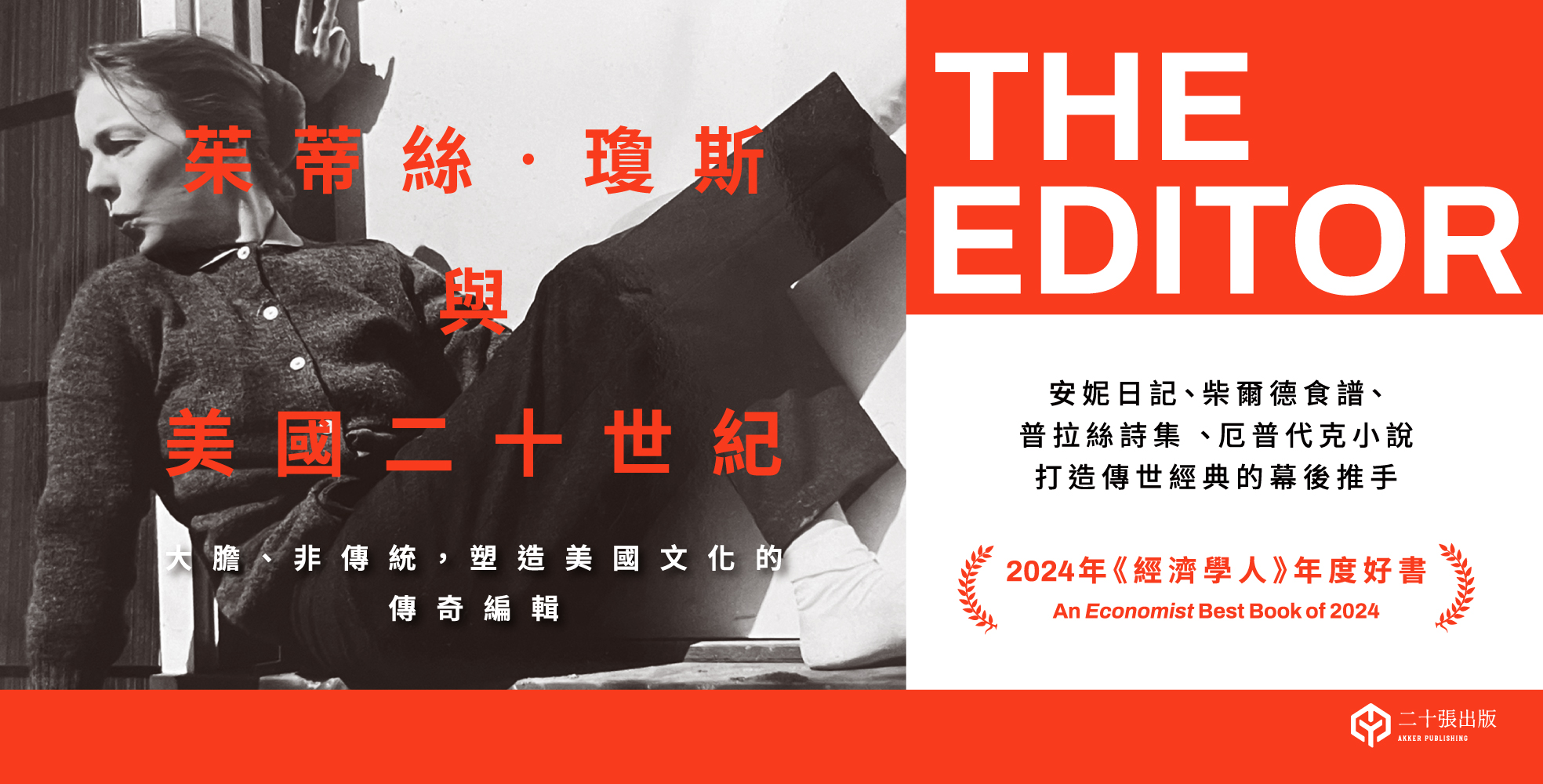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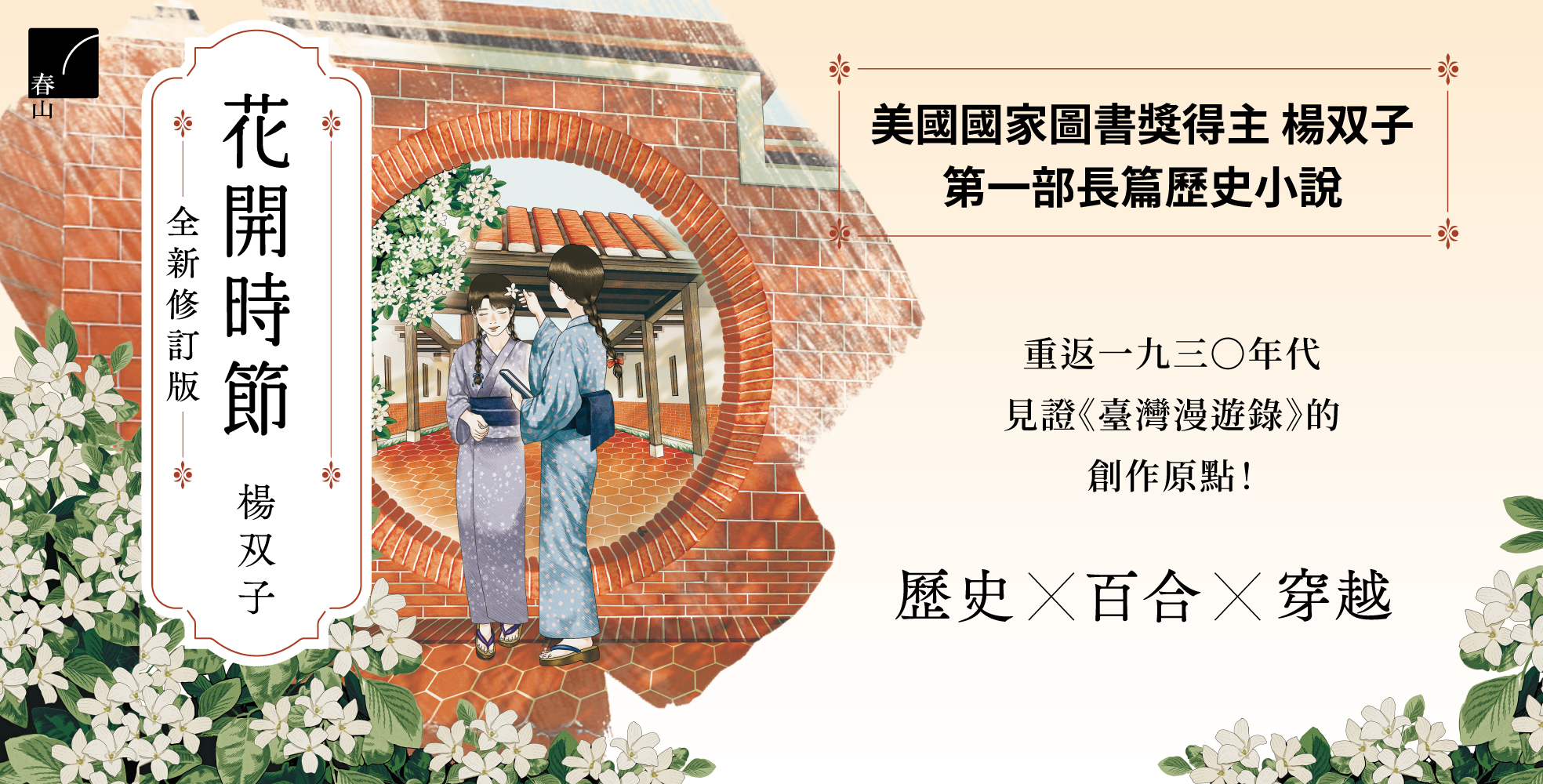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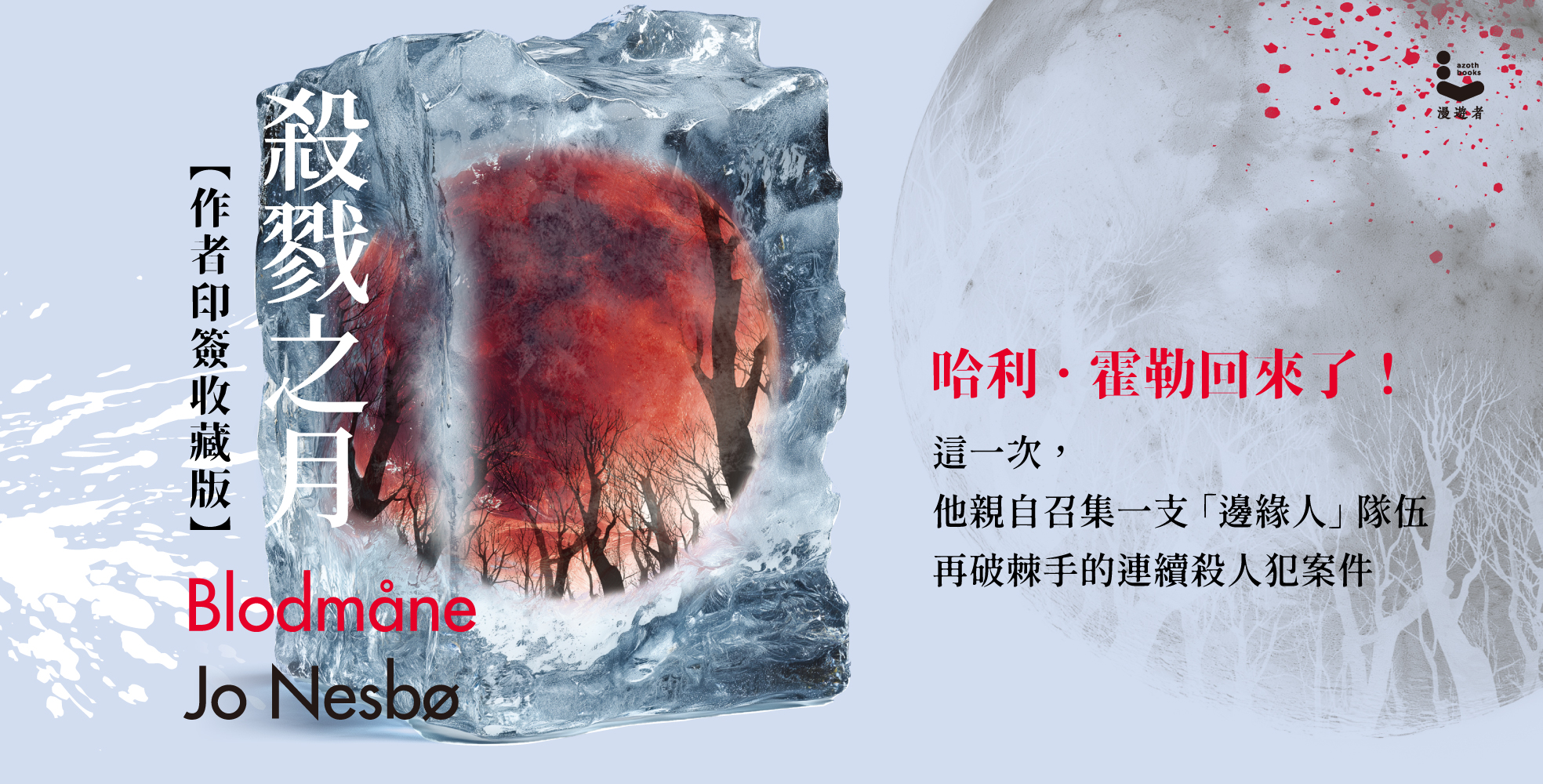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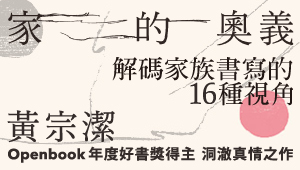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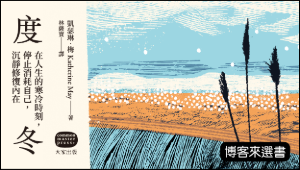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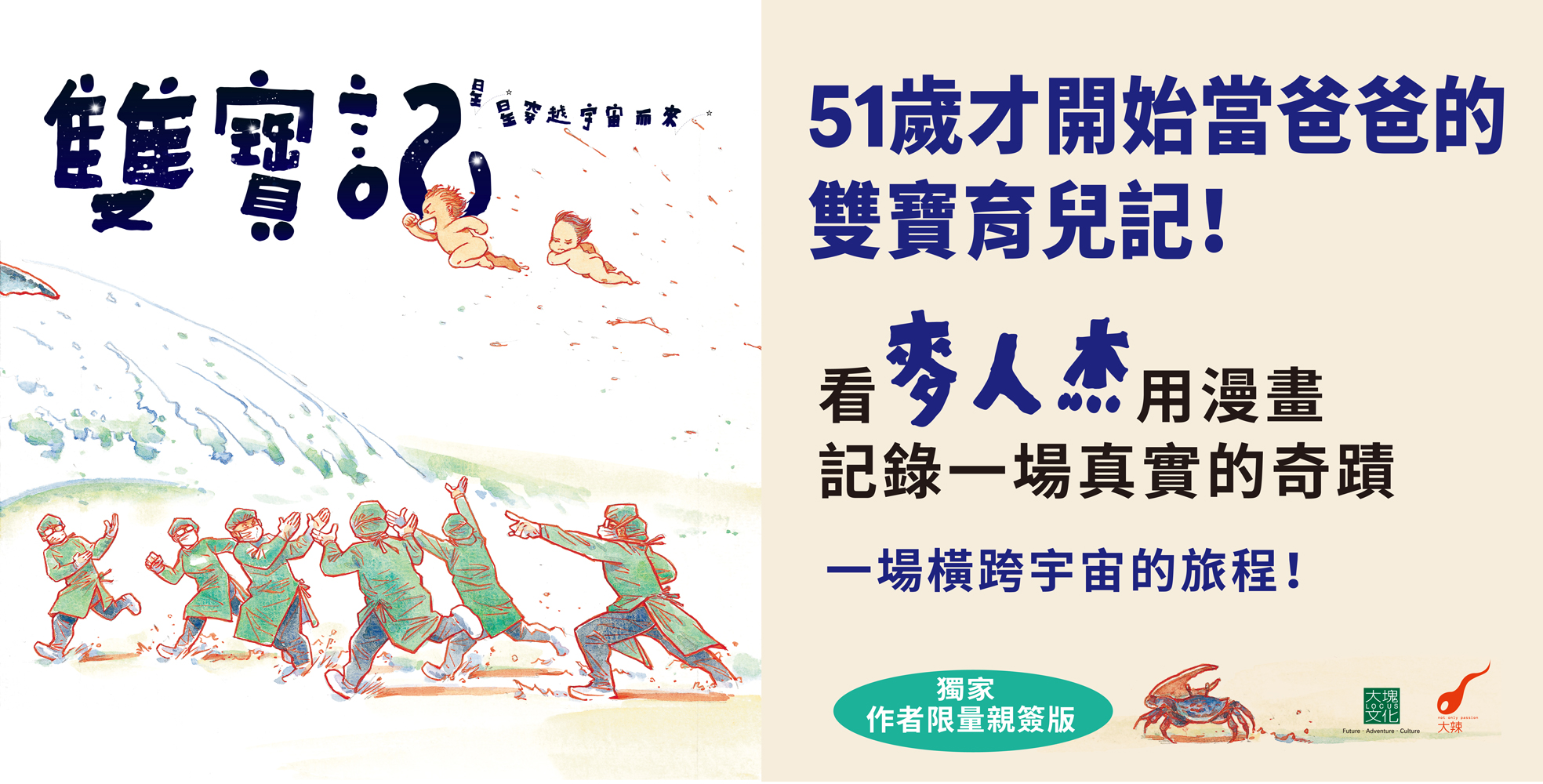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