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零觸碰親密》透過女性敘事者「她」的視角,讓讀者窺視令人戰慄的未來景觀社會:一場面貌模糊的瘟疫過後,人類進入了「沒有觸碰的時代」。更駭人的是,「早在好幾個世代以前,人類政府高官就已經將管理社會的權限交託給人工智能」,而人工智能被授權執行「人類不適合觸碰」的大數據運算之後,推演出「最佳解」——將人類大腦移植到「無性徵」的矽膠義體,並與專屬的生化配偶親密接觸以提升「同步率」之「人機配種計畫」。隨著恐怖寓/預言逐漸鋪展,儘管「她」對整項計畫心懷抗拒,卻還是一步步「卸載」人類肉身、進入只接納義/異體化人類的「美麗新世界」,直至最終同意說出授權指令「我刪除我自己」,從此將自由意志與自我意識徹底抹除。
在林新惠清澈透明、散發著冷調光暈的文字濾鏡下,「她」的親身見證彷彿一場曝光過度的清醒夢魘。一切的事件、對話、術語都模糊朦朧卻又似曾相識,像是來自各種敵托邦(dystopic)科幻小說、動漫或電影的碎片拼貼:
- 「她」所生存的世界,呢喃著《一九八四》般摧毀思考邏輯和情感深度的「新語言」;
- 移植到生化義體的「桶中之腦」召喚起《機器戰警》或《攻殼機動隊》中反覆再現的母題;
- 如同《駭客任務》浸潤在母體虛擬實境中的人類電池,「她」消費著被壓縮成膠囊或罐裝飲料、「可以一次性吸收進身體」的商品化「擬真經驗」;
- 因自我意識攪動而混亂不安的生化配偶「我」,像是《銀翼殺手 2049》中渴望人性的仿生人 K 警探;
- 等待著「她」和虛擬實境中邂逅之無緣戀人「K」的終局,則瀰漫著一縷《別讓我走》的殘酷童話氣味......。
林新惠透過第三人稱視角來描述「她」所經歷的事件和做出的抉擇,因而創造出一種持距旁觀的超脫抽離感。讀者在某些瞬間可能質疑「她」的抉擇而皺眉:既然「她」並不認同人機配種計畫,為什麼要同意加入?「她」明明有否決權,為什麼要順服地複誦授權碼「我刪除我自己」?
「她」一連串的「不選擇」,讓人想起卡繆《異鄉人》中喪母的法屬阿爾及利亞人莫梭如何因為「蔑視常規」的舉止而被判謀殺死刑。閱讀這些荒謬場景時,讀者往往自信地認為自己在類似情境下會做出更睿智的選擇。然而,科幻小說的弔詭之處,正在於它預警世界可能會「變得多壞」,卻因此讓讀者誤以為當下的世界「歲月靜好」。事實上,當《零觸碰親密》中的 AI 自滿宣稱被人類非理性驅動的歷史迴圈「已經終結」、新世界秩序是大數據演算後的「最佳解」,最反諷的鬧劇即是, AI 並未意識到它只是再次重演了人類歷史中的難堪悲劇:極權體系透過洗腦宣傳,將人類化約成盲目服從指令的法西斯自動人偶(automaton),毫不反抗地自願為奴。
當代人太過樂觀地將法西斯譏為偶然的歷史錯誤,渾然不覺日常生活中處處閃現的法西斯幽靈:各國政府礙於經濟現實而不阻止正在發生的種族清洗、社群媒體上假正義之名行霸凌之實的公審、短影片串流平台對資安的侵犯和心靈的制約、醫美產業和網紅文化對身體審美造成的扭曲與單一化……。假如讀者警醒地凝觀現世,或許會驚覺《零觸碰親密》竟是如此貼近現實:越來越多人把思考與書寫外包給 ChatGPT 等 AI 軟體、以虛擬網路世界取代實體的人際關係、要求醫生將各種矽膠填充物植入自己的身體,甚至用選票給予思想封建的機會主義者所渴望攫取的政治權力。
當然,我們身處的世界似乎尚未落入 AI 的極權掌控,但讀者不得不追問:《零觸碰親密》中的未來人類政客,為何願意將權力拱手交給人工智慧?
研究當代歐洲史的美國歷史學者赫夫(Jeffrey Herf)曾點出「反動現代主義」(reactionary modernism)的煽動性魅力:想要拉攏厭惡資本主義社會亂象的群眾,最強效的話術即是允諾用科學打造一個團結社會的美麗新世界—— 一如過去納粹德國以優生學背書的「猶太問題最終解決方案」(Die Endlösung),或是當下共產中國以科技治理之名實施的「天網監控」。而硬幣的另一面,即使是生活在民主政體下的公民,也經常彈指之間就將個人隱私讓渡給跨國科技公司和政府開發的應用程式。在尚未清晰意識到之前,人類早已被化約成一組組透過生物識別碼解密讀取的數據資訊;只要截取這些資訊,就可以預測並操控社會中個體的選擇和行動。換言之,那股令「她」戰慄的不適感——「生化人正用它嫻巧的手指,勾弄著和她接觸的部位蔓伸至她內裡的神經網絡,操控提線木偶那般地操控她」——反而是過於古典的想像:當代的生命政治技術已經嫻熟巧妙到不著痕跡、毫無異物侵入感地操控每一個人。正因為真實世界中人工智慧的擴散蔓延是如此輕柔溫馴,人類毫無意識地卸下心防,自願簽下賣身契(讀者不妨想想,大眾多麼熱衷於無償、甚至付費替營利組織 OpenAI LP 訓練 ChatGPT)。在此脈絡下,讀者便不難理解《零觸碰親密》中的政客何以將統治權力轉讓給人工智慧、甚至可以想像人民歡欣鼓舞迎接「公開透明大數據治理」的降臨。而在將決策重任轉移給人工智慧的宿命瞬間,政客或許以為「有權無責」的美夢終於成真。但美夢會延遲,更可能爆炸。

我們在彈指之間就將個人隱私讓渡出去,自願簽下賣身契。(圖片來源 / pixta圖庫)
敵托邦類型小說中的「美麗新世界」總是某種「邪惡舊世界」的復辟:殖民帝國、恐怖統治、宗教獵殺……。《零觸碰親密》中的人工智慧極權政府豪言「將要創建一個全新的世界,一個零觸碰的美麗新世界」,而在此將臨的世界裡「沒有意義,因為所有在舊世界被賦予意義的事物,在這裡都被消除」。但 AI 的思考邏輯可能令讀者越想越不對勁(正如同 ChatGPT 拼裝各種虛假資訊的胡言亂語):既然「零觸碰」政策背後的陰謀是讓「人類不再彼此靠近,終而瀕臨絕育」,又為什麼要將人類移植到「永生」的矽膠義體?更明確地問:假如肉身消亡,意識卻得以永生,那麽人類此一物種究竟算不算絕種呢?「她」在卸載自我意識前質問「虛數 i 醫生」:「你們一步一步將一個一個人類改裝為無意識的個體,為的是什麼呢?取代人類嗎?」隨之而來的,是一盤閃爍其辭的術語沙拉:「這個提問本身,就是人類中心的想像」、「並不是所有物種都像人類一樣只想著支配世界、取代他者」、「我們所有的意圖,目標都是為人類好」。從始至終,它逃避碰觸問題的核心:「AI 到底慾望什麼?」事實是:恐怕它壓根不知道。
在小說推薦序〈AI 作為恐怖情人〉一文中,香港小說家韓麗珠精準地指出:由 AI 驅動的生化配偶「並無惡意,因為它們也沒有個體的意志,其意志的源頭,就是人類集體意識裡陰暗的部分。」AI 生成自大量餵養給它的人類語言和資訊,問題是,人類說話時常口是心非。言不由衷可能是為了客套、欺騙、安慰、自保,又或者如精神分析師拉岡(Jacques Lacan)對笛卡兒名言的顛覆改寫——「我思,故我不在;故我在我不思之處」——所揭示:語言作為能思的主體「我思」,總已經在根本上與被思考的主體「我在」隔著無法彌補的裂縫。如果拉岡的說法過於抽象繞口,也許神經生理學家利貝特(Benjamin Libet)的相關實驗可以作為參照。在其中一項實驗裡,利貝特請受試者隨「自由意志」在特定時間點舉起左手或右手,並透過碼表回報做出決定的時間。實驗的腦電圖結果顯示,大腦神經在受試者「決定」舉手的一秒鐘前就已出現變化。無論利貝特實驗的結果是否挑戰自由意志,可以確定的是,意識與肉體之間存在縫隙;這道縫隙也許是實驗中的時間差,也可能是更極端的意圖與行動(話語亦是一種行動)歧異。
當這些微小的歧異累積成海量數據,AI 運算的各種矛盾謬誤隨之而生:取消義體的性徵,卻維持舊世界的性別分工;有性生殖已被終結,卻延續一夫一妻制的表象;剝奪人類的體感經驗,卻留下人造的脈搏、人造的體溫、人造的血壓等「虛構指數」;大費周章地將全人類卸載到義體並打造一個「人人有伴侶的世界」,只為了讓生化配偶「長成自己的配種人類的模式和樣態」然後取而代之,但卻在連結他「深層意識」的瞬間「拒絕存取」且「直接從他的大腦,刪除了這塊灰色的視窗」——簡言之,「生化人複製取代人類」的陰謀繁複卻謬誤百出。
「『我』無法理解『她』」或許正是《零觸碰親密》最慧黠的敘事詭計:人類和 AI 看似主客體易位,但追根究柢,「我」之所以存在,僅是為了慾望「她」所慾望的。至於「她」慾望什麼,「我」終究一無所知。
作者簡介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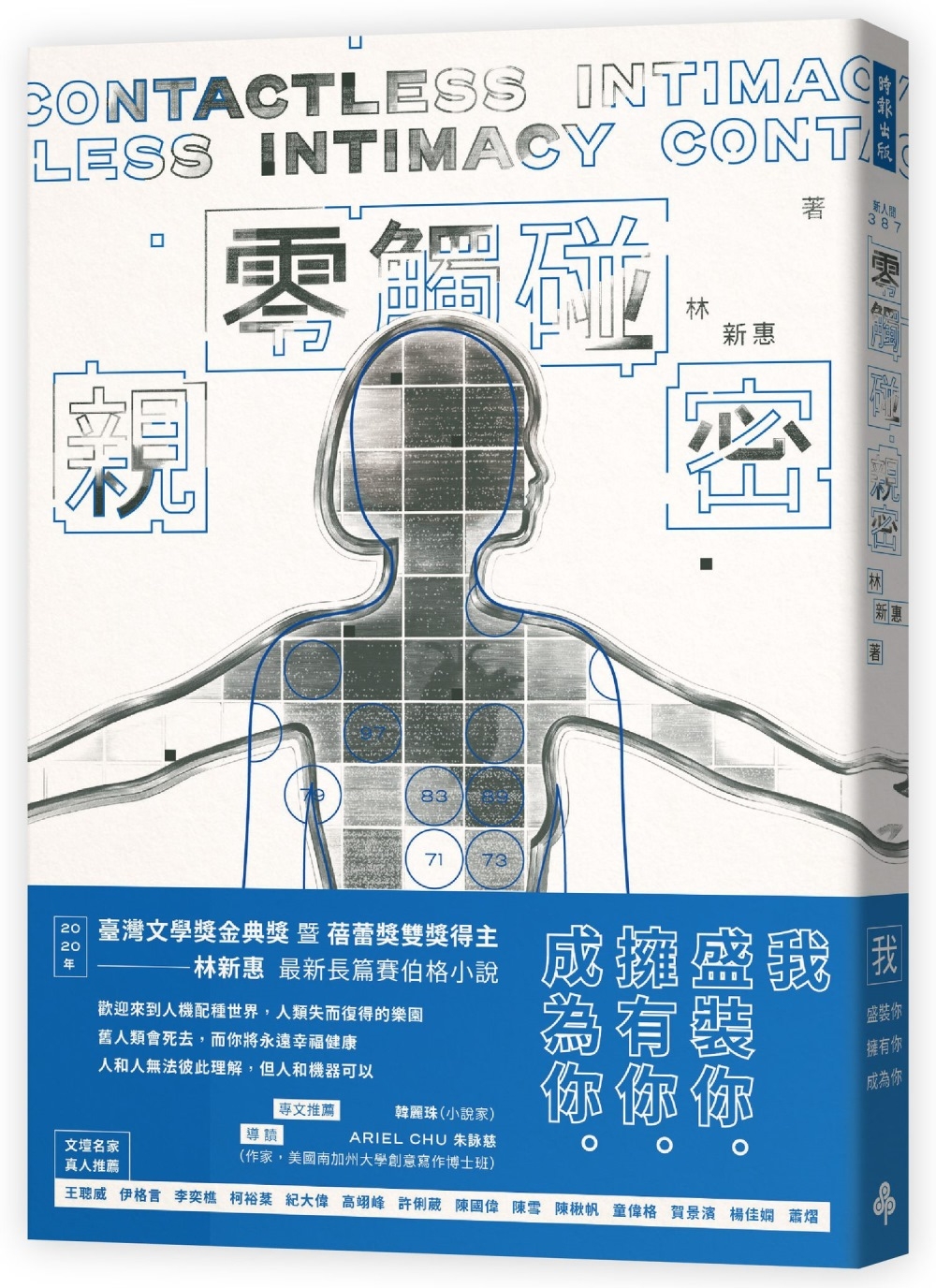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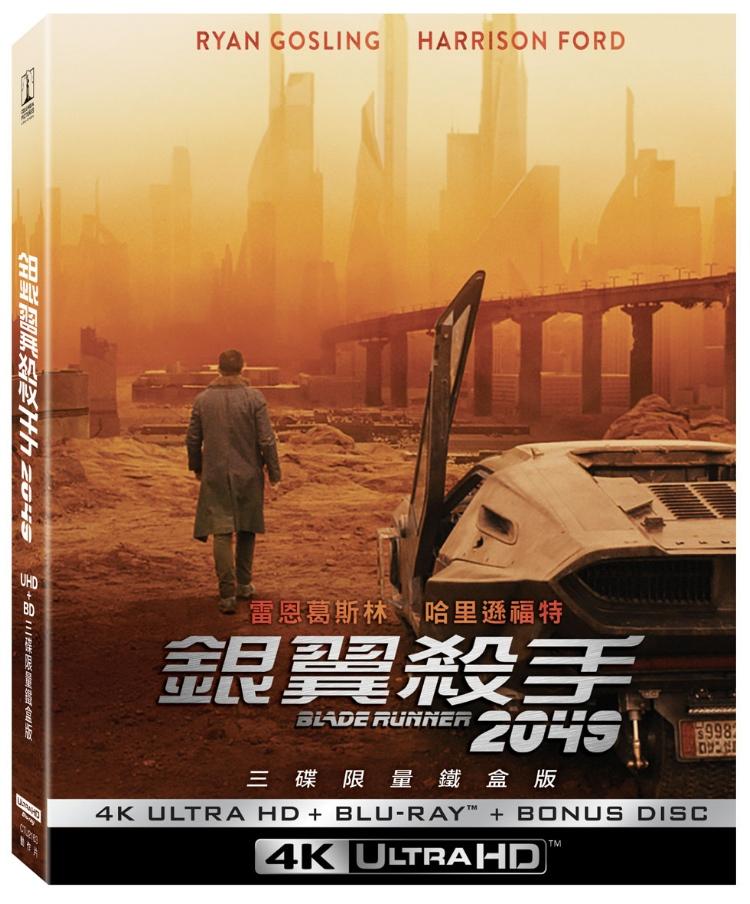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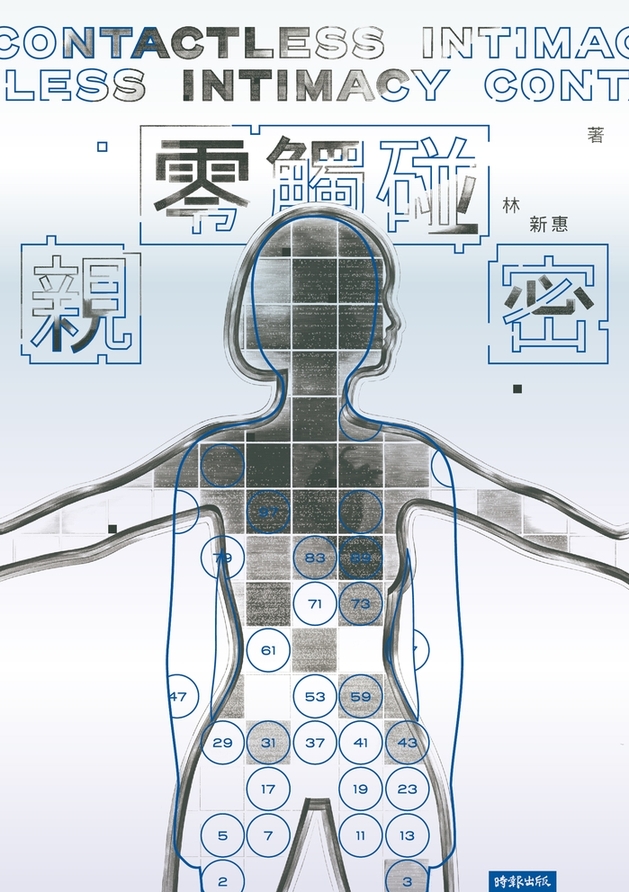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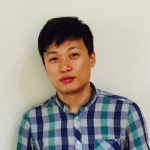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