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室報告│星空燦爛,像無數燃燒的小宇宙,創作的能量正在爆發。這一切是怎麼開始?為什麼要寫?要怎麼繼續?本企畫邀請深受年輕讀者歡迎、高中校園文學獎評審經驗豐富的作家,擔任文類導師,請他們回溯養成、相談創作之路。看青春與創作怎麼碰撞、怎麼摩擦?原來現在厲害的大人們,在創作的最起步也曾經猶豫徬徨。老師們又想給年輕創作者什麼建言?請看我們的訪問────
回溯養成:
「踏上寫作之路」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可以說是一個人發覺/認定/承認/探索自己作為一名作者的行為?
Q.是什麼契機,啟蒙你走上寫作這條路?
陳柏煜: 寫作需要啟蒙嗎?不像是壁球、單簧管或者駕駛客機,通常需要一點機運、一點炸藥,碰一聲把石頭彈飛,讓駕駛中的某人緊急轉彎,寫作不像那樣,一般的人生多少會遇上必須寫作的時刻,聯絡簿上的日記(注音拼寫)或填充格子的作文,興味索然的報告,興高采烈的廢文,太長的致詞,太遲的情書——生而為人,連和同事八卦兩句,你都不自覺地加油添醋。
如此一來,「踏上寫作之路」到底是什麼意思呢?我們可以說是一個人發覺/認定/承認/探索自己作為一名作者的行為?在一連串不斷替換的動詞中,他開始變成吝嗇的地主,築起一道籬笆——原先從腦中、口中冒出的語言就像山羌、獐、狍與梅花鹿自由奔馳,消失在山林的世界——籬笆圈定了它們的活動範圍,使領域內的事件,覓食、交配、遊戲,都得到標記。口中冒出動物的人不再流失它們,絕對的延續性保障了一種嚇人的權益:從今以後,不僅美麗的斑紋與毛皮,連優美的縱躍與旋身,都屬於他。

Q. 你認為詩像是什麼?為什麼?
陳柏煜:詩像皮箱。可是也不是普通的皮箱,是使用過的皮箱。我曾在北美館看過塩田千春的《集聚──找尋目的地》,數百個舊皮箱以紅色的繩子自天花板懸掛下來,輕輕晃動、碰撞,形成浩蕩的隊伍。彷彿看不見的鬼魂提著他們的皮箱。或者沒有主人,只有皮箱。訪談中藝術家表示:「紅繩子像是扮演每個箱子的臍帶,代表人們與過往積累的經驗之間的連結」。詩像皮箱。
Q.你是怎麼定義「好作品」?對於目前自己的成績是滿意的嗎?
陳柏煜:詩像皮箱,好詩像好皮箱。據傳鐵達尼號沉沒四分之三世紀後,美國海軍從殘骸中打撈出一只Louis Vuitton,撬開後,裡頭的物件甚至沒有受潮。(管它是不是真實故事呢?若是品牌的行銷也夠厲害了。)話說回來,這裡說的皮箱也只是譬喻的皮箱。
有時品牌的確事關重大。將一名夠好的詩人所寫的壞詩認定為好詩,這種情況並不罕見。你說,真可恥,名氣蒙蔽雙眼。但實情不盡然如此,經典的圖案有其價值。
關於第二題,我對自己總是很滿意,不過成績往往是別人說得算。
Q.音樂對於你的詩創作造成最有感的影響是什麼?
陳柏煜:在我的個人生命史中,音樂(展演)與文學(創作)很早就分開了。從小學一年級開始學習鋼琴,進展快速,老師將我視為具有天份的孩子栽培,她不知道我有一天會成為作家。同樣地,開始在文學獎嶄露頭角的我,面對熱中寫作的同儕與對手,也少有機會透漏自己音樂的經歷。因為提前選擇了演化的岔路,音樂與文學分別開展的譜系(在我心中)已互不相干。可是這也是單就表現層面來說,作為音樂與文學內容的接受者,即,閱聽與鑑賞者,兩個領域實際上構成同一片知識與審美的網絡——當然,這張緻密的網也在我創作時提供支持。
若要在音樂的範圍內找一件影響我創作的事,或許和聲音的關係比較小:閱讀樂譜。音樂是時間的藝術——也是空間的藝術,當它落實在紙張上。如果我們可以用朗讀、默讀探觸詩在文意以外的「聲音塑造」,紙上音樂呈現的敘事、結構與張力,同樣具深刻的啟發性。

精進技藝:
若是未完成的作品,我的態度就很決絕了,我很忌諱它們「被看到」。
過早掀開,會使裡頭醞釀的、還沒長好器官的東西快速壞死。
Q.作品「被看到」這件事,曾經令你有害羞或困擾的感覺嗎?「寫出來」到「能發表」的過程,你做了甚麼?
陳柏煜:對一篇發表的作品來說,讀者與評論家的目光是十分有益健康的,就像綠色植物需要充足的日曬。對作者來說,倒不一定,我覺得關鍵在於作者與作品的關係。假若把作品當作自我的延伸,把「對作品的看」混淆為「對我的看」,勢必會造成誤會。另一種情形是,作者和作品間仍殘存某種「隱形的臍帶」,投射在作品上的看,間接讓作家察覺了,彷彿被陌生人盯著背影。至於要強化還是弱化這種「過剩的感覺」,就看個人決定了。我自己滿喜歡「被看到的害羞」。
然而,假若是未完成的作品,我的態度就很決絕了,我很忌諱它們「被看到」。過早掀開,會使裡頭醞釀的、還沒長好器官的東西快速壞死。作品等於直接完蛋了。你可以說是迷信,也可以想像:創作過程的黑暗、內向、微微潮濕,就像裹在一團厚被子裡呼著熱氣。
「寫出來」到「能發表」的過程,做了什麼呢?沒做什麼。我寫出來的東西就能發表了。
Q.你的作品主題多為愛情,什麼樣的愛情詩最能造成記憶點?
陳柏煜:一開始,我覺得問題應該要這樣問:「什麼樣的愛情,最能造成記憶點」呢?想想又覺得,我根本是把問題搞得亂七八糟,因為答案已經寫在問題裡,無論是愛情或情詩,都需要記憶點,精確來說,需要「點」。單一、固執地精確、偏頗也好。我有一首詩叫作〈鴿子〉,寫得是與情人爭執後,兩人躺在床上,一人對天花板做出鴿子形狀的手影,他們養的貓直立起來,一次又一次想搆到天上的鴿子。
Q.你覺得是什麼驅動力造就你持續產出作品?
陳柏煜:實務面上是自律,情感面上是貪心。
職業意義上的「作家」和一般意義上的「作者」的區別在於,後者僅提示創作勞動的行為者,即「完成作品的人」,前者則隱含責任及超越單一作品的目標,或許可以說,「出於責任與目標而持續完成作品的人」。譬如上健上房,雕塑單一肌肉的努力與長程的、對整體體態的想像與實踐,是兩回事。作家需要自律。
然而,自律冰冷且乏味,負責推進的總是欲望。回到地主的譬喻,你不會僅僅滿足於擁有一塊領地,雖然它們都是精心建設的。獲取更多地盤,沒有壓迫與環保的問題;你的名字將永世雋刻於莊園的大門。當然,作品要對得起自己的標準,不然惡名也是一輩子的。
Q.創作者眾多,如何避免與他人太過雷同的思考方式?
陳柏煜:最簡單的方法就是物理隔絕:讀不同的書、交不同的朋友、不加入文學組織、不參加文藝營。我一半認真一半不認真的這麼說。可是哪裡比較認真,哪裡比較不認真,我也不很肯定。讀不同的書在最多的情況下是正確的。剛出版的新書容易被注意、被討論不難理解,可是當大家都擠上浪頭,你卻汲取海洋深層水,區別自然出現。可是向深處探測勢必得忍受一些孤獨、一些自我懷疑。我不希望這會抹煞閱讀的樂趣。即使發現一本罕聞的傑作樂趣是加倍的。

致創作新鮮人:
如果文學此一行當是一座金字塔的話,文學獎大約是位於腰部、中低階段的關卡,
有志於攀登者,很快就會見到它、認得它。
Q.你認為現在年輕的寫作者優勢是什麼?
陳柏煜:新世代的寫作者擁有前所未見的數位資源。查索、檢閱在數個關鍵詞之間即可收穫,藝術資訊(書訊、講座、報導、評論)琳瑯滿目,內容之豐盛營養與其取得的低廉是不成比例的。我們不在讀菜單點菜的餐館時代了,身處迷宮般的豪華buffet,分子料理與原形食物爭鳴,極致美味與濫竽充數並陳。在選擇、預算的限制下,餐館的哲學是木心所說「一生只夠愛一個人」;buffet非常慌忙、非常興奮,準確、有策略的決斷,需要被大大提倡。
最後一點觀察是,新世代寫作者的文學典範漸趨多元,「影響主流」不再顯明,但各路「模板」仍在。以反面回頭思考上一問「如何避免與他人太過雷同的思考方式」,我的想法是,雷同也未必不值得推薦,玩得都是經典的老把戲,你可以玩得比別人更好。
Q.去年連續得到文學獎大獎的你,可不可以談一下,得獎前後的心境變化?以及你怎麼定義「文學獎」?
陳柏煜:如果文學此一行當是一座金字塔的話,文學獎大約是位於腰部、中低階段的關卡,換句話說,有志於攀登者,很快就會見到它、認得它。如同其他的技藝專業之塔,它不以全貌示人——眾人從平地經過,偶爾也作觀光客,象徵性地在入口拍照留念,抬頭望見「文學獎」,認為也算是很頂端了,更上頭則雲霧繚繞。使用這個譬喻,並不是企圖顯示文學很高級、不懂文學的人下等又無知,完全不是這回事;我想說的比較接近「由位置而引發視錯覺」,因此把向上的塔,換成向下的谷地也不是問題。因此,對方入門的新朋友來說,文學獎的確可以作為某種明確的標的:由此向前。可是很快地,甚至比一般人想像得還快,我們就通過它——它頓時轉為混淆的幻術:背後的它仍以雋刻的字跡告訴你,由此向前。於是有些人踟躕迷惑了。比如,眼光手法尚未臻純熟的新鮮人得獎鍍金,有突然躋身殿堂的錯覺;比如,眼光手法卓然成家而一再落馬——這樣的人根本不需要背後那塊失效的路牌。或許需要的是獎金,或許需要的是由此引發的關注熱度——很悲哀的是,即使是你的同行,雲端的文學太曖昧太迷茫,很多人終究選擇折返,去守那塊路牌。

Q.寫完詩,到看到作品拍成詩影片,文字和影像會抵達到相同的地方嗎?你最驚喜處在哪裡?
陳柏煜:文學和影像要如何抵達相同的地方?抵達同個地方,會是我們未言明的希望嗎?最後,當我們說它們抵達了同個地方或不同地方,究竟是甚麼意思?
所謂「地方」指的若是「藝術效果」,我認為是不可能的任務(即使影像中仍保留了原詩的文字):影像對文本進行程度不一的介入,增長、截斷,使之以前所未有的面貌示人。這個「新文本」與影像,在「作品」的船上逐漸融合,在這個意義上,是的,當然,它們會抵達相同的地方。
浮現第二個問題,或許是起於原著與改編,媒介間翻譯,亙古存在的預設與迷思?再一次,他們幾乎不會抵達同個地方。不過,如果抱持著某個願望,而設下特定的「會面點」,相遇也不是辦不到的事。
前兩個回答間接觸及了第三個問題:「相遇」的意義。我想這是關於「神髓」的問題,也就是說,影像和文字是否把握了相同與近似的「精神」、「核心」,或者,更實際一些,特定的「要點」?我想回到「會面點」的概念。文字與影像的創作者,勢必有各自的「要點」——它們是否「會面」,則包含了兩種型態,其一是疊合(抵達同處),其二是散開(抵達它處)而拉開具張力的架式。我認為兩種會面都很好。
驚喜的地方是,室內棚拍、抽象雨景、濕潤模糊的色調皆與我的預想南轅北轍,而自有其道理與情調,導演是以第二種方式與我會面。
陳柏煜作品&譯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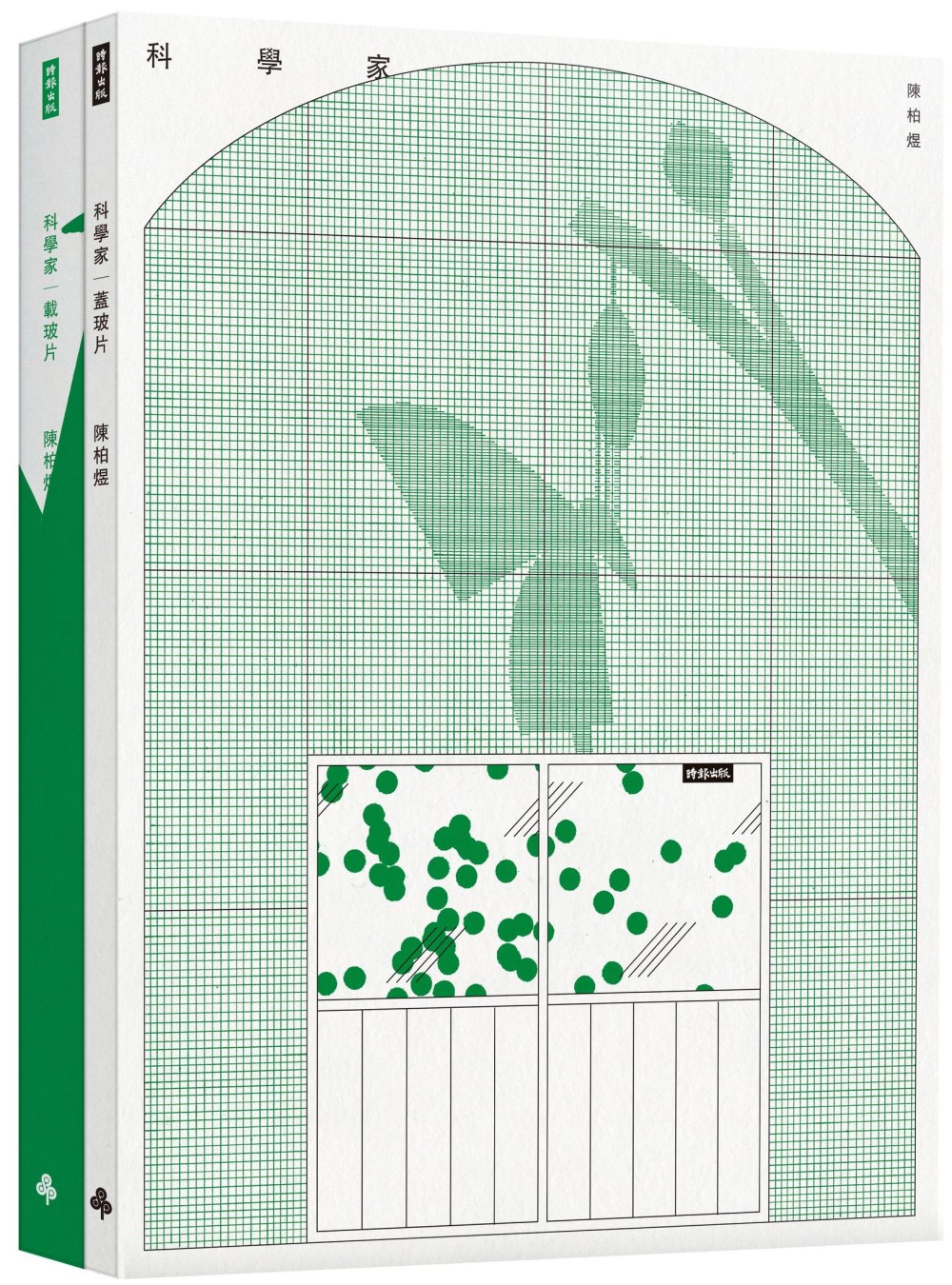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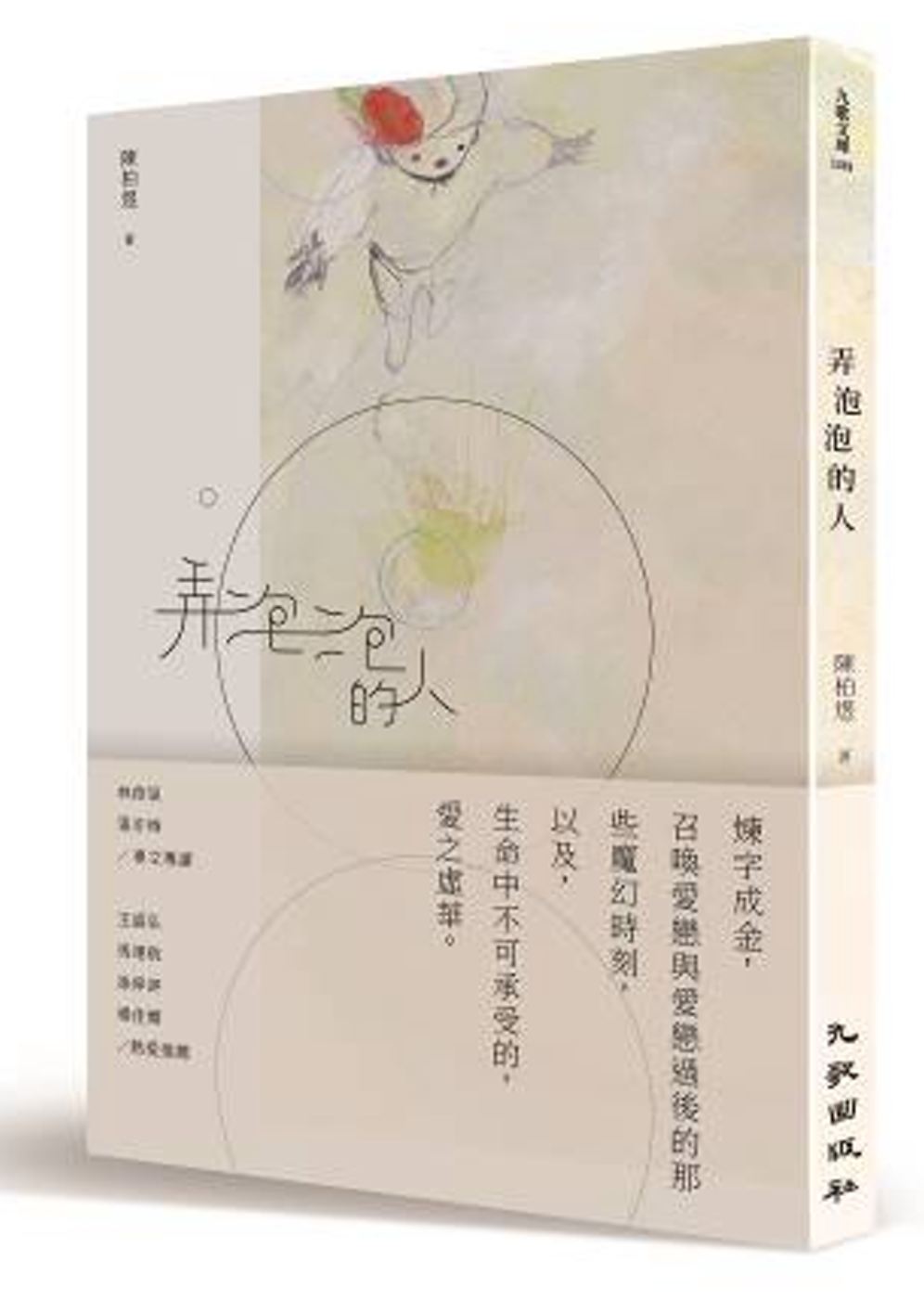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