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大利一句陳腐的雙關語:traduttore, traditore(「譯者即叛徒」)......之所以能源遠流傳,就在於其背後隱含了許多文化對於中間人普遍存在的懷疑,認為他們不是能力不足就是意圖不軌。
──《譯者的難題:美國翻譯名家的9個工作思考》
當一個群體、一個國家、一個文化訓練某個人去深入了解異己的語言與思維,最常見的期待目標無非是他/她成為兩個陣營之間的中介,代替整個群體去摸清那些陌生的詞彙、文法、邏輯,以便更有效率地獲益於經過迻譯後的外來知識或資訊。但兩個陣營的中間、非此亦非彼的位置是個難以找到參照與支持的孤寂地帶,被派去那裡的人,怎麼能確定自己對所聽所讀的每個字眼──以及背後的弦外之音──理解無誤?要怎麼讓「自己人」相信他/她的努力與忠實?在一個不論喜愛或浸淫得多深,都終究無法屬於自己的語言之中,他/她該如何找到定位?
編輯向我提議替《名為帝國的記憶》和《名為和平的荒蕪》寫一篇談主角境遇也談翻譯心得的文章,我很拿不定主意要先以兩個主題中的何者為開頭,寫出第一段之後,卻發現怎麼好像兩者都已經講了。這兩本書之內,有一位越是接近自己心之所向、就越可能走上叛徒之路的主角,書之外則有一位也戰戰兢兢害怕成為叛徒的譯者。
我相信這世界上的譯者和原作有緣分多寡和合適性高低之別,有需要極度費力才可領會的文本,也有非常輕易自然就能揣摩到神髓的作品。而我必須承認我和這套二部曲之間並不是天作之合的關係,相反地,書中有許多段落令我覺得舉步維艱,對一字一句充滿猶豫,懷疑自己的理解和表達力,並且屢次在心中悲問作者為什麼要用如此複雜、抽象、詩意的語彙來打造一個原本就較不容易讓讀者親近的科幻世界。
雖然我對科幻文類並非完全陌生,但處理這兩本書的難處不在於天文宇宙、科技器械等專門名詞或敘述(事實上這部分遠比想像中可親,即使不喜「硬」科幻的讀者也可放心),而是描摹、建構這個世界時所使用的諸多細節。例如小說開頭,主角瑪熙特身為來自宇宙邊陲的使節,腦中裝載著以「憶象機器」保存的前任大使意識去到星際帝國的核心,探索這個令人嚮往卻又陌生危險的社會,她的所有「內心戲」中幾乎都同時含有兩個互相交融但仍各具獨立輪廓的靈魂/人格,她在思考所見所聞之時,與自己的對話、與前人意識的對話(後來甚至還多了前人的另一個較新「備份」版本的意識)形成不同層次,有時邊界稍顯模糊(畢竟依據書中設定,前人的經驗與記憶應該逐漸被她吸納為自己的一部分),但為了協助讀者清晰理解,每一段內心對白的語氣又不能真的無所區分。
另外,風格上混搭了未來與古典、進步與神祕的泰斯凱蘭帝國,描寫起來也多有需要琢磨推敲之處。他們同時具有侵略異星的軍武勢力,以及人工智慧、全像投影通訊等尖端科技,但也以生活文化中無所不在的詩文辭藻、歷史情懷為傲,自恃為世界的中心,甚至將帝國的疆域視作文明世界範圍的同義詞。研究拜占庭帝國(及其與周圍民族往來關係)歷史出身的作者Arkady Martine以中世紀的拜占庭作為泰斯凱蘭的部分藍本,從君士坦丁堡穿過山脈通往周邊藩屬的隘口,在泰斯凱蘭轉化作類似於蟲洞的「跳躍門」,使都城派出的星艦能夠迅速殖民數十光年外的星球。因此,決定這些外星/外國聚落是否遭受帝國征服的關鍵不是物理距離或地形天險,戰場更在於外交折衝、在於帝國的文化「外宣」能否在攻克領土之前先擄獲民心,能否讓來自各小國的外交代表傾慕帝國的富饒高雅、繼而成為甘願賣國的間接叛徒[註],無論故事舞台是中古東歐或科幻宇宙皆然。
除了拜占庭元素,泰斯凱蘭的人名、官職名和宗教祭儀則從阿茲特克古文明中獲得靈感,最明顯的例子是三海草、六方位、十九手斧等「數字+名詞」構成的特殊名字,還有世界設定中自創的職稱,例如「ezuazuacat」(皇帝於戰爭時的護衛、承平時的宮中心腹),乍看連原文讀者也會一頭霧水,簡體中文版以音譯處理(伊祖伊祖阿卡),繁體譯文則意譯為「勳衛」,忍痛放棄如實呈現原文的異國詞源──也忍受這一點點對作者巧思的背叛──選擇簡明易讀的效果。
同樣地,故事中段宮門深似海的權鬥戲碼,加上泰斯凱蘭自命的地位形同「中央之國」、對外人抱持近似「夷狄入中國則中國之」的心態,中文讀者或許看了也會想到古裝劇中的明清盛世。那麼……帝國的皇帝能不能自稱「朕」?敬稱又應該是「皇上」或「陛下」?皇宮發出的布告要算是「聖旨」還是「諭令」?(如果尚未看書的讀者感到好奇或疑慮,其實最後的決定還是沒有讓泰斯凱蘭如此「中國風」,畢竟中國宮廷許多制度與用語奠基於父傳子的親族倫理,但它和這個虛構世界有太多地方不相容。)總之,每多發現一個參考或聯想的藍本元素,翻譯時就要多煩惱一次該用什麼樣的文風和名詞譯法,才能讓這個帝國裡的人、事、物呈現出豐富與奇異的樣貌,但又要不失整體感、不致像是粗率任意的雜燴拼貼──同時還不能忘記區分哪些元素在哪些時刻對主要角色而言是(如同對讀者一樣)陌生的,哪些又已是理所當然的存在。
<瑪熙特,記得妳第一次讀偽十三河的《帝國擴張史》……然後妳心想,終於有文字能描述我的感受,而那甚至不是我自己的語言──>
記得,瑪熙特說。記得,她記得。那種痛楚:嚮往伴隨著一種狂暴的自厭,卻只讓嚮往更形強烈。
<我心有同感。>
我們心有同感。
他們倆的聲音,幾乎一模一樣。電流在她神經裡灼燒,被人理解的甜美感受。
──《名為帝國的記憶》
翻譯工程開始之後,我就像匆促間從遙遠邊境剛抵達帝國都城的瑪熙特,時時焦慮著帝國臣民的每段繁複文句裡隱藏了什麼一時難以參透的言外之意,對眼前的宮廷建築、服裝、星球地景眼花繚亂,同時還要摸索當地通訊網絡的運作方式、人際肢體語言和表情的規則,曾經令她如魚得水、充滿優雅文化底蘊的外語,如今成了一道將她隔絕成局外人的壁壘,留她在富麗的都城、廣袤的宇宙中寂寞一人孤立無援……。甚至到了最後,隨著瑪熙特逐漸揭露前任大使(亦即她腦中憶象的原主)遭人謀殺的始末真相、捲入的帝國皇位繼承之爭也愈演愈烈,她必須在益發緊迫的時間內靠著紛雜的各方資訊為自己和母國找到生路,而我就和她一樣靠著充滿自我懷疑卻仍不得不放手一試的心情在運作,設法將眼前所有陌異複雜、意義未明的事物吸收並轉譯進自己的語言和認知之中。
通常到了這種地步,我應該已經對如此折騰我的一本書由愛生恨了,但這次沒有。反而,在此期間,最讓我感覺自己的工作心情被同理、了解、如實再現出來的,就是這個故事本身,譯寫的過程中只見愈來愈多段落讀起來共鳴滿滿,儘管偶發的磕碰、卡稿仍然時時提醒我,這個故事的原文終究不是我的語言。
如此苦甜參半、擺盪在成就感和精神打擊之間的時刻,總是讓我多愁善感地想,翻譯的確就像瑪熙特這麼一位在自己人與外人之間曖昧游移、近乎裡外不是人的角色。無法肯定自己該更偏向哪一方、沒有完全的自信能為另一個語言/陣營的發話者代言、時時發覺自己對兩邊的了解好像都不足夠,可是又已經因為當初那一份「終於有文字能描述我的感受」的悸動而走到了這裡、接下了這個任務,縱使常常不知如何自處,卻無法抗拒那些偶然獲得的驚奇讚嘆、無法放棄意外鑽進心裡的情感共鳴,於是仍舊留在這個偶爾顯得危險又孤寂的中間地帶。一路上努力避免悖離原作也試圖顧及讀者的我,交稿之後只希望終於能放下「譯者即叛徒」的恐懼,並且想要拍拍同樣左右為難深受考驗、但也同樣不甘背負叛徒之名的瑪熙特,說一句「我心有同感。」


〔註〕參見來源1、2
葉旻臻
「泰斯凱蘭二部曲」譯者。目前為自由譯者,曾任紀錄片拍攝團隊助理、字幕翻譯。總是渴望更貼近自己欣賞的故事,所以喜歡翻譯。譯有《不能贏的辯護》、《布娃娃殺手3:遊戲終結》、《醜女與野獸》、《我的解剖人生》等書。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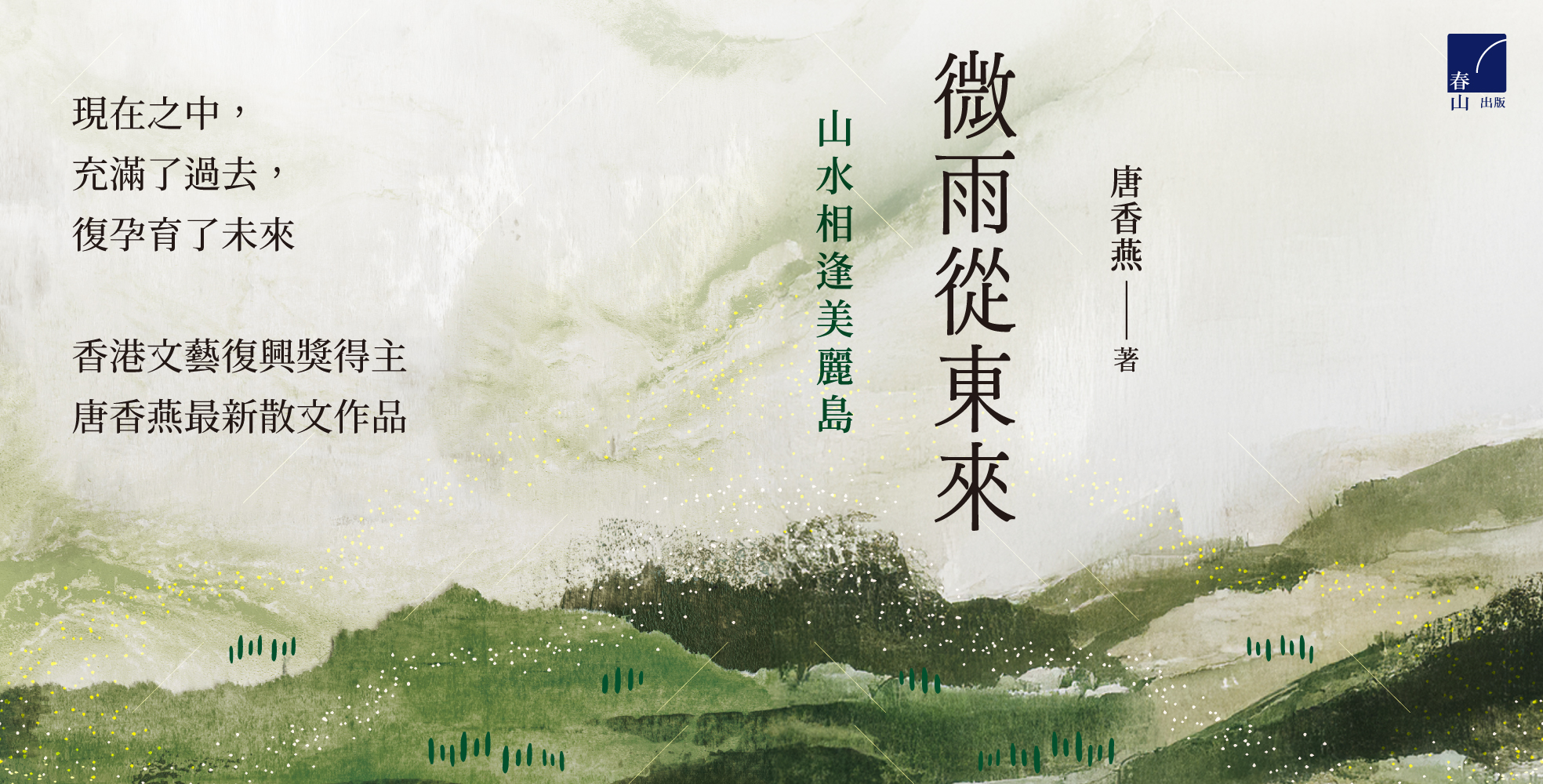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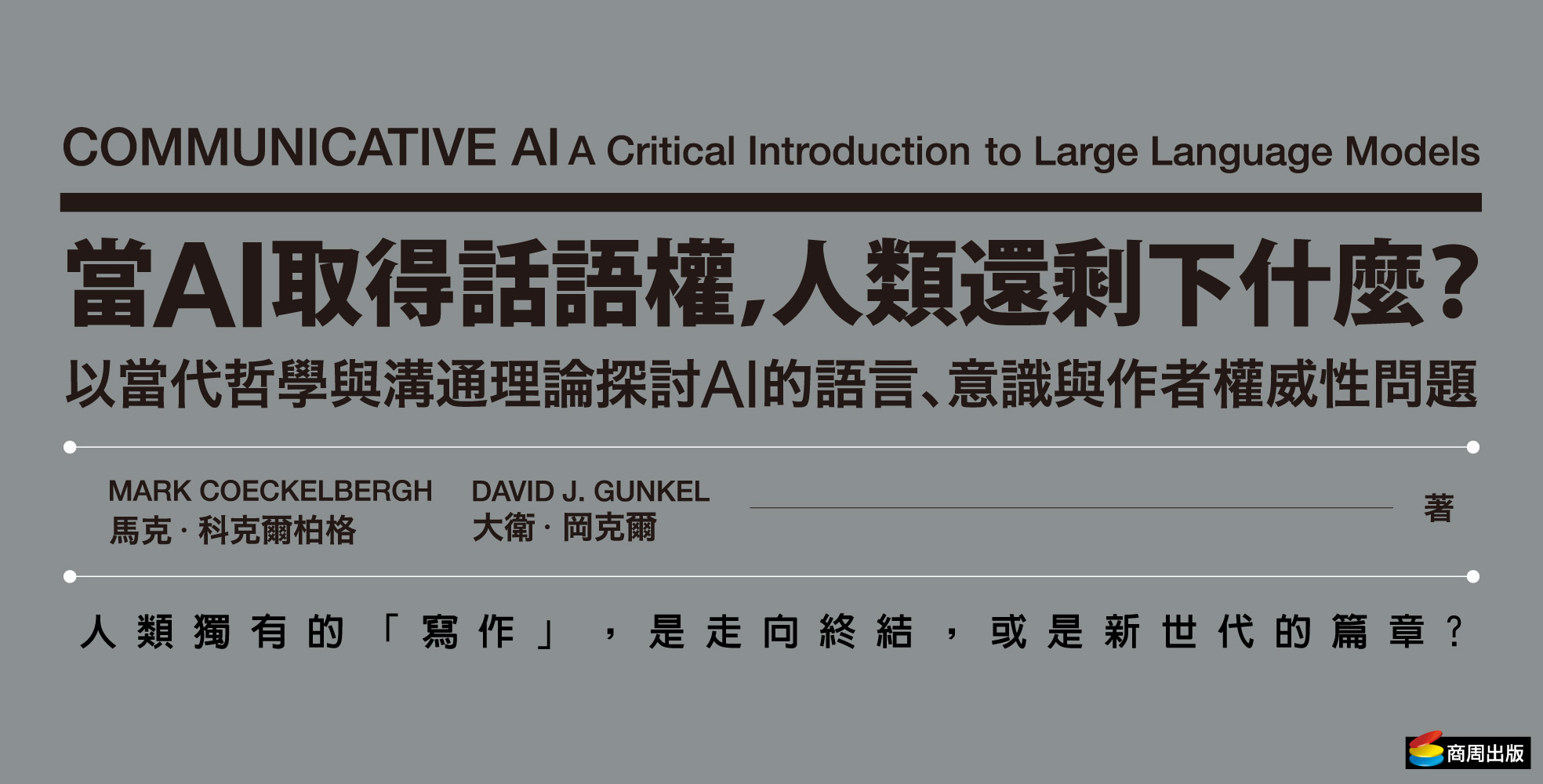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