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快秋分了,近黃昏的天光仍敞亮。分別在三總北投分院與台大精神科服務的張復舜和廖偉翔一前一後,在長日將盡時暫卸白袍,登入另一個身分——《兩種心靈:一個人類學家對精神醫學的觀察》的譯者。日前三級警戒期間,兩位接受了OKAPI的線上訪談。
《兩種心靈》於2000年在美國出版,作者譚亞.魯爾曼(Tanya Marie Luhrmann)本業是人類學家,為了研究文化與精神疾病的關聯性,一頭栽進田野,歷時四年潛伏在精神科前線當「間諜學徒」,她從臨床會談、病房巡視、治療團體到論壇交流無役不與,甚至親身接受300多次精神分析。這本高達26萬字的醫界生態筆記,細細紀錄了精神科醫師與他們的產地——像張復舜、廖偉翔這樣進入醫院服務未滿十年、尚在捏塑精神醫療信仰的年輕心靈,正是魯爾曼當年鎖定的觀察對象。
掀開診間簾幕的生態觀察
當新進醫師踏入作者形容為「痛苦、悲慘、高薪也難以彌補」的訓練過程,另一雙眼睛不動聲色地黃雀在後,拾起各種零碎線索,以扎實的紀錄讓《兩種心靈》有如傳送門,將兩位聯手翻譯本書的現職醫師帶回實務現場,尤其她精準(並帶黑色幽默)的側寫,簡直句句命中靶心。
「比我自己講還更細膩、更清晰!」談起翻譯本書的啟發,張復舜直言,「在生物精神醫學體系裡,個案所講述的內容,被視為『症狀』,他的故事會變成一組組『病理學名詞』。這本書能幫助需要跟精神醫療打交道的人了解,你置身的這個體系為什麼會長成這樣?也反思:你在抵抗的是什麼?」
問起投身精神科的初衷,廖偉翔表示,「我想看到更『完整的人』,而非症狀或疾病。」張復舜則說,「想深入了解人,並且真實互動。」
他們的回答,恰好都呼應了魯爾曼寫作本書的初始好奇。踩在醫學與人類學的對蹠地,「兩種心靈」原指美國在80、90年代精神醫療訓練中的兩個主流──仰仗「談話」為工具的心理分析,和承襲生物醫學的精神醫療。兩大門派對於一個人為何失常、該怎麼治療各有擁護,而這些觀點如何刀削斧鑿出一個人,正是人類學家窮追不捨想探究的。
沒有人會選擇精神病,它只是「發生」了。——譚亞.魯爾曼
馬奎斯短篇小說〈我只是來借個電話〉,投射出大眾對精神醫療的噩夜想像:將人關進病房軟禁折磨至神智不清,或視整個社會如資本主義搭建的大型監獄……。當新手醫師脫離了黑白分明的教科書,第一課就是先墜入各種灰色地帶──有人認為「我的悲傷不是病」、不必吃藥,也有同僚深信診斷幫助病人得到解脫。因此,張復舜首次讀到《兩種心靈》時興奮難抑,「台灣很少有書像《兩種心靈》說得這麼細膩且不帶批判,讓精神醫學與社科領域有了共同對話的基礎。」他一方面懾服於心靈之謎浩瀚如海,一方面也因懸殊觀點的價值衝撞而心旌動搖,如同魯爾曼所說的:「還在讀書時,常聽自由派朋友抨擊『精神醫療監禁』的罪惡,我原本想像病患在醫院受到不公平對待,但實際上,他們可能在該受治療時無法得到臨床照護。我看見的精神醫療不是壓迫,反而是資源有限。」
張復舜與廖偉翔皆是「公醫時代」平台創始成員,願意讓繁浩的翻譯工作榨取所剩不多的餘暇,多少說明了兩人潛在立場。首度翻譯書籍的張復舜說,「譯書過程很像孵蛋,必須來回沉浸並尋找適合的語言,永遠還有更好的譯法。」後期加入的廖偉翔已有多本譯作,如《在懸崖邊緣,接住你》、《精神病大流行》(合譯),他笑說,「翻譯的樂趣在於必須精讀,譯得愈多愈知道如何掌握,夾在忙碌行程中反而有紓壓效果。」
那份遣詞斟酌切換到訪談上,不難發現兩人對言辭的細慎,例如不說「生病」而說「有狀況」,用「釐清」替代「處理」。因為語言不僅僅是語言,也鋪設了一個人據以立足的后土,而「不評斷」是精神科極為重視的態度訓練。張復舜說自己使用DSM(精神疾病診斷手冊)時總會自我提醒,人不會無緣無故坐在這裡,要記得看見更多的故事脈絡、眼前的人有故事需要傾訴,「如果我腳斷了,當然希望直接把骨頭接好,不必問是不是很難過啊什麼的;但精神科不一樣,在這裡特別需要聆聽。當你看到個案身處在某種受苦狀態裡,你不會覺得他荒謬,或這人怎麼那麼差勁……你會告訴自己應該對這狀態有更完整的了解,而非丟下評斷就走了。因為我是要一直跟他工作下去的,必須更貼近他的感覺。」
在說與聽之間,迂迴靠近
張復舜說,「當我感受到自己的工作有價值,往往是受苦之人從我這裡獲得了一些什麼的時刻。」所謂的「一些什麼」在廖偉翔身上,則是見證個案的「不一樣」。是指狀況好轉嗎?「不一定,」廖偉翔解釋,「比如他光是更清楚自己有時會情緒低落、有時會浮躁,能退一步想再慢慢磨合,就很不容易。那是種陪著個案一起分擔的感覺。」
「一起」很重要,因為很多時候連醫生也沒有標準答案,只能併肩在路上。
幾年訓練下來,廖偉翔摸索出彈性,「體系定義他是個病人,但我們也可以跳出框架看他,透過蛛絲馬跡了解他的處境。不墨守某個診斷或倚賴藥物,仍然能幫助眼前的人,而且都是符合醫療規範的方式。我們不會一成不變地面對個案,因為每個人有不同的需要。這也是我想走精神科的原因之一。」廖偉翔務實地說,「要在兩種模式之間不斷換檔一直蠻有挑戰,但也創造出更多路,關鍵在怎樣結合得更好。如果問心理治療該怎麼學,其實就是去做啊!」
隨經驗長出的,還有對「模糊」的包容。廖偉翔坦言,「剛開始會緊張看不懂怎麼辦,急著討救兵。後來慢慢覺得看不懂也不會怎樣,就找人討論或等線索浮現。」尤其有時個案認為治療沒用,有時覺得醫生不懂,再也沒出現在診間,「有時候你得先解決眼前的狀況,才有機會問出更多端倪——是失眠或憂鬱?還是藏了更多原因?讓他願意看下一次、讓時間去消解不確定感,反而是更重要的。」張復舜附議,「精神科比較沒有檢驗,多半依賴言談和行為判斷是否符合症狀。要能忍受一直存在著『不確定』,我的作法是盡力保留空間,讓『不確定』慢慢被從渾沌變澄清。」
這樣的治療步調聽來踟躕又緩慢,而不追求一次做對,是因為在變動無常的世界,對錯換位都是一瞬間。唯有在每次嘗試中,一步步更靠近。
儘管二位譯者對《兩種心靈》中的寫實深感共鳴,但書中場景畢竟發生在上個世紀,不免令人困惑這20年來,在與精神疾病的戰役中,我們改變了什麼?張復舜解釋,「是有改變啦,但不見得往好的方向。藥物相對來說始終是經濟又有效率的選擇,那個傾斜我想一時半刻很難扭轉。但各種治療方式與科學驗證的整合路線,確實有愈來愈主流的趨勢。」廖偉翔接著補充,「在地的文化也很重要,各國會有不同遺緒,比如曾經歷高壓統治的國家,精神疾病有一定比例與政治犯不脫關係,我覺得《不正常的人》就是蠻好的本土研究。」
從「透鏡」的相遇,發現世界的相異
包括體系中的邊緣位置、健保財政顧此失彼的權衡、精神醫療在倫理間的兩難……種種盤根錯節不易三言兩語說分明。張復舜對此感觸良多,「翻譯《兩種心靈》讓我對身處的體系有更深入的理解,而且帶著歷史縱深,例如『精神分析醫院』的爭議論戰過程非常精彩,但在我們的精神醫學教育裡未必會教到。」廖偉翔同意精神醫療有其內在的多元與矛盾,他苦笑了一下,「相對於內外科,精神科是冷門科別,這好像也影射了某些精神科醫師或病人的邊緣處境。」但他也聲明,「我或復舜並不能夠替精神醫學代言,只是身為參與者,提供一些角度。」
魯爾曼撰寫《兩種心靈》其實是想提供另一枚「透鏡」,以截然不同的方式顯相我們曾深信不疑的真實。廖偉翔說,「當你學會用精神醫學的透鏡看世界後,就回不去了!人類學大概也是,受過訓練後眼光就回不去了。這會讓你思考個人責任與疾病之間的對立關係,兩者未必不可並存。」而看到之後的世界,是更混沌或更遼濶,無人有資格斷言。或許重要的不是平息沙塵暴,而是在風暴中放緩腳步、盡力看清人類心靈變幻莫測的光景。
除了明白世界不只一種透鏡,還需要更多的好奇,無論是對我們生活的土地,或是對陌生未知的領域。訪談最後,廖偉翔告訴我們,「醫學也許沒有想像中偉大,但我相信,光是可以更開放、更多元的理解各種經驗,不急著下評斷,就回應了人類學的初衷,而這也是精神醫學的初衷。」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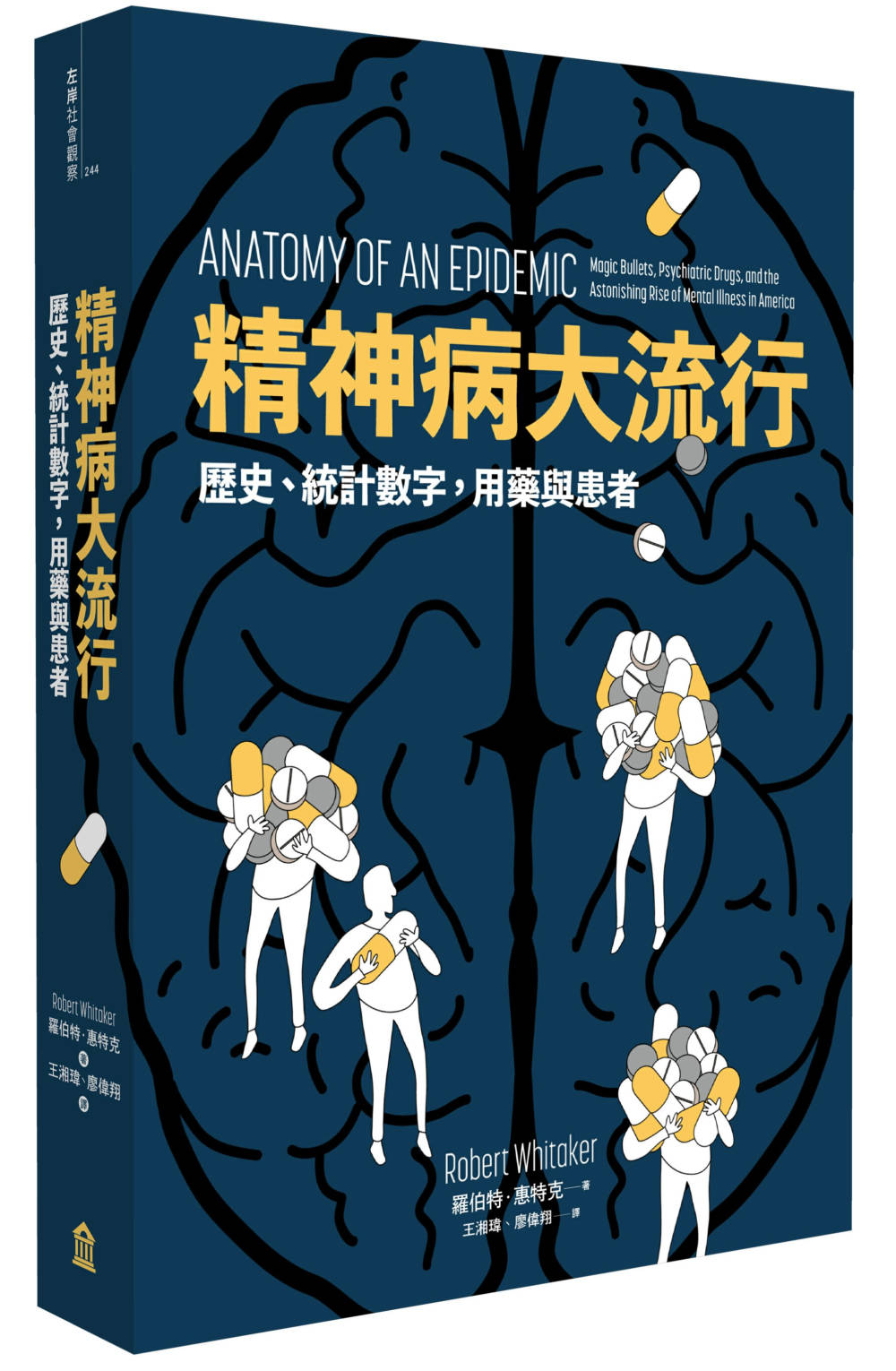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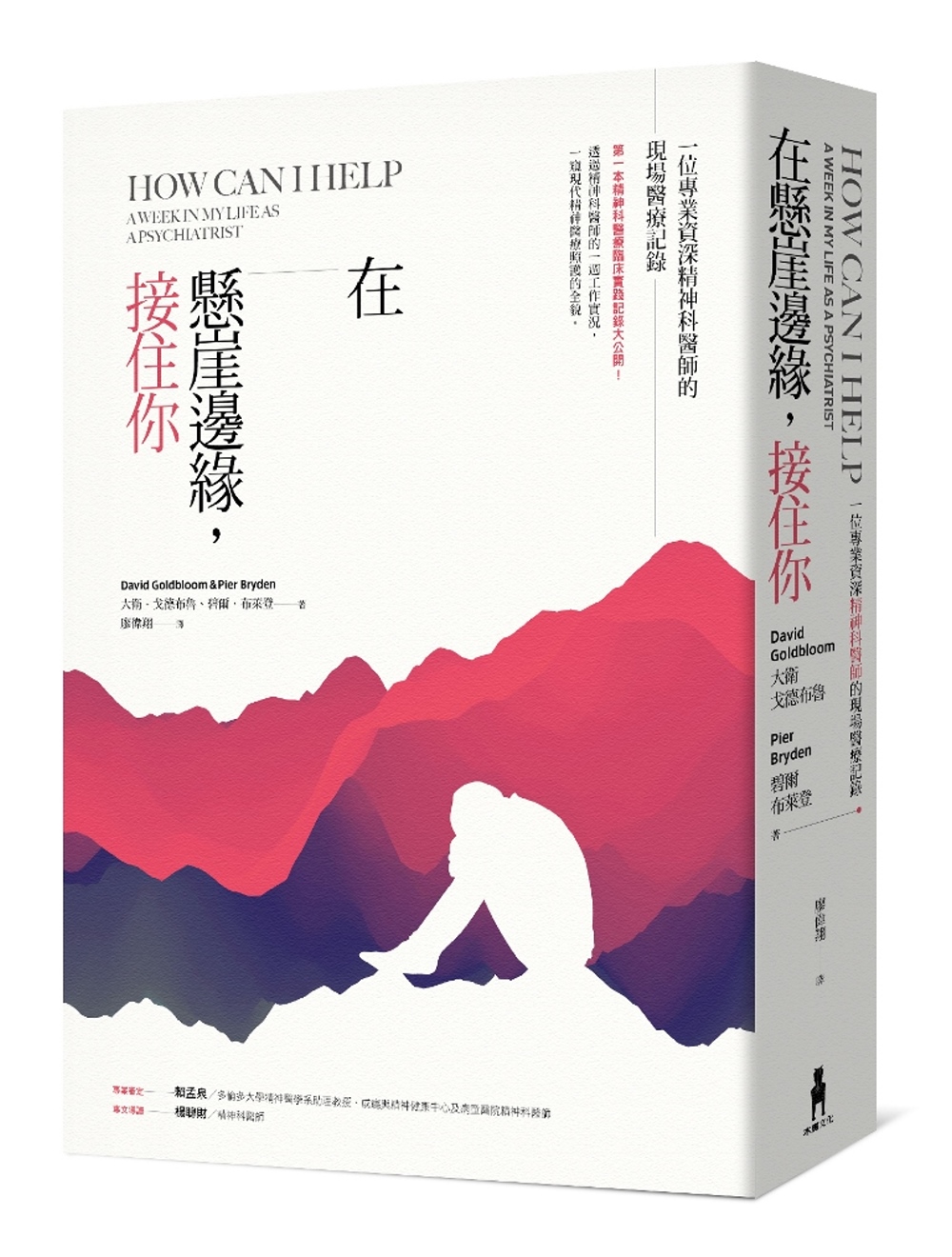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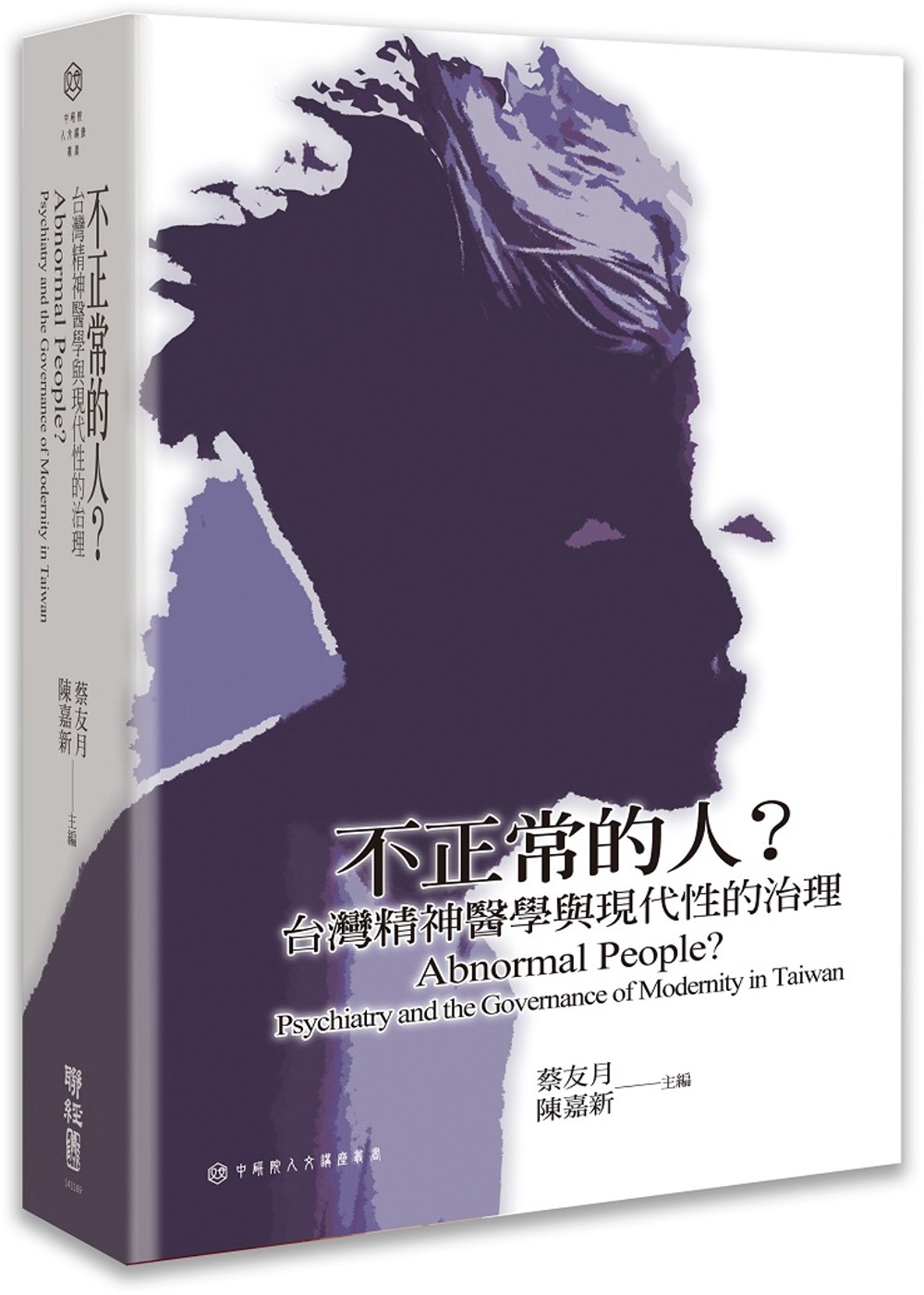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