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日作家李琴峰甫以《彼岸花が咲く島》(暫譯「彼岸花盛開之島」)獲得第165屆芥川賞,是該獎項第二次由非母語寫作者奪得,也是台灣人首次拿到這個獎。
幾年前,我邀請留日青年學者劉靈均到我任教的大學演講,他介紹了兩位日本同志文學的新亮點──長年往返台日、援助台灣同志運動的日本歌人小佐野彈,以及旅日就學工作、聚焦於女同志題材的李琴峰。那是我第一次聽到李琴峰的名字。
後來,《獨舞》獲群像新人賞,由作者自譯為中文出版。主角從台灣到日本,命運如影隨形,她從獨自面對傷害、以為被世界拋下而想尋死,到終於察覺到隱然存在的情感支持網絡,再回到異國面對往後的人生。小說尤其彰顯出種種汙名如何含蓄與不含蓄地作用,能隨時成為霸凌素材,也綁架了其他人對主角的認識,彷彿她是個同性戀/被強暴者/憂鬱症者,就不再是人。
以非母語寫作,就像永無止境的破冰旅行。對於日本讀者來說,李琴峰《獨舞》和《倒數五秒月牙》,主角均設定為在日生活的台灣女同志,其生活中多數困境和進境,來自語言和文化,台日之間又存在著漢字與殖民歷史的葛藤,關係更形複雜──這是當代日本文學讀者普遍感興趣的事情嗎?而尚未翻譯為中文的芥川賞作品,具有強烈女性自覺和從背負著殖民地陰影的台灣來的一份「憤氣」(野島剛語),加上她在推特批判安倍一事受到右翼網民攻擊,顯然,其寫作與思考,貫穿性別、文學、歷史與政治,敢於踩踏荊棘與尖石之地,日本文學讀者們又將如何看待這樣一位來自異國、富稜角的年輕作家?
日本的女同志書寫,我所知不多,從吉屋信子到中山可穗,乃至藏身在少女百合圖文與幻想遊戲中的親密身影,有其豐富面貌。然而,總體來說,當代日本社會於性別議題上仍趨保守,性侵受害者反成為眾矢之的(想想伊藤詩織!),西蒙.波娃所批判的「女性氣質」之害仍占據性別文化主導地位,更何況是性少數的處境(即使文學與影視作品似乎對此友善)。在此環境下,來自台灣的李琴峰,由台灣、日本、中國文學浸潤長大,敏感於社會文化差異,高度關注當代性別政治,她筆下的女/同志樣貌,在攻克重要文學獎後,能否衝擊、刺激日本文學?
從另一方面看,《獨舞》和《倒數五秒月牙》展現的台/日女同志表與裡,又對於「同志文學」這個在台灣已經蓬勃發展三十年的文類,有什麼刺激?毫無疑問,李琴峰小說以日語讀者為首先考量,但是,《獨舞》主角趙迎梅(紀惠)來自台灣,可是和我們一樣讀邱妙津賴香吟長大的;《倒數五秒月牙》林妤梅、孟月柔也必須從兩國文化差異、語言文字的使用等等來尋找座標,重新校正自己與愛情的軌跡,孟的名字也很難不令我們想起《藍色大門》的孟克柔。在生死愛欲邊際匍匐掙扎,如同擠出血膿那樣刺痛誕生的女同志台灣文學,終於也成為奶與土,沃育了往後世代的女同志寫作。此刻,「跨國同婚」議題懸而未決,李琴峰小說裡的異國戀人們也替我們拓展了認識與感受。
通曉中文與日文的寫作者,翻譯自己的日文作品為中文,似乎理所當然。其實,李琴峰對於翻譯這項事務極有自覺,也知道作者自譯時擁有更大的調度改寫權力。在文字上,中文版力求「自然」,沒有「翻譯腔」。她的自覺還展現在文體的選擇與交融。張愛玲當年寫〈連環套〉,被批評「把純粹《金瓶梅》《紅樓夢》的用語,硬嵌入西方人和廣東人嘴裡」,張解釋是希望能藉過時詞彙呈現出時空距離之感。李琴峰也基於對寫作的多樣考量,運用了看似「過時」的文化資源。
在《獨舞》和《倒數五秒月牙》中,日本女同志向台灣女同志以錯誤(或說別具一格)方式解讀杜甫詩,台灣女同志則向日本女同志引用中國古典詩歌來傳遞感情,比如已經化入普通語言的「心有靈犀一點通」,以曹操詩句和《還珠格格》主題曲互證,甚至依格律寫了兩首七言律詩送給心儀對象。雖然使用了典故與詞彙,仍能妥善地映照當前情愫,具有時代差距的形式將心意摺疊起來,更強化了那份難言曖昧。同時,也反向回應了當代日本語文教育中輕視古文與漢文的趨勢,並意圖改寫日本文化中「漢詩」與「漢文」的陽剛氣質和公領域特質(相對來說,和歌比較屬於陰柔的、私領域的)。在《倒數五秒月牙》的後記中對此說明詳細,請讀者務必參看。
1968年,川端康成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時,得獎演說講題即是「美麗的日本的我」(美しい日本の私,或譯「我在美麗的日本」);1994年,大江健三郎獲得同一獎項,演說題目和川端遙遙對話,「曖昧的日本的我」(あいまいな日本の私,或譯「我在曖昧的日本」)。李琴峰受訪時,說最希望忘掉的日文是「美麗的日本」(美しい日本),令人聯想到安倍晉三提出的政治口號「美麗的國家,日本」(美しい国、日本),也讓人想起川端康成。甚至,再想得遠一點,另一位同樣曾獲日本文學獎的非母語寫作者艾力克斯.柯爾 (Alex Kerr),不也曾以日文寫下《消逝的日本:美麗日本的殘像》(美しき日本の残像)嗎?意識並參與到此一形象的多元表述中,也顯示出李琴峰及其文學的意義。
作者簡介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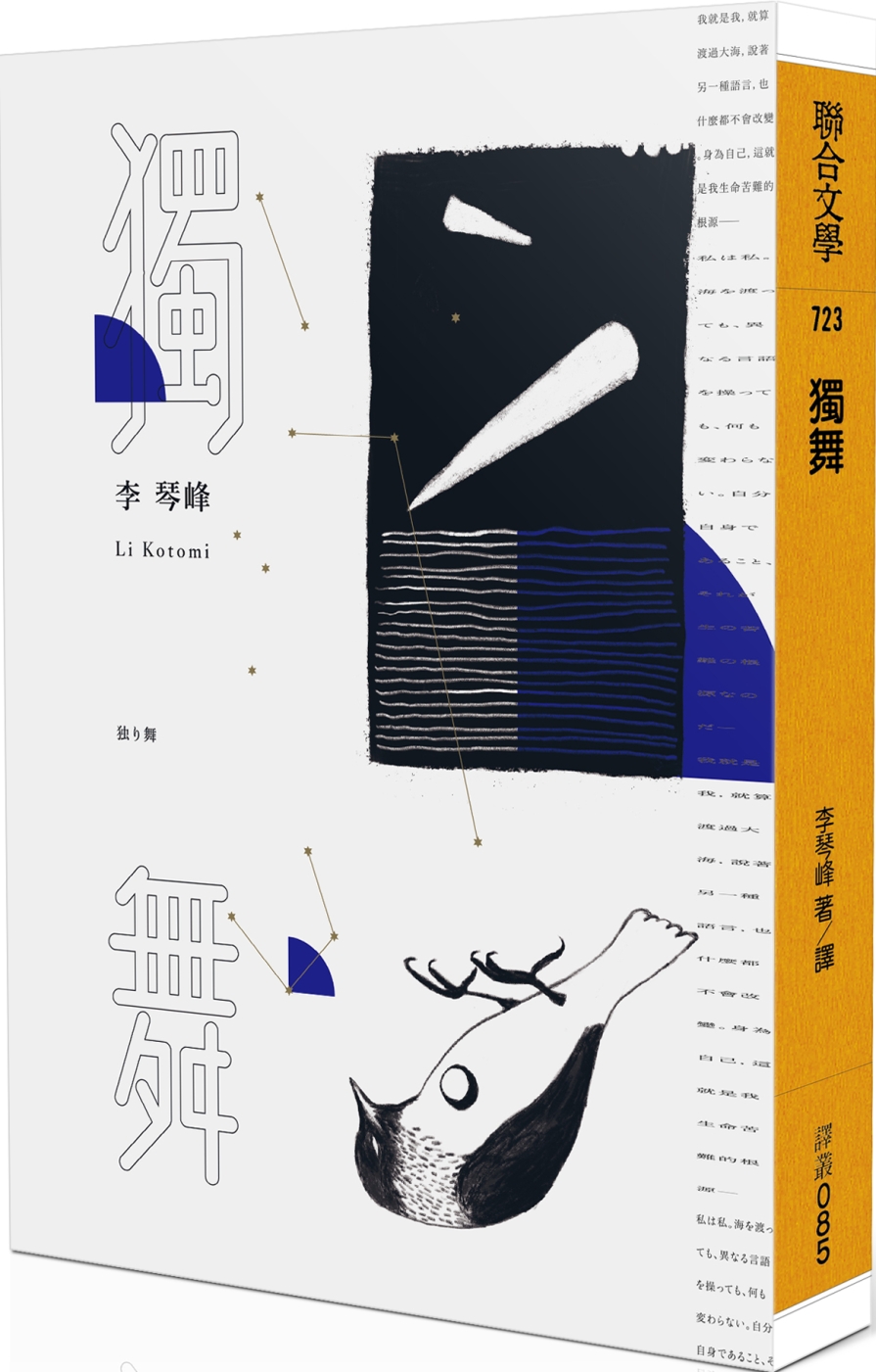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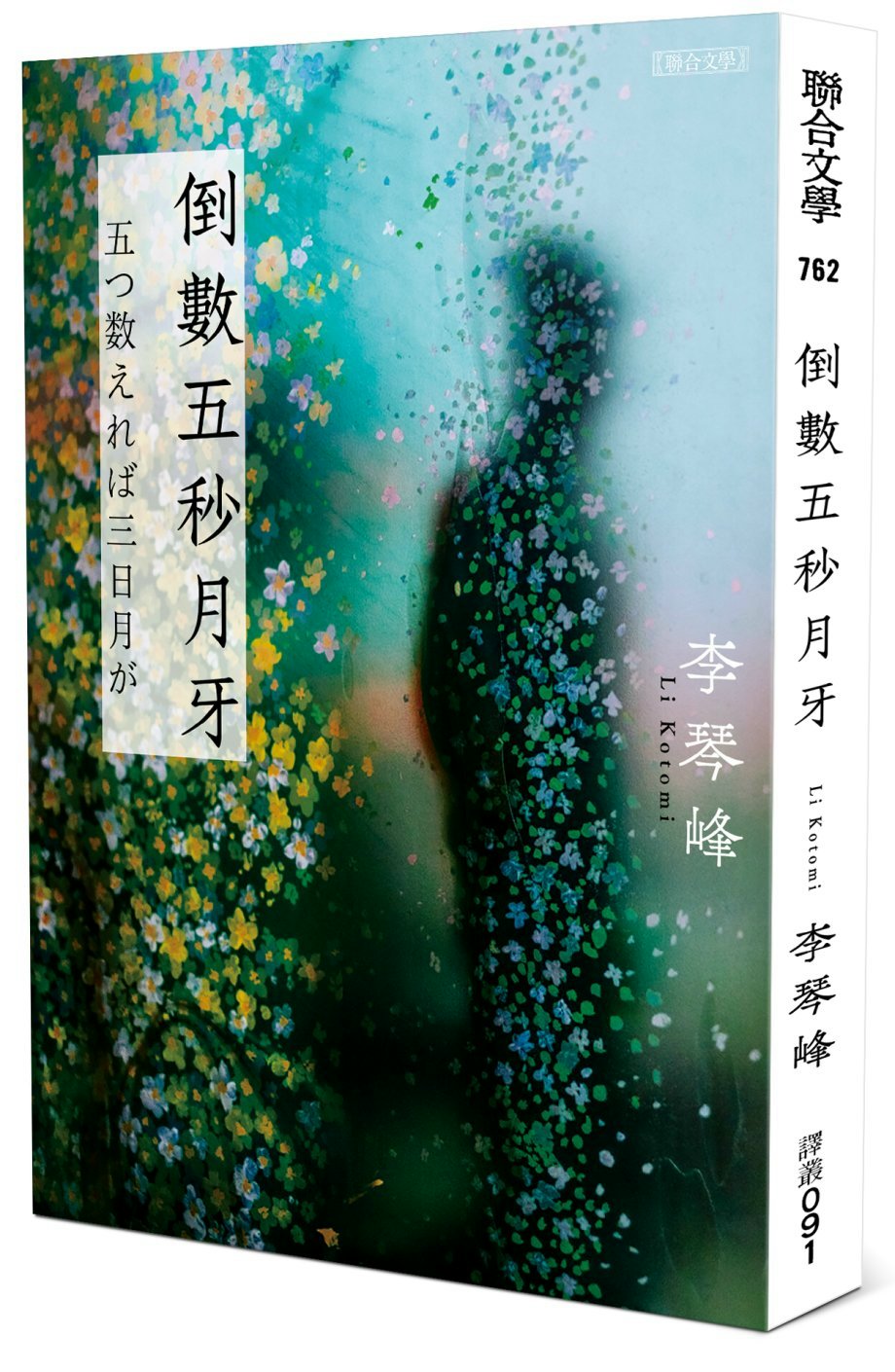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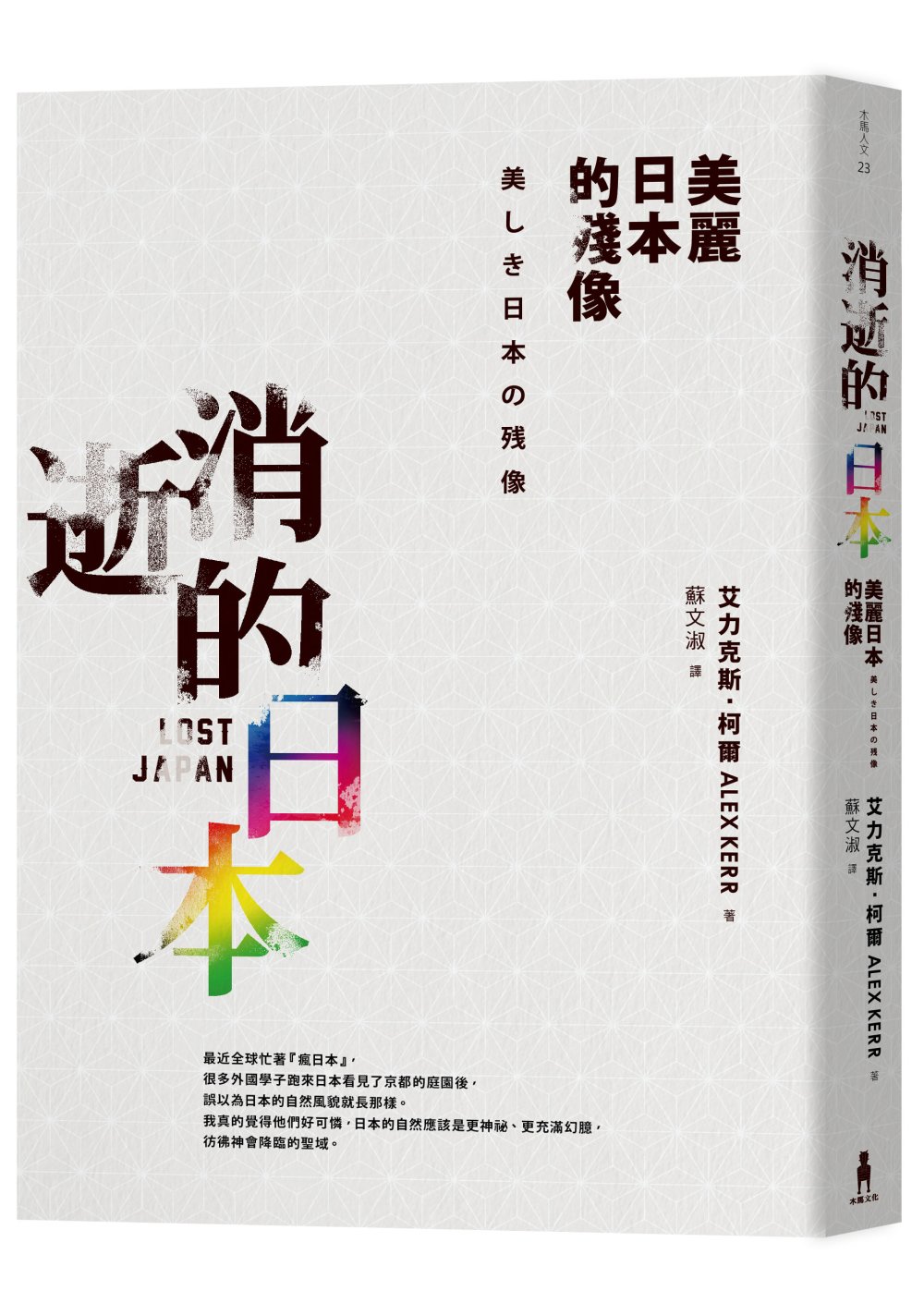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