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那一天,秩序毀滅又重構
恰克.帕拉尼克(Chuck Palahniuk)的新作《革命的那一天》,也許可視為他在出版《鬥陣俱樂部》之後,相隔二十多年的回歸。回歸並不代表重複。出版於1996年的《鬥陣俱樂部》,寫的是21世紀末以歐美為首的消費主義最為高漲時,X世代(1960到1970年代出生者,也就是帕拉尼克所屬的世代)所面臨的虛無、倦怠,以及被高速運轉的資本主義侵吞人生意義的焦慮。相較於此,《革命的那一天》在意的是Y世代(1980到1990年代出生者)身在看似穩固、平等而進步的世界,反倒像被壓力鍋悶著一樣,渴望秩序的毀滅和重構。
相較於《鬥陣俱樂部》結束在浮華消費世界的崩解,《革命的那一天》卻直指世界之所以構成,有其本質上的虛無。一如哈拉瑞在《人類大歷史》提出的著名論點:人類的文明核心,是中空的,是想像出來的虛構。
哈拉瑞指出,現代社會賴以存在的三大基礎——金錢、帝國、宗教——根本上都是想像的。由一群人共同虛構了一張紙的價值(金錢)、一個民族運行規則(帝國和國家)、一或多個超人類的存在(宗教),以這些虛構凝聚了超出人類生物性可以組成的群體規模極限,並且讓無數個陌生人感覺彼此有共享的特質(例如「我們都是台灣人」這類想像),甚至會讓人為了虛構的價值,甘願付出自己的心力和身軀,只為了鞏固這個虛構的文明。而《革命的那一天》即是藉由「新秩序取代舊秩序」的過程,彰顯了文明的虛構性。
什麼樣的新秩序、什麼樣的舊秩序?
《革命的那一天》描寫一個新秩序在舊秩序中埋伏、壯大,最終顛覆舊秩序的過程。舊秩序即為我們目前熟知的社會現狀:以歐美為首的全球資本主義為根基,強調認同政治上的平等,並以此平等的程度來評估一個社會「進步與否」。新秩序則企圖徹底抹滅這個舊秩序:所有相信新秩序的人,全都擁抱一本由謎樣人物陶伯特所寫的《審叛日》,就像紅衛兵以《毛語錄》為核心、納粹以《我的奮鬥》為教條一樣。他們相信《審叛日》傳遞的價值觀,認為如今的多元社會,都是菁英階級操弄社會的把戲。他們反對平權,並且在網路上成立黑名單,暗自虐殺那些名單上的人,通常是大學教授、新聞從業人員和政治人物。
然而,直到書的最後,都沒有辦法知道這位鼎鼎大名的陶伯特到底是誰、為什麼要創造這個新秩序、為什麼要傳遞這類一反當今社會的法西斯式教條。或許更諷刺的是,這位陶伯特,可能只是一位魯蛇大學生華特的幻想。這位總是嗑茫、腦洞大開的大學生,照著(可能是他想像出來的)陶伯特指示,印製和散布《審叛日》,以及架設黑名單網站。最終,這個玩笑一般的幻想,卻釀成一個運作系統過於龐雜,超出個人控制的新秩序,而新秩序也殘忍地抹除了舊秩序。
比《鬥陣俱樂部》更宏觀,卻也更虛無
讀到這裡,可能讓人再度想起《鬥陣俱樂部》:謎樣男子德頓也是敘事者的虛構人格,並且也組辦了地下化的組織,最終領導眾人炸毀多棟金融機構。《革命的那一天》比《鬥陣俱樂部》更宏觀,卻也更虛無。宏觀在於,《革命的那一天》並未停在《鬥陣俱樂部》式的一次性報復行動,而是描寫一個秩序(或者「文明」)如何誕生、自我鞏固、毀滅其他秩序,最終自身又成為人民亟欲逃叛的對象;虛無在於,不同於《鬥陣俱樂部》中俱樂部的眾人尚且能找到一個名為「德頓」的實體,《革命的那一天》中卻沒有人知道陶伯特是誰,也不知道黑名單從何而來,只是遵循陶伯特的教條,持續擴增黑名單。
因而,當故事走到最尾端,只剩下虛軟的感嘆時,我們不禁從中照見人類歷史文明根基的不堪一擊:我們所相信的,所賴以生存的,會不會,從來也只是偶然性的幻想呢?文明會不會只是一場集體妄想症?我們相信金錢、國家和宗教,其實無異於小說中所有人堅定不移地相信《審叛日》。然而我們所相信的這些,如同哈拉瑞所言,只存在於人類自己發明的故事,並且「除了存在於人類共同的想像之外,這個宇宙中根本沒有神、沒有國家、沒有錢、沒有人權、沒有法律,也沒有正義」。而這或許是《革命的那一天》最終的諷刺:那麼多條交雜的敘事線,交織出一個華麗新秩序的誕生,然而那個新秩序,就像所有曾經發生的舊秩序,在根源上是「什麼都沒有」——就如同那位從來都不存在的陶伯特一般。
作者簡介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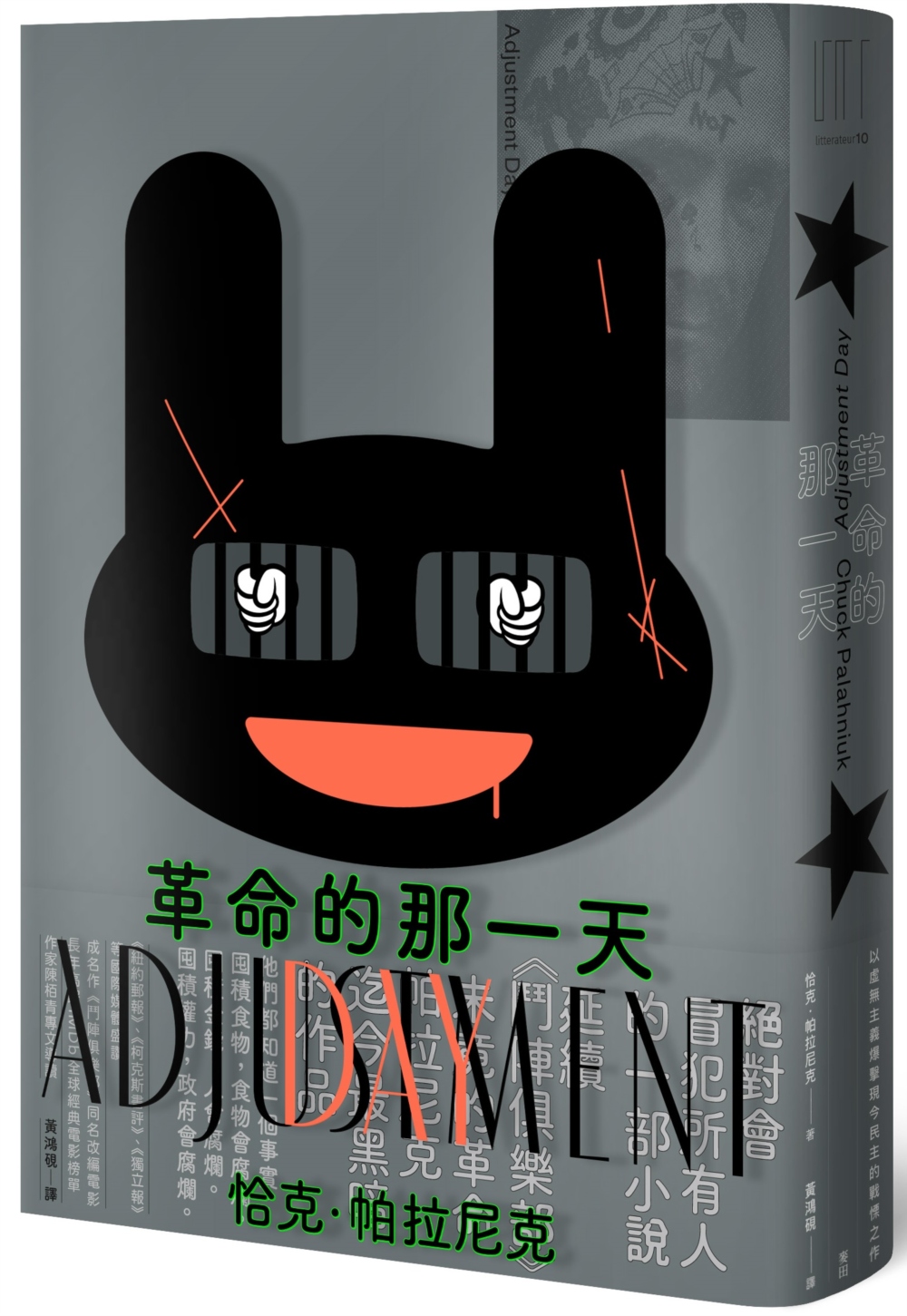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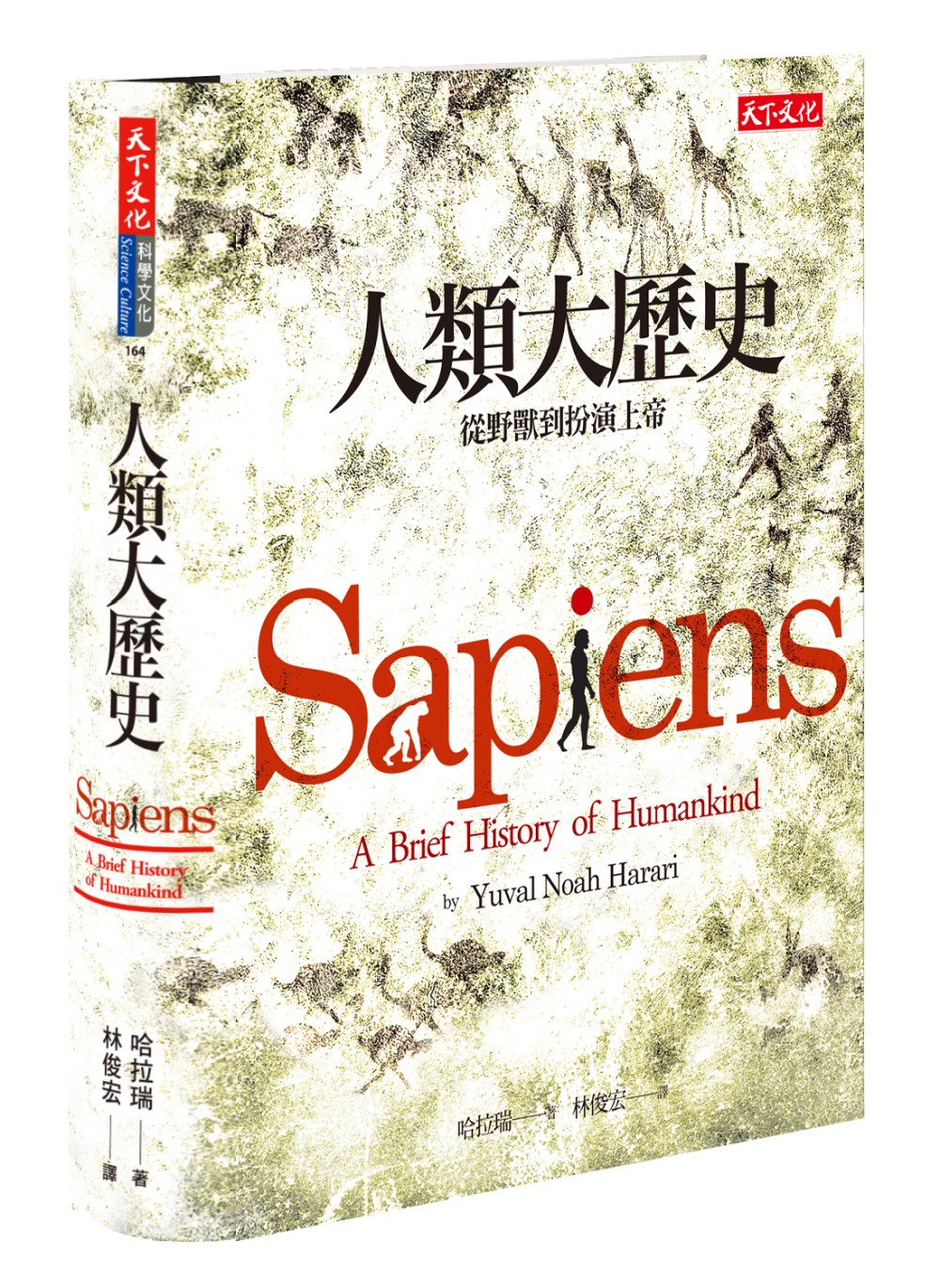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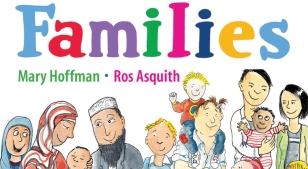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