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對於國內的古典樂迷來說,吳家恆這個名字當不陌生,除了經常在媒體或表演機構讀到、聽到他介紹古典音樂的堂奧與趣味,也能在臺中古典音樂電台、臉書粉絲頁「Music Pad 古典音樂筆記」持續接收他轉譯的音樂密碼。在他長年與音樂建立、維繫的各種關係裡,「譯者」這個角色相對低調,分量卻不得了。
《鋼琴怪傑顧爾德:天才的狂喜與悲劇》、《心動之處:先鋒派音樂宗師約翰.凱吉與禪的偶遇》、《舒伯特的冬之旅:一種迷戀的剖析》、《關鍵音:沒有巴哈,我不可能越過那樣的人生》、《早安,巴哈先生:無伴奏大提琴組曲、卡薩爾斯,與我的音樂奇幻之旅》,到近期出版的《指揮家之心:為什麼音樂如此動人?指揮家帶你深入音樂表象之下的世界》,都出自吳家恆的譯筆。雖然他翻譯的書不局限於音樂領域,但早年負笈英國讀音樂的背景,加上身兼編輯與數次經手翻譯大部頭音樂叢書,讓吳家恆成為出版界尋覓音樂類外文書譯者的最佳人選之一。


儘管曾長期在出版界任職,待過天下雜誌、時報出版、遠流出版,熟悉業內生態的他,對於要接手翻譯的書,他並不主動參與選書,而是等出版社的書稿上門。身為愛樂者,加上自認個性「很好講話」,遇到音樂類書籍,只要時間允許通常就會接,「但每一本書的問題都不一樣……」吳家恆面露苦笑,好比擺在眼前這本《指揮家之心》的問題級數,在他形容,是冰山等級。
吳家恆解釋,音樂由音符和旋律組成,不似語言有一定的客觀性,仰賴人類以感性趨近理解,要說抽象也真是抽象,也因此,用語言表述音樂的書,第一道門檻就是作者用語言這羅網捕捉空氣(音樂)的能力。面對一本音樂外文書,這道門檻譯者幫讀者先跨過,接著,就是吳家恆口中的「搬運」功夫考驗了:在把原文「搬運」成譯文的過程中,那道門檻是成了墊腳石,還是更難跨越的擋土牆?
譯過音樂大師巴倫波因(Daniel Barenboim)玄之又玄的對談,也譯過約翰.凱吉(John Cage)挾帶「美國式」禪宗思想的音樂自述,一開始,《指揮家之心》作者馬克.維格斯沃(Mark Wigglesworth)這位英國指揮家的文字給人平易近人的印象,吳家恆分析,「通常,英國作者喜歡一句即成一段,裡頭盡是複雜的子句構句;但維格斯沃的句子簡潔,我不疑有他,縱身跳入這個『平易近人』的池塘後,才發現池子深得很。文辭雖然簡練,底下承載的意涵卻很多,根本是一座意圖使人輕快撞上的冰山。」
或許是轉譯音樂的行當做久了,吳家恆非常擅用具象的比喻,為我們描摹翻譯世界裡的抽象風景,除了深池塘、大冰山,他還如此描述翻譯《指揮家之心》之難,「英國人講一句話背後含意好幾層,你翻譯過來很像搬一盤盛滿的洋芋片,一搬好幾片掉下來,沒辦法搬完全。」
既然搬的不是石頭,而是洋芋片,想來在吳家恆眼中,這精神勞動終究是有滋有味的吧?或者套用他的形容,是值得一再躍入的池塘或深潭。但,做為一個跳池塘的人,該具備哪些能力,或該選怎樣的池塘跳?除了音樂類,也合譯過犯罪心理剖析的《破案神探(首部曲)》、史學家史景遷的《大義覺迷》等不同領域,吳家恆自認,專業知識型的作品都是他勇於噗通一跳的池塘,雖然不知道有多深,但跳進去就力求適應池塘的屬性,在翻譯行文風格上有所變化,同時也要知道自己的限制,他援引翻譯名家傅雷寫給兒子傅聰的家書,該文提及某本書「錢伯母(指另一位翻譯大家楊絳)可以,我處理不來。」
吳家恆的「處理不來」,他坦承不諱,就是文學小說。他解釋,「一方面是作者的語言風格需要多所拿捏,再來,小說家多為雜學家,內容涉及知識上天下海,一旦譯者裝備不夠,就可能發生常識誤譯、貽笑大方。」而最教他卻步的,是文學小說或傳記作品難免深入人物心靈最幽闇之處,「當譯者尾隨作者文字,想盡辦法進到那世界,卻可能回不來,情緒很受影響。」講到這,他拋出的比喻是,「那邊有狗在叫,就避遠一點,免得你覺得無所謂卻被咬住了,就得跟牠糾纏一陣子……」
雖然說容易被書中人物境遇影響心情,但當初一度被其他譯者以「內容太殘忍噁心」而拒絕翻譯的《破案神探(首部曲)》,吳家恆卻毫無罣礙地接手了,也沒被書中 FBI 專家對連續殺人犯的作案細節弄得吃不下飯睡不著覺。「翻譯做為一個技藝,我比較在意怎麼把這些東西從那邊搬到這邊,至於搬的是一團血肉模糊的東西或是巧克力,不是那麼困擾我。我在意的是把原文變成另一種文字、把訊息變成另一種訊息,還是可以成立。搬不過來會困擾我,但血肉糢糊不會。」

搬運也好、跳池塘也罷,一旦鑽進原著,把訊息帶回來,安放成新的字,吳家恆的自我要求是,文字能否簡練,形成一股文氣。「我寧可字數少一點,也不要給出囉嗦的譯本。」但他隨即笑說,聽其他譯者開玩笑,但凡遇到「God」,一定譯「上帝」而捨「神」。理由不言自明,譯者稿費是以字數計……
至於聽來抽象的文氣,其實跟音樂有點接近,說的是文章的流動或內在節奏,吳家恆認為,譯者的外語能力通常可以分成兩三級,「但最後的翻譯成果,往往取決於中文表達能力。」在鍛鍊中文能力上,他和已故譯者友人彭淮棟看法一致,認為讀古文很有幫助,「古文的表達多樣性豐富,一種說法有好幾種表達方式,即使同樣的意思反覆換句話說,也不詞窮。」
「文氣可以用唸的來檢驗。如果想照顧得更好,就唸原文、再唸中文,看看中間有沒有一種對應。」他提到一位早年譯者王佐良所翻譯的培根〈論讀書〉,就是用一種俐落近似文言的構句,對應培根凝煉的行文風格。吳家恆讚嘆,「這種連韻律感都照顧到的譯文很厲害。」

說起來,吳家恆對音樂和語文的興趣,似乎都建立在聲音美感的享受上。訪談尾聲,他忽然丟出自己學習英文的「家學淵源」——他的父親在台大教授外文。正當我們要發出驚嘆,他立刻說,「不過我父親當年教我英文的方法,一度毀掉我從國中到高中對英文的胃口。倒也不是嚴苛,他只是在我連字母都還不會的時候,就直接拿一本《金銀島》原著給我讀……」
其實,這是民國初年以降許多華人知識分子學英文的方法,一如錢鍾書曾說,學習外文要一開始就接觸最好的作品,學德文就讀歌德,學西文則是賽萬提斯,義大利文當然是《神曲》……吳家恆苦笑,「這是消化能力強的人的方法,我們消化能力普通的,就是補藥吃了變瀉藥啊。」後來,他之所以對英文重新發生興趣,一是高三時老師給讀了英國小品短文,那種諷刺幽默的調調很吸引他,二是聽了莎劇《冬天的故事》錄音帶,雖然聽不懂,但英文朗誦的聲韻美感從此牽動他,讓他和英文的關係有了一線曙光,也推著他一路走成了一位「搬運」很多音樂書的譯者。
曾對父親的英文原典教學法無法適應,成為譯者後,英文卻成了吳家恆與父親的通聯棧道。兩人會一起反覆斟酌某句原文的譯法,「現在想起來,很感謝有這樣的事情,我們有了溝通的管道,要不是這樣,不見得能跟爸爸這樣對話。」雖然繞了一圈遠路,吳家恆與英文保有的各種關係裡,還是幽幽微微,繫上了一條跟「家學」彼此纏繞的線。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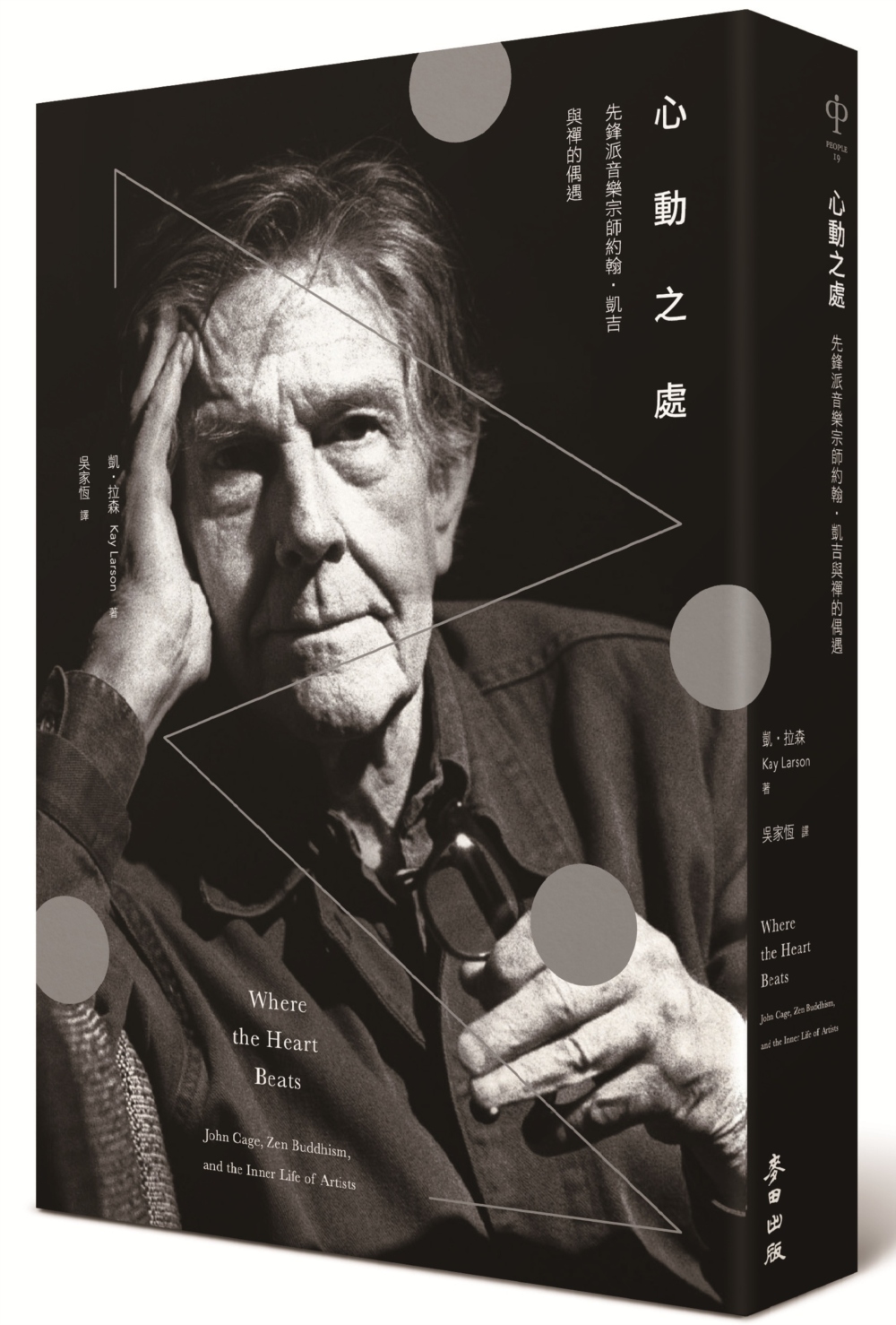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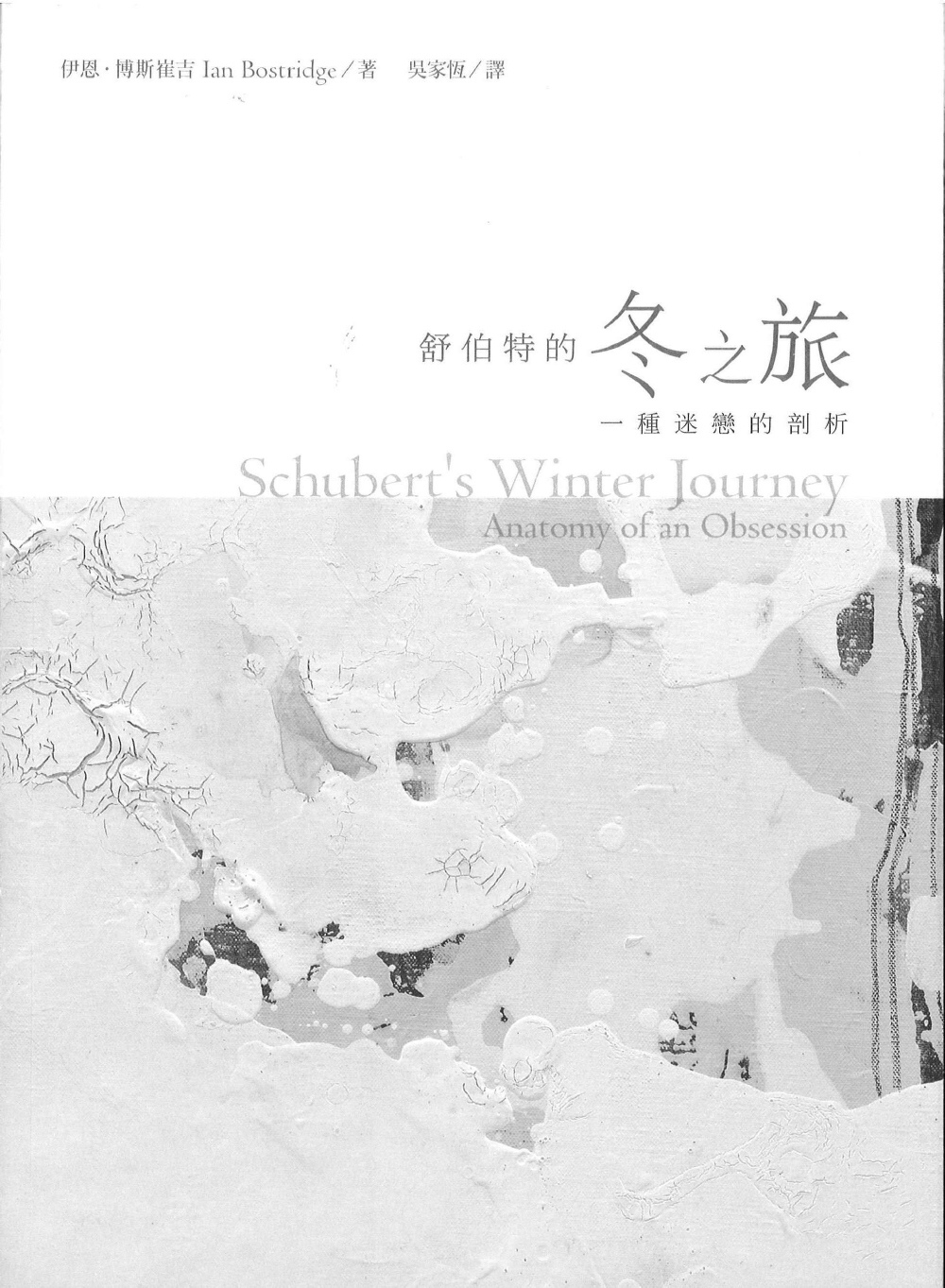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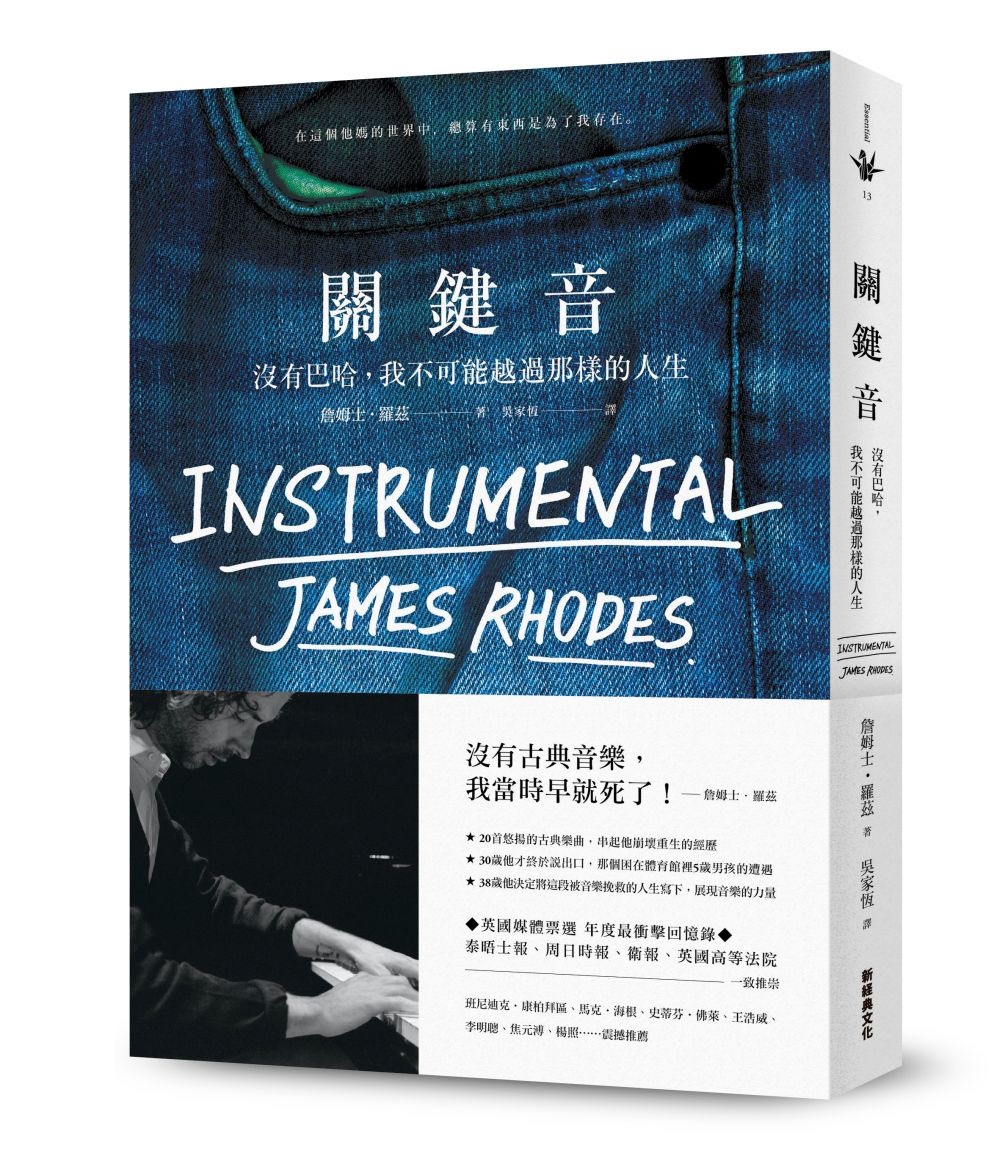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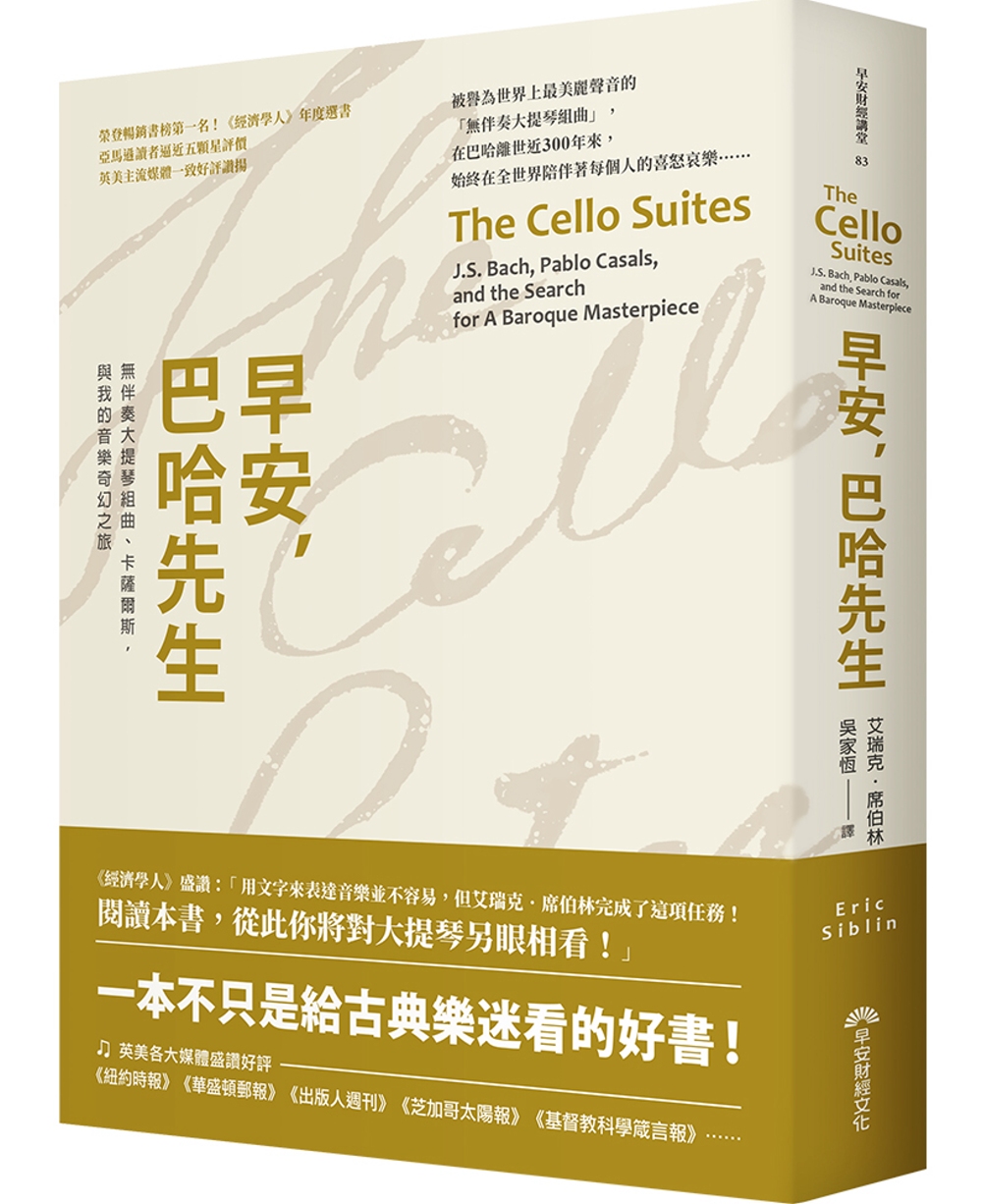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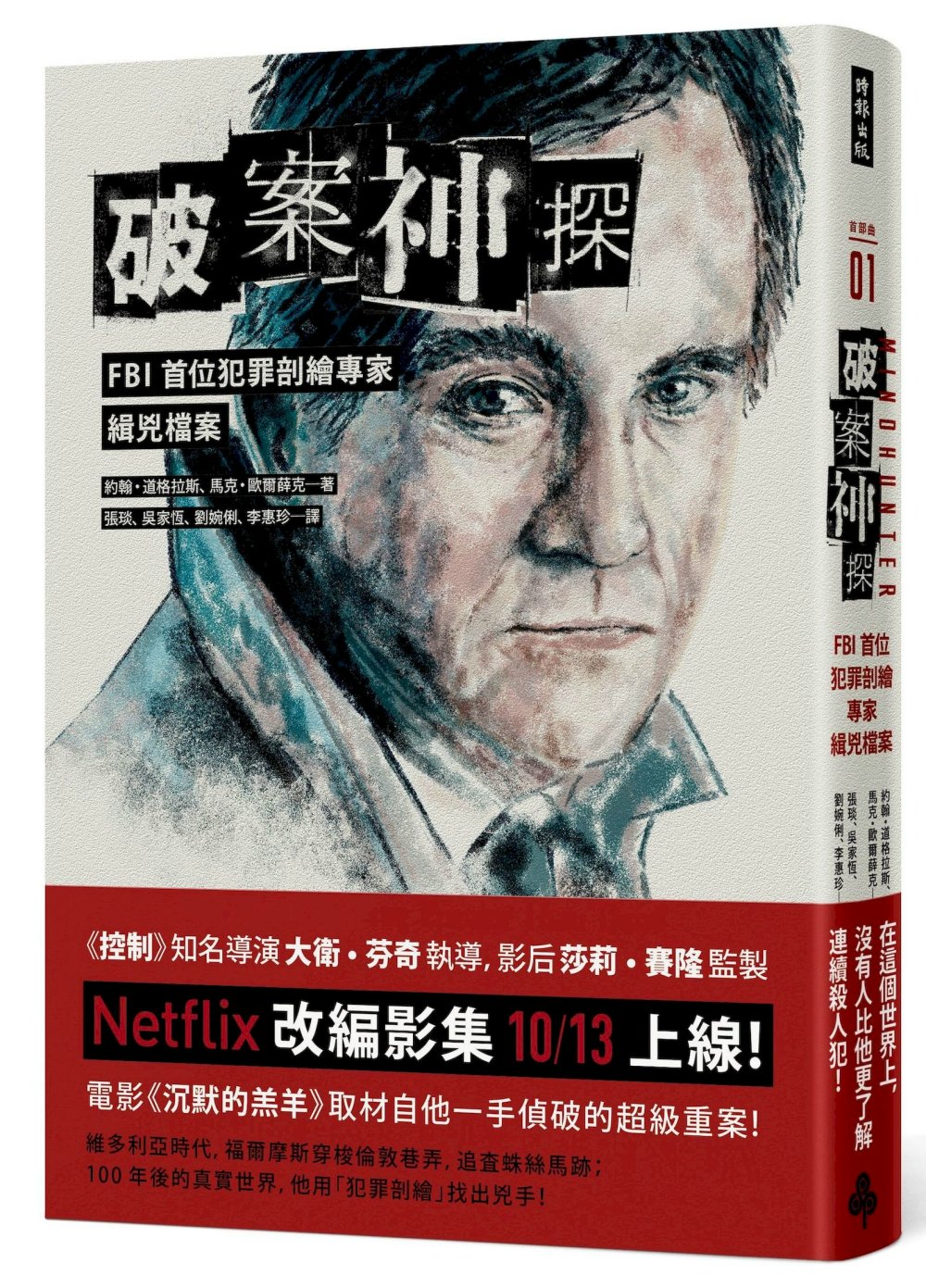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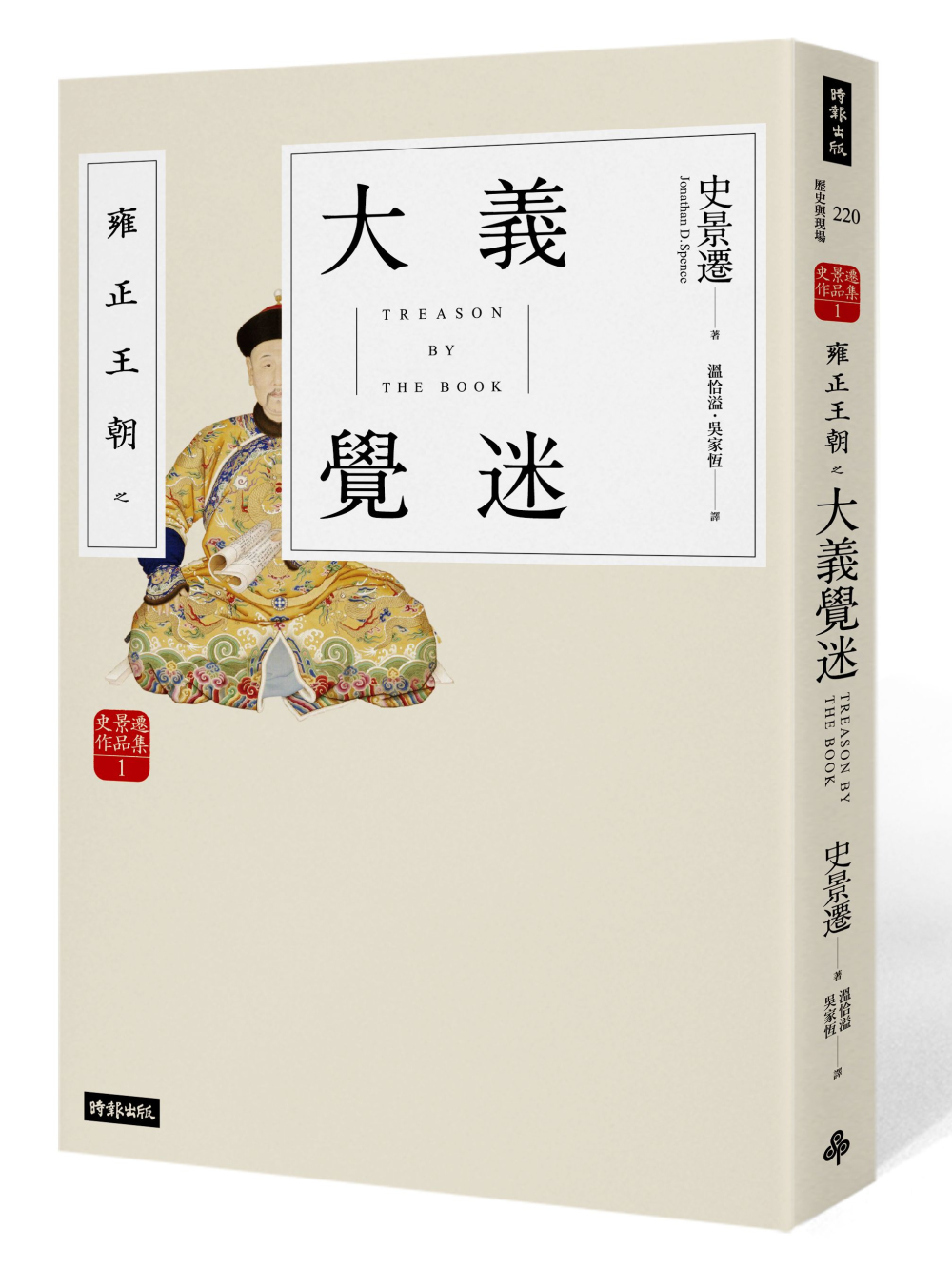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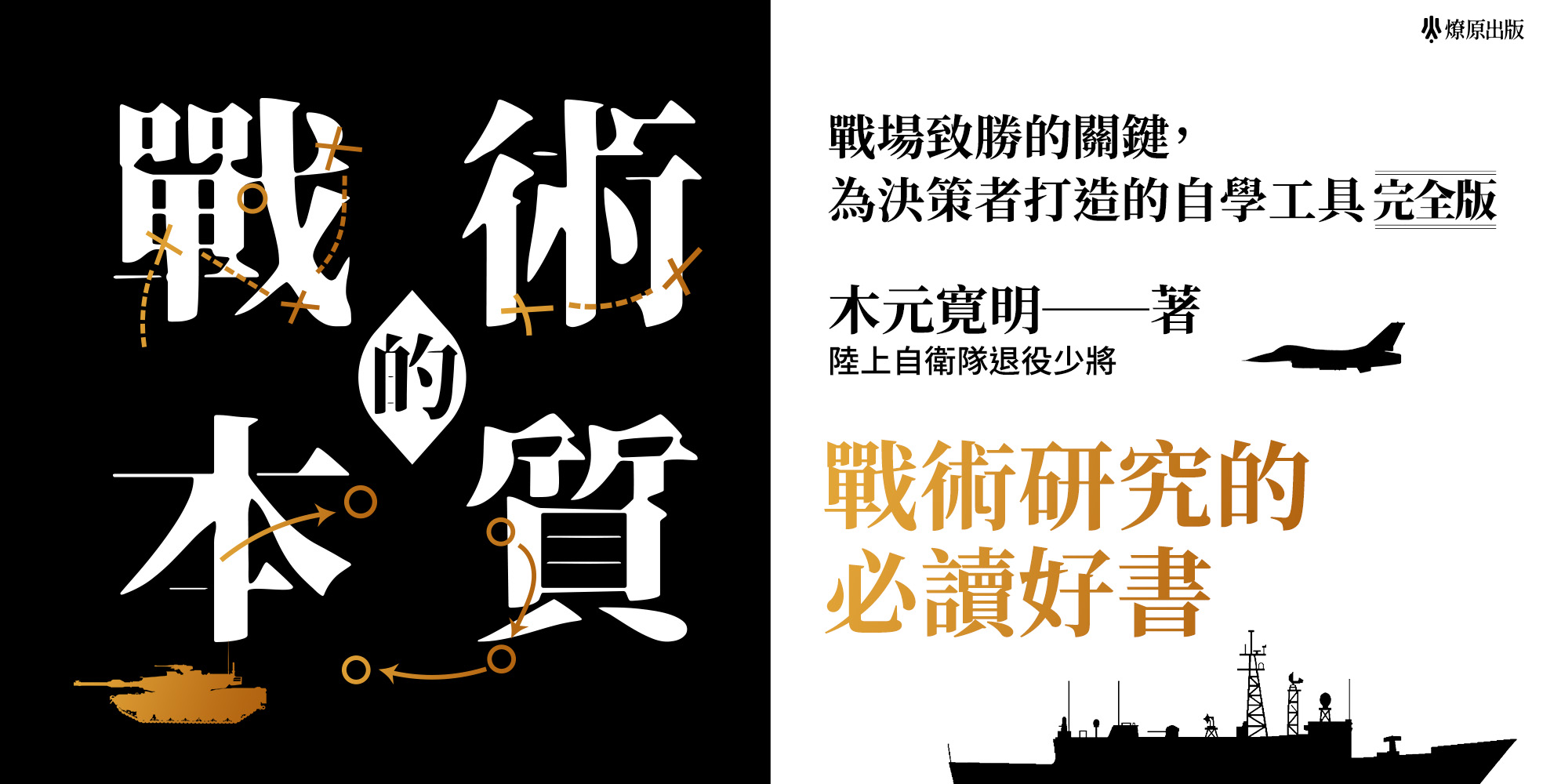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