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先是在一本在叫《單讀》的文學雜誌上讀到黃燦然的詩(後來我從他的詩集《奇跡集》獲得了某種啟發)。當時被這首寫於1998年的〈老人〉吸引:
他知道自己並不比別人特殊
讀書、工作、戀愛、結婚
退休、喪偶、孤獨、散步
沒有做過別人沒有做過的事情
沒有浪費別人沒有浪費的生命
他筆下的人物大部分就如那段詩,是「不比別人特殊」的市井小民。例如〈靈魂人物〉裡的堂叔:「同樣的話在別人口裡/只是廢話而已。小時候我就非常愛聽他說話,到三更半夜我也精神抖擻。」我感到那種「不比別人特殊」的話中話,讀了不少他的詩,就發現一切都有「不比別人特殊的特殊」。他寫一個女人從騎樓要步入陽光中:「她掏出一把折傘,打開了/才走路,彷彿她前面是一場暴雨/而不是炎陽。」從此以後我看見正要步入炎陽下的女生開傘,都會想起他這個比喻。
又有一個「不比別人特殊」的案例〈瘦竹竿〉:「我想起一個爬山者,他非常瘦/像我家鄉人們所稱的瘦竹竿........」他寫的是一個「空氣人」,一個面貌平凡、安靜、和隊友也不太交談的人──「你跟他擦身而過就像你在大街上/跟任何人擦身而過那樣自然/你永遠看不清他的面貌/因為你總是先被他那兩條腿吸引住/而且注意力再也無法收回來。」
他其實是沒有用特別的形容詞,句子也很普通,就直接寫「她的小腿特別性感」、「都是那麽美、那麽有活力」等。讀詩的人大約都會發現詩至少分兩種(當然這是很粗略的說法):一種用地上的話寫;一種用外太空的話寫。在《波赫士談詩論藝》這本小小的演講集裡,一段小小的話就可教大家怎麽看詩的好壞:
大家通常把它(詩)區分成平淡樸實與精心雕琢的風格,我認為這種區分方式是錯誤的。因為重要而且有意義的是一首詩的死活,而不是風格的樸實或雕琢。
(頁115,〈詩與思潮〉)
波赫士在後面舉例,兩種類別各有好詩,有白話型卻很震撼的,也有古文型令人背脊一涼的。重點是寫「死」還是「活」。讀者感受到是「真」的還是「假」的情感。
除了寫人物,還有「不比別人特殊」的小事,透過一首詩完成他的「靜思」,例如〈阻礙〉寫出門時遇驟雨,到咖啡店坐坐避雨,這是大雨帶來的「阻礙」。他這樣解:回到街上時看見雨已經停了/街上被清洗得一乾二淨/才驚覺你剛才避過雨/生活也是這樣,當它阻礙你/擠壓你,你就在你身邊、在那阻礙附近/休息一下,順便找點事情做……當你回到原來的軌道上,你將驚覺/發生過的事情好像沒發生過……
我也很喜歡他的那些「不比別人特殊」的「靜思語」,例〈鼓勵〉:
所以對於絕望的人我鼓勵他更絕望些
對於滿懷希望的人我鼓勵他滿心也希望
對於沉默的人我說還可以更沉默還有更沉默的
對於愛說話的人我說你說得還不夠
他並不是表面上在玩押韻、玩對比。絕望又再絕望?沉默又更沉默是什麽意思?我後來看到李修文這篇〈羞於說話之時〉又想起了他說的「沉默又更沉默」:
(前略)我一直記著這句話,記了十幾年,但是,卻也愛恨交織。它提醒我,當造化、奇境和難以想像的機緣在眼前展開之時,不要喧嚷,不要占據,要做的,是安靜地注視,是沉默;不要在沉默中爆發,而要在沉默中繼續沉默。多年下來,我的記憶裡著實儲存了不少羞於說話之時:聖彼德堡的芭蕾舞,呼倫貝爾的玫瑰花,又或玉門關外的海市蜃樓,它們都讓我感受到言語的無用,隨之而來的,是深深的羞愧。
我們讀完〈鼓勵〉全詩,也留意最後一段:
對於想從事詩歌和藝術的人,我鼓勵:
生活美好,但詩歌和藝術更美好。
對於想退出詩歌和藝術的人,我鼓勵:
詩歌和藝術美好,但生活更美好。
勤勞或懶惰,靈魂潔白或烏黑,
都正常,不是因為存在就合理,
而是因為不合理也存在。
我永遠站在正面一邊,
我永遠正面,哪怕在負面和消極中
我也在正面和積極中,但我背後就是負面,
正面就是背對但承認負面。
當我走向你我們都是正面,
下一刻我們都是負面,
我們都向後望時我們又都是正面
同時又處於負面中。
我有時候加上或不加上這一句:
只要你目標清晰,並因為你這決定和行動
而更加清晰。
不加,因為無目標、混沌、猶豫
和不行動,也非常美好,像躺在床上
既不睡覺也不起來,醒著或半醒著,
而屋外下雨或陰天或陽光普照。
所以對於絕望的人我鼓勵他更絕望些
對於滿懷希望的人我鼓勵他滿心也希望
對於沉默的人我說還可以更沉默還有更沉默的
對於愛說話的人我說你說得還不夠
我還可以一直這樣說下去,
最後變成沉默,而沉默
滔滔不絕,浩瀚如海……
本名不重要。出生於大馬。高中畢業後赴台灣迄今。
美術系卻反感美術系。停滯十年後重拾創作。
著散文《帶著你的雜質發亮》《我不是生來當母親的》《沒有大路》;
詩集《我們明天再說話》《我和那個叫貓的少年睡過了》;
繪本《馬惹尼》、《詩人旅館》、《老人臉狗書店》等數冊。
作品入選台灣年度詩選、散文選。另也在博客來OKAPI寫繪本專欄文。
偶開成人創作課。獲國藝會視覺藝術、文學補助數次。目前苟生台北。
Fb/IG/website keyword:馬尼尼為 maniniwei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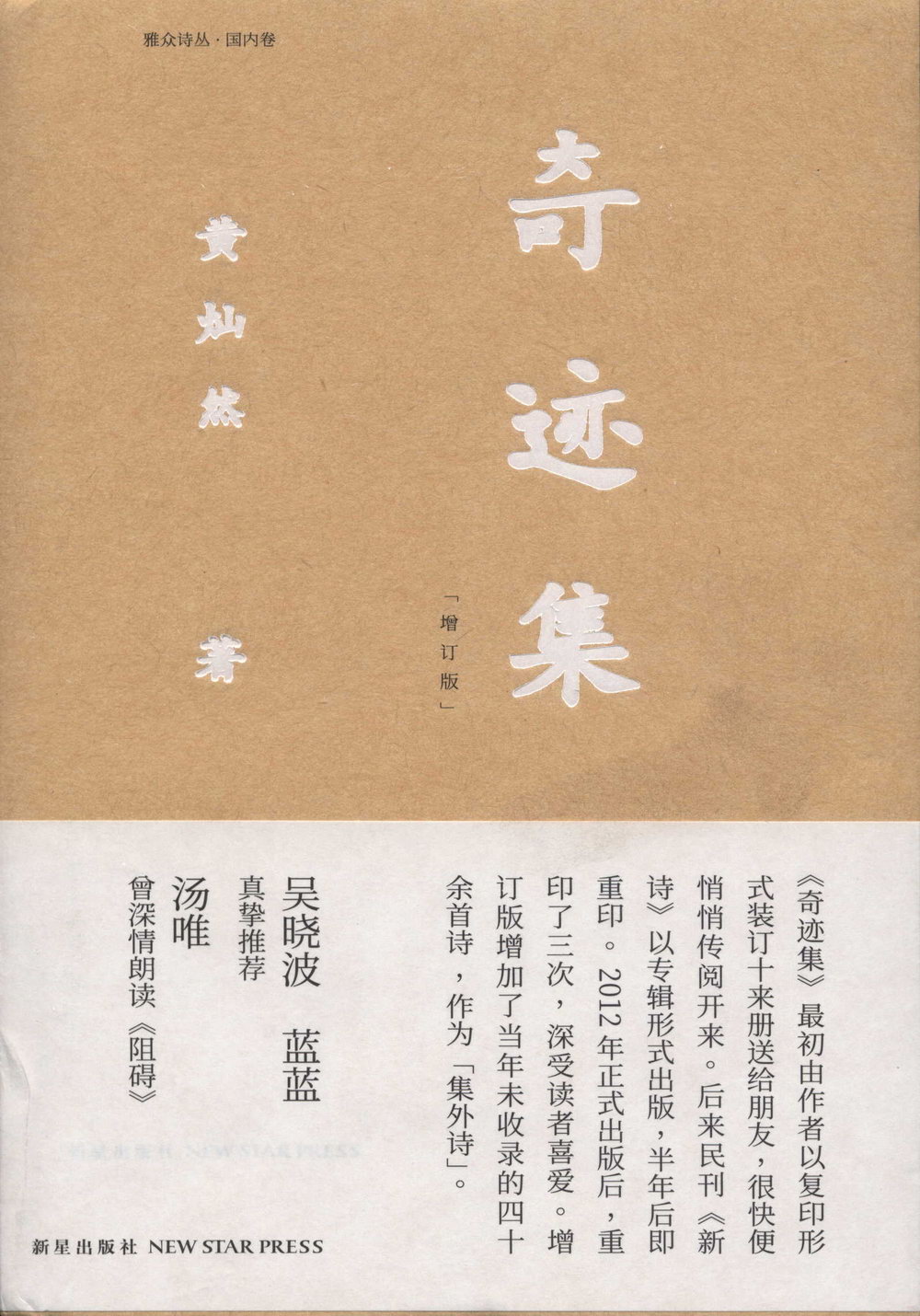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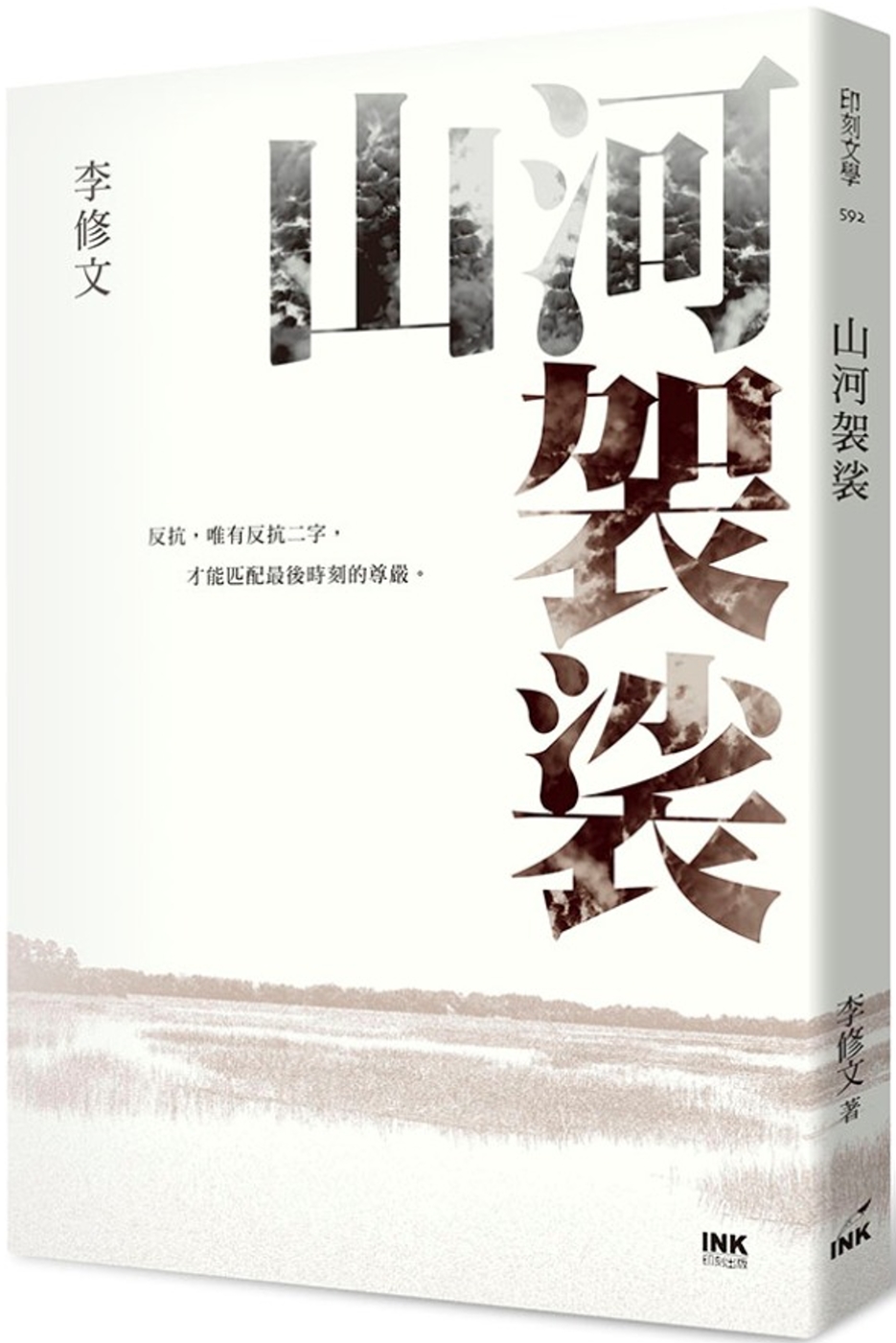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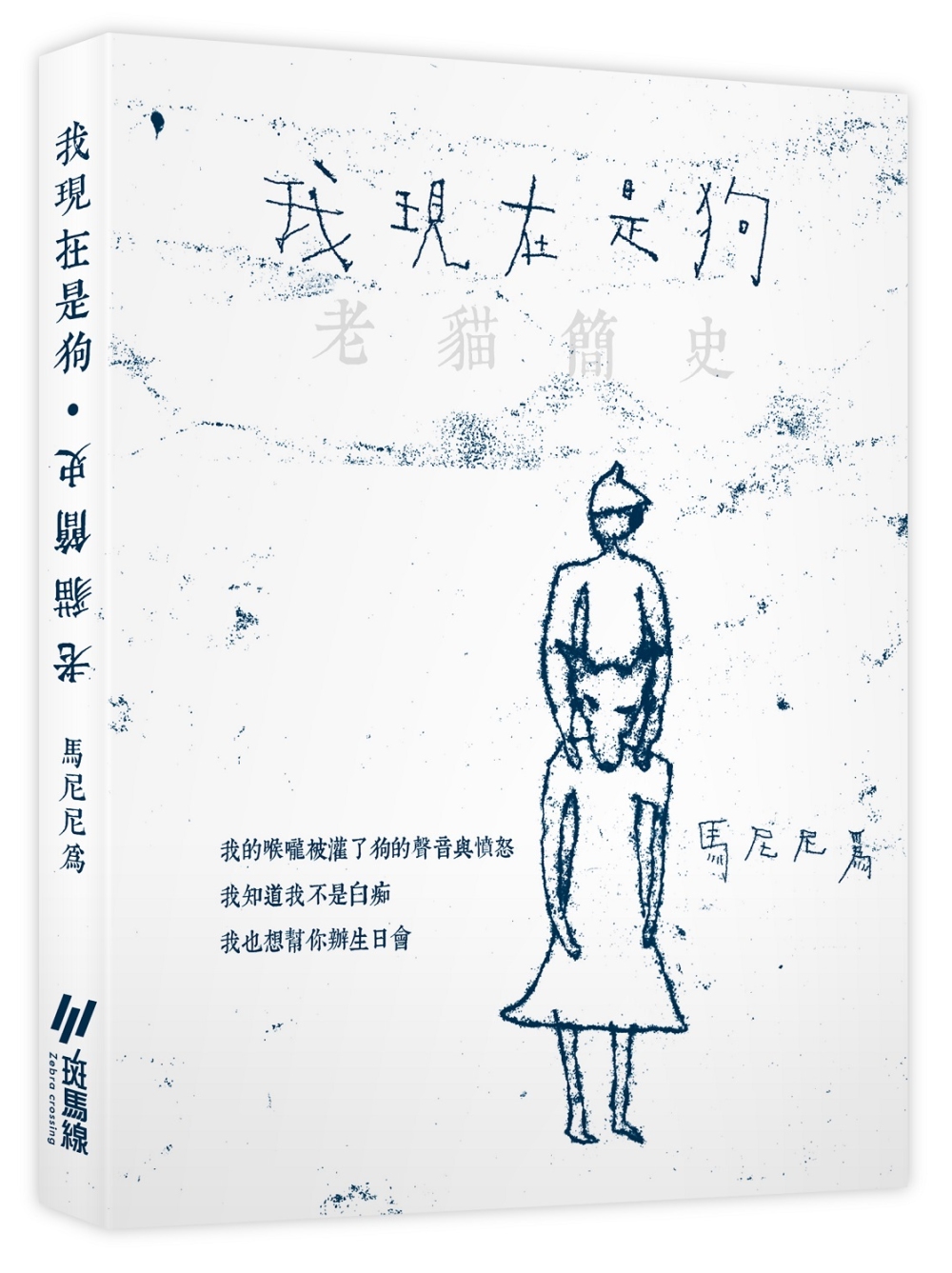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