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論東西方哲學都有個古老命題:人活著就是受苦。若要問,是什麼支撐著人在苦難中繼續生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答案。
澳洲小說家馬格斯.朱薩克(Markus Zusak)2005年以《偷書賊》回答過一次:是閱讀,或者說是文字的力量。
時隔13年,馬格斯.朱薩克又以《克雷的橋》再次回答,這次他藉由回歸西方文明的起點,希臘,告訴讀者:悲劇本身就能提供解答。
小說的主角克雷是鄧巴家裡排行第四的男孩,他們的父母麥可.鄧巴與潘妮洛普.鄧巴總共生了五個,都是男孩。
鄧巴家的五個男孩養了五隻寵物:騾子阿基里斯、金魚阿伽門儂、虎斑貓海克特、牧羊犬蘿希、鴿子泰勒馬庫斯。除了蘿希以外,其餘俱是希臘史詩《伊利亞德》、《奧德賽》裡的傳奇人物──是什麼原因讓澳洲雪梨郊區小城的一戶平凡人家孩子給寵物取這些名字?
即使那牧羊犬之名蘿希,也是出自《伊利亞德》,原是形容黎明時天空的顏色如同玫瑰一般(Rosy),荷馬以擬人化的說法寫出來,鄧巴家最小的兒子湯米還以為是人名,潘妮.鄧巴向他說明後他便記住了,日後給牧羊犬取這名字時便有懷念母親為他講述這一刻之意。
這些出現在鄧巴家裡的希臘文化的源頭正是來自母親潘妮洛普.勒丘什科(日後嫁給麥可改冠夫姓鄧巴),冷戰的年代她出生在東歐紅色鐵幕這邊,她的母親在生下她後便即過世,是父親一手帶大,這嚴厲的父親教給她兩件事:讀這兩本希臘史詩,以及彈鋼琴。後者讓她得有機會出國比賽,在一次又一次出國回來讓上級領導感到放心之後,最後一次父親偷偷在她行李箱裡放進這兩本書以及一個信封,裡面有一疊美金及一封信,要她無論如何都不要回來。
讀到這裡一股歷史的沉重感便襲上心頭,讀者很難不跟著潘妮洛普在火車上一路哭到維也納。
然而這只是故事的開始,成為難民的潘妮洛普輾轉來到地球的另一端澳洲(離家萬里遠),結識了在地男子麥可,夫妻倆一起生養了5個男孩,打造了鄧巴家庭。看起來是移民奮力打拚在異鄉開創幸福的血淚故事,但這樣想只對了一部分。
鄧巴家的老大馬修是故事的敘述者,他一開始就不斷明示暗示讀者:「我們的母親過世了,我們的父親逃了」,甚至以「過來人」及「預言者」的口吻說接下來還有什麼事情將要發生,或者何種厄運將會在第幾章降臨。
整部小說這樣寫的用意,很明顯是希望讀者透過馬修的角度來看命運如何施加在他們這一家父母及五兄弟身上的歷程,馬修既是當事人,大多時候也是旁觀者,他是最懂事的老大,也是父母都不在之後撐住鄧巴家的支柱;然而不要忘記馬修的成長教養也是來自父母──尤其是母親潘妮洛普。潘妮洛普的成長教養則是來自父親,而他只教給潘妮洛普兩件事:讀那兩本希臘史詩,以及彈鋼琴。
既然五兄弟在鋼琴上的造詣沒人能及得上母親分毫,反過來看那兩本希臘史詩則是影響鄧巴五兄弟最大的因素了,因為那已成為他們與母親最深切的連結,沒有之一;鄧巴一家的命運就此與希臘史詩所帶出的種種關於歷史及悲劇的哲學緊密聯繫──相信這也是作者的用意。
「悲劇所一心關注的是苦難。」伊迪絲.漢彌爾頓在《希臘之道》一書中如此說道,然而並非所有苦難都是悲劇,「唯極能忍受苦痛的靈魂之受苦,才是悲劇。」
從這點來看,相當程度說明了為何馬修是最適合的敘事者,因為在整個鄧巴家族的苦難歷史中,最能夠體現希臘悲劇意識的應屬這四個人:母親潘妮洛普萬里流徙的遭遇自不必說,但後來卻因病過世(臨終時另有蹊蹺);父親麥可同樣也歷經滄桑,卻不是身體的,而是感情及心理的,潘妮洛普的過世對他是沉重的一擊,他因自我放逐而離家,造成兒子們心懷怨恨;最能理解他的則是老四克雷,也是克雷最先重新接納父親,並且願意與父親一起打造那座「克雷的橋」,但他們都是經歷苦難傷痛而默默承受卻同樣失語的靈魂(克雷也要等到失去親密愛侶凱莉之後才更能理解父親),因此無法述說;只有在克雷之後、理解了這一切的老大馬修,才能夠重拾祖母的打字機,將上下三代的家族故事一絲一縷娓娓道出,至於其他三兄弟,雖也各有其重要的象徵位置及功能,但如果從他們的角度來看,鄧巴家的苦難就未必是悲劇了。
在造橋過程中,克雷問學美術出身的父親為何對米開朗基羅的大衛像情有獨鍾,麥可說「那些扭曲而掙扎的軀體,他們拚了命想脫離石頭」,他一直想發掘出這種偉大的美,其原因卻一時如哽在喉說不出話來。
「我們過的是囚徒們的生活。」克雷代他說出來。
這就是鄧巴父子乃至鄧巴一家的悲劇,生活中的所有悲苦喜樂若抽離來看都是平凡的日常,並且「家家有本難唸的經」,但他們必須從有如土石泥淖的生活中打造出自我來,才能超越命運加諸其身的悲劇,這非有一個「希臘的心靈及精神」不能做到;正如同漢彌爾頓在《希臘之道》所說:「希臘心靈從不單獨而孤立地看一件事物,而總是把它與更偉大的事物連結在一起,希臘精神則從每件獨立的事物中看出美與意義來;這心靈與精神兩者創造了希臘悲劇,也創造了希臘雕刻與建築。」此所以克雷父親在經歷了那一切後不是再拾畫筆,也不是從事雕塑,而是要去造一座橋,而唯一能夠體會並理解他的克雷便選擇加入。
造橋其實只是一個象徵,似乎如此可以把親愛的家人連繫起來──就還活著的家人而言的確是如此,但對已逝的家人這就完全是徒勞的,所以在造橋的過程中仍然得保持這種痛苦的覺知,這是為何克雷在造橋的過程中三不五時得回家,在後院曬衣繩下緬懷母親(她過世之處),在褲袋裡總是藏著一個曬衣夾──為了記掛著母親臨終的那一刻;最重要的,是爬上自家屋頂(後來也帶女友凱莉一起上去),看著那個他們成長的小城,試圖感受超過他們生活範圍之外的世界,此舉別具深意:「若對超過我們掌握之外的無限廣袤沒有一點感受,最後我們能成功傳達的只是苦難──而非悲劇。」卡爾.雅斯培如是說(《悲劇的超越》)。
馬格斯.朱薩克的前作《偷書賊》全世界熱賣,還曾改編成電影,成績不惡;《克雷的橋》重建一個移民家族的史詩企圖心更大,特別是文字敘述的畫面感十足,改編難度在於多線交織可能過於複雜,但若有機會剪裁精煉,相信會是一部深刻動人的電影,我非常期待。
詹正德
影評人686、前有河book書店店主、友善書業合作社前理事主席、《閱讀的島》前總編輯,著有影評集《看電影的人》,曾獲2016台北國際書展大獎。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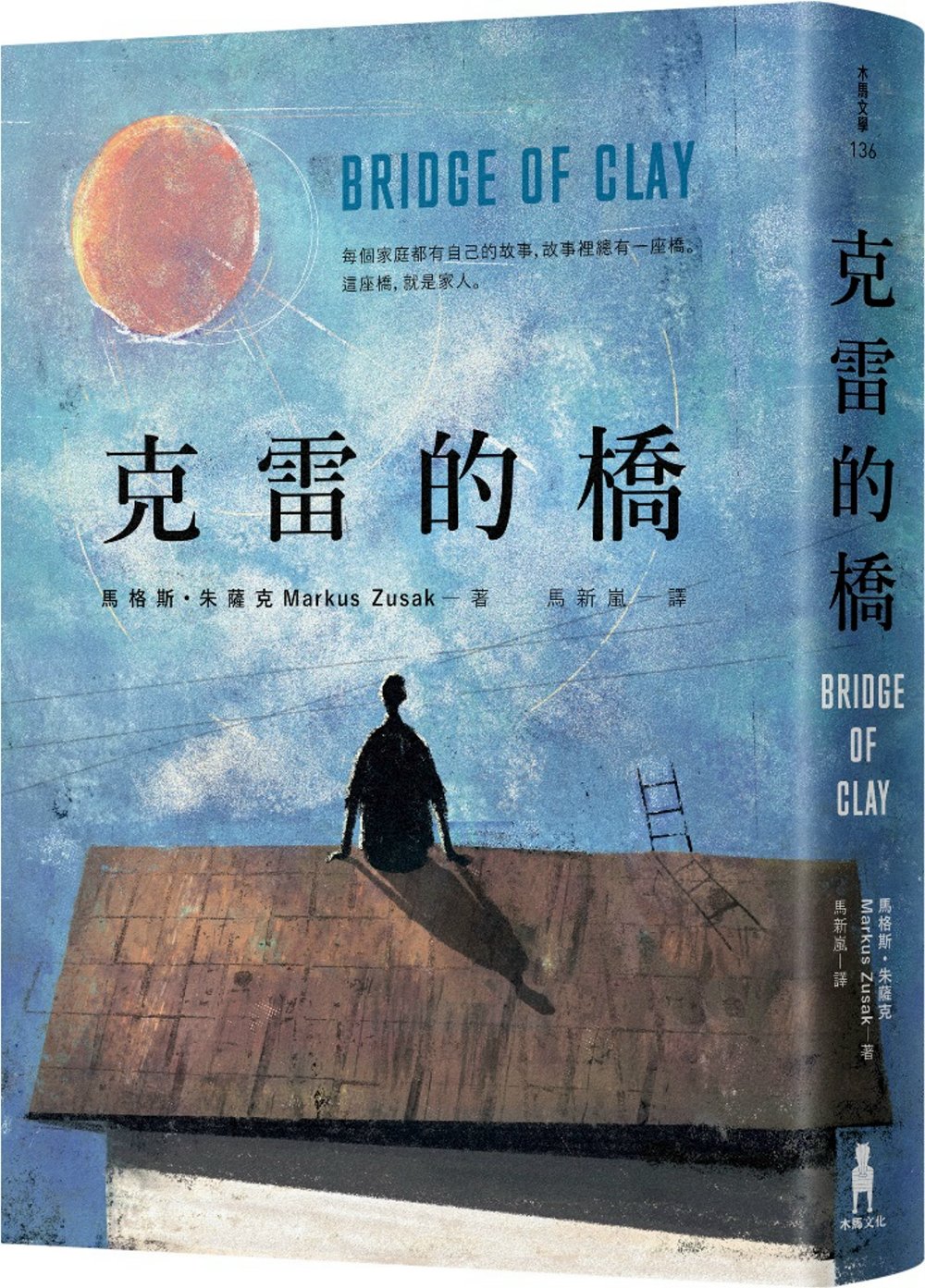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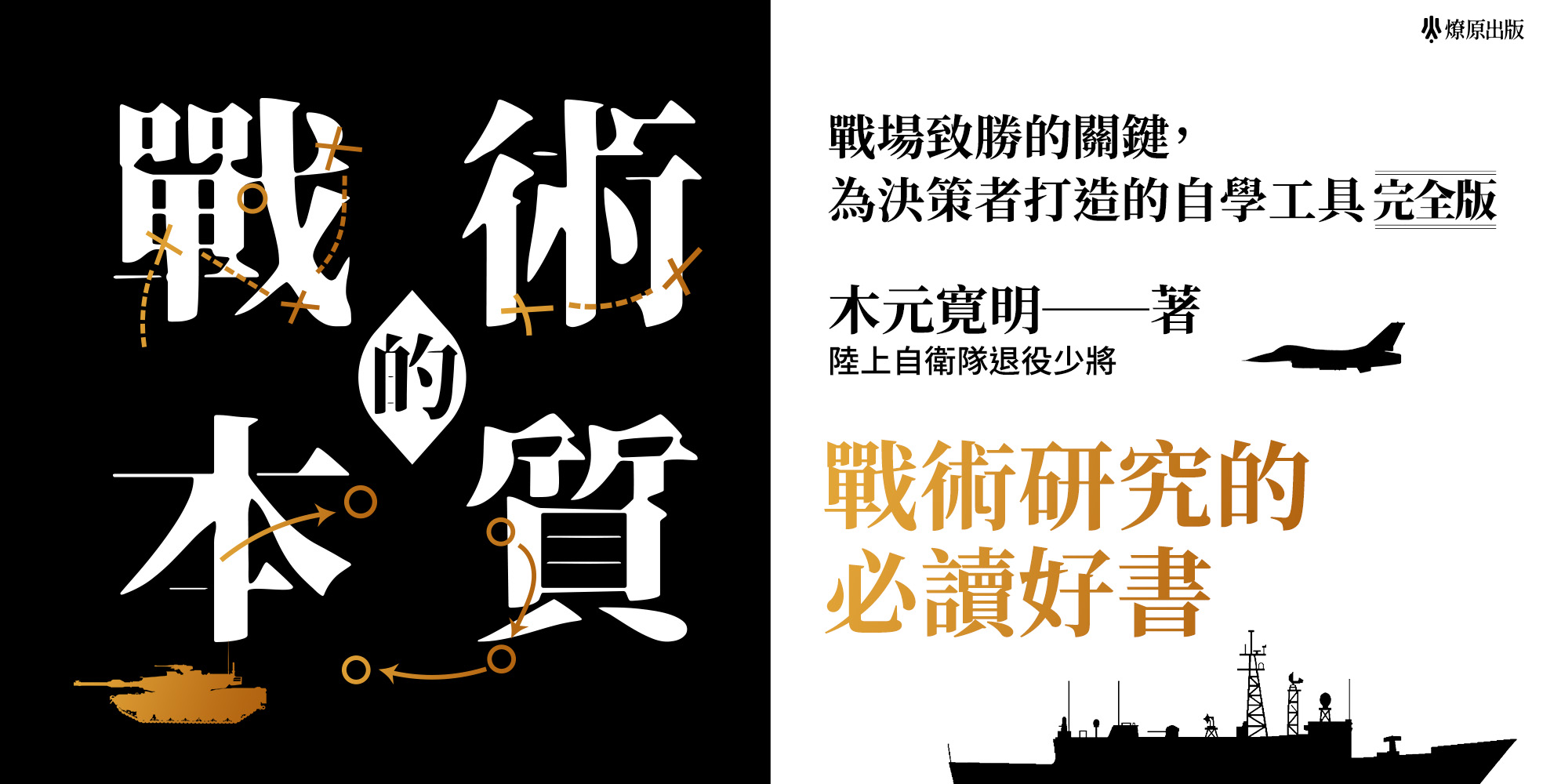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