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這世界啊!我沒有什麼本錢跟你齜牙裂嘴的搏鬥,
但我仍有一支筆來當小刀,以為陰暗可以被我劃出一道一道縫隙來。讓那裡透出來稀微的光,能刺眼出我久違的眼淚。
一起敬這殘酷又美好的世界吧!
它被我們搞壞了,但我們仍有傾斜看它的角度,一眼認出它曾經的美好,於是抱得滿懷,即使即將失去。
這就是電影存在的理由,紀念我們所有可能失去的美好,還有我們曾經被拍下的純真。
※本文可能有劇透,請斟酌閱讀 這電影其實更像是一個寓言故事,有一個男子歸鄉後,鑿著父親那個冒不出水的井,日復一日,人們譏笑著,然而希望就是個丑角,它是每個畸人的心臟。
這電影其實更像是一個寓言故事,有一個男子歸鄉後,鑿著父親那個冒不出水的井,日復一日,人們譏笑著,然而希望就是個丑角,它是每個畸人的心臟。
你看,山嶺上有一棵野梨樹,它結的果實沒有經濟效益,它天生就長得歪脖子一樣的,沒有觀賞價值,跟它生長的家鄉恰納卡來一樣都是被人遺忘的確切存在,生在旱地裡也能獨自活著,且到處都是,果實雖醜卻滋味甘美,但誰會去吃呢?
這時代,誰不在自言自語?主角穆南則像許多寫書人,絮絮叨叨他想的一切,即使對面有人,他的話語能被聽到的內容仍極其有限。不只是他,我們的天地首次如此遼闊,沒有牆壁也沒有門,每個人都在這遼闊的房間裡,對著看不到的牆壁,自言自語著。網路就是樹洞,人講個不停,浸泡在自己的話語海裡,每個人的聲音都飄不到彼岸。
而這部電影,以一個生存嚴峻的偏鄉環境,記錄一個寫字旅人的返鄉,同時驗證了他此生旅程的無窮盡。
這部電影長達三個小時,你會看到一個想寫書的人,已習慣所有的碰壁,在文學的法力快速弱化之際,他們像窮途末路的魔法師,即便是暢銷作家,如今也只能以寥寥的魔法,讓人回憶起很久以前天空還有星辰。
轉瞬間,那只像煙花,因為跟生活都無關了,跟能幫人醉生夢死的那些都沒關,很快的就成為一個傳說,一個傻子會做的事。你會想起很久以前塔可夫斯基電影《鄉愁》裡那個在廣場上自言自語的多明尼克,講著雖是智慧的言語,但正因如此而看似更為愚痴。
這故事很美,雖然寫實,但更像一則寓言,一個乳臭未乾的小子穆南,想出他第一本書卻沒資金,返鄉想籌錢圓夢,但長大後,眼中的家鄉貌似更往邊緣推了,一鎮只剩老老小小的,日子是拖拉的過,生活的擔子壓得人臉皺鬆鬆。
在這邊還保有夢想本就是非常奇幻的,如穆南去找地方官與採石場的商人談論可否出資幫忙出書,採石場那商人在地方上向來以愛讀書聞名,穆南看著他辦公室裡空有書櫃,但幾本書像裝飾品,彷彿有錢之外還需要有點更特別的,他看穆南如同化外之民,固然不想出資,但臉上的嘲笑怎麼也藏不住。
那裡的年輕人盤算著未來只能考小學教職與防暴警察兩條路。穆南說他要出書跟他父親說要挖口井一樣奇怪,看不到實際效益的努力,讓他們像到處招人嫌的野梨樹一樣,被視而不見。
最美的一幕是穆南遇到以往的女同學哈蒂杰,顯然是他曾心儀的女孩,她幫著母親提水,躲在梨樹下與他抽根菸。就一根菸的時間,一陣風大到不行,把那漂亮女孩的頭髮給吹亂了,像大量的眼淚流過一樣,推翻了他們之前若無其事的問候,女孩無法讀大學,知道男孩認為這裡的人都等著腐敗。這是沒希望的小鎮,她心知肚明跟這心儀的男孩沒有結果,也不能提什麼心意,只說了一句:「我將嫁給珠寶商,一個你不認識的人。」穆南問她那她的心怎麼說,女孩回她的心很久沒跟她說話了。
趁著那陣風,女孩吻了他,把他嘴唇咬破,像為自己的初戀告別,至少讓對方記得一陣麻疼,男孩從剛剛就看傻了,像看著故鄉裡最美好的風景,但也就一根菸的時間。他目送著女孩走了,再看到也就是他老遠看她出嫁時的身影,新郎看似長他們一輪的男性,將車開遠,一群男孩都看著不捨,誰也娶不到她,那地方僅有的是窮,她是必須出城的。
 一陣風大到不行,把那漂亮女孩的頭髮給吹亂了,像大量的眼淚流過一樣,推翻了他們之前若無其事的問候
一陣風大到不行,把那漂亮女孩的頭髮給吹亂了,像大量的眼淚流過一樣,推翻了他們之前若無其事的問候
故事繼續很美地拍攝,是因那裡的貧瘠,讓夢都做不完整也做不完,讓生活多幾分恍惚,以為殘酷之後總有點別的。
於是錫南即使看起來再不濟,他的眼神下的故鄉除了朝生夕死外總還有些別的,他跟許多提筆的年輕人一樣有憤怒、有想挑釁的,更多的是有點天真,但他還有個特質是他真跟自己過不去,這點比起才華,其實更接近文字。
那就像有神從天上丟下一些文字的種子,那些樹發育不全也營養不良,但本質非常粗礪,穆南跟野梨樹一樣看來非常不討喜,窮酸賭氣,不像書封上那些作家,一身長大衣,保持滄桑與智慧的眼神,像個浪漫的當代展示品。那點展示氣息,就像過了好時期的美,反而告知人們別太靠近的那種諷刺美。
他沒有,他就是沒有被磨過的粗糙原石,滾熱又刺人的不知怎麼好,沒有風雅可以妝飾人間,文人沒有那些供人想像的雅趣,簡直就像耶誕節沒有那些紅綠沒了賣點。他就跟文字一樣老死,跟文字一樣是他爸那挖不出水的井裡大石頭、跟文字被奚落但飄飄走走的好像孤獨。那種跟自己過不去的特質,表面上酸苦別人、嫌棄他不成材的父親,他討厭家鄉如討厭自己,他想寫字,因為寫字其實是跟自己溝通。
 他就跟文字一樣老死,跟文字一樣是他爸那挖不出水的井裡大石頭
他就跟文字一樣老死,跟文字一樣是他爸那挖不出水的井裡大石頭
穆南那些不討喜的逞強與成長,映照到我們。人都說青春美好,其實青春正是自卑與自視甚高的巔峰期,他四處衝撞出大人的答案,一位資深作者跟他說:「你太天真了,這世界不是只有一個現實。」「不是你寫的東西,而是你如何寫,到處都是題材,只有作者可以看到它。」「就去寫,不需要有藉口。」那些自憐與自傲的都不是什麼寫作理由,只是你生來就是個孤單的歪脖子樹。
穆南也與宗教人士碰撞,他追求先知的精神,對方跟他說:「每個人都忙著逃避現實,每個人忙著救自己,你如何確定人們真正想要什麼?」他把自己的不得志都怪罪外界的醜陋、怪他父親自暴自棄,他母親含淚說:「所以你了解一切,而我們都不懂?」
直到後來他後來看到父親貼了尋狗啟事,以退休金還債,自己獨居,才接受他因與父親心性相像而討厭對方的事實,「只有狗不評斷我。」他父親說。「當我十六歲時,其他人都在談錢,只有你父親跟我談田野的顏色。」他母親說,後來她寧可他俗一點,家裡最好一本書都別留,因她要承擔的是這只剩生存的鎮上人都將這對父子當成瘋子,一個在枯地上想挖出有水的井;一個想寫書。
最後這對父子兩人在這看似盡頭的地方坐著,前方有著那個雖有青蛙卻沒水的井、有著歪脖子的野梨樹。父親是唯一細細看過錫南寫的書的人,他說:「如果你喜歡你做的事,在哪裡都可以活。」只是想除了活著,還想貪點希望的兩人,認知了自己的不適應與孤獨。
 只是想除了活著,還想貪點希望的兩人,認知了自己的不適應與孤獨。
只是想除了活著,還想貪點希望的兩人,認知了自己的不適應與孤獨。
父親承認自己失敗了,兒子則開始在挖井,是幻影還是真實?下字幕時,你仍聽到錫南鑿井的聲音,希望彷彿就要冒出來泉水來了,如同文字能在某些誰的眼中死灰復燃。
這是一個寓言故事,有一個男子歸鄉後鑿著父親那個沒有水的井,日復一日,人們譏笑著他們,然希望是個丑角,它是每個畸人的心臟。
如果2013年的《絕美之城》是在目送藝術與文學最繁茂的光景, 2017錫蘭執導的《野梨樹》則是文學種子灑於荒地上,無論隨風吹散還是能生根,長大了的都是棵野梨樹,如電影文案所寫的:「果實畸奇,但果肉甜美」。
 《野梨樹》
《野梨樹》
《野梨樹》(The Wild Pear Tree)是一部2018年劇情片,入圍第71屆坎城影展官方競賽單元。入選第71屆坎城影展主競賽片。曾以《冬日甦醒》摘下金棕櫚獎的土耳其導演努瑞貝其錫蘭新作,電影探討父子間難以割捨的連結,故事描述一年輕人錫南為出書返鄉籌錢,迎接他的卻是父親的龐大債務,一心圓夢的他,是否能化解與父親的水火不容。由攝影師轉執導筒的錫蘭,錫蘭電影風格優雅詩意,人性刻劃入木三分,曾五度入圍坎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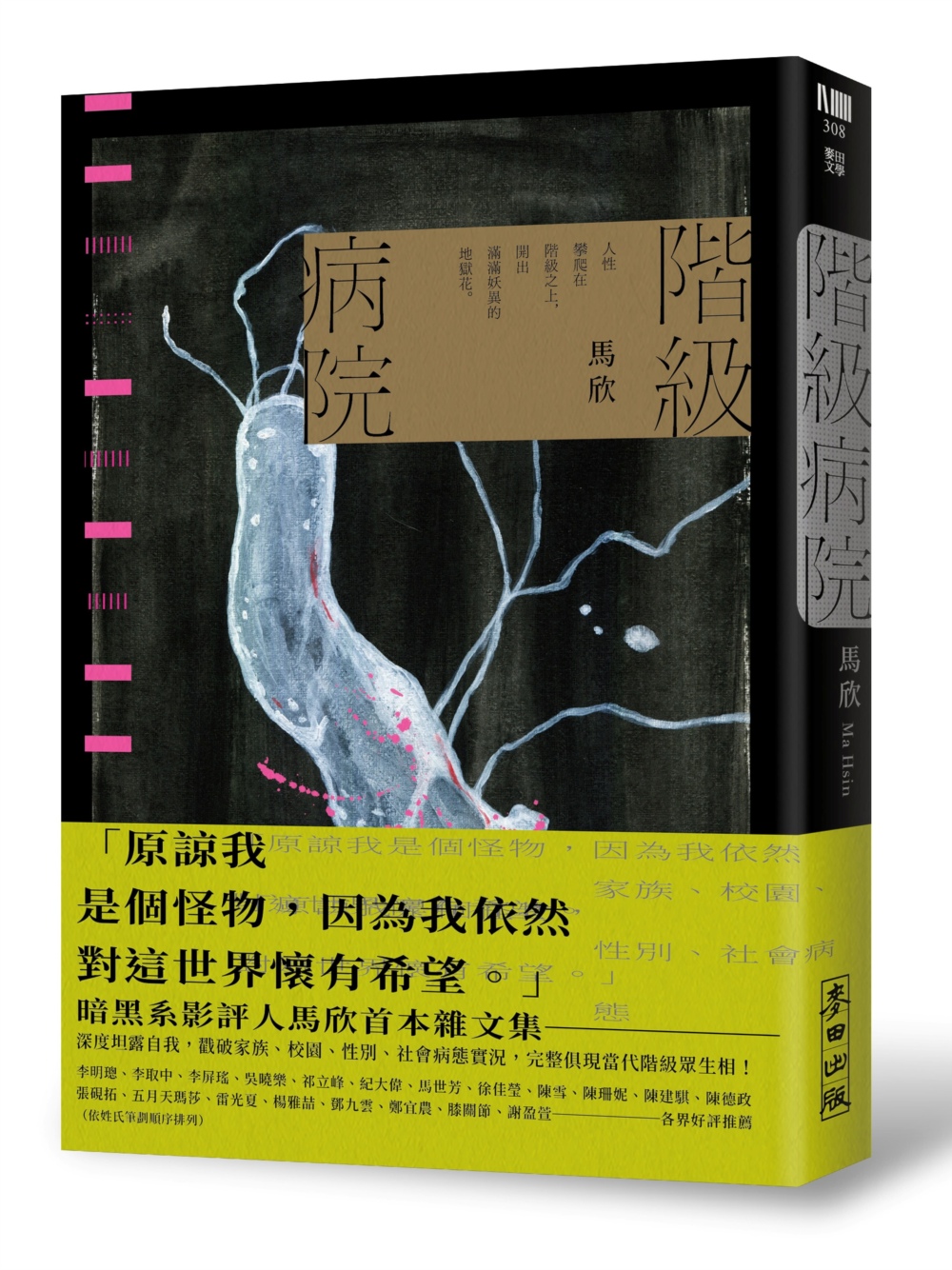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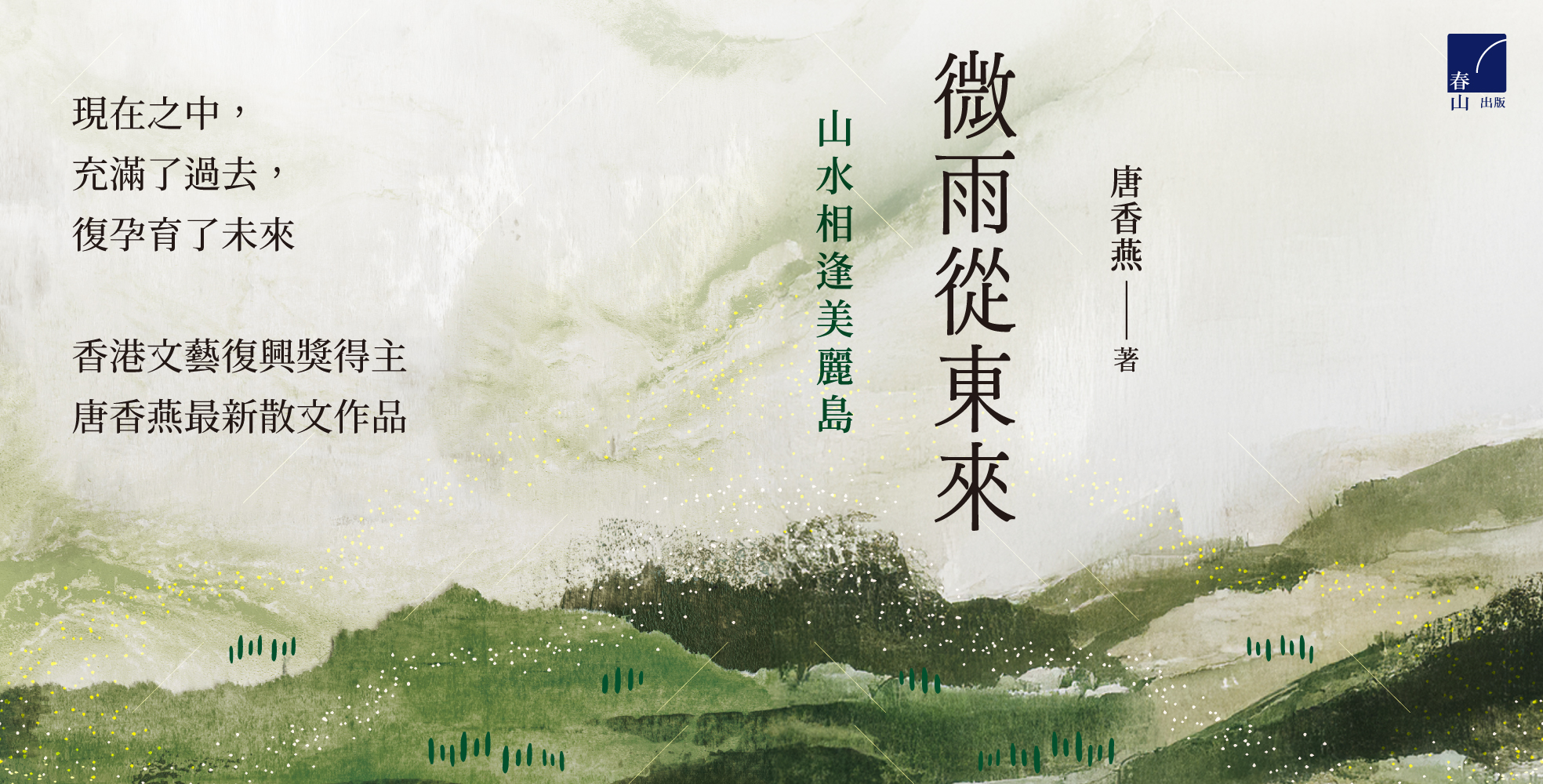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