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這世界啊!我沒有什麼本錢跟你齜牙裂嘴的搏鬥,
但我仍有一支筆來當小刀,以為陰暗可以被我劃出一道一道縫隙來。讓那裡透出來稀微的光,能刺眼出我久違的眼淚。
一起敬這殘酷又美好的世界吧!
它被我們搞壞了,但我們仍有傾斜看它的角度,一眼認出它曾經的美好,於是抱得滿懷,即使即將失去。
這就是電影存在的理由,紀念我們所有可能失去的美好,還有我們曾經被拍下的純真。
※本文可能有劇透,請斟酌閱讀 這世上所有空虛的本身,都曾炙熱地燃燒過。電影中的Ben跟鍾秀說他定期燒溫室(無論是否真付諸行動),如同早期村上春樹文學的核心點,原本就是什麼意義都沒有的物慾燃燒,這部電影更進一步要驗證那把空虛的火,如今在這世上是燒不完的,且無意義的都正在燃燒著生命。
這世上所有空虛的本身,都曾炙熱地燃燒過。電影中的Ben跟鍾秀說他定期燒溫室(無論是否真付諸行動),如同早期村上春樹文學的核心點,原本就是什麼意義都沒有的物慾燃燒,這部電影更進一步要驗證那把空虛的火,如今在這世上是燒不完的,且無意義的都正在燃燒著生命。
這故事說難不難,說簡單不簡單。只是空虛的力量一鬆手,沉甸甸的起不了身。
你可以看成是兩個男人的對話,一個極貧困與一個極富有。他們中間有一個女孩叫海美,像海市蜃樓一樣的存在過。她的形象裡被填塞了所有人們的慾望、物質化的即溶本質,以及渴望自由的淺嚐即止,像如今感覺黏手的金錢糖衣。你我都如口腔期孩童般地離不開它,但舔完糖衣後,除黏膩的記憶外,連核心是什麼都嚐不出來就化掉了。
對於「海美」這個像金錢世界的縮影,天秤上兩端的這兩個男人都因為她而認出彼此的「一無所有」。
 鍾秀(左)與Ben(右)因為海美而認出彼此的「一無所有」。
鍾秀(左)與Ben(右)因為海美而認出彼此的「一無所有」。
這世上所有空虛的本身,都曾炙熱地燃燒過。電影中有錢人Ben跟鍾秀說他定期燒溫室的意義(無論是否真付諸行動),如同早期村上春樹文學的核心點,原本就是什麼意義都沒有的物慾燃燒,他只是要驗證那把空虛的火,在這世上是燒不完的,以及無意義的都正燃燒著生命而已。
「溫室那種東西,燒了也沒人覺得可惜,也不會有警察關心。」Ben無所謂的說。無論在電影與小說裡,躲起來的小貓、溫室或是他們眼中的「海美」,與童年海美曾跌進的井,誰也說不出來何者是真實。
如同鍾秀說的,目前的韓國正身處於一個充滿蓋茲比的世界,蓋茲比正是金錢遊戲中代表,有一票人因新產業成為鉅富,不知財富從何而來的錢滾錢。「黛西」對蓋茲比來講真的是心儀的對象嗎?還是他生命中唯一象徵一點真實的東西,他真心所託的一點綠光,讓他能在慾望之舟上如潮起潮退的徘徊。
對鍾秀而言,他雖沒發跡,但心態跟蓋茲比一樣貧窮,在他與海美做愛的那道斜陽下,他眼中緊盯的窗外景物,這剎那,是對這城市的表徵是沒有實在感的擁有與宣洩。海美出國旅遊後,他幫她餵貓,那隻貓從沒出現過,他在她房間裡自慰著,仍然緊盯窗外斜陽下的景物,他愛的是這個世界中女性印象給他的安慰。
「海美」少女似的撒野、適度的作亂、更多的孩子氣與嚮往自由,其狂妄的生命力有著原始力,足以將他包圍,家中破落的鐘秀,需要抓住這花花世界的這點憐憫,甚至在日復一日的低收入勞動中,克制著想追隨那女孩一起自毀的衝動。
 家中破落的鐘秀,需要抓住這花花世界的這點憐憫。
家中破落的鐘秀,需要抓住這花花世界的這點憐憫。
對富有的Ben來說,「海美」這存在又是什麼?他們在一次流浪之旅相遇,海美與如今很多人一樣,藉由旅遊找尋生命的真實感,他玩賞著這女孩的掙扎,卻不經心,知道那就是蛾子趨光的飛舞,直到因為海美而認識了鍾秀,他才起了一點好奇心,因兩者都有逃不掉的空虛。
這世上,不是每個人都識得空虛的,在空虛裡的人,有多數變成空虛的本身,如同Ben的好友們,索然無味的對話,仍定期相聚,正因為他們交換的資訊都意在顯示自己的階級與品味,這樣已變成「空虛」的人不會知道空虛的存在。
因此Ben在旁的玩賞眼光變得很冷冽,他對鍾秀的好奇在於他在這一片無意義中,看到一個仍堅持有意義的存在。光是鐘秀堅持想當作家這件事,就讓他好奇,這也是作家出身的導演李滄東與村上小說結合的理由,因為文學就是對於「有意義」的堅持找尋,在最該放棄的困境中,他極度好奇鐘秀看破這一切後仍想找尋的理由。
 Ben對鍾秀的好奇,在於他在這一片無意義中,看到一個仍堅持有意義的存在。
Ben對鍾秀的好奇,在於他在這一片無意義中,看到一個仍堅持有意義的存在。
兩人互為表裡,Ben這一面如此嘲笑著眾人的墮落,鐘秀這一面在社會的踐踏中,尋找一個找不到的東西。包括讓他最執著的是在小時候「井底的海美」,這個被所有物質文明標註,也成為別人慾望的化身的人,卻時時近乎於消失的存在,她表演著一切慾望,卻代表著沒人在乎她,「海美」在每個景幕裡都是沒人在乎的可有可無,如同玩具城裡任何一個公主娃娃。
除了兩個男主角外,人們都輕賤著這麼便宜的慾望,因此鍾秀執著的海美說的那井底,其實是懷疑真實的「海美」從來沒有爬出來過,日常的她是如此的不真實,讓他執著得想哭想找她。
被改編的村上原著《燒柴房》中,海美幻化成他們心中一點抒情的存在,男主角鍾秀在海美身上寄託的是根本性的慾望,孩童性地渴望融進那柔軟地帶,有成人動物性的追求,身為各種角色扮演的Show Girl海美,在他者眼中等於花花世界的象徵,鍾秀向這花花世界求歡著,所以在無人的海美房間中,每到日頭落下後,他無人知曉地在窗邊自瀆著。
 「海美」在每個景幕裡都是沒人在乎的可有可無,如同玩具城裡任何一個公主娃娃。
「海美」在每個景幕裡都是沒人在乎的可有可無,如同玩具城裡任何一個公主娃娃。
這部電影好讀取的是表象,表面是主角懷疑他暗戀的人被殺了,從而從Ben這謎樣人物找尋線索,但難得的是這部電影裡的影像符號,所有看到的東西與人都是虛假的,找不到被燒的「溫室」只是其中的象徵,看不到的井與難辨真偽的貓,才是主角鍾秀在這世上遍尋不著的真實。
裡面有兩段台詞說明了李滄東想表達的當代年輕人困境。海美企圖流浪找生命意義,到了肯亞看到壯麗的晚霞,看它從清亮到滿佈著澄光的西沉,從沒看過這樣大片天空的海美說:「好想跟著這光暈一起消失,但卻害怕死亡。」雖然生活在這麼多道景劇的虛假裡,但仍不能承受人生有如此真實的一面。
Ben在同一個場景裡說:「我從沒掉過淚,沒有眼淚當證據,無法確認什麼是悲傷。」抓不出什麼確切的感受,這樣浮浮沉沉在慾望之都裡,抓到的情緒斷簡殘篇的,眼淚是個外顯的證據,那些無法外顯的,在這世上都看似無價值,久了你就會麻木。對於每個人如今過度外顯的歡笑與眼淚,你滑了一輪論斤寸兩也不是,你踩踏而過才發現是一攤人來人往的混水。
那些無法外顯的,時不時與外界的空虛牴觸,你能從對外的螢幕裡能抓回幾分真實的自己?
這部電影長達兩個半小時,多數時候是走表情的隱喻,當下並不悅人。事後你才發現主角口中燒的溫室,是大片大片無意義的表象,但燒不完,你永遠在別人放大的「燃燒烈愛」之中,自己只能像劉亞仁演的鍾秀一樣,感到冰冷的四處尋找,尋找什麼?尋找早被螢幕化的「海美」,在那些笑顏暫停與重播間,她還身在無人知道井底的真實面。
法國哲學家布希亞曾說過:「如今真實的定義已經變成了,不僅可以一再被複製,而且早已經只是複製品了。」安迪沃荷的那每人成名的15分鐘也非獨一無二了。真正的價值是什麼?李滄東從一個富人與窮人的對話中,試圖引出如果引誘兩者的都是空虛,真的值得人「燃燒烈愛」的,不是那個餘燼象徵的「海美」,而是她口中的那片晚霞,那個每個人至少可以「真實」的15分鐘,甚至有勇氣延長的那些時分,無論村上的文本(收錄在《螢火蟲》一書),還是李滄東改編過的這部電影,空虛都重重地掉下來,證實了Ben那沒有眼淚的,日以繼夜的悲傷。
《燃燒烈愛》(Burning) 此片讓韓國導演李滄東拿下坎城影評人費比西獎,故事改編自村上春樹短篇作品《燒穀倉》(又譯《燃燒柴房》,此短篇出於《螢火蟲》一書)。新世代影帝劉亞仁與《陰屍路》史蒂芬元、新星全鍾淑主演。講述生活圈完全沒有交集的兩個極端男人鍾秀(劉亞仁飾)、班(史蒂芬元飾)和女主角海美(全鍾淑飾)之間發生的故事。主角鍾秀原是送貨員,在某個平凡午後,邂逅了名叫海美的女孩,偶然聊天的過程中發現兩人原是同鄉,因此也更拉近了彼此的距離。然而在無法預期的情況下,海美身邊多了一個男伴Ben,雖然Ben看起來非常和善,但仍讓鍾秀對他產生顧忌,後來鍾秀開始一直聯繫不到海美,卻在班的車上看見他送給海美的手錶……。本片在71屆坎城Screen刊物上獲得3.8的高分,並獲選為第71屆坎城影展正式競賽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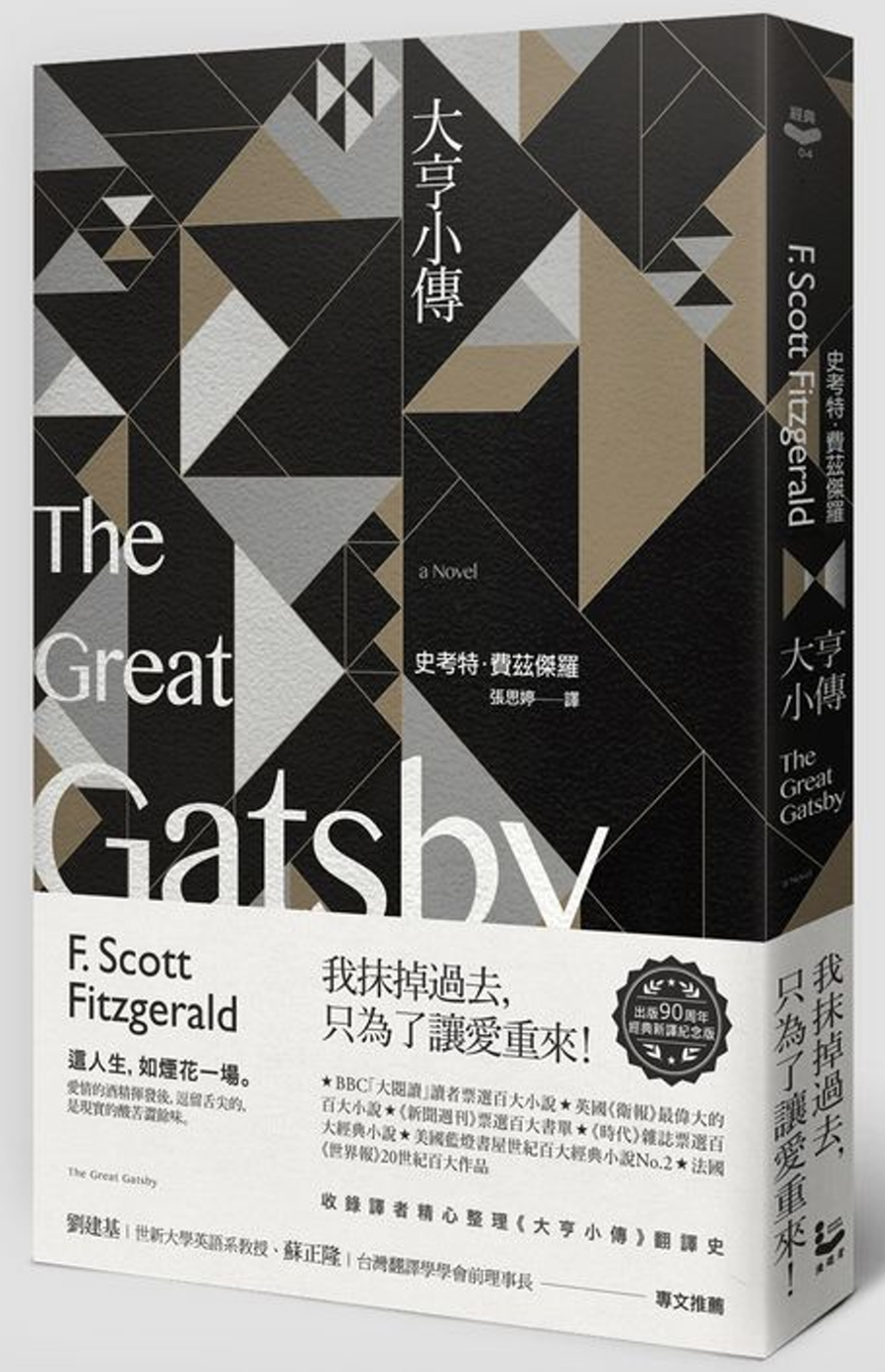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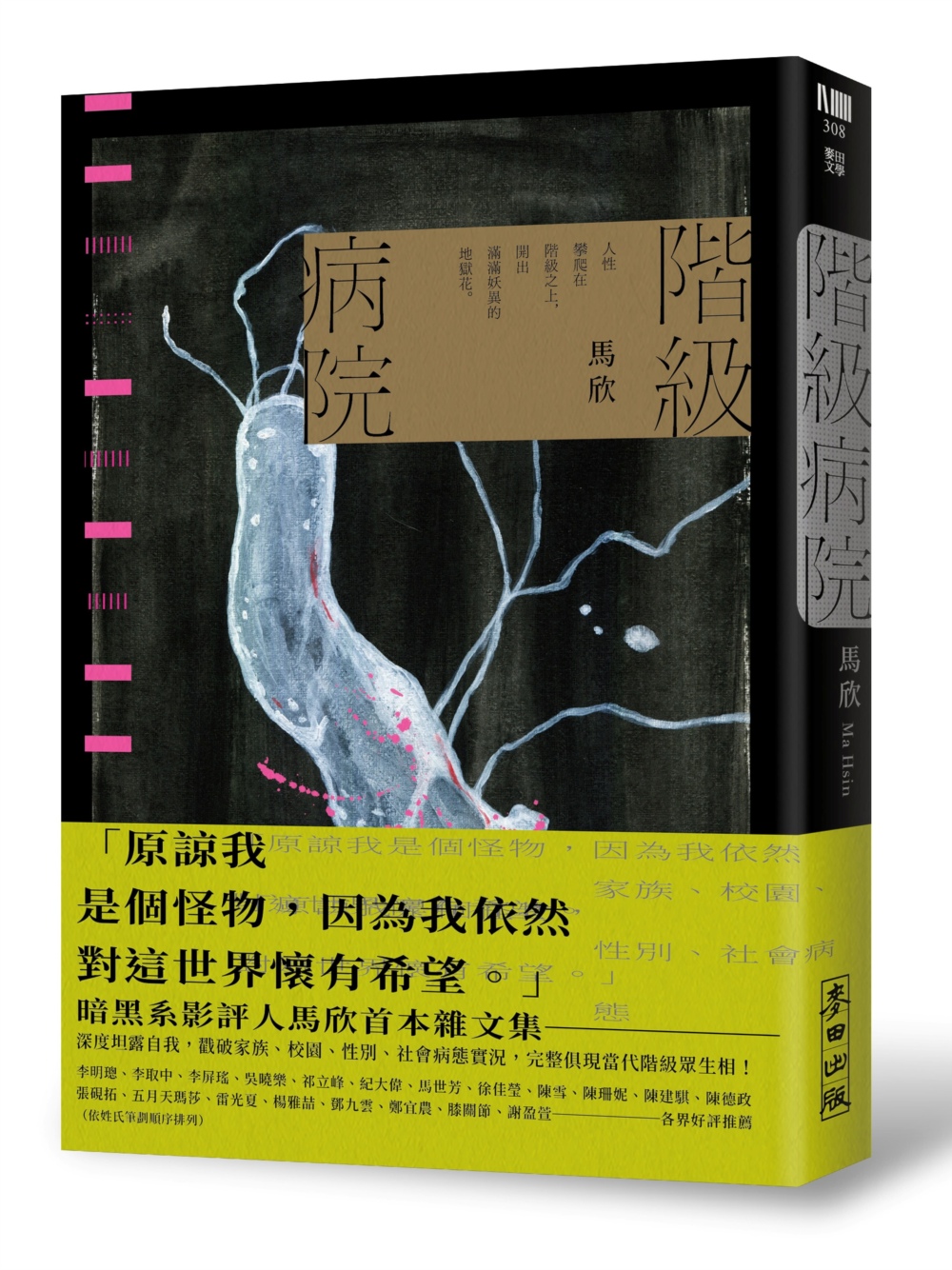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