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字母LETTER:童偉格專輯》的延伸專題為「致新世界」,源起於童偉格作品經常凝視臺灣做為新興國家,在現代生活中最徹底失敗的鄉村地區。如何給予苦難與終將消逝的一切以人性的答覆,可能就是文學家的不同之處。換言之,死亡會在這樣的凝視中重新思索出人的條件。這也是特別使用瑞士象徵派畫家勃克林(Arnold Böcklin)畫作《死之島》(Isle of the Dead)的原因:家園即便是死之島,也是船上之人唯一前往的方向。
「新世界」當然是一個危險字眼,充滿現代性下歷史與權力的相對性,這個詞彙或許意味著當時文明眼中的新(甚至是蠻荒)國度,或者是某個地區經歷革命或體制的巨大質變。人類在18至20世紀,以現代性為核心,製造出許多「新世界」,它們在經歷傷痕累累的帝國殖民或掠奪後誕生,各自因受到壓迫的殊異歷史而形成不同的苦難與衝突,百餘年來逐步在不同政權中走向現代(資本主義)之路的臺灣,也是如此。
專題擇選「基列三部曲」、《行過地獄之路》、《二手時代》、《極樂之邦》與《美傷》等五本文學作品,呈現美國、澳洲、前蘇聯、印度與印尼這五個國度面臨的深刻難題。透過這些書評,我們將理解種族壓迫、戰爭、極權與屠殺等這些人類無法終止的悲劇,文學家企圖以人性校準歷史時鐘的努力。
《行過地獄之路》與野蠻詩學
在奧許維茲之後,寫詩是野蠻的。
Nach Auschwitz ein Gedicht zu schreiben, ist barbarisch.
——阿多諾( Theodor Adorno)
這句典出《文化批判與社會》(Kulturkritik und Gesellschaft)的格言早已被引用過無數次,幾乎散發一股陳腔濫調的氣味。然而,讀者真正理解阿多諾意欲傳達的訊息了嗎?史坦納(George Steiner)斷定阿多諾的潛臺詞是「在奧許維茲之後不該繼續寫詩」,洛森菲爾(Alvin Rosenfeld)則將阿多諾的辯證簡述為以下結論:「在猶太大屠殺(Holocaust)後寫詩已不可能且不道德。」也許問題的核心是:阿多諾的企圖是全面否定文學陳述(literary representation)的可能嗎?又或者,他想說的,僅只是「在猶太大屠殺之後的詩帶有野蠻的特質」?假如是後者,野蠻又所指為何?
首先,「寫詩是野蠻的」是一句現在直陳式:大屠殺之後,寫詩仍是持續發生的事實。換言之,宣稱在奧許維茲之後「不可能寫詩」或「詩不存在」恐怕皆是對阿多諾的誤讀。形容詞「野蠻的barbarisch」源自希臘文barbaros,意指「外邦的(尤其是『語言』)」,而這層原始意義有助於理解阿多諾在《文化批評與社會》中所演繹的論述:「文化批判面對著文化與野蠻之間辯證關係的最終階段。在奧許維茲之後,寫詩是野蠻的。」許多人誤解這段話真正的意義,因為他們並未意識到「辯證關係的最終階段」所暗示的,正是「在奧許維茲之後,文化和野蠻已經不再是正反對立的關係」。阿多諾拋出令人不安的反詰:倘若在奧許維茲之前,野蠻意味著「無視古典成規濫用語言,將外來語混雜在拉丁文和希臘文之中,透露著對文化的無知」,那麼熟稔文化精髓、掌握古典語言的優生德意志民族又展現了何種高貴的文明情操?如同歷史所銘記的,文明的納粹德國建造出精密衛生的殺人機器,高效率而大規模地屠殺野蠻的猶太種族。
在《我輩外邦人》(Étrangers à nous-mêmes)中,克莉絲蒂娃(Julia Kristeva)進一步追溯「野蠻」與「外邦」兩者間的詞源關聯:barbaros脫胎自嘲笑外邦人腔調的擬聲字bara-bara,因此無法掌控自己母語的希臘人也可能被貼上「野蠻」的標籤。克莉絲蒂娃點出了文明本質中的排他性以及法西斯潛勢,同時也為「在奧許維茲之後,寫詩是野蠻的」敞開另一種詮釋向度:大屠殺之後,詩的核心難題將圍繞著外邦人—亦即倖存的猶太人(當然,將猶太人與外邦人畫上等號不無歷史反諷,畢竟聖經中的「外邦人」本指「非猶太人」)—而且詩的敘事美學將轉向一種彷彿失語外邦人所吐出的含糊夢囈。最能完美示現阿多諾所說野蠻特質的,便是保羅.策蘭(Paul Celan):一位來自德語區東境邊陲,從大屠殺中倖存,餘生皆用謀殺者的語言書寫的詩人。
然而,這不是一篇關於《行過地獄之路》的書評嗎?為何要喋喋不休地談論阿多諾和策蘭?細心的讀者必然會注意到小說開頭的獻詞:
獻給戰俘335號
母親啊,他們寫詩。──保羅.策蘭
 《行過地獄之路》作者理查.弗蘭納根(Richard Flanagan)(圖片來自作者官網)
《行過地獄之路》作者理查.弗蘭納根(Richard Flanagan)(圖片來自作者官網)
透過訪談,我們知道「戰俘335號」是理查.弗蘭納根(Richard Flanagan)的父親亞契(Arch Flanagan)在戰俘營時的編號,但小說家為何要獻上策蘭的詩?這個問題可能的答案,便隱藏在阿多諾的格言中:阿多諾所說的詩是個涵蓋一切文學陳述的提喻(synecdoche),而奧許維茲集中營亦指向戰爭暴行和滅絕焦慮—Auschwitz立即讓人聯想到德文動詞ausschwitzen「冒汗」—是以我們或許可將阿多諾的格言改寫為「在戰爭暴行之後寫小說是野蠻的」。在一篇訪談中,丹尼斯.哈里圖(Dennis Haritou)提出了尖銳的提問:「《行過地獄之路》引用俳聖芭蕉和丁尼生,小說中刻意營造的文學腔調和與之並存的殘忍罪惡令人不安。英雄醫官杜里戈和虐待狂中村少佐都熱愛文學,請問你如何解釋這點?」弗蘭納根的回應略顯狡猾:「我無法解釋,策蘭也無法。本書獻詞所引用的策蘭詩句『母親啊,他們寫詩』完美呈現了你所提到的矛盾悖論。」
我們無從得知哈里圖在提問時是否想起(或誤讀)了阿多諾的格言,但引自策蘭詩作〈狼豆〉(Wolfsbohne)的獻詞真的能做為《行過地獄之路》書寫策略的辯詞嗎?詩句「母親啊,他們寫詩」中的他們又是誰?我們不妨先閱讀一小段〈狼豆〉:
母親啊,謀殺者們
曾住在那兒。
母親啊,我
寫了批信。
母親啊,沒有回信。
母親啊,有封回信。
母親啊,我
寫了批信給—
母親啊,他們寫詩。
母親啊,他們不寫詩
除非那首詩是
我為了妳
而寫,為了
妳的
神
而寫。
策蘭簡潔到幾乎貧脊的詩句再次呼應野蠻(事實上,他寫詩即是對阿多諾的回應):一種彷彿失語外邦人的風格。依據前後文,「他們」除了「謀殺者們」之外別無他指,但敘事者談論起「他們」時總是欲言又止(「我寫了批信給—」),前後矛盾(「他們寫詩/不寫詩」)。這些語言症狀透露了大屠殺遺留下的心理創傷:敘事者企圖透過回憶和書寫銘記被謀殺的母親,但每一次回憶與(使用謀殺者語言的)書寫都再一次將她謀殺(「昨天/他們中的一人來了然後/第二次在/我的詩中/殺死妳。」)。弗蘭納根似乎認為〈狼豆〉中寫詩的謀殺者呼應了小說中邊虐囚邊吟誦俳句的日本軍人,但策蘭詩作赤裸光禿的語言加倍彰顯《行過地獄之路》引經據典,文字流暢華美到近乎煽情,絲毫不野蠻。
哈里圖的問題核心,顯然在於「殘暴的戰爭罪犯也可能熱愛文學嗎」?小說家的答案似乎是肯定的:「中村開心發現古田大佐跟他都熱愛日本古典文學。他們談一茶的俳句多麼樸實有智慧、蕪村又是多麼偉大、芭蕉的俳文集多麼神奇了不起。古田說《奧之細道》就是總結了日本精神的才氣之作。」(儘管弗蘭納根隨即加了但書:「說是詩深深感動他們,不如說他們感動於自己對詩的敏銳。」)事實上,哈里圖的疑問略嫌天真:翻開史書,熱愛文學的殺人魔不計其數,我們很快便可舉出近代最出名的三人:毛澤東,史達林,希特勒。(策蘭在〈狼豆〉開頭引用荷爾德林(Friedrich Hölderlin)詩作,正是壓抑地吶喊著:納粹熱愛詩歌。)哈里圖依稀感到不安,卻又無法準確提出的問題,恐怕便是「殘酷與美學可能共存嗎?謀殺者是否可能同時是美學的愛好者,甚至是美學的天才」?而這正是阿多諾的格言—「在奧許維茲之後,寫詩是野蠻的」—所企圖觸及的幽微內裡。如同我們先前已試圖爬梳過的,阿多諾的重點並不在於「文學不該繼續存在」,而是探問「怎麼樣的後大屠殺文學才可能是合乎倫理的」?他顯然認為,延續大屠殺前的美學標準是缺乏反省的道德意識。阿多諾的看法並非不可挑戰,但他的確敏銳地察覺到了文學風格斷裂性的劇變。若讀者曾閱讀過奧許維茲倖存者的回憶錄,很難不注意到字裡行間滲透出的意識掙扎:倖存者感受到銘記自身經驗的焦慮—「如果我不寫下我們的親身經歷,未來誰會記得這些曾經發生過的恐怖事件」—卻又對文字是否能準確陳述過去的創傷經驗深感懷疑,甚至覺得存活下來的自己無論用何種方式回憶死者皆是一種褻瀆。他們企圖書寫,卻又抗拒書寫。這樣的兩難最終化成彷彿口吃般遲滯而笨拙的文字風格,因為他們字斟句酌,唯恐吐出任何一絲錯誤的細節。
上述倖存者文學的風格暴露出《行過地獄之路》做為介入文學(committed literature)的尷尬(「介入文學是野蠻的」阿多諾如是說):弗蘭納根對戰爭的文學陳述弔詭地承襲了一種(發動戰爭的)舊世界的美學:繁複、睿智、雄辯滔滔。這樣的美學反映在角色塑造上—中村少佐對自己的所作所為充滿信念:
戰爭很殘酷,沒錯。哪個戰爭不殘酷?戰爭是人造的。戰爭就是我們。我們的作為。蓋鐵路可能會讓人喪命,但是創造生命不是我的事,我只管蓋鐵路。進步不需要自由,自由對進步沒有用。……醫生,你認為這是不自由。我們叫它魂,國家,天皇。醫生,你所謂的殘酷。我們管它叫天命。不管有沒有我們,這就是未來。
而戰爭英雄醫官杜里戈亦是「那種年輕時代就浸淫古典文學、很少涉獵其他領域、口味已經僵固成偏見的人。碰到現代文學,完全不知所云,最喜歡半世紀前的文學風格,也就是維多利亞時代詩人與古文學家」。杜里戈的文學品味乍看之下無可責難,但請別忘了維多利亞時代正是大英帝國殖民主義的高峰,許多文學作品暗藏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幽靈,而長久以來大英帝國和澳洲本土統治者的殖民主義—諸如同化政策和白澳政策—亦是諸多苦難的根源。值得注意的是,當杜里戈談論起澳洲現代主義詩人哈利斯(Max Harris),他說「完全不解這在講什麼鬼」。
小說家和其筆下人物的意識形態不能混為一談,但當弗蘭納根選擇讓角色吐出某些話語或呈現某種角色樣貌時,他已經透露了自己的道德判斷:「這些文字是可以寫在小說裡的。」我們不得不追問,「為何要讓軍國主義者在一本陳述戰俘苦難的小說中侃侃談論大和魂?」弗蘭納根必然可以給出一系列的回答—為了讓人物更有血肉,為了讓異己(the other)也有自己的聲音,為了銘記曾經蒙蔽集體人類的荒謬信念。但這些可能的回應帶出了更關鍵的問題:「為何要寫一部二戰時期澳洲戰俘被日軍奴役,修築泰緬死亡鐵路的虛構小說?」殘酷的事實是,《行過地獄之路》不是第一本戰爭小說,也不會是最後一本,而且無論寫再多的戰爭小說都無法治癒倖存者創傷,亦無法阻止戰爭繼續發生。也許聽起來無理取鬧—「憑什麼質疑別人寫作的正當性?」—但這正是阿多諾格言「在奧許維茲之後,寫詩是野蠻的」拋給所有人的嚴肅問題。
弗蘭納根曾說,「我過去並不想寫這部小說,因為它充滿了失敗與災難。」但目睹父親亞契—也就是「戰俘335號」—日漸衰老,他開始感受到一股焦慮,
 理查.弗蘭納根的哥哥馬丁.弗蘭納(Martin Flanagan)(圖/來自penguin.com.au)
理查.弗蘭納根的哥哥馬丁.弗蘭納(Martin Flanagan)(圖/來自penguin.com.a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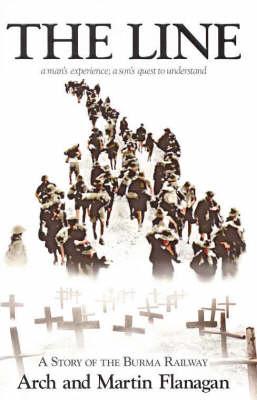 由理查的哥哥馬丁和父親亞契合著的《鐵路》
由理查的哥哥馬丁和父親亞契合著的《鐵路》
「我意識到如果不把父親的故事記錄下來,我未來可能再也無法寫作。」然而,他在訪談中極少提起一件事實(甚至在曼布克獎的領獎謝詞上也未致敬):他的哥哥馬丁和父親亞契在2005年早已合寫出版了一本名為《鐵路》(The Line: A Man's Experience, a Son's Quest to Understand)的回憶錄。在處理父親修築死亡鐵路的回憶時,身為紀實作家的馬丁.弗蘭納根採取相當謹慎的態度:「我嚴格限制自己只談確實知道的部分,因此我有意識地留下巨大的空洞。有許多我不知道的事,我也不想憑空臆測—對我來說,這是身為記者應遵守的準則。」被問起他如何看待《行過地獄之路》時,馬丁如此答覆:
我想強調的是我們今天在這裡談論的是一本小說。一本虛構的作品。而這對我來說意味著我們必須把它和它的情節所參考的那些真實事件區分開來。理查的小說成功做到了這一點。這本小說充滿了我過去曾經聽過的故事,但卻又不完全是那些故事,因為只要他覺得必要,他便會拆解,然後重新部署那些故事中的各種元素。……我看見父親和〔杜里戈的原型〕鄧祿普(Weary Dunlop)貫穿整本小說。我的父親是個平凡人,鄧祿普則一點都不平凡。
一位署名Nerida White的澳洲讀者在閱讀《鐵路》一書後,留言指控小說家不誠實:「《鐵路》詳細記錄了亞契的回憶,《行過地獄之路》卻對此隻字未提。我深感受騙,甚至覺得這是一種剽竊行為。」這位讀者的指控也許過於嚴厲,但她的質疑確實難以迴避:建構在他人真實經驗—尤其是極端創傷經驗—的虛構敘事是否合乎道德?難道小說家能夠比倖存者本人更貼近真實嗎?假如小說的價值在透過虛構增添敘事的可讀性,這本身難道不是一種對倖存者的褻瀆:「透過重述/閱讀他人的悲慘遭遇,我獲得了美學上的滿足?」紀實文學和小說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文類,但歷史小說—尤其是介入文學—介於兩者之間的灰色地帶。當小說家以真實歷史事件為素材,他應該如何為虛構辯護?哈里圖在訪談中如此詢問弗蘭納根:「你有仔細研究法庭筆錄嗎?你是否能透過研究資料來理解日本軍人犯下醜陋罪行時的心理狀態?」而他得到的答案是,「我沒有做什麼研究。我訴諸自己的生命經驗。大部分都是我虛構的。」弗蘭納根曾前往日本拜訪二戰時虐待過父親的低階軍官,也就是故事中「巨蜥」的原型。「我在一間東京計程車行的辦公室裡見到他,一位溫柔的老先生。……我要求巨蜥賞我耳光,就像獄卒曾經對戰俘做的那樣。一陣遲疑之後,他遵從了我奇怪的要求。……看著這位惶恐的老先生,我知道不管邪惡究竟是什麼,它並不在這裡。」在與巨蜥那次奇異的會面之後,弗蘭納根「意識到寫實並不能充分傳遞真實」。於是他決定「返回家中,坐定,重新開始虛構」。或許,小說家理查相信透過虛構,他可以填補哥哥馬丁在父親回憶錄中所刻意留下的「巨大空洞」。
我們究竟該如何理解虛實交錯的《行過地獄之路》?阿多諾的格言「在奧許維茲之後,寫詩是野蠻的」又與它何干?由此格言所衍伸出的一連串針對真實(事件)與虛構(文學)的辯證似乎從一開始就不留餘地定了後者的罪,但事實並非如此,因為—我們再次想起—阿多諾未曾說過「不能創造文學」。這句嚴酷的格言與其說是判決,不如說是尖銳的審問:文學如何回應歷史中(被文學滋養)的暴行?弗蘭納根恐怕選擇了一種最弔詭的策略(也因此令哈里圖與其他讀者感到不安):熱愛俳句的日本軍國主義者凸顯了文學成為法西斯觸媒的可能。讓我們回到克莉絲蒂娃所說的野蠻外邦人:將外邦人視為野蠻是一種簡單的二元對立策略,只要將異己(the other)描述成非人的邪惡,便可以毫無愧疚感地憎恨,甚至屠殺他們。美軍如此對待日本平民(被逼問廣島和長崎核爆時,杜里戈說:「你根本不知道他們是怎麼樣的怪物。」),日本軍人如此對待澳洲戰俘,納粹如此對待猶太人,猶太人亦曾如此對待迦南人—神命令約書亞征服迦南地,「又將城中所有的,不拘男女老少,牛羊和驢,都用刀殺盡。」(《約書亞記》6:21)法西斯主義及其變體(軍國主義、納粹主義、史達林主義、毛主義、白色恐怖)的運作邏輯,便是宣傳光榮崇高的同一性(大和魂,純種德意志,共產烏托邦,反共抗俄),然後碾碎所有與此同一性對立的反面。民族和國家認同(identity)正朝向此種同一性,而文學是創造認同看似最純潔無害的工具:「我生長在澳洲,但我熱愛英國文學,我是大英帝國的子民,我為大英帝國而戰。」
弗蘭納根深知民族認同暗藏法西斯潛勢,亦曾公開駁斥右翼分子將《行過地獄之路》閱讀成愛國文學、挑起歷史仇恨—「看看那些野蠻日本人怎麼虐待咱澳洲人」—的企圖。因此,他特別強調自己來自澳洲的邊陲:「我來自塔斯馬尼亞,現在仍定居在那。那是個離澳洲本土幾百英里的南方島嶼。所以我不太懂身為澳洲人是什麼感覺。」澳洲「Australia」的辭源來自拉丁文「terra australis incognita」—未知的南境之地—而此新世界以南的塔斯馬尼亞島更是邊陲的邊陲。當弗蘭納根拒絕給自己貼上澳洲作家的標籤,他正是展現與此種同一性邏輯對抗的姿態:「我以身為邊陲的野蠻人為傲。」或許有人認為阿多諾與其格言「在奧許維茲之後,寫詩是野蠻的」都已過時,但法西斯的幽靈從未曾散去。無論我們如何理解阿多諾,他確實指引出文學在文明破產後繼續存在的一條奧之細道:走向異己,並變成他。
(本文轉載自衛城出版《字母LETTER:童偉格專輯》)
辜炳達
臺南人,倫敦大學學院英國文學博士,臺北科技大學應用英文系助理教授。目前延續博士論文《日常微奇觀:尤利西斯與流行》的文化考古路線,挖掘資本主義社會中現代文學與流行文化和視覺科技之間的共謀關係。翻譯駱以軍《西夏旅館》獲2017年英國筆會第二屆PEN Presents翻譯獎。
延伸閱讀
1.【書評】死者尚未離開,歷史還沒被當權者粉刷──陳又津讀《美傷》
2.【書評】黃麗如:你的地獄,我的景點──讀《行過地獄之路》
3.【書評】胡培菱:成王敗寇或許只是世事流轉──2014年曼布克獎得主《行過地獄之路》
4.【專欄】何穎怡:有時譯者必須含淚接受一聲與三聲的差別──《行過地獄之路》譯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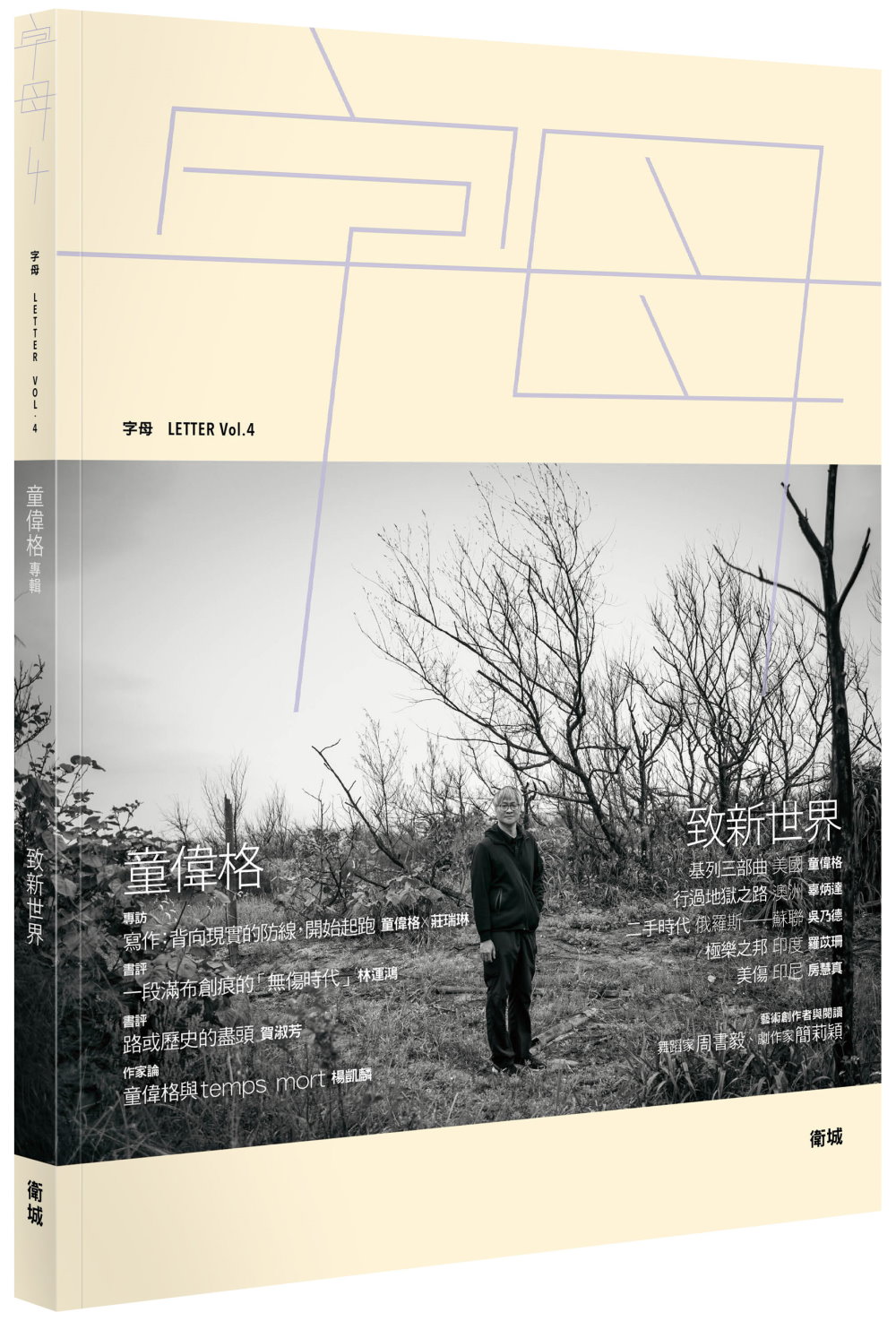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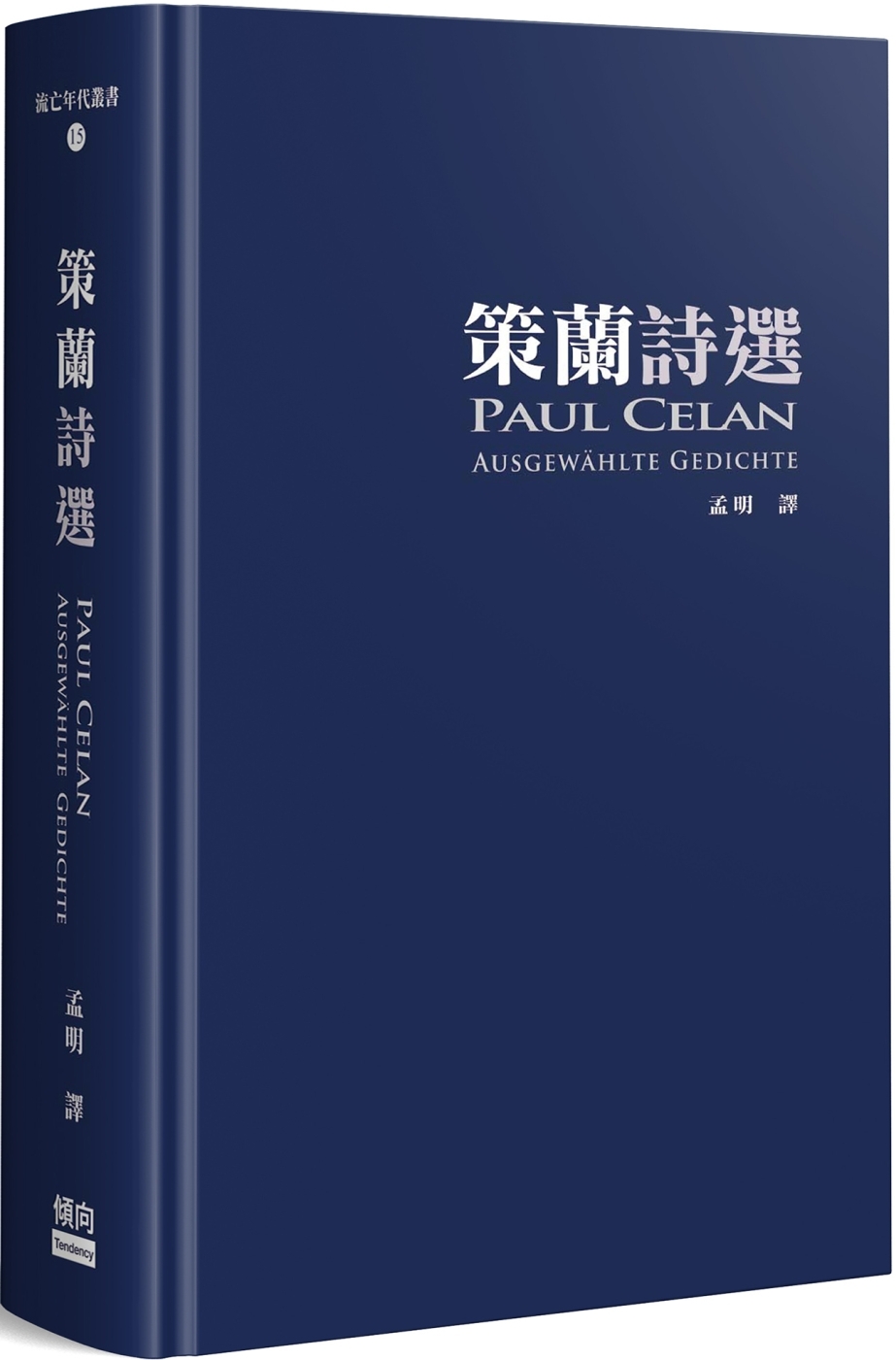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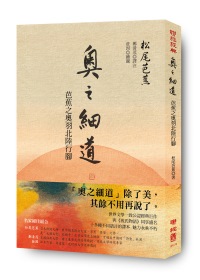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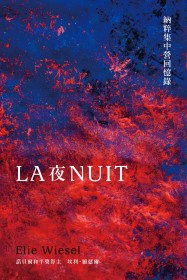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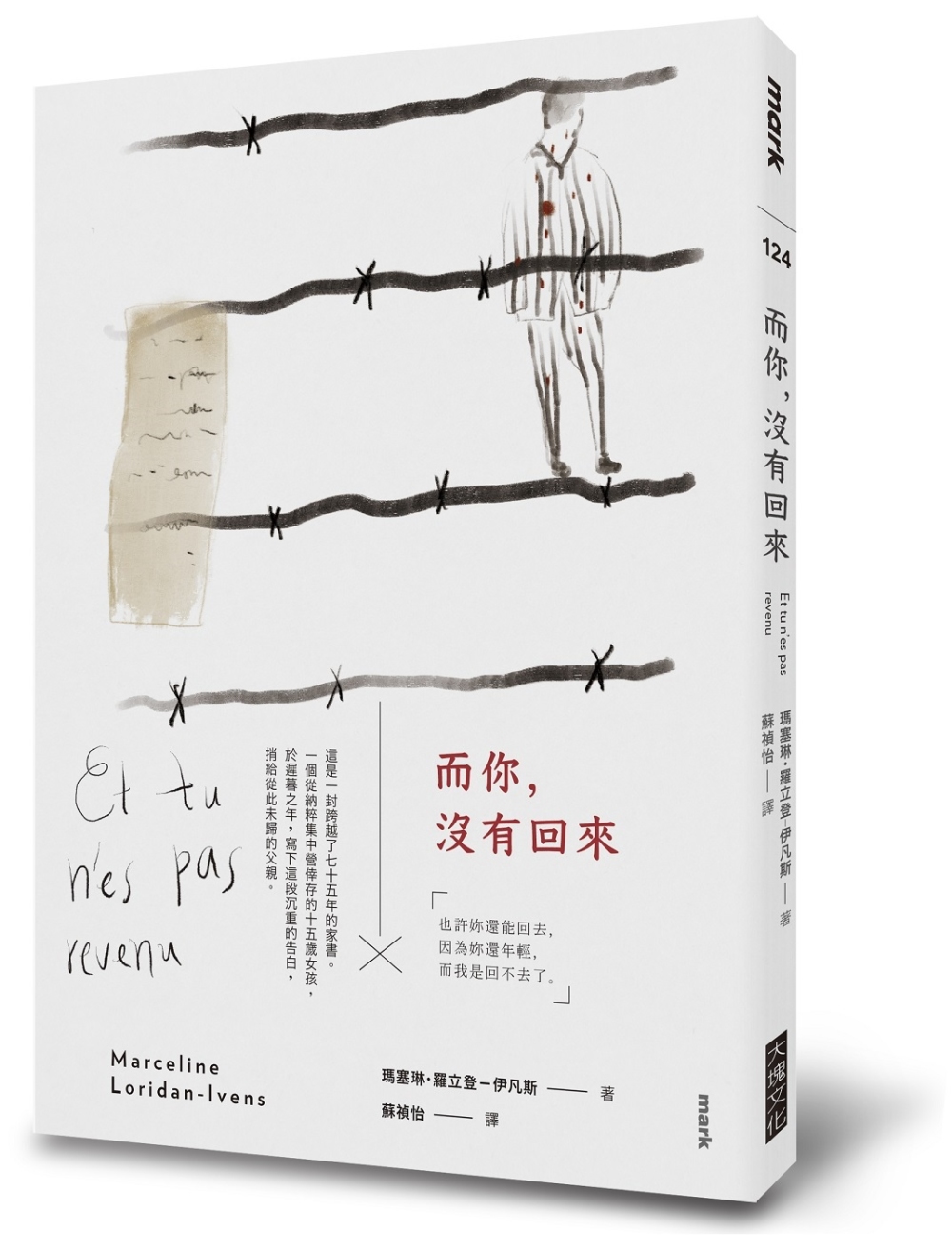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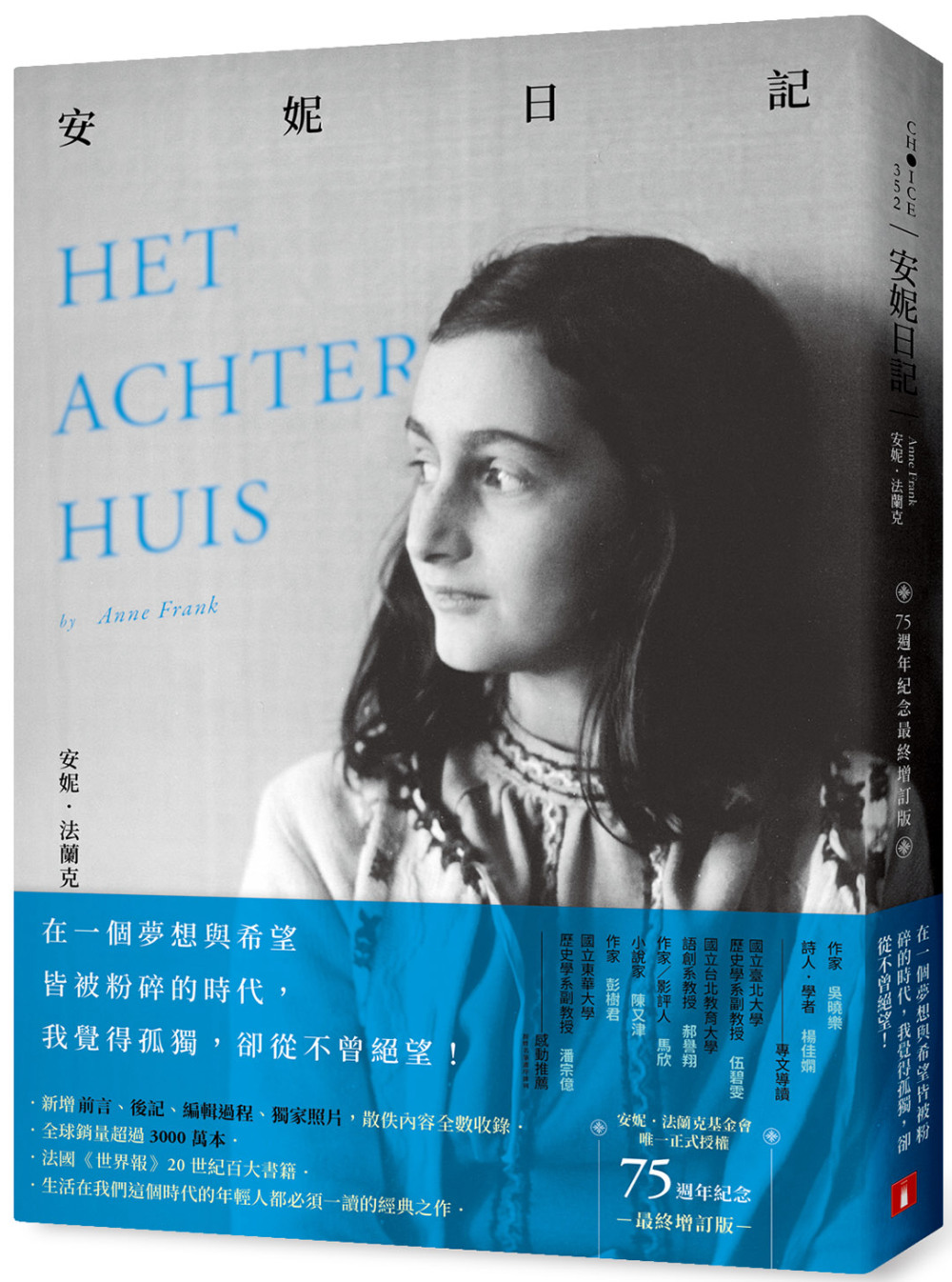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