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家齊邦媛。(攝影/顏涵正)
90歲的齊邦媛和候她片刻的我們致歉,年齡已令她待客受訪略顯吃力。剛結束午休的她,說自己不是午睡,而是醫師囑她每日午後必須平躺不動,略作休息,她只得照辦。
「我只希望我能健康出席。」說的是2月14日,出版社為她的新書《洄瀾:相逢巨流河》舉行的相逢會。這無疑是個完美的日子,既是元宵節,也是西洋情人節,更是齊邦媛的舊曆生日。這天,她將與因《巨流河》結緣的親友、學生、讀者重逢或初會。
85歲時,齊邦媛寫成25萬字的家國回憶之書《巨流河》,出版後引起華人世界一陣不小騷動,採訪邀請、讀者來函、評論⋯⋯不斷寄至出版社與齊邦媛的信箱。這些因《巨流河》而生的文字,正是《洄瀾》一書的主要內容。
光是讀者來函,就超過六百封。這些多半以手寫、貼上郵票寄送的信件,齊邦媛珍而重之,「我每天晚上都會把信拿到床頭再看一次,也想一一回信,但年紀愈來愈大,很多事情做不動了,信沒法好好回,很抱歉。出這本書,很大的原因也是因為沒有回信,所以用這書把(後續)情況說一說。」
《洄瀾》固然是《巨流河》的補充,然而這些來自外界的書簡、評論,讀來卻很有續集的戲劇感。齊邦媛的學生,作家簡媜不僅在《巨流河》成書過程扮演協助、鼓勵她著書的推手,兩篇精采側寫更補足了成書中、出書後,齊邦媛的心境流轉,以受業晚輩與文學同袍之筆娓娓道來,深情動人。
《巨流河》在中國出版所引起的迴響,更是齊邦媛想都沒想到的。「我以為這書在大陸是出不了的。」沒想到,《巨流河》不只出成,書中對二戰前後中國局勢的回顧與戰後來台的「移民經驗」,無疑引起了中國讀者的好奇。十餘家媒體透過書信、電話、親自來台與齊邦媛進行深度採訪外,她也獲頒《南方都市報》所辦「華語文學傳媒大獎」的「年度散文家」獎項。
更出人意料的是讀者來函。由於書中所述人物涵蓋一整個戰禍離亂的世代,許多髦耋讀者的信件,除對齊邦媛寫出同代人的回憶致謝外,或有詢問,或為書中人物的行蹤「補遺」,使《洄瀾》與《巨流河》宛如拼圖般,會合成一部凝聚集體情感的民族之書。
其中,最令齊邦媛吃驚的,是來自張大飛飛虎隊同袍的信件。張大飛是《巨流河》的關鍵人物之一,是齊邦媛少女時期鍾情的對象,可惜於飛行任務中犧牲。他的戰友陳鴻銓在信中回憶自己認識的張大飛,並向齊邦媛說明張大飛的死亡原因。「收到這樣一封信,太意外了,令我震撼。」齊邦媛說,這些回應,是寫書時未曾預料的。「不過,說句公平話,像是張大飛和我先生(註:被譽為「台灣鐵路電氣化之父」的羅裕昌)這一類人,並不是容易的。我碰巧遇到這些有特別能力和決心的人,他們所做的事情,都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這也是齊邦媛之所以高齡而不輟筆的原因。「我的故事真的代表很多人,我死了就沒人知道了。我出書時已經80多歲,我知道的,在我之後的人都不知道,在我之前的人都死了,所以我要說的是別人不知道的事。」
以80多歲的意志力、記憶力,寫出一部足以撼動史家與文壇的作品,齊邦媛瘦小身子裡蓄積的能量,直到現在仍難以小覷。儘管訪談中不時惋惜已然衰退的體能,一談到中國二戰時期的史料陸續面世,她雙眼炯炯,毫無疲色,「我接下來想做的事太多了,」不為著書,而是藉閱讀蒐集這些時間蒙塵卻令人憤怒依舊的史事,「我最近關心的,是對世界政治的真正了解。」
她將一本厚重的英文書推到我們面前。書名 Forgotten Ally,被遺忘的盟友,由英國牛津大學專研中國近代史的芮納.米德(Rana Mitter)所著,寫的是中國1937-1945年二戰期間的歷史。「這本書太棒了,簡直是我的知音!他從客觀的學術角度寫中國,書的前言叫做〈City on Fire〉,講5月4日的重慶大轟炸,當時重慶整個在火海裡——我就在這fire裡。」一面說,她一面觸摸書封上,火焚之後一片赤紅的中國。
「Mitter寫出當時中國真正發生的事情,」她欣慰在《巨流河》之後有這樣的論著出版。「我在乎的是真相。我不懂為什麼這些人沒人寫。現在終於有人從客觀的角度寫了,否則我們講死了,人家也還是說那是你自己講的。」她愈說神色愈凝重,執筆敲得桌子咚咚作響,「我很遺憾自己寫得不夠,礙於篇幅,也因資料不夠。但是接下來慢慢會有更多歷史研究出來⋯⋯一定要讓這段歷史被寫出來,把那些白死的幾百萬人、這段百年沉冤給寫出來。」
受限於資料和自認對政治了解不夠而未寫之事,在齊邦媛心中沉甸甸積壓著,未曾或忘。比如,她在《巨流河》中略而不提的華北第一守將,國共戰爭時開北平城門迎共軍,對國共戰局逆轉頗為關鍵的傅作義。齊邦媛曾在書中提到一位支持共產黨的女同學,卻在她的姓名上打了問號,此人就是傅作義的女兒。「有讀者寫信告訴我她的名字,以為我忘了,但我不是忘記,我只是不想說。」
不想說,是因為感到羞恥。原為國民政府效力的傅作義,竟對共軍大開城門,齊邦媛至今說起,仍痛心疾首,「我最失望的就是聞一多跟他。但我不是政治人物,材料不夠,沒法寫他。」
「中國歷史上有不少守城將領,守不住了是自殺的,與城俱亡。我不能希望每個人都這樣,我不希望他死,可是也不希望他開城門,怎麼辦?我不能說輕鬆話,但如果是我,寧可死也不開的。」
憤慨若此,然而回歸書寫,必須有憑有據,齊邦媛話鋒一轉,對她一代人的流離身世被形容為「失敗者」不願認同。「我們不是逃難,不是敗兵,」她強調。自己受聘到台灣任教,在此成家立業,沒花太多時間傷懷怨世;最終,她和丈夫以其文學、教育、交通等專業,參與了台灣的基礎建設,也在這島嶼上開枝散葉,綻放出燦爛的花果。
「我們不說廢話,都在做事。」從故鄉的戰禍來到新天地,面對從零開始的人生,齊邦媛發現,一路走來,無論自己或丈夫、友人,始終以踏實態度踩出每一步,「從這觀點,我就能寫台灣了。在台灣這些年,我有正面的人生,我的朋友也是,因此有可寫之事。」
莫能禦之的大時代,將齊邦媛的生命切割成中國、台灣兩個截然不同的塊面,卻一如《巨流河》與《洄瀾》兩書,兩相激盪出跌宕、壯闊卻完整的生命。齊邦媛以書寫造出這股沛然洪流,可以想見的是,它不會輕易斷絕,一代一代的人將繼續透過閱讀,被捲入其中。無數的離合,經由文學,經由書寫,久別重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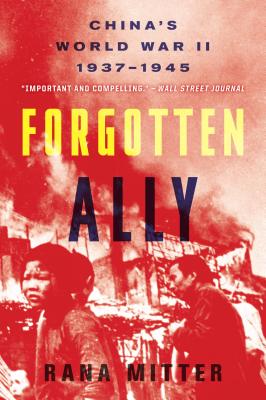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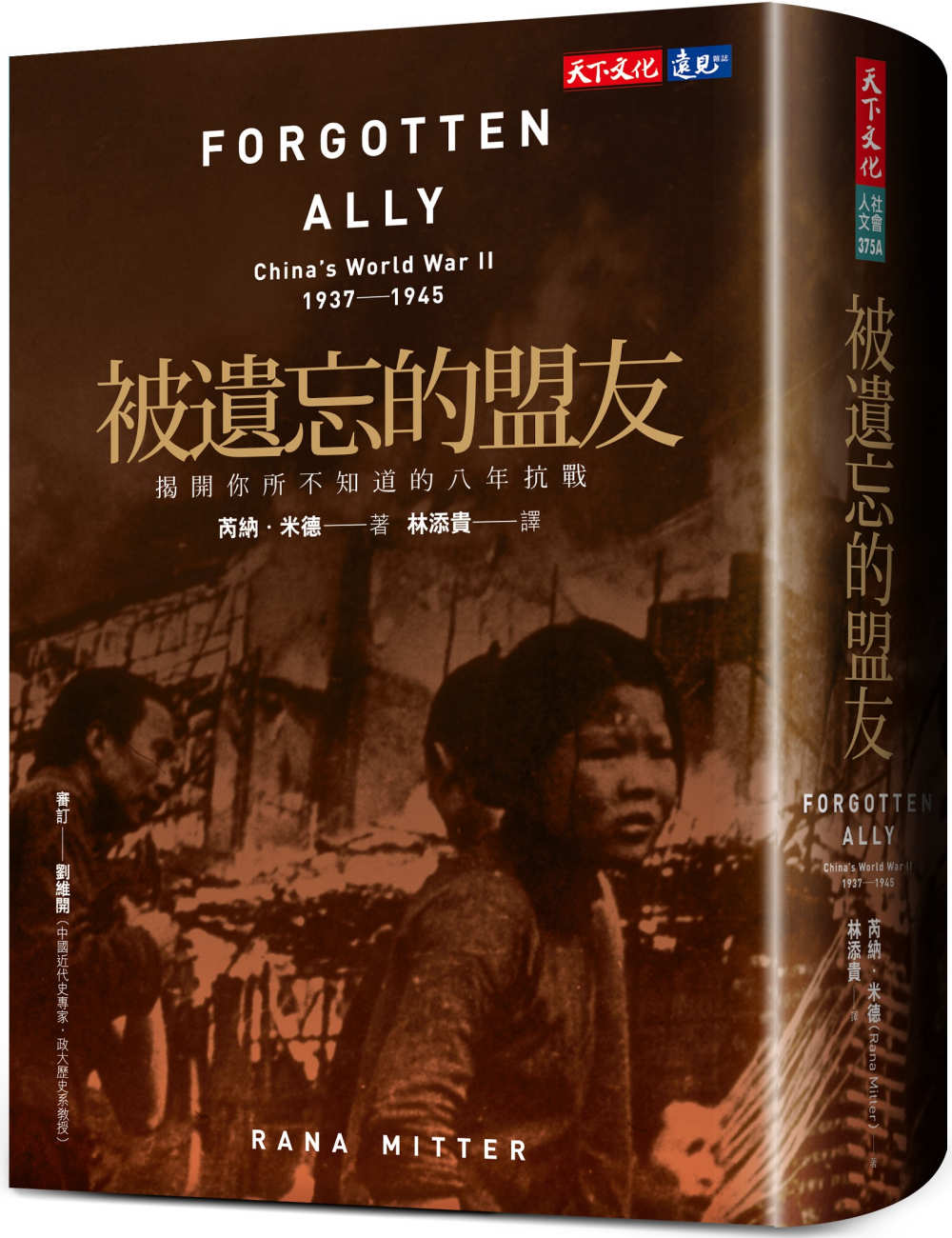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