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開人性顯相室,我們可以看到似曾相識的自己,
解開只封存在記憶中的世界殘影,
讀取種種人們暗示的訊號回聲,劃下尚未結疤的傷痕,
拍打起角落裡累積的記憶塵灰,
這是我們身處的大世界,也是我們受困的小房間,
眾生內心在這裡顯相,紀錄妖魔天使齊聚一堂的人類樣貌。
 雙葉對「家」的概念與其他人完全不同,她包容四個沒有血緣關係的人,每一日都為圍著一爐火而有了目標,一生以一日來看待,而非每日來成就一生。一生是稀釋了人,是個連加減都沒憑據的空無演算式,而一日終究可以披掛在身上,讓人有個歸途盼望。
雙葉對「家」的概念與其他人完全不同,她包容四個沒有血緣關係的人,每一日都為圍著一爐火而有了目標,一生以一日來看待,而非每日來成就一生。一生是稀釋了人,是個連加減都沒憑據的空無演算式,而一日終究可以披掛在身上,讓人有個歸途盼望。
心每天都會髒一點,總要洗洗刷刷的,但還會留下一點頑垢,在內心積存著,那些卡在夾縫中的心事,像隔夜的菜渣,你知道它們發酵未全,隨著肌肉痠澀到分不清在哪裡積壓得更深。那些髒啊,你看雙葉她彎著腰用水沖著,嘩啦嘩啦,讓那澡堂香噴噴熱呼呼的,於是今天終於可以得到一點平靜等級的乾淨,好讓自己像幼兒一樣再貪睡一會兒。
說來說去,人就是想回到不知世事的童年,午後醒來,是某個無憂無慮的下午。當時並不知道那「下午」過去了就不會再回來。
奈何雙葉那家人很早就知道世事了,那沒有煩惱,醒來就期盼被什麼人擁抱、覺得這世界哪裡都飛過一陣輕風,你會留神窗口那個風鈴聲的單純時間。當時時間的意義還只是「時間」本身,不帶著焦慮、期盼、願望的擱置、積存未滿雜念的空間意味,就是很乾爽,一晾在歲月裡就乾爽的「時間」,你還不會與它為敵,也不會因它而失落,那還沒對生命構成具體威脅或盤問的「時間」。
於是你看日本電影,少男少女總是一溜煙的跑過去、動畫人物的躍起、對抗那巨大、增生又冥頑不靈的巨大猛獸,或是像他們中年人總在電影中接受了「時間」的安置,淺眠且安靜的讓時間將自己變成一個壓縮檔,極其無聲的包覆心頭呼嘯的噪音,期待巷口或許有個類似「深夜食堂」的小店,或街角有個雙葉他們一家經營的澡堂,讓那些絮語隨蒸氣散失。一碗熱湯或一池熱水都好,淋過那些部分石化了的自己,縫隙裡的埋怨藉著沖刷或能少了一些。隨熱水被排去哪裡?看能去哪裡就去哪裡吧,那像小河不知去向一樣的自己,去不到海裡,也可能會半途蒸發,年長後,心事是不驚動他人,不習慣走漏自己風聲的一池淺灘。
但那淺灘似的記憶中卻是有風有雨的,於是就先「安置」吧,它就是個浮油般的常態,融不進日常的速度裡,卻沒人比雙葉這女生還習慣的了,她這單親媽媽帶著女兒,你看她勤快地操持家務,去麵包店打工,她那不告而別離去的老公,留了一個澡堂給她們,廢棄在附近,久了各種氣味都有,過期的溼沼氣,悶在最裡面,她鎖好那歇業招牌,持續硬朗地維持著自己想要的樣子。
你遠看這麼溫柔的媽媽,勤快地像在逞強什麼?身為她鄰居的你,覺得自己擔心得有點多餘,但為何感覺她像珠子一串若不綁得緊,就要鬆掉似的顆顆散落。後來你知道她生病了,好像原本的胰臟癌擴散了,那男主人被她找回來了,女兒跟她媽媽一樣每天清掃著自己的日子,母女兩人自律地將日子刷得整整齊齊的,每個嶄新的日子絕不讓昨天蔓延進犯。
澡堂再次開張,他們一家被鄰居傳出彼此沒什麼血緣關係,男主人頭上包著紗布,還是一臉散漫狀地帶著一個在外生的女兒出現,雙葉也接納了,有人覺得不可思議,但對我們這每天收工後睏到睜不開眼睛的社區來說,日子想過得有點盼望,也就必須不清不楚的利著眼醒著。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錙銖必較是好社區、好人家的事,我們這社區,爸爸打柏青哥逃避現實、母親不堪生活的聊賴繁瑣,出走是有的事,像雙葉母親當年離開她、鮎子母親約好隔年生日來接她後的消失,離開這區,要去哪裡才圖個指望,那些女性的出走,或把孩子留給年邁父母養,在這個經濟停滯的場域與時代,並不是多稀奇的事情。日子被切割得瑣碎,每人勞動力秤斤算,我們對自己的認知也如銅板落袋般零碎,大人注意力分散且愣住了。
於是你看到雙葉忙裡忙外的身影,會有多珍惜有她,打起精神面對這原本已沒有什麼鬥志的地方,這裡如果還有什麼美的,大概就是你失去了目標仍能打起精神來的樣子,我們有一百個厭世的理由,但她一個也不選。
 我們有一百個厭世的理由,但雙葉一個也不選。
我們有一百個厭世的理由,但雙葉一個也不選。
光是展現想活著的樣子,就已經耗損許多力氣了,雙葉的女兒安澄以不起眼的方式跟世界彆扭著,希望自己隱形般格格不入,因為將四周都看進心裡,於是這世界小小惡意鮮烹熱煮的氣味是讓她卻步的,同學也聞得到她與多數不同的道德潔癖與那點恐懼,沒來由地就照原始本能霸凌她。
安澄那細細碎碎的聲影,不敢露出太多的自己,總是企圖把自己個性收得很好,那滿室招搖的、同學意圖以語助詞跟隨主流的大量廢話,她根本無法插嘴,那裡的「沉默」是經年累月的垢,老師息事寧人的姑息,電影裡沒有語言比沉默更明顯的,只有安澄的制服被偷時,她以脫到只剩內衣的強烈表達,戳穿了這一切聊勝於無的廢話堡壘。
那裡的女孩們,令人想到《惡人》裡的小城女孩,有的岌岌想嫁到遠方、嫁到更好之地,有的則如雙葉與安澄,一桌熱食挺一天的信念,因此大量鏡頭在用餐上,那堅守一個家的完整,是一桌人的用餐,其他時候,命運的侵略性則虎視眈眈,她們每天都向命運舉牌:「不是今日。」厭世的浪漫在於還有人在意,但那裡沒有這東西。
 她用一桌人的用餐時刻堅守一個家的完整。
她用一桌人的用餐時刻堅守一個家的完整。
安澄也是被生母拋棄的,多是年輕時懷孕,啞巴的她發現肩頭的現實壓過來,基於一種求生本能;或是像為女兒鮎子隨便找個父親,甚至搏命運緊張到發抖的幸子。那些求生與雙葉活著的態度是完全不同的,雙葉在死前的兩個月,企圖帶給她兩個女兒,或她周圍的人,包括搭便車的拓海,都是一種「活著的樣貌」,習慣了這生活沒出口的磨損,但目標與宣教般的女性雜誌幸福早就不是她所追尋的,而是與死亡正面迎擊地活著。
這並非在癌症擴散後才有的積極,而是命運如碎紙機將日常碎得面目全非時,她沒跟著際遇飄盪,而是相信為了每天的某一刻美好,每個小時登山越嶺似地活著。為何安排旅人拓海出現在他們母女旅行裡?因拓海的富裕家庭讓他去哪裡都無所謂、讓他有了什麼也不會稀奇,對照那些逃出這城鎮的女孩,兩方「人的樣子」早就被磨損,如今的厭世情結是來自這裡吧?有什麼是追求到了以後亮晶晶的?如果都失去了「人的樣子」的話。所以雙葉要沒目標的拓海去北方,沒有一定可以獲得什麼,而是那段日子你有了想「長途跋涉」的心。
電影的最後,快死的雙葉找到了當年遺棄他的母親,在很優渥的社區過著三代同堂的日子,卻不肯承認她曾有另外的女兒,多符合現代人「家」的定義,堡壘、保護、階級、血統與成功的象徵、是人評估你價值的標準之一,她是進不去那女人的除錯系統的。
跟雙葉「家」的概念完全不同,她包容四到五個沒有血緣關係的人,每一日都為圍著一爐火而有了目標,一生以一日來看,而非每日來成就一生,一生是稀釋了人,就連個加減沒憑據的空無演算式,而一日終究可以披掛在身上,讓人有個歸途盼望。
那澡堂有什麼好?跟幸福有關係嗎?除了聚回了離散的人,那種眾人在裡面拍拍打打的、那被水大力沖掉的、讓身體浮沉出真實表情的,那些早被忽視的疲憊……無非是句「你今天已經做得很好了。」

一頓餐、一池湯可以告訴你的,比起一生功過終將是個問號多了許多訊息。以日子為單位,人起碼能因而站得穩些,睡得更深點,於是最後煙囪送走雙葉而冒出的煙是粉色的。那能收留人的,別傻了,就晝夜而已,人生是場前不著村後不著店的旅程,人總誤以為此生被誰或神答應了什麼?但就只有今天這日子發光,也只有這樣,才能連厭世的基礎都沒有、連幸福這煩惱都讓人發笑。當代家庭價值是怎麼毀的?是誰答應了誰未來的過度驕傲吧,沒今日卻有明朝,難怪凡人多庸擾。
《幸福湯屋》(Her Love Boils Bathwater)為中野量太自編自導之作,由宮澤理惠、小田切讓、杉咲花、松坂桃李主演。描述一位所剩時日不多的母親雙葉在離世前,決心讓家中的傳統湯屋「幸之湯」重新開張,此外要找回離家出走的魯蛇老公,讓在學校被霸凌的女兒變得堅強獨立,還要完成全家期待已久的長腳蟹之旅。超乎想像的結局,激盪出無限淚水與生命力的親情物語。此片在蒙特婁影展、多倫多影展、釜山影展、東京影展都頗獲好評。在第41屆報知電影獎獲獎,導演兼編劇中野量太因此片拿到了新人獎、宮澤理惠得到最佳女演員獎、飾演女兒的杉咲花拿到女配角獎,《幸》片意外成為奪得最多獎項的大贏家。第40屆日本金像獎(又稱日本奧斯卡)頒獎典禮,宮澤理惠也憑《幸福湯屋》奪下第3座日本奧斯卡影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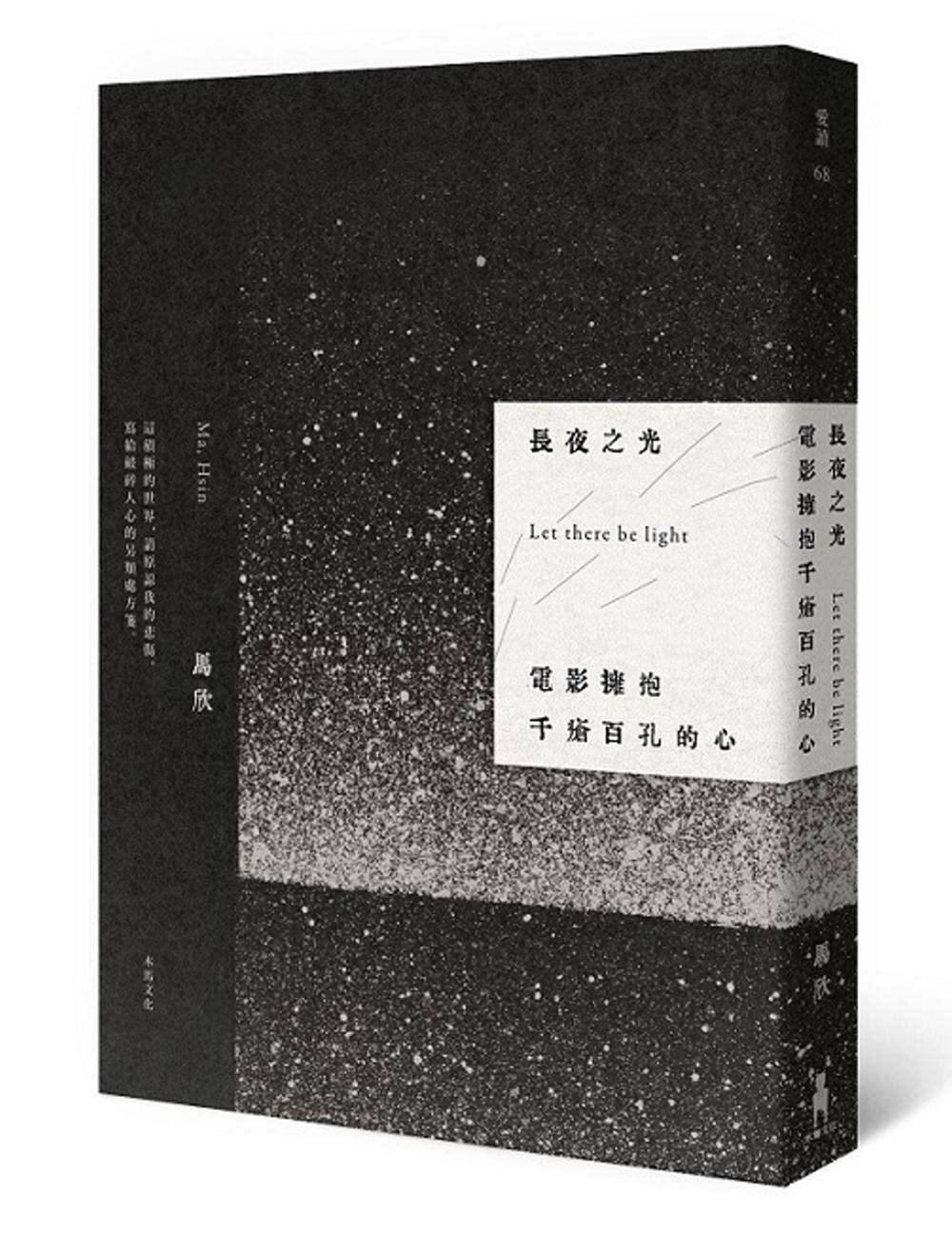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