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些人會將性侵單獨看待,其實性侵更潛在的本質是一場人格的殺戮,無論長期或短期,都是人格的謀殺。直接把他人的身體權剝奪,並且攻城掠地的宣示主權,靈魂會因此失去了下落或四處無家的呼喊,《最好別想起》這本書對焦了女孩們遭受這般精神殺戮的狀態。有的倖存於仇視自己身體,有的再也無法辨識出自己,叫任何名字都好,名字對此書中的受害者們已是失去意義的線索,不同只在於記憶將是荒蕪還是被捏造的。
卡夫卡的小說裡面,主角都以一個字母代替,因為預設他們早或晚都將被人格謀殺。那就像是進入記憶的迷宮,從災難發生的當下起,記憶被濃縮成一個點,找不出其他的確據。
珍妮.克拉瑪少女時期在離家不遠的樹林裡被強暴,全身有嚴重撕裂傷與瘀傷,並被尖銳物標記出傷痕,一個類似走獸標註印記的傷痕,像聲明是誰的所有物。她滿身是傷地躺在樹林裡,四周的灑水器如同以往噴灑著,讓她想起不久前的自己還可以繞著那裡嬉鬧,那時草地綠蔭都還漾著美好回憶的氣味,直到警察問起她:「走進樹林前,灑水器有沒有開?」時,一切回憶都被錯置了,都被覆寫上苦澀的記憶訊號,跟自己的日子當下碎裂一樣,成為一個個提醒警戒的符號,成為被拉進記憶深淵前最後的那句吶喊。
身體意識硬生生與內在撕扯開來
事發之後,自己還認得自己嗎?在這人格被剝奪的過程之後,自己要如何辨識自己?強暴不只是身體的侵害,更是一場突發的人格殺戮,你的身體權像野獸被扒除外殼與軟皮組織,硬生生與你的內在撕扯開來,只剩下一團人獸不明的血肉嗚咽。
美景鎮是個很小的地方,很少發生重大刑事案件,是個基本上富裕的城鎮,人們享受這安穩的郊區生活,是白領夢想的田園詩,珍妮.克拉瑪更是鎮上有名的家教嚴謹女孩,她是田園詩的代表,父母都有著象徵成功的事業。珍妮從小就被灌輸「只要身心夠強健,人生就會一帆風順」的積極人生觀,她謙和有禮、樂觀開朗,所有的一切都是「美景鎮」象徵的價值觀,與她父母所引以為傲的。但那天,沒有什麼原因,就偏偏是她,在治安良好的城鎮中,因為想離開那令她傷心的派對,而被隨機強暴了。
受害沒有理由
這件事情什麼原因都沒有,它就是隨機發生了,從此「珍妮.克拉瑪」變成美景鎮一個心照不宣的符號,一個極力掩飾的集體傷痕,不能輕易被提起,人們只能若無其事且異常尷尬著。「一切都會好轉的。」人們與至親都安慰她的爸媽,這「好轉」代表的速度,讓當事人無法理解消化,甚至她父母也被迫快速收拾自己的崩潰,以愛為名,讓美景鎮迅速恢復原狀,這裡像被催眠的城鎮一樣,這一家四口一旦過了他人認知的憂傷期限,除了「堅強」,別無選擇。
而當事人珍妮怎麼辦?
父母採取新的藥物療法,更動創傷的事實,也就是讓她忘記曾經被強暴的事實,《最好別想起》作者溫蒂.沃克(Wendy Walker)在後記提到,科學家已利用書中描述的療法,企圖更動曾上戰場、且面對創傷症候群的士兵記憶,但是否適用於民間引起了爭議。然而,人真能利用「記憶更動」,改變曾遭受的巨大創傷嗎?身體的創傷記憶真的可以跟腦中記憶分離嗎?心的疼痛真的可以被腦子改寫嗎?
腦中被厭棄的肉身 失去認知自己的線索
書中描述的珍妮個案與士兵記憶更動失敗了,雖然表面上成功,珍妮不記得發生過什麼事,但創痛感如影隨形,她甚至不知道來自哪裡,為何無休無止的記憶中有錯寫檔如鬼魅跟隨著她。不知因何而來的,便不知道如何消化與傾訴,於是她割腕自殺了,兩邊都劃下很深的傷口,空氣灌入傷口時固然痛楚難當,但身體想回復記憶的渴望更加催促著她,是曾有什麼樣巨大的痛苦,讓她畫下第二刀後,竟痛到如釋重負?
還原了那時靈魂被撕裂的當下,自己像一灘不明的生命剩餘物,即使被醫學重組了,仍然禁不起任何一個念頭,記憶像會嘲笑的載體,身心分離地如稻草人,夜幕一下,它就變凝視。身體是受不了被任何記憶棄置的,那汽球人消氣後的風景想飛又沉,種種不堪。
珍妮的父母對記憶改寫療法持不同意見,父親懷疑這真能好轉嗎?母親則因曾被繼父誘姦的經驗,腦中有個被自己厭棄的肉身,而不斷追隨與切割內在殘穢而掙扎不已。她知道性暴力下當事者的自我譴責,於是堅持女兒要做這個療法,也堅持女兒已經「好轉」,母女兩個都任由生活掩蓋一切,像一面破碎的鏡子,已失去認知自己的線索。
當時要怎樣抵抗才夠?自責為何身體屈服了?
母親夏綠蒂因為早年被繼父性侵,長期處於驚恐狀態,成年後仍有個「壞的自己」深藏心中,時不時需要被自己拿出來「鞭打」一下,必須藉由懲罰性的無高潮性愛來嚴懲自己,且上癮於「被懲罰」,不配這一切生活的自我排除只會更強大——為何沒有抵抗?當初要怎樣抵抗才夠?為何身體屈服了?為何讓人將你像動物一樣擊倒?為何覺得這樣的自己這麼噁心?
你可以發現,這兩個受害者的靈魂都被撕裂,風吹四散,失去線索或線索早被羞恥感覆蓋。只是活著,失去任何認知自己是誰的力量,被自身的動物感霸佔。
少女們被視為獵物的驚恐與陌生
小說中,主述者是個企圖回復珍妮記憶的心理醫生,他描述著某一德高望重、在地方頗具聲望的人物的性成癮狀態:「他的自尊跟高速公路上看板一樣高傲……」習慣將對方當成走獸,享受對方失去主體權的做愛,即使不是性侵,也可能是一種領土征服。有一種性,是滿足自己「集點」似的虛榮,而被這樣無禮對待的女生,常被眾人質疑為何屈服於那權力的征伐?讓人無法分辨她當時的意願。這對男性來講或許是故意漠視的模糊,但對女孩們來說,則是陌生而驚恐的。
讀《最好別想起》時,我想起林奕含筆下的女主角房思琪,多年後知道發生當初的是什麼樣的暴力,但一場性暴力發生時,無論是性騷擾或性侵,受害者很多時候會愣住,過度驚恐,不知所措,會因痛苦而抽離當下,因為許多少女對自己身體的反應如此陌生。如書中描寫珍妮母親夏綠蒂早年被誘姦的過程,即使心生反感,即使感到噁心,作者直指,身體是一台機器,你完全不知道它會有何反應,同時會深深為自己的身體而憤怒著。「他看起來像抓到獵物的野生猛獸。」身為獵物的身體到底該如何反應?該如何掙扎?這副身軀,再怎樣都是被自己狠狠怪罪的。
被人格殺戮後 如何拿回自主權?
事後,夏綠蒂的母親反而是趕走自己的女兒,夏綠蒂也因負罪感無所怨尤,甚至以為自己可能愛上繼父,一如很多人不解房思琪經過5年後的認知,因為性侵就是一場人格謀殺,當人像可被宰控的走獸折磨,並被拔除身體掌控權時,她的尊嚴與價值很可能也被割除;也有人或為了減輕痛苦,選擇說服自己:這是愛。不同於其他暴力,它就是個宣示主權的壓迫,片甲不留的侵略,《最好別想起》描述的是:無論當事人失去記憶與否,要拿回自己身體與尊嚴的掌控權有多困難;要有多大的意志,才能從某一點的記憶攔截,喚回對自己整體的感知。
書中各個受害者,都迷失在自己的記憶裡,竄改與否,回憶都潛藏著禿鷹盤旋,利爪一伸的獵捕性。
人會消失在自己的身體裡,讓它長時間沒有主人,可能已經部分死在事情發生的當下,或以倖存姿態,仇視或旁觀著自己人生的路過,如書中結局的另一個秘密主角。
任何性騷擾都不能等閒視之,因為人可能如此保持呼吸地死去。
作者簡介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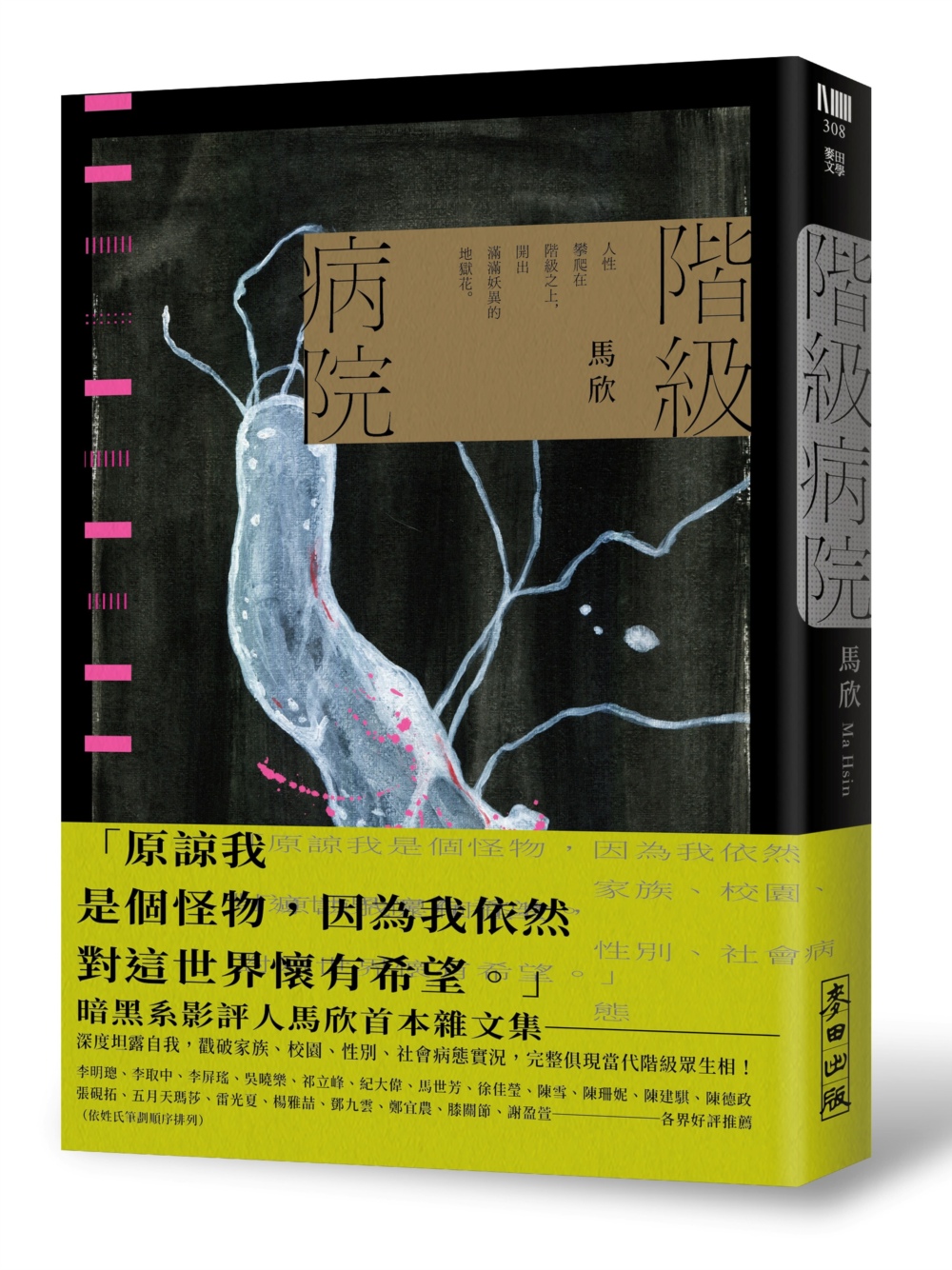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