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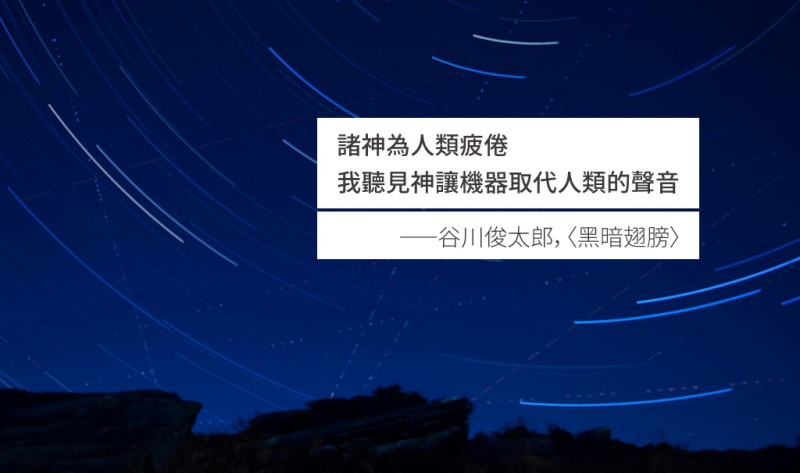
村上春樹筆下的田村卡夫卡,以及岸本齊史所畫的宇智波佐助,是我讀過最孤獨的兩個離家少年,為的卻是幾乎相反的理由,前者要逃避父親那比死亡還痛苦的弒親亂倫預言,後者則是急欲獲得報復能力,殺了那滅絕家族的唯一兇手——他自己的哥哥。
整部《火影忍者》超過一半,其眾多支線所匯聚的大河,就是鳴人尋找佐助、要將他導回正途的過程。但這接近慘情BL追逐戲碼的設定並非此處要討論的重點,我想破解的是,為什麼在加上無愛少年「我愛羅」之後的這三個遺族同期生中,我始終對佐助最感不捨,好像可以的話,把幸福的扣打分給他也沒關係。
或許,是因為他是三者中唯一清楚經歷了「成為孤兒」過程的人。當鳴人和我愛羅只能透過觀察和想像去感受落差時,佐助是活生生經驗了墜崖的人,像鯨向海寫的:「你不能給人家點火又吹熄這樣他比完全的黑暗還痛苦。」
當然,痛苦就像洋蔥,同樣招惹眼淚,但還是有許多層次。我以為可愛的老人谷川俊太郎非常會描繪各種無以名狀的痛,如傳說愛斯基摩人有許多關於雪的辭彙,年紀大了,對心傷這種翻譯到世界各地都不需要注釋的人類天分,自然也會懂很多吧。像他的〈二十億光年的孤獨〉所寫:「人類在小小的球體上/睡覺起床然後工作/有時很想擁有火星上的朋友」、「萬有引力/是相互吸引孤獨的力」,用遙遠得像神明馬拉松的距離道出突如其來卻不可得的渴切,而那急需靠近某生命體的求救訊號,確實也像煙和霧也有想被地球抓住的時候。
或是〈悲傷〉:「在聽得見藍天的濤聲的地方/我似乎失落了/某個意想不到的東西//在透明的昔日車站/站到遺失物品認領處前/我竟格外悲傷」。
大概沒有比這更適合描述佐助出走的心理背景了。失落是成長,失落了意想不到的東西,則是跳級打怪,只能努力活著,去實踐尼采所言:「凡殺不死我的,必使我更強大。」只是不知,原來真正的悲傷,是在真相翻盤過後,發現付出的代價已不可逆,站在失物招領處,就算找到了失落之物,已經僵硬的心臟也難以恢復彈性,凹痕將永遠在那裡等待填滿。
且畢竟已經以告別的手勢種下了恨,被悲傷撲倒的日子,是每天仆街遭路面痛擊般無止境的懷疑。以另一首谷川俊太郎的〈日日〉來說明吧:「某天我這樣想/難道有不被我舉起的東西嗎//翌日我這樣想/難道有被我舉起的東西嗎//我傾斜地走在/容易生活的日日//這些溫馨的日日/彷彿以可疑的畏懼心情凝視著/接二連三與我擦肩而過」,實在是寫出了人生難處之一,即是被吸食意志的問號包圍。放大一萬倍看,正如同佐助的大絕之一「天照」:使用寫輪眼直視,讓目標被溫度接近太陽、連火焰都可以併吞的黑色火焰侵噬。
 寫輪眼(圖/ Wiki)
寫輪眼(圖/ Wiki)
我喜歡張惠菁在談論田村卡夫卡時,說他不似許多作家所寫的旅程,都是讓角色去尋找新生的象徵;15歲的少年之所以踏上征途,可能只是要防止自己繼續流失,繼續失去……其實套用在鳴人和佐助的身上都很適合。只是,重生和止血真是截然不同的概念嗎?死守著再多一秒就成滄桑的悲傷,時常提醒自己別為了吐露真心而造成他人困擾的我,又更接近何者?
只能給自己,給佐助,給鳴人,也給田村卡夫卡一首詩了。谷川俊太郎猶如創世紀為所有無中生有之難題做出解釋的〈黑暗翅膀〉——
天降落下來
厚厚的帷幕之上有無數星星的跡象
最大的規律
我聽見它在哭泣
月亮被誹謗
雲朵緘默不語
天空和土地的氣息
是我們全部的氣息
可是我們
真的知道自己的處境嗎
天空變得醜陋
樹木和青蛙彷彿憎恨著誰
諸神為人類疲倦
我聽見神讓機器取代人類的聲音
時間是玻璃的碎片
而
空間已被喪失
今夜 我帶著黑暗翅膀
為了弄清一切有關本質性的問題
湖南蟲
1981年生,台北人。淡水商工資處科、樹德科技大學企管系畢業。得過一些文學獎,入選過一些選集。著有散文集《小朋友》《昨天是世界末日》、詩集《一起移動》。經營個人新聞台「頹廢的下午」。
點圖閱讀更多【詩人╱私人讀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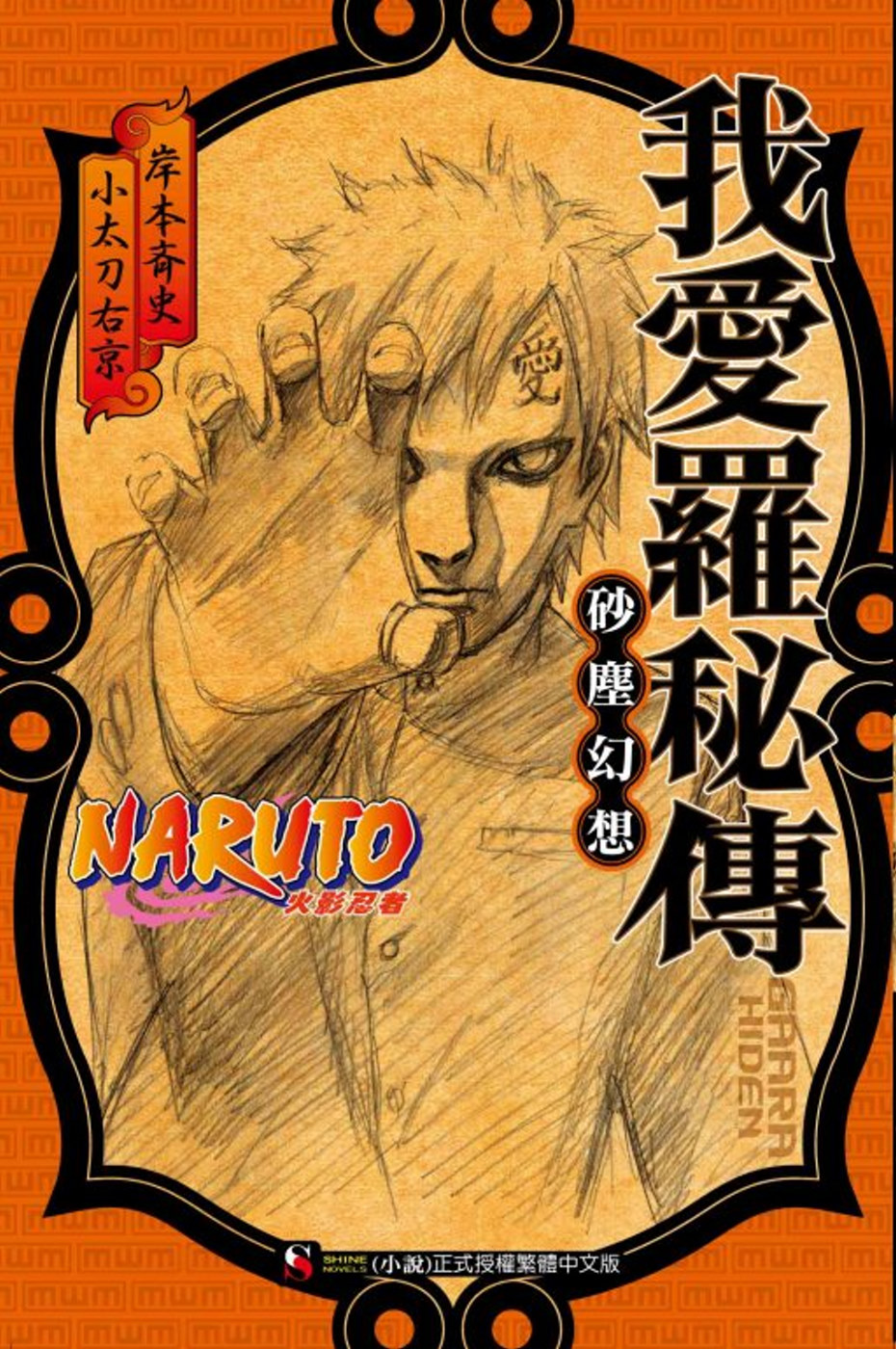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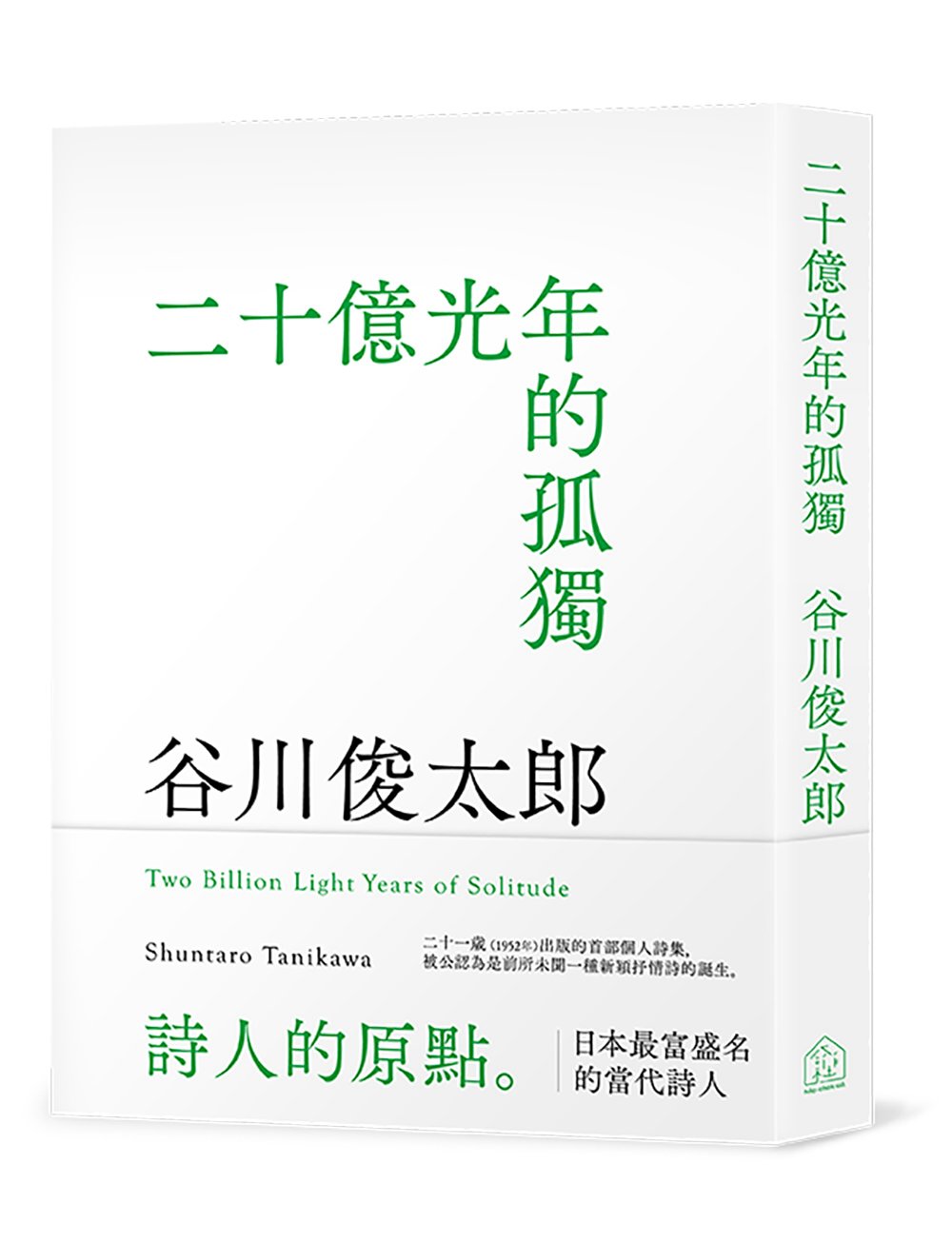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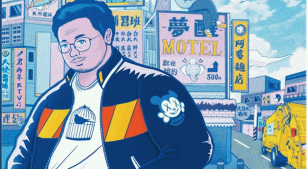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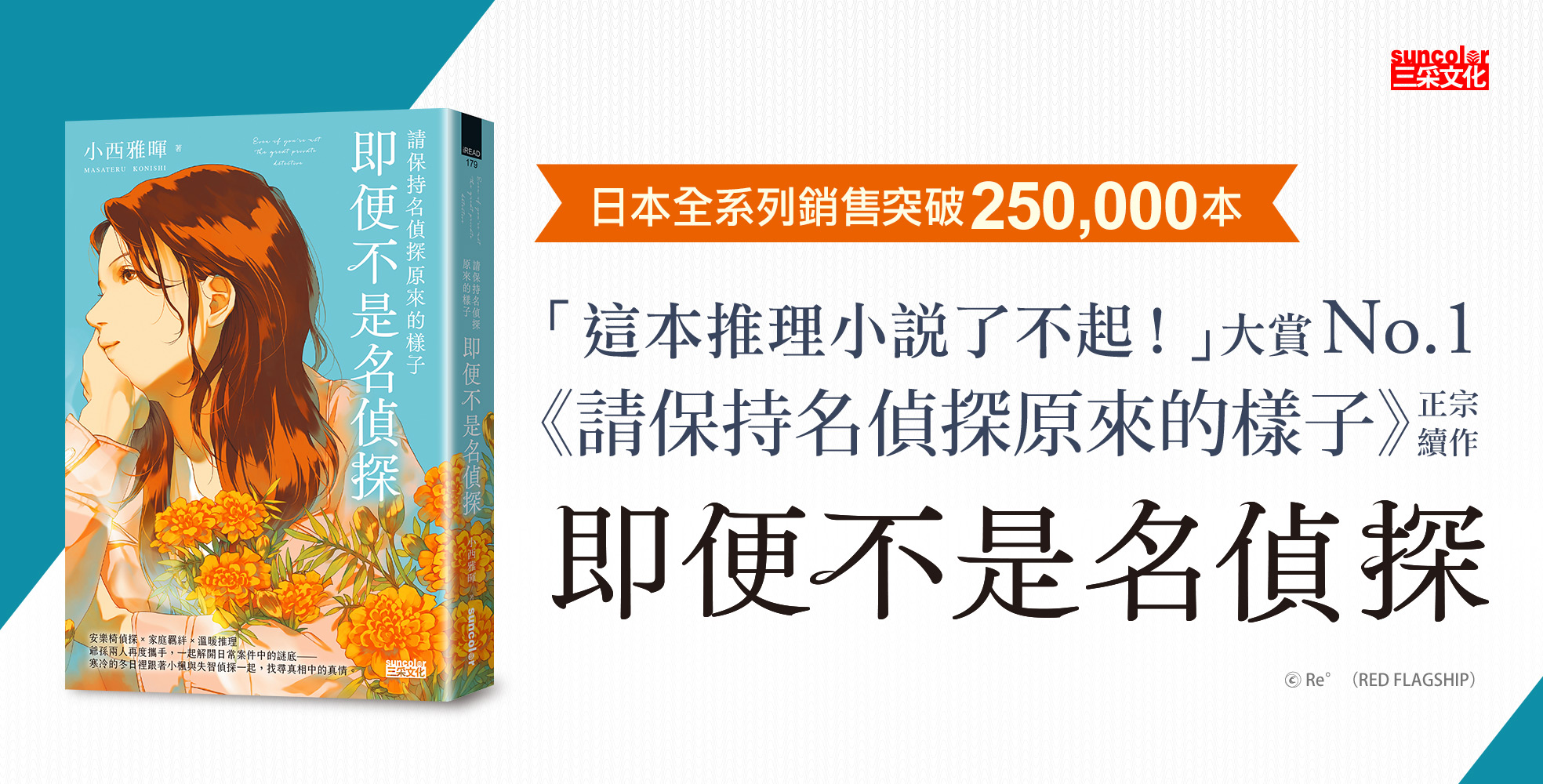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