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讀完《倫敦腔:兩個解釋狂的英國文化索引》之後,我忍不住打開塵封已久的部落格,翻找2007年剛到倫敦時寫下的日記,我在那年中秋節飛抵早先只在電影與廣播中存在的大城,連續幾個月寫的札記都充滿了灰與藍,在一篇被我名為〈Bridge〉的札記裡,這樣寫下一條泰晤士河分隔的階級與注定失敗的語言:
奇怪的是光是駛過一座橋眼睛就上了濾光鏡,畫片裡的倫敦狡猾又佯裝神閒氣定地坐著,奇怪的是我可以單單從人們的步履判定她們的去處,她們的手勢是旗語,風衣下襬是我的地圖。
過分熟練的語言是傷害,不熟練的是憂鬱,我遠離傷害之處迎向憂鬱,公車上有人為我們爭吵、和好。這個城市的音樂都在行人的耳朵裡,沒有誰與誰分享。
做一個異鄉人,你便無法脫離遭城市收編同時在城市浪遊的命運。《倫敦腔》作者白舜羽在「牡蠣卡 Oyster Card」(書中關鍵字在此以粗體標示)一詞裡詳細解說了源自莎士比亞名言的這張倫敦大眾運輸儲值卡,最末自嘲又甜蜜地下了結語:「世界不一定是我的牡蠣,但牡蠣卻是我的倫敦。」這場以「London A to Z」為骨幹的寫作,正展現了此般深入淺出的試圖持平之眼,讓可能乏味可能獵奇的異文化探索挾帶一股古典散記興味。
選字是寫作者的眼睛,正如取景洩露攝影師的心,以寫作者費心揀選的關鍵字所起始的寫作,本身便不可能脫離私書寫的個人性。城市屬於公共、同時深揣秘密,即使在同樣的關鍵字底下,我們也多得是縫隙得以另闢蹊徑──
 Claire de Rouen Books書店
Claire de Rouen Books書店
讓我們回到「布洛克利 Brockley」吧,這裡是歷久不墜的英國綠黨大本營,出了車站迎面而來的小咖啡店The Broca在冬天會有帥氣吧台手調製出一試難忘的Chai Latte,Kate Bush和John Cale分別在不同時期蝸居在Wickham Road儲備他們即將搖動世代的音樂;膽子大的話,或者從小小的Ladywell車站逃票上火車直達市中心的「滑鐵盧車站 Waterloo Station」,記住要避開上下班時段及其後一小時,否則在出站天橋上遭埋伏的警察罰鍰20鎊可就是窮學生一整週的菜錢;從查令十字路與Manette Street轉角的色情書店上二樓,你會遇見倫敦首屈一指的攝影書店Claire de Rouen Books,它所在的位置,正是華美偌大的「佛伊爾斯書店 Foyles」整修前的舊址(當然,占地約莫只是Foyles的樓梯櫃大小),L形格局略嫌侷促,卻是全城攝影迷的美夢,時有珍本攝影集與年輕攝影師初試啼聲的創作展。2014年書店靈魂人物Claire過世的消息使人無比感傷,我記得猶豫一整日之後又折返回去買下荒木經惟限量攝影集的午後,滿頭華髮的Claire為我將書收進提袋,淡淡地說:「他很不錯。」那為我們這些影像的困獸守護美夢的女子,其優美的靈魂仍在二樓小小的窗口亮著永遠的霓虹;更別提離開倫敦已五年,至今仍無法戒除使用「快煮壺 Kettle」的習性,即使我們心知肚明:如何相同的茶葉與一致的溫度都無法沖泡出記憶裡的倫敦茶,那是硬水流淌的脾性,頑固的城市氣味。
倫敦究竟是一座怎樣的城市呢?我總以為自己已經盡情寫過一次,在小說裡愛死愛生了。我羨慕魏君穎與白舜羽學究漫游式的日常節奏感,倫敦在我身體裡是無論如何絕不平靜的,它時醒時醉,是比瓶裝水還便宜的《衛報》,是Amy Winehouse的鳥巢頭攻占東南區青少女造型的一年,是年輕到嚇人的The xx崛起的夏天,是James Blake還在「金史密斯學院 Goldsmiths」學生咖啡廳裡閒晃的成名前刻,是入夜之後愛欲橫陳的地下舞會,Soho的Candy Bar、Hackney的 Dalston Superstore、Visions。邁入29歲那晚,朋友喝得太急、橫倒在地下酒吧Bardens Boudoir的階梯上,我被許多人摸頭擁抱,沒有回家,生日願望是「不要怕求救、希望一晚只喝一種酒、寫專注力更強的東西」。那些日子我的關鍵字是「Underground party」與「Race Fetish」,輟學那年倫敦才真正找上我,對我說妳是怪物但不要怕、我愛妳,整座城市以不絕愛語與極限體驗招引失去一切的孤兒應喚沉淪、而後佯裝無謂地伸出雙臂如實承接。
憤世的我始終沒有加入假造護照大隊、如願破壞國界政治,至多請朋友偽作了在學證明以取得歐陸入境簽證,最後的最後我終究離開了那座必須以大量金錢與自尊堆砌維持的城市,心有不甘,血液深深記住了那些年所聽聞的倫敦腔。那腔調既擁有高雅睥睨的姿態、也尾隨低俗不堪的暗影,我費盡心思嘔啞嘲哳地呀呀學語,從內到外依樣打磨細節,久久才知曉它為我點穴通懂的,不是別的,竟是根深蒂固不曾深究的台灣腔。疼痛褪皮之後從此成為一名不畏懼自己能操爬說語的少年,確認自己可以願望成為佛地魔或是哈利波特,我的惡星情人倫敦使我明白自己是一條怎樣的蛇,與誰真正擁有一道電光石火連結命運的傷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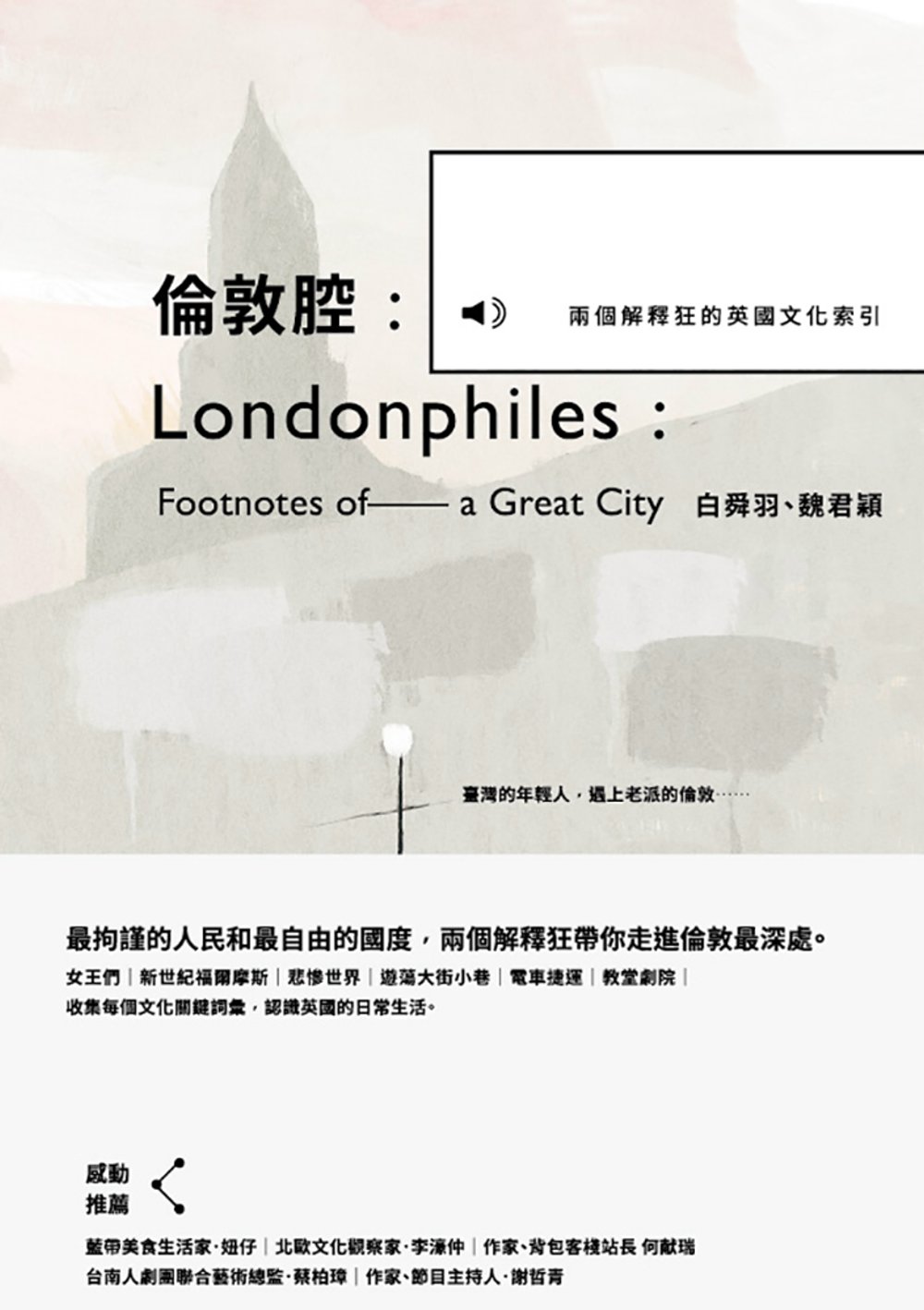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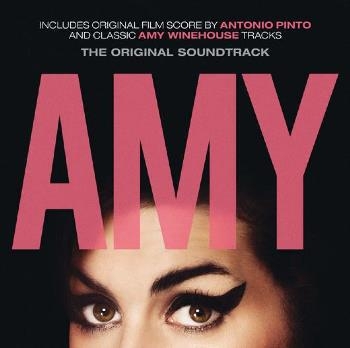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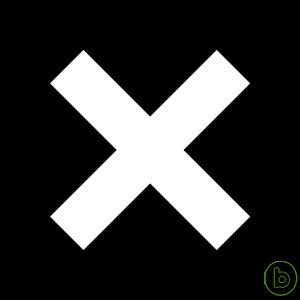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