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若你問徐麗松,翻譯這份工作帶給他什麼感覺,他會說,是種享受。
「譯書的時候,我最喜歡晚上七、八點就睡,凌晨兩點起床,泡一杯茶,然後直接工作。」徐麗松鉅細靡遺地描述著,語氣中不無興奮。「那個時間你醒來,幾乎所有人都睡了,萬籟俱寂,沒有任何干擾,連車聲都沒有,那種感覺特別珍貴,可以很安靜地做很多事。一打開電腦,就能立刻進入工作狀態。」電腦開機,人也開機,一做就停不下來,直到天明。「你的工作興致高昂,效率極佳;等到需要停下休息時,剛好看到窗外日出,那樣的過程很美。」在朦朧的晨光中好整以暇地吃個早餐,接著又進入第二輪的高效率階段,午後才把腳步稍微放慢,給自己一份下午茶;黃昏時自螢幕前抽身準備晚餐,天黑就睡,深夜再起。一天可以譯上足足16小時,如此持續一個月。這是徐麗松最理想的譯書作息。
以這樣近乎鐵人的紀律,2012年從法國返台定居的徐麗松,短短數年內,接續翻譯了《反抗的畫筆》《品牌概念店》《成熟風格的基礎》《沒有地圖的旅行》《法式誘惑》《走路,也是一種哲學》《騎乘鐵公雞:搭火車橫越中國》等數本英、法文作品,中間兼及《蔬菜是怎麼長大的呀?》《皮耶.艾曼,可以教我做法式甜點嗎?》等童書(他說童書篇幅較少,有些甚至一天就能譯完),速度與數量皆十分驚人。而其中《夜訪薩德:薩德侯爵對談錄》一譯,讓他獲得第一屆「台灣法語譯者協會翻譯獎」,見出徐麗松不只產能傲人,品質更不遑多讓。評審之一的文化大學法文系教授胡安嵐認為他的譯筆「對語言及表達的層次有極佳把握,中文與法文呼吸著同一空氣,聽到的是相同的聲調」,這是他所得過最感動的評語,也是從事翻譯以來,始終不變的追求與執著。
 徐麗松近年的部分譯作。
徐麗松近年的部分譯作。
但徐麗松倒也不是一開始就矢志成為一名圖書譯者。雖說從事翻譯工作多年,然他承接的多為跟著業主到處跑的隨身口譯,或是短打型的文書翻譯。「我老覺得自己應該無法靜下心來好幾個月,好好譯完一本書。」笑說自己總是「不安於室」,連身邊朋友也說他一點都不像喜歡待在家裡的巨蟹座,「但後來當我成了專職譯者,我逼自己必須每天待在家裡,才發現原來我可以過這種生活,而且甘之如飴。」
甘之如飴的理由,細說起來,不只是這些作者為徐麗松打開一扇扇不同的世界之窗,更因為從那些窗看出去的形形色色,新奇中總帶有一絲熟悉。「例如翻譯《走路,也是一種哲學》時,書中提到尼采晚年住在南法的艾日村(Eze Village),我想起20年前,我去法國的第一年,偶然去到那裡,就走過一條『尼采小路』。」當時的他絲毫不以為意,及至譯書之時,驚覺自己的足跡曾與大哲學家交疊一起。或又他也從這本書中,得知自己旅法時期,每回開車前往義大利、穿過阿爾卑斯山的那條路徑,數百年前大思想家盧梭也曾一步一步踩踏而行。「翻譯就是會在不經意的時候牽動了太多東西,讓我知道我曾和這些人看到同樣的風景。譯書有太多這樣的快樂了。」

《夜訪薩德》除了為他帶來獲獎的肯定,也給了他更大的驚喜。「我以前對薩德只有很朦朧的瞭解。20年前剛到法國時,第一次去巴黎市中心的書店,一進去就看到一本法國史學家香塔勒.托瑪(Chantal Thomas)所寫的《Sade》(1994年出版),基於好奇我便買下,跟著我搬來搬去,搬回台灣。」原本也就是一部與書架上諸多書籍四處遷移的書,無甚特殊之處,最多也就在他承接《夜訪薩德》的翻譯時,和其他同為薩德主題的書,從架上移到桌前來。
但在《夜訪薩德》得獎之後,命運埋下的細線才輕輕扯了一下。原來頒獎典禮上的外賓,其中一位就是香塔勒.托瑪。「這讓我太震撼了──我譯了薩德、得了獎,才有機會參加典禮;而碰巧是受邀貴賓的香塔勒.托瑪,她寫的薩德是我在1994年剛到法國時買下的書。」這說不清的巧合,成了徐麗松與香塔勒.托瑪友誼的契機。那天,他們聊起彼此的法國生活,比對出兩人竟曾是前後隔一條街的鄰居,到過同樣的店家,買過同樣的鹹派,看過同樣的花開花落。「誰能想到,居然會有一個20幾年前的線索,從我去到法國,一路延伸到今天。這一切奇妙的經歷,都是翻譯帶來的。」徐麗松說。
正因如此,當這位譯者被我們笑稱簡直是個工作狂,他也笑著承認自己真的就是,絲毫不以為忤。「為了翻譯必須很宅,我甘願當個百分之一千的巨蟹座。那真是非常享受的事。」他又重複了一次。可以想見,在他往後的翻譯生涯裡,必定會再重複無限多次吧。
〔徐麗松譯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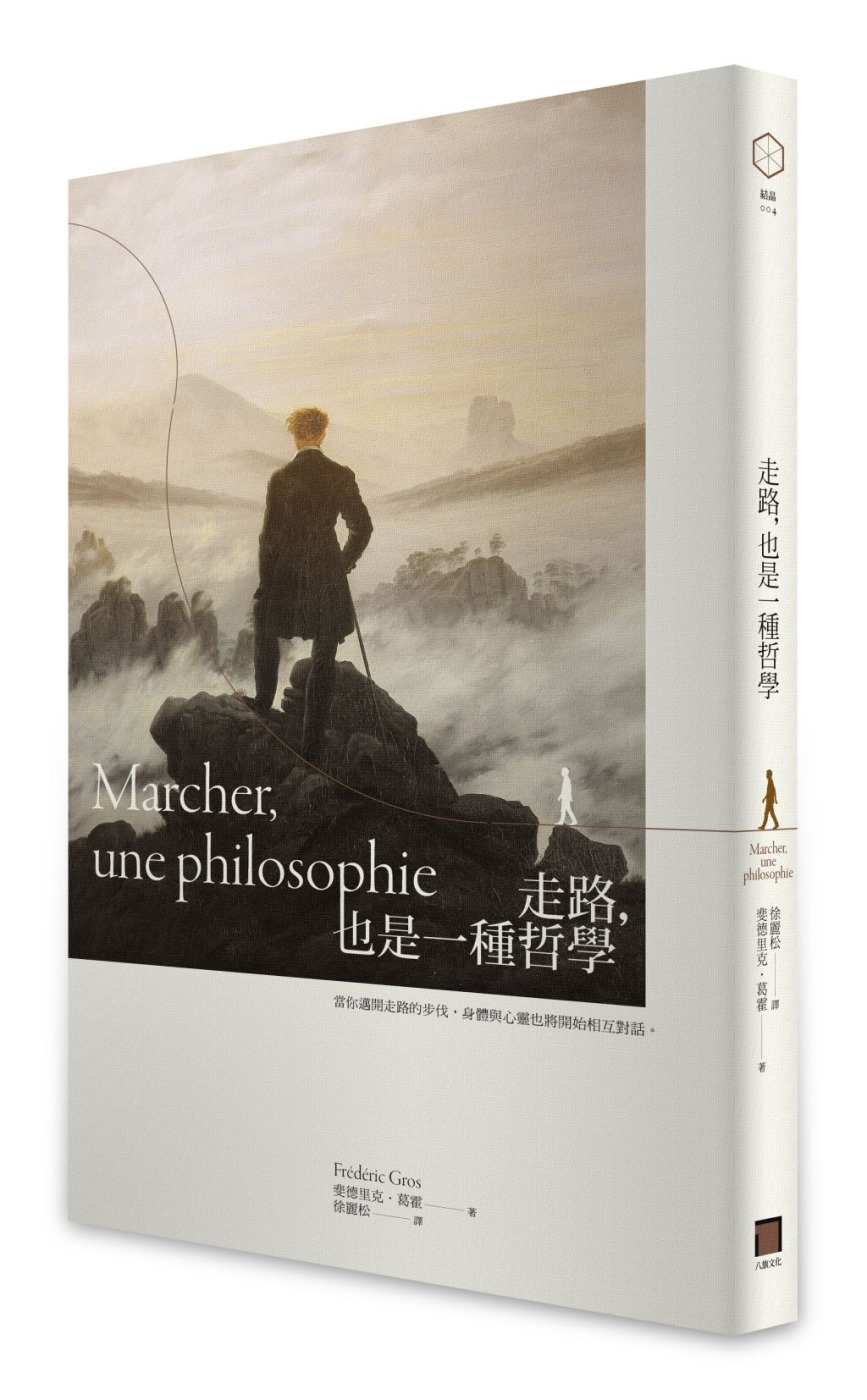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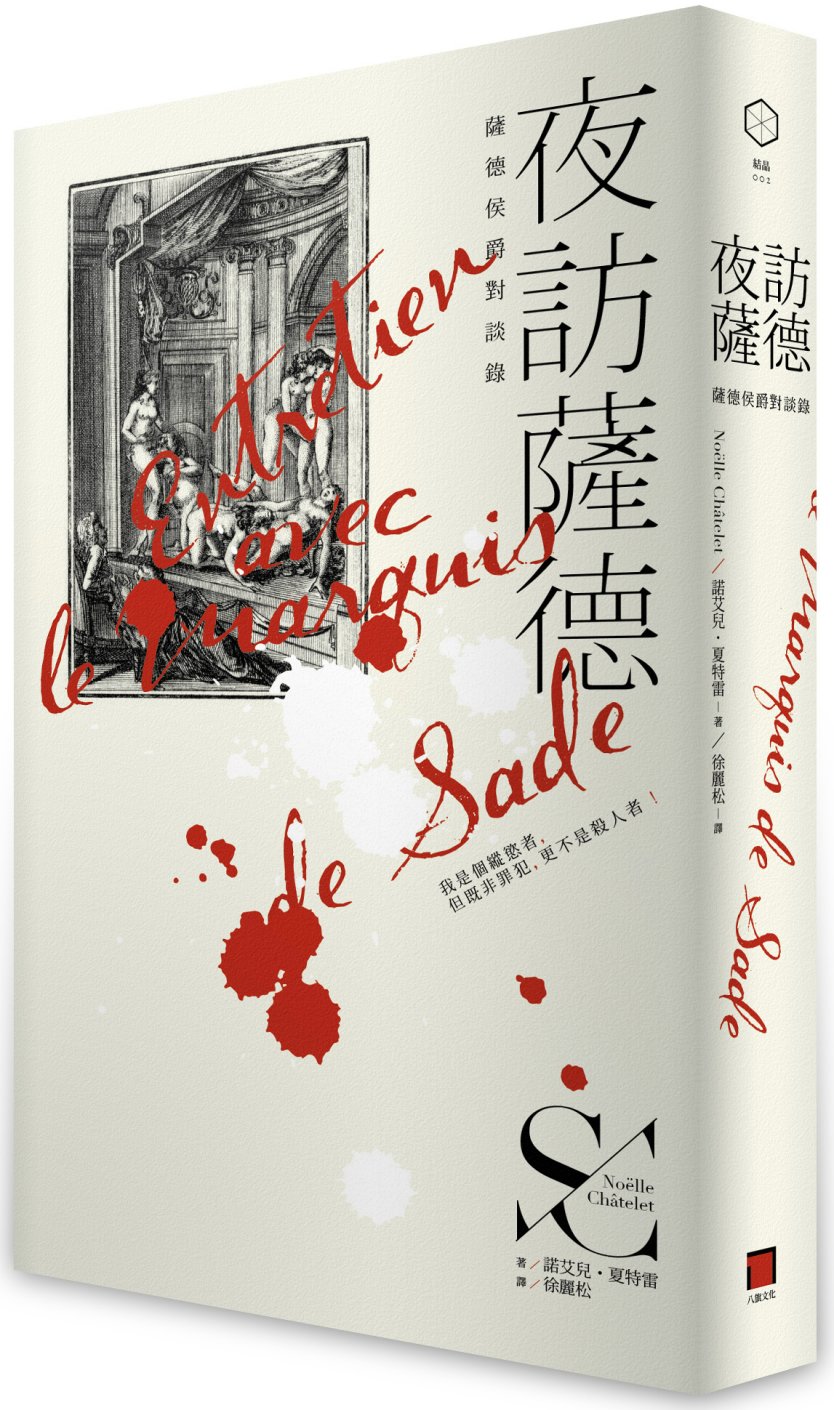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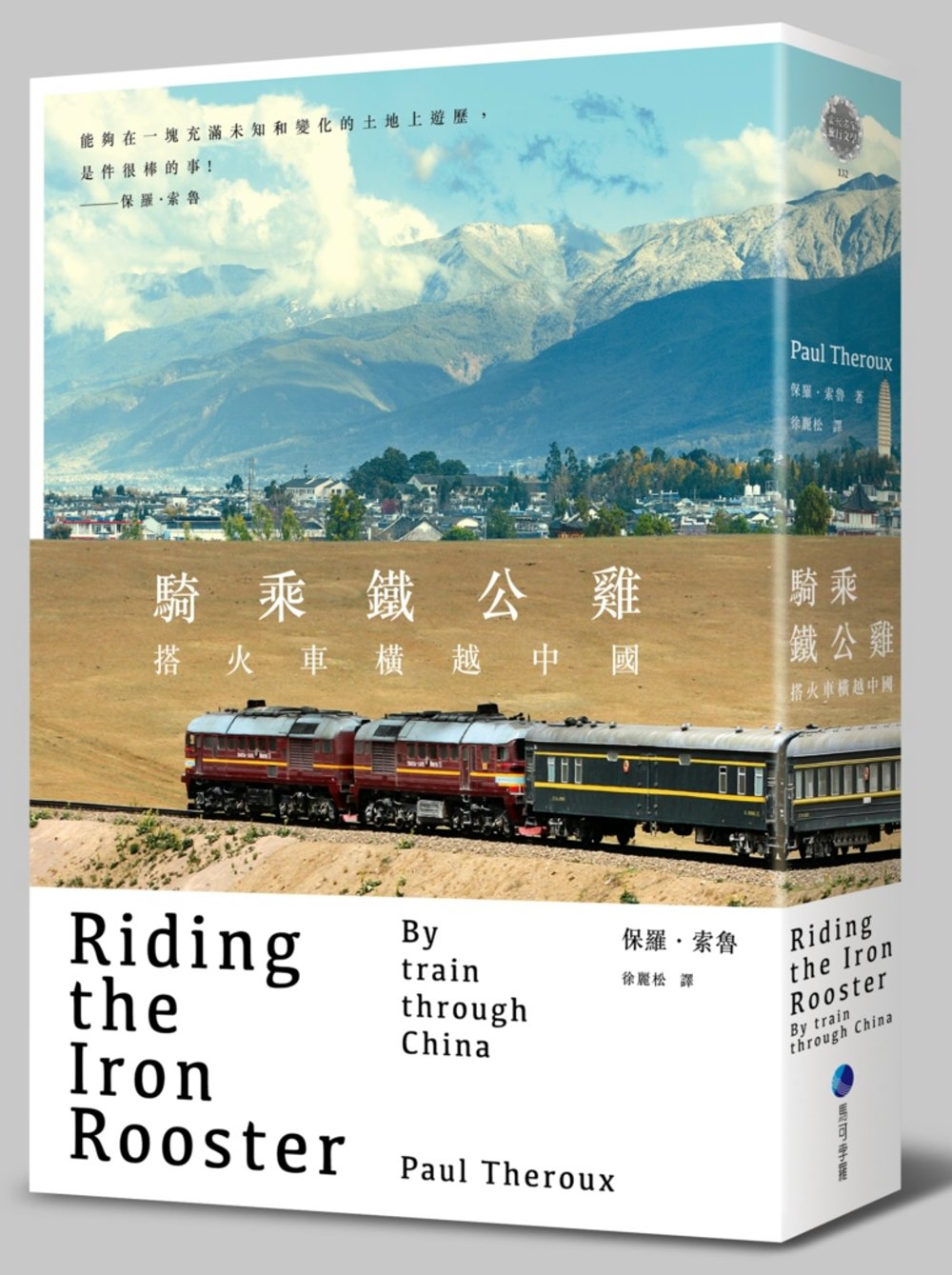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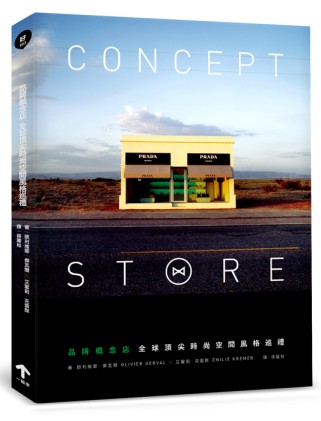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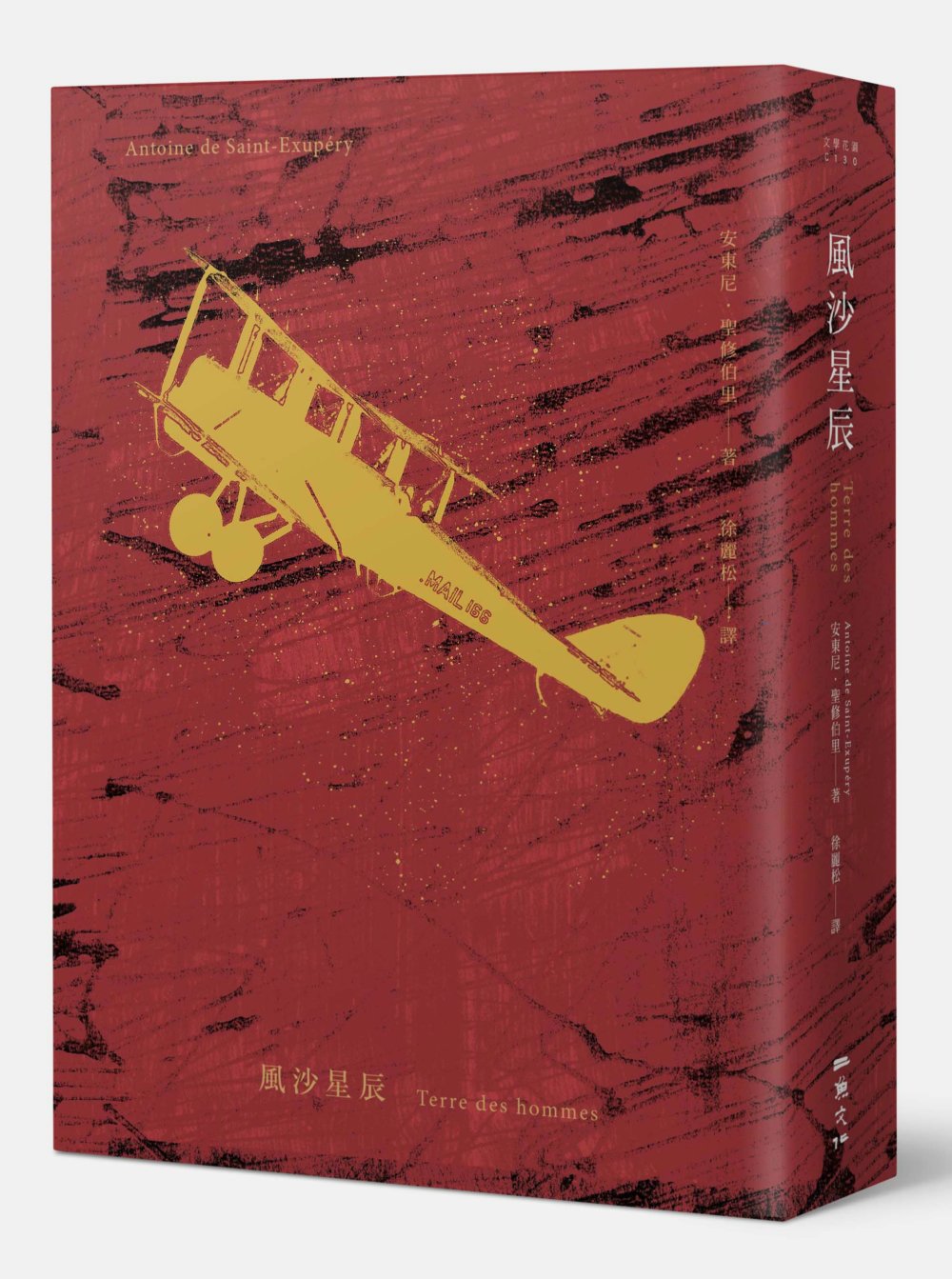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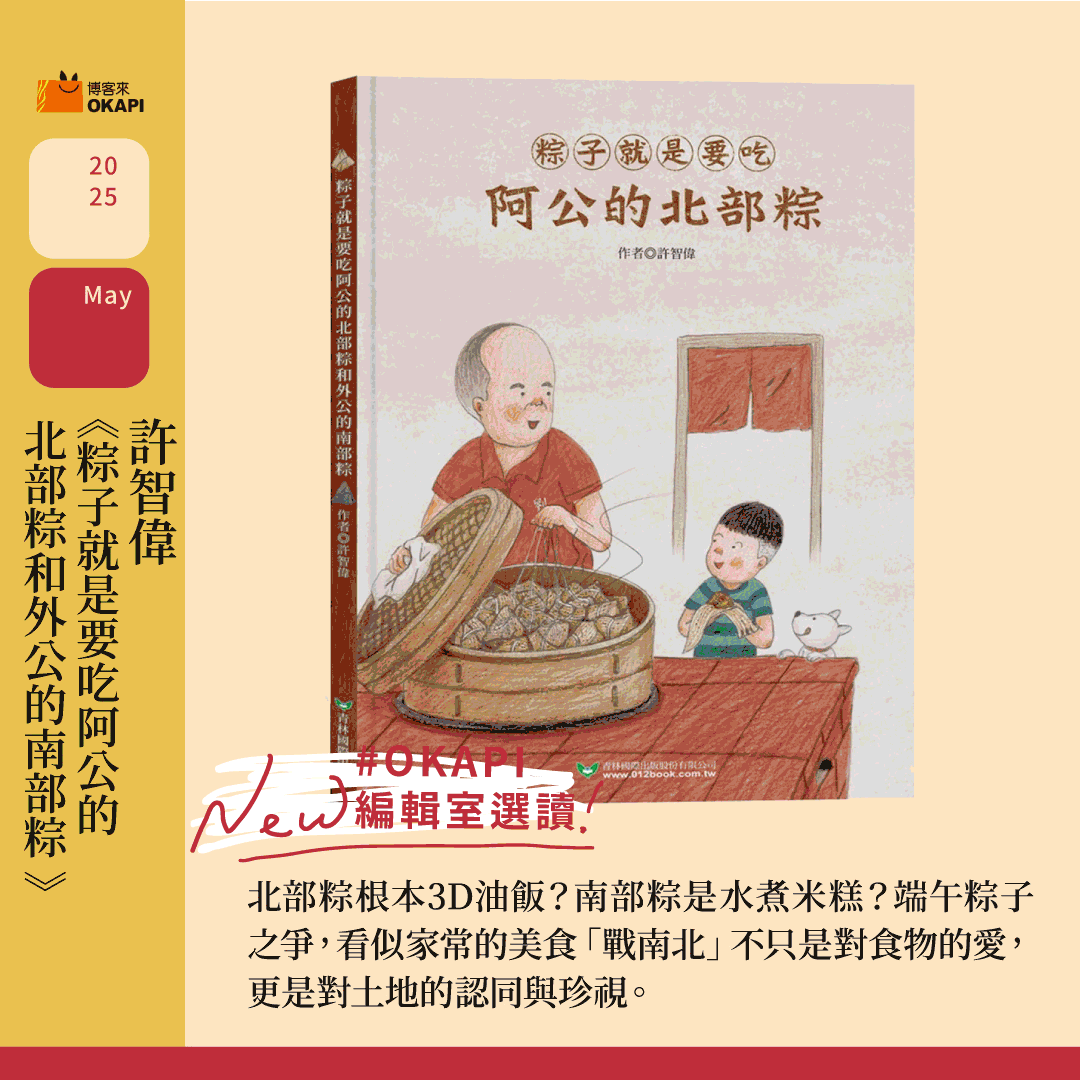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