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據我所知」,描寫原住民的同志文學極少。更精確地說,描寫原住民同志的「中文」文學極少──同志文學和大部分的台灣文學一樣,都是中文介面,都預設了漢人中心主義,都將原住民(原住民作者、原住民讀者、原住民文學角色等等)嚴重邊緣化。正因為中文介面文壇中的原住民和漢人各別屬於弱勢和強勢,所以原住民文學的研究者在乎「區分身分」(區分誰是原住民,而誰不是):研究者重視具有原住民身分的作者,鼓勵原住民描寫自己人。漢人身分的作者,以漢人角度觀看原住民,通常就落在原住民文學範圍之外。
雖然原住民文學研究者重視「區分身分」,但是同志文學研究者不能夠只看原住民身分作者所寫的原住民同志,也要看漢人身分作者寫了什麼。漢人身分作者筆下的原住民同志形象可能讓原住民文學研究者大不以為然,但是這些不為人所喜的文學形象終究還是同志文學的歷史痕跡,我不能假裝沒看見。
「據我所知」,原住民同志只在下列樣本出現:白先勇的短篇小說〈滿天裡亮晶晶的星星〉(1969)、席德進(1923)的《席德進書簡──致莊佳村》(1982)、白先勇的長篇小說《孽子》(1983)、伊苞(1967-)的短篇小說〈慕娃凱〉(2000)、伊苞的散文《老鷹,再見》(2004),以及我上個月已經在OKAPI討論過的郭強生2010年代三本小說《夜行之子》《惑鄉之人》《斷代》。「據我所知」,這批作家中只有伊苞表明具有原住民身分(排灣族),只有伊苞的作品算是原住民文學。其他作家的作品算是漢人文學。(我在此特別感謝瑪達拉.達努巴克、Freya、政大台文所洪瑋其同學跟我分享閱讀經驗)
上面兩段強調「據我所知」,並不是要說「我很厲害」,反而是要承認「我很有限」:描寫原住民同志的文本散置各處,總量必定超過我所知道的樣本數。不過我並非只是要搬出「掛一漏萬」這類公式化的客氣話,而是要強調:任何人只要一站在「我」這種旁觀者的位子(旁觀同志文學的讀者、旁觀原住民文化的漢人等等),就應該承認自己能力有限。
雖然我同意「區分身分」對原住民研究很重要,但我想指出「身分的區分」是一種雙面刃,有利也有弊。不少人就樂於操弄「身分的區分」,把芸芸眾生之中的原住民(或同志,身心障礙者等等)挑出來,然後進行歧視。原住民和同志這兩個族群之間存有種種差異,但卻共享一種命運:總是遇到喜歡調查身分的旁觀者。有某一些旁觀者特別粗魯,見到不熟的人,就當場逼問對方:「你是不是原住民?」或者「你是不是同性戀?」。潛台詞是「我看你明明就是,我就知道」。這種無禮的旁觀者把自以為是的快樂(「我就是知道」──我掌握智慧,掌握別人的身世)建立在弱勢族群人口上面;「我」是主動的知者,弱勢族群的人是被動的稀有動物。有一些旁觀者「比較有禮貌一點」,避免直接逼問被觀看的人,退而求其次,跟自己人說悄悄話:「媽,你看剛才那個護士是不是原住民?」「爸,你看,上次那個警察是不是同性戀?」這些指指點點,與其說可以證明旁觀者的洞察力,不如說更可以曝露出旁觀者對於刻板印象的迷信(某人皮膚黑、某人娘娘腔等等)。
面對文學作品的時候,每個人都是旁觀者,也就是讀者。許多人一談到「同志文學」就想要「定義同志文學」,然後就想要進入「區分身分」的遊戲(區分誰是同性戀,而誰不是):只有同性戀身分作者寫的作品才算是同志文學……(那麼,朱天文的《荒人手記》就不算是同志文學嘍?)只有將同性戀身分角色當作主角的作品才算是同志文學……(陳雪的好幾本小說主人翁是雙性戀,那麼,這些小說就不是同志文學嘍?)我想提醒,這種對於「區分身分」的執迷,跟上述「我就是知道」的心態脫不了關係。讀者要怎麼知道作者有沒有同性戀身分呢?我通常無法確認同志文學的作者們是不是同性戀(除非她們自己曾經公開承認過),也沒有進行確認的興趣──掌握作家的私生活軼聞絕不等於掌握文學作品(更何況作家私生活軼聞的可信度可疑);我也往往不確定文學角色的身分認同:我不確定《孽子》眾多角色是異性戀還是同性戀,是漢人還是原住民,是台灣人還是外國人。小說並沒有明說每個角色的身分認同。然而我也要承認,這種不確定的感覺,正是閱讀樂趣的重要成分。
不可否認,某些文學作品選擇放棄不確定的感覺,偏偏要把文學角色的身分認同昭告天下:自白體、日記體、「羅生門式」的文本寫出「我,就是同性戀者」這種句子;某些文本貪圖方便,安插「本報訊:某官員捲入同性戀醜聞」、「本新聞台快報:某星流出斷背慾照」之類的爆料,形同宣稱「他,正是同性戀者」。這種打開天窗說亮話的文本帶給讀者方便,讓讀者輕易洞察文學角色的身分認同,但是也同時簡化了讀者的閱讀樂趣,並且簡化了文學寫作技藝。
我還要補一槍。時至2010年代,自白體、日記體、羅生門式眾聲喧嘩、「本報訊」插曲等等手法都已經是老套(就像「後設小說」一樣是1980年代、1990年代的老套),早就被頻繁濫用,我一看到就打哈欠。如果文學作品要交代文學角色的身分認同,為什麼一定要用這種講效率的速食麵手段,而不能夠小火慢燉呢?
簡而言之,「據我所知」,原住民同志文學很少見,就是因為「我」(以及站在讀者這個旁觀位子的各種人)有問題:旁觀者受困於漢人中心主義的視野,洞察力有限。但我也不希望當今的寫作者努力製造「可以讓人清楚辨識原住民同志」的作品,因為這種努力治標不治本,只會虛掩「原住民同志文學很少見」這個問題(彷彿只要在台北多種一百棵樹就可以解決台北嚴重沙漠化的問題),而且很可能動用上一段提及讓人打哈欠的老套手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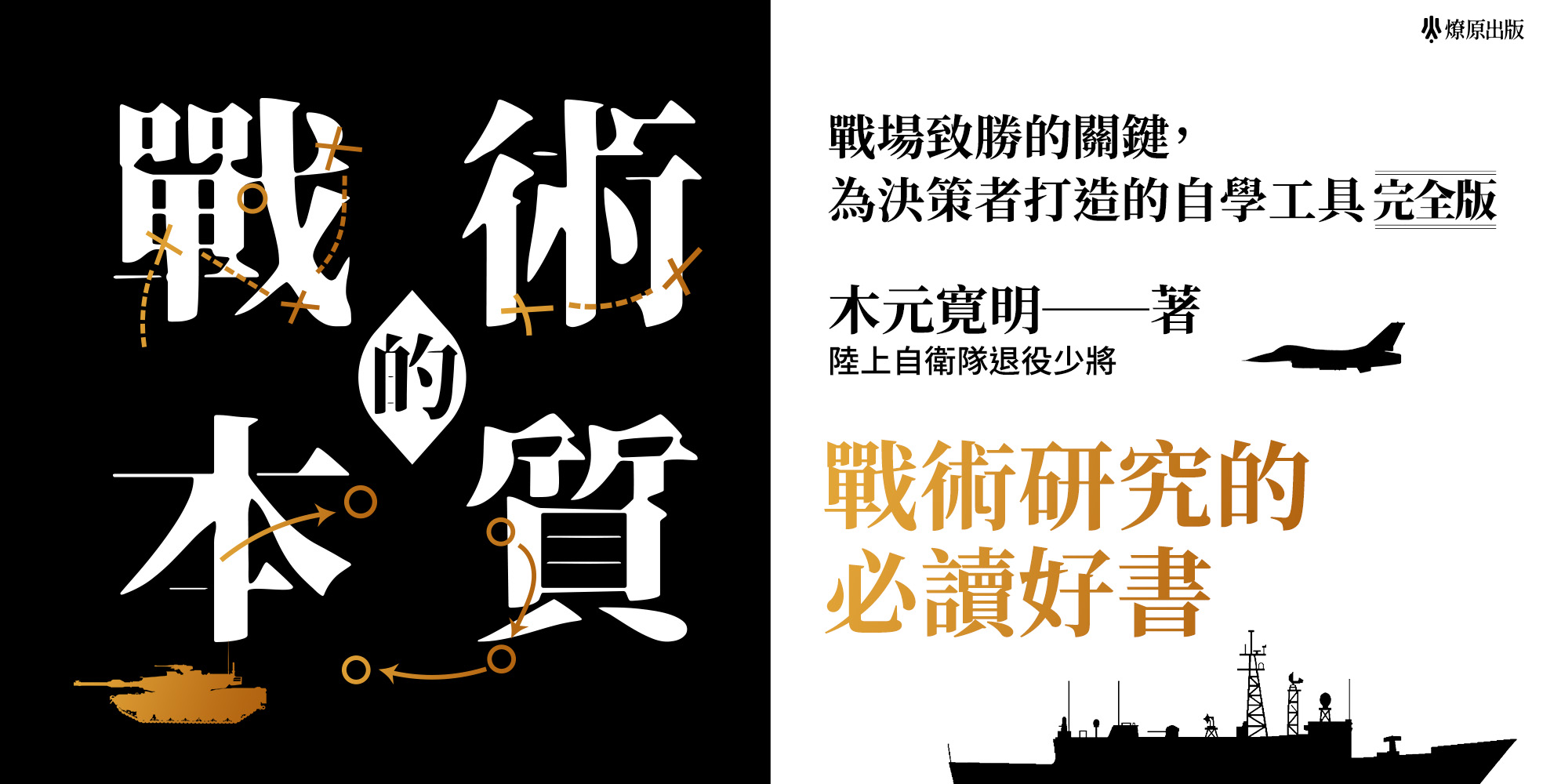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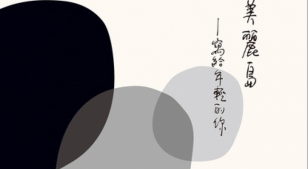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