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與死是托爾斯泰窮盡一生探究的問題。對他而言,死亡從來不是抽象的概念。托爾斯泰年幼時父母相繼去世,使他的童年蒙上陰影;兩位兄長因為結核病英年早逝,更教他執著於思索死亡的意義;在高加索與克里米亞,托爾斯泰見識到戰爭的殘酷;身為人父,子女的死亡令他傷心欲絕。死是什麼?如何死?若終究免不了一死,為何還要活?托爾斯泰研究東、西方哲學,反思生命經驗與宗教信仰,試圖尋求解答。在日常生活中,他對死亡近乎偏執的關注也反映在晚年的日記習慣:完成每日的筆記之後,他會預先寫下第二天的日期,然後以三個字母註記「若我活著」,次日再以「活著」開始新的記事。日復一日,像是一種練習。
從《童年》到《戰爭與和平》,從安娜.卡列妮娜到伊凡.伊里奇,在托爾斯泰的作品中,處處可以看見死亡的蹤跡。死亡也是本書收錄的幾篇小說共同的主題。在這些故事裡,死是個謎,卻也是覺醒的契機。透過書寫死亡,托爾斯泰試圖揭露存在的本質,並且展現自我和他人、和信仰之間的關係。
▌暴風雪中的夏日印象
〈暴風雪〉是本書作品中最早的一篇,構想來自作家的親身經歷。在風雪中迷途是俄羅斯文學的經典主題,危急的情境突顯人的渺小和自然的力量之強大,同時也體現了命運的嚴峻考驗──或無情的捉弄。在這篇小說中,托爾斯泰藉由詩的語言和結構安排,不只細緻地描繪感官經驗,更展示了流動的意識中人和死亡的不期而遇。奔馳的雪橇上,主角感受到死亡逼近,卻忍不住打起盹來,在夢中回到夏日溫暖的陽光下自家花園的池塘邊。然而,他依舊無法躲避死亡──他陷入了目睹農夫溺水而死的回憶之中。池水寧靜、美麗,卻散發不祥的氣息。若暴風雪象徵毀滅,夢境裡的意外事件彷彿暗示死亡無所不在,隨時可能從意識的深淵中浮現。嚴冬與盛夏、現實和夢漸漸交融,雪橇的鈴鐺聲傳到池塘邊,白茫茫的雪地也成了無邊的海洋。在恍惚之間,旅人愈行愈遠,所見的景象也愈來愈怪誕,喜悅與憂傷、愛與恐懼交織,死亡仍然如影隨形。
值得注意的是,托爾斯泰勾勒車夫們的外貌與性格,不僅賦予角色生動的面孔,也呈現社會階級之間的對比。主角不顧旁人勸阻,執意上路,面對生死攸關的危機卻又束手無策。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夏日的夢境裡:他見到農民溺水,先是想跳入池中搶救,但隨即意識到自己泳技太差,只能旁觀。相反地,車夫們明白風雪的危險,知道如何生存,或至少掌握應對的方法:抽煙斗、說故事、唱歌、時不時活動身體,或者冷靜地將命運交付上帝。他們或值得信任,或不那麼討人喜歡,但都更清楚生活的道理,懂得敬畏自然、信任夥伴──如那位喜愛發表高見的車夫所說,馬會自己找到路。別忘了,在雪橇上睡著了的菲力普可是最先平安抵達目的地。
▌主與僕的寓言
〈主人與雇工〉裡的瓦西里和尼基塔走得更遠。
托爾斯泰晚年主張藝術應該簡單通俗,傳達普世的道德價值,民間傳說、寓言故事和宗教文學於是成了創作的重要參考。本書中的作品大多都體現了這樣的美學觀點,其中又以〈主人與雇工〉最具代表性。
這篇小說鮮明的角色對比營造出強大的戲劇張力。商人瓦西里以金錢計算一切事物的價值。對他來說,宗教是生財的工具,兒子也不過是產業的繼承人罷了。他的姓「布列胡諾夫」源自俄文詞「撒謊」,說明了他狡詐的性格。瓦西里處處剝削雇工尼基塔,簡直占盡便宜。他視自己為「主人」,因為作主的權力來自擁有。也正因此,他欲求更多。瓦西里只在乎過去與未來,總是忙著清點財產、規劃下一件買賣。
尼基塔則活在當下。他善良而謙卑,逆來順受,待人寬容,吃苦耐勞。他跟隨瓦西里,一路服從。尼基塔雖然曾經貪杯誤事,但卻能在歡樂的節日堅定地抗拒誘惑,滴酒不沾;他善待動物,當主人只顧著滿足自己的需要,他不忘先照顧心愛的馬。
暴風雪遮蔽一切,卻也揭露事物最真實的樣貌。面對危險,尼基塔計算自己一生的罪,心裡念著真正的「主人」,坦然接受即將來臨的死亡。瓦西里則忙著估量買賣的收益。他嘗試獨自逃脫,卻是徒勞一場。在這個故事裡,聖尼古拉的神跡並非即時救援,而是深刻的覺醒。
瓦西里的犧牲不見得出於高尚的道德情感,或許是恐懼使然,畢竟在冰天雪地裡相互依靠也是求生的本能。不論如何,隨之而來強烈的喜悅見證了神聖的頓悟時刻。托爾斯泰曾經在日記中提醒自己:「在神的事業中,你是做工的人。」對他而言,人的生命是勞動。在過程中,個人得以超越自身利益,為更大的目標努力。〈主人與雇工〉也是瓦西里體會服務的價值、「成為工人」的過程。終於,「他明白了。」瓦西里不再害怕,愉悅地擁抱另一個世界,因為他的生命已經掙脫了自我的侷限,在他人身上延續。至於對已經準備好面對死亡的尼基塔來說,這樣的安排是不是划算的交易,則又是另一個問題了。
托爾斯泰對人類貪婪習性的批評也表現在〈人要多少地才夠〉裡。故事的主角帕霍姆不知滿足,不停追求更廣大的土地。有趣的是,托爾斯泰筆下巴什基爾人看待空間的態度像是「陌生化」了財產的尺規,帕霍姆不但不懂得用時間丈量土地的方法,更敗給了自己無限的貪念。人要多少地才夠?托爾斯泰給了明確的答案。

托爾斯泰(1828-1910)的宗教哲學與道德觀被稱為托爾斯泰主義,包括簡樸生活、自我道德完善、寬恕一切、不仇視他人、不以暴抗惡。(圖 / 1848年20歲時的托爾斯泰。 wiki)
▌戰慄的形狀
「阿爾札馬斯恐懼」是托爾斯泰生命中的關鍵事件。1869年,他在一趟購置地產的旅途中於阿爾札馬斯的旅館過夜,突然感受到莫名的巨大恐懼。幾年之後,托爾斯泰經歷空前的精神危機。「我的生命停了下來。」他日後回憶,「我像是活著、走著,來到了深淵邊上,清楚看見前方除了死亡,什麼也沒有。」一切如常,他卻突然警醒,終將來臨的死亡使生命成了煎熬的等待,家庭幸福和所有世間的成就都失去了意義。此後,托爾斯泰在信仰中尋求救贖。
〈瘋人日記〉是未完成的作品。托爾斯泰晚年曾經幾度提及,似乎有意改寫,但直到他逝世之後,小說才在遺作集中出版。故事裡,敘事者回顧「瘋狂」的經過,描述他如何意識到死亡的必然、陷入絕望,然後藉由信仰逐漸克服恐懼,終於重新感覺到喜悅。這個故事也反映了作者面對存在困境、掙扎求生的心路歷程。
就情節而言,〈瘋人日記〉或許並非托爾斯泰最精彩的作品,但小說中關於「阿爾札馬斯恐懼」的敘述可以說是他對死亡最簡單、直接的描繪。「瘋人」先是在旅途中突然驚醒。來到旅館,他急著逃離,嘗試釐清恐懼的來源。我為何在這裡?要往哪裡去?他彷彿對自己的生命提問,然後聽見死亡無聲的回應。特別的是,在這篇小說裡,可怕的並非迫近的危險,而是在平靜的日子裡意識到生命的有限──活著、等待生命的結束原來比死亡更令人毛骨悚然。托爾斯泰賦予了那幽微的感受特別的形貌:「紅色、白色、方形的恐懼」。直接而冷酷,抽象又具體,一目了然卻也無比神祕。
▌告別的三種姿態
在托爾斯泰的早期作品中已經可以看見他生命思想的輪廓。〈三死〉描寫貴婦人、老車夫和樹的臨終場景,這樣的對照令許多人感到困惑。托爾斯泰的堂姑亞歷山德拉擔心小說裡貴婦人的形象是對基督教信仰的批評,作為回應,托爾斯泰解釋了小說的意涵:「貴婦人可悲又令人厭惡,因為她一輩子都在說謊,臨死之前依然如此。她所理解的基督教無法為她解決生死的問題。」他強調,老車夫信仰與他共存的自然,深刻明白世界運行的法則,所以能夠正視生命的規律,平靜地死去。同樣地,「樹死得安詳、正直而美麗。美麗──因為不說謊,不裝模作樣,不害怕,不遺憾。」
在故事中,貴婦人不僅欺騙自己,也阻撓身邊的人們正視她病入膏肓的事實。她的眼中只有自己,總是怪罪他人,一心相信只要去南方療養就能康復、寄望偏方治病。最後,她出於恐懼,不得不求助宗教,但仍然無法接受現實、放下心中的執念,當然也未能獲得心靈的慰藉。老車夫在秋天離開人世,彷彿循著自然的節奏走向生命的終點。他平和、從容地面對死亡,不哀怨也不抵抗,還大方讓出新的靴子。旁人對待他雖然有些不留情面,但卻也相當真誠。樹先是顫抖、害怕地搖晃,接著平靜下來。如同老車夫的死使他人受益,倒下的樹騰出了空間,周圍的樹木也能生長得更好。因此,大自然歡欣鼓舞,樹木也並不覺得哀傷。對托爾斯泰而言,這樣的情境或許是死亡最美好的形式。他相信,個人的存在只是生命世界的一小部分,生與死並不是存在的開端與終結──隨著身體死亡,消失的只是作為個體的意識。如同水滴落入池子,死是解放,也是融入萬物合一的共同生命必經的歷程。
▌破瓦罐,或一幅聖像
〈瓦罐子阿柳沙〉不只展現托爾斯泰的晚期風格,在某種程度上,也揭示了他的生命理想。這篇小說講述阿柳沙終日勞碌、為眾人服務的一生。綽號「瓦罐子」說明了他所扮演的角色──作為物件、工具,阿柳沙為他人而存在,辛勤勞動,完成各種任務。令人心疼的是,他始終以微笑承受生活的艱難和人們的惡意。阿柳沙的快樂單純而卑微。好不容易,他有機會感覺到愛,幸福似乎近在咫尺,卻又被現實無情摧毀。阿柳沙先是笑,然後哭了一場,依舊溫順地面對殘酷的世界。
讀者不免感到疑惑:百依百順,服務刻薄、自私的主人瑣碎的要求,這樣的勞動是有意義的付出嗎?若阿柳沙沒有自由的意志,無力捍衛自己或為所愛的人挺身而出,服從是不是一種消極、冷漠的態度?或許是這樣的矛盾──在故事裡,阿柳沙似乎更像是無辜的犧牲品──使托爾斯泰遲疑,最後並未完成、發表這篇作品。不過,阿柳沙確實反映了托爾斯泰心中農民質樸、善良的理想形象。他善待他人,聽從命運的安排。相較於正義的凱旋,托爾斯泰更重視內在的力量、崇尚以善行回應邪惡。阿柳沙在日常生活中的服從或許也是某種世界觀的抵抗。他純粹的心靈散發出神聖的光芒,使這篇通俗故事更像是聖人的行傳。
托爾斯泰晚年對東正教會僵化的教條、複雜的形式有許多批評,認為宗教體制充滿虛假、背離了信仰。改寫自民間傳說的〈三隱士〉也可以作為對照。主教以為教導了三位隱士正確的祈禱方法、「神的話語」,甚至有些洋洋得意,殊不知隱士們雖然無法正確唸出禱告詞,但因為虔誠修道,竟然能行於水上。故事的寓意簡單明瞭:信仰不重形式,而在於心。
阿柳沙或許看起來駑鈍,但正是因為如此,他的善良完全出於直覺,沒有絲毫的矯飾。他不識字,不記得禱告的話語,但每日雙手合十、畫十字祈禱,以謙卑的態度無私地服務,自然而然地實現信仰。阿柳沙的死亡也展現了這樣的特質。他微笑著,對一切心懷感激,最後,「兩腿一蹬,便死了。」平淡、簡單的描述中,阿柳沙的「詫異」尤其令人好奇。他感到驚訝,但並不抗拒。在生命的最後一刻,他似乎有了新的感受。在托爾斯泰的作品裡,臨終的恐懼通常是執著於自我的表現,阿柳沙本來就實踐了無我的精神,所以能坦然、輕鬆地離開這個世界。
▌記得人終有一死
1883年1月1日,新年初始,托爾斯泰又想到死亡,在日記裡寫下:「我們活著,即是正在死去。好好地活,就是好好地死。新的一年!祝福我和大家好好地死。」對托爾斯泰而言,死亡是生命中必然存在的一部分,好死即是好活、有意義地活。面對死亡,他曾經恐懼,卻也期待著,與其說害怕,他似乎更擔心自己無法做好準備、正確地死去。
托爾斯泰的作品展示不同的生命情境中死亡的各種面貌:在有限與無限之間,死是關卡,也是最終的啟示。樸實而雋永的故事反映了作家一生感覺、思想的核心,同樣重要的是,字裡行間彷彿也能聽見他殷切的提醒:人終究會有一死。記得,然後好好地活。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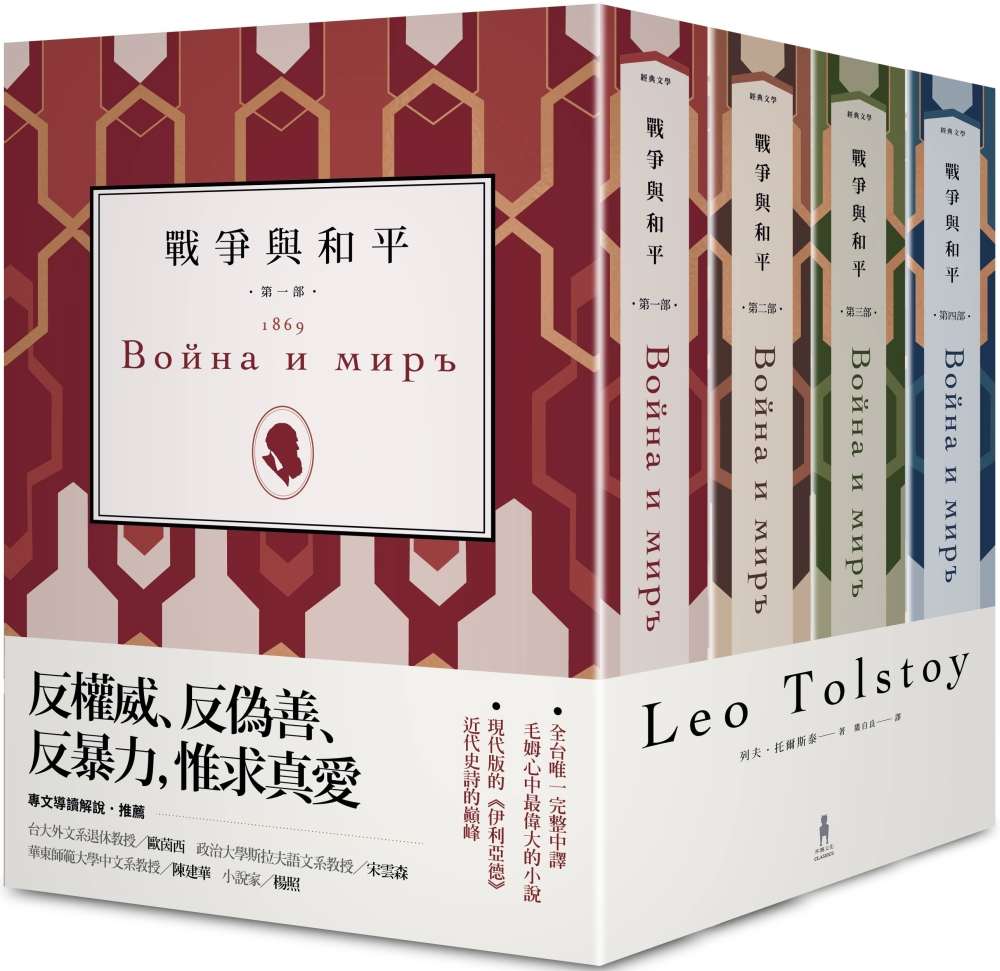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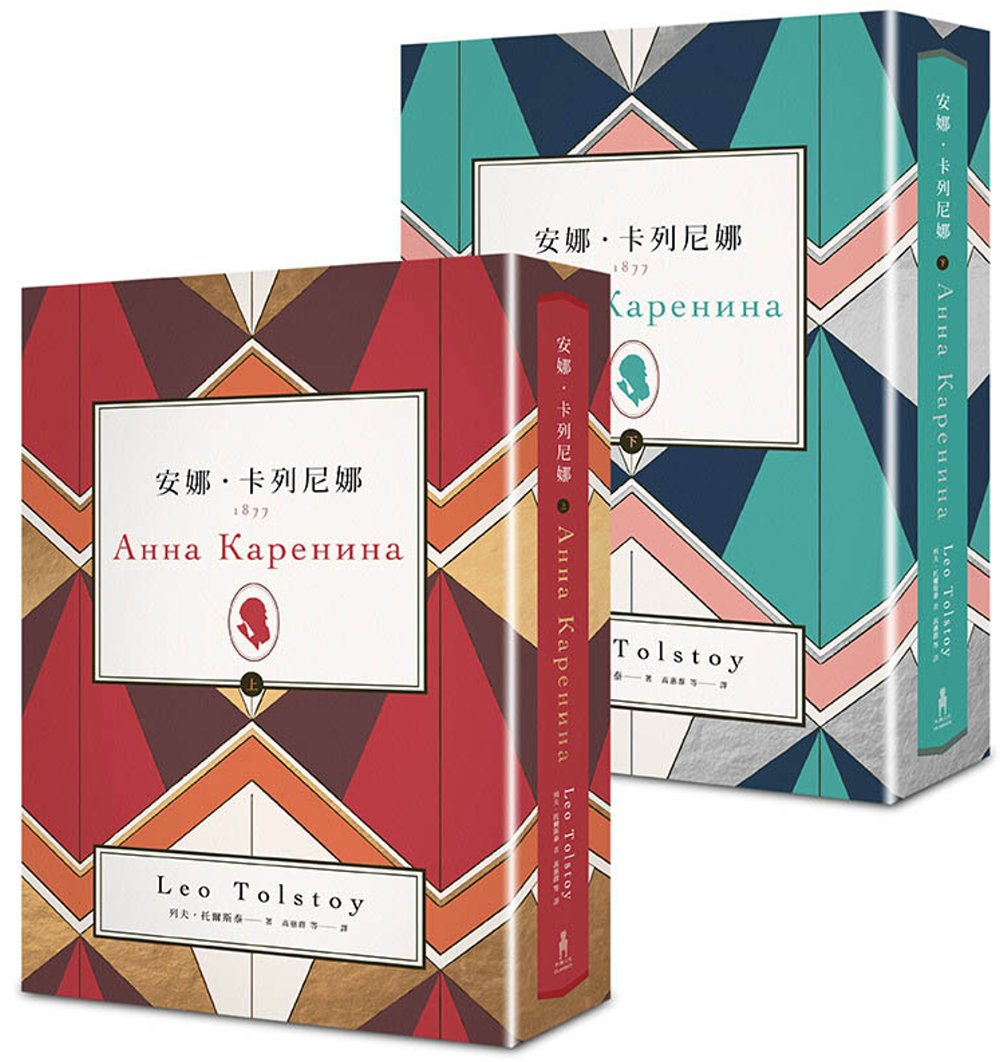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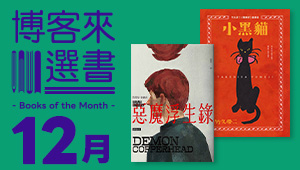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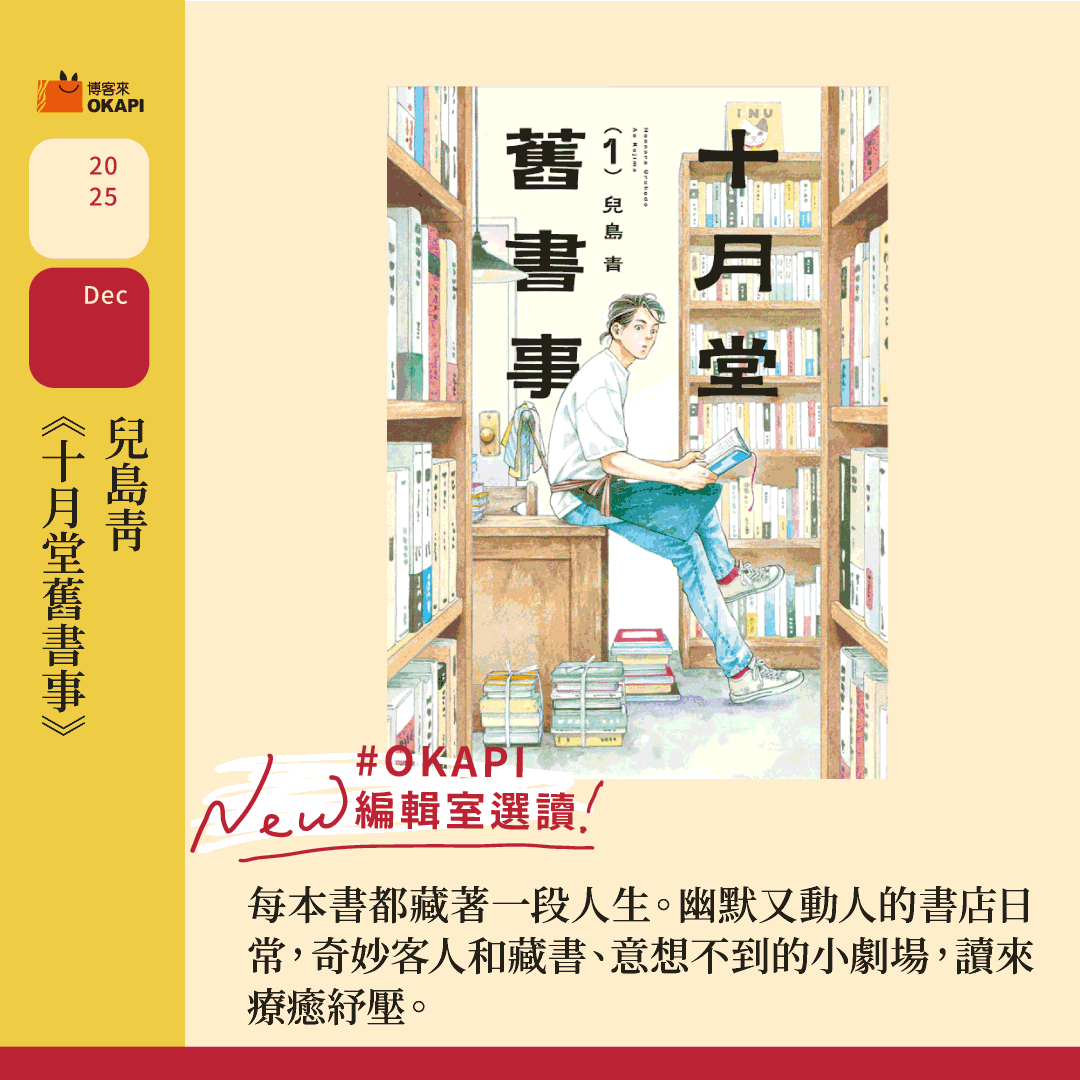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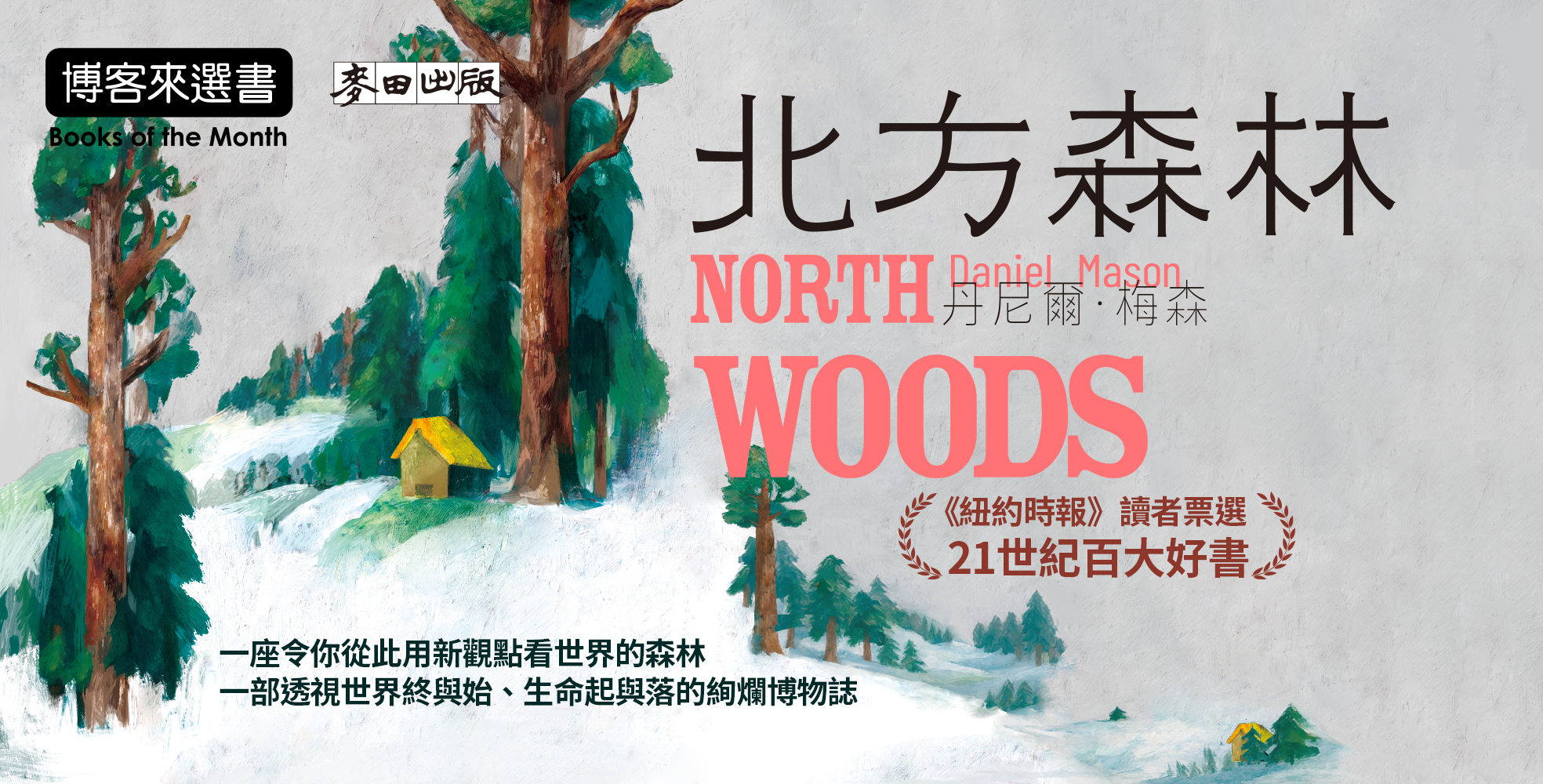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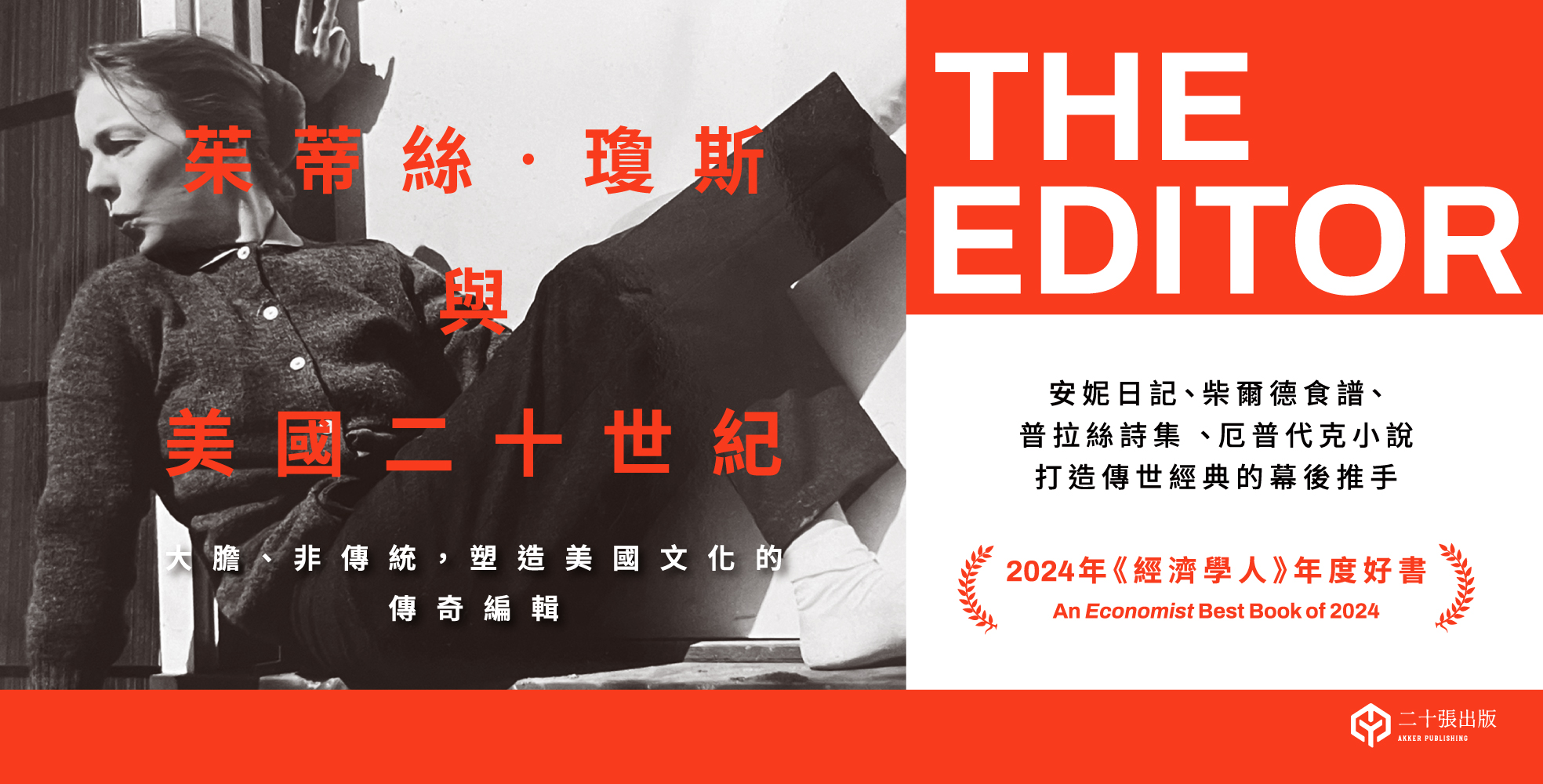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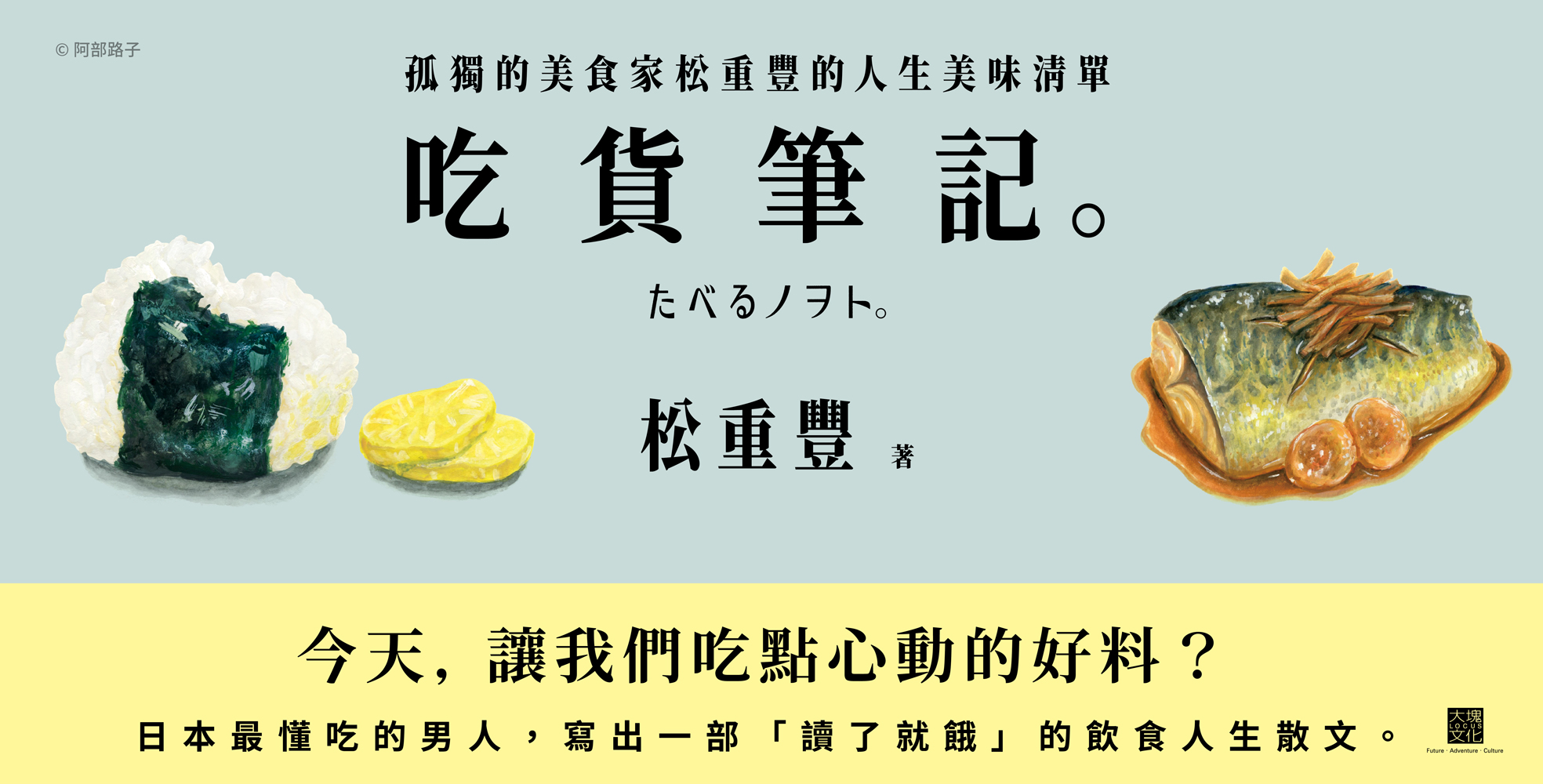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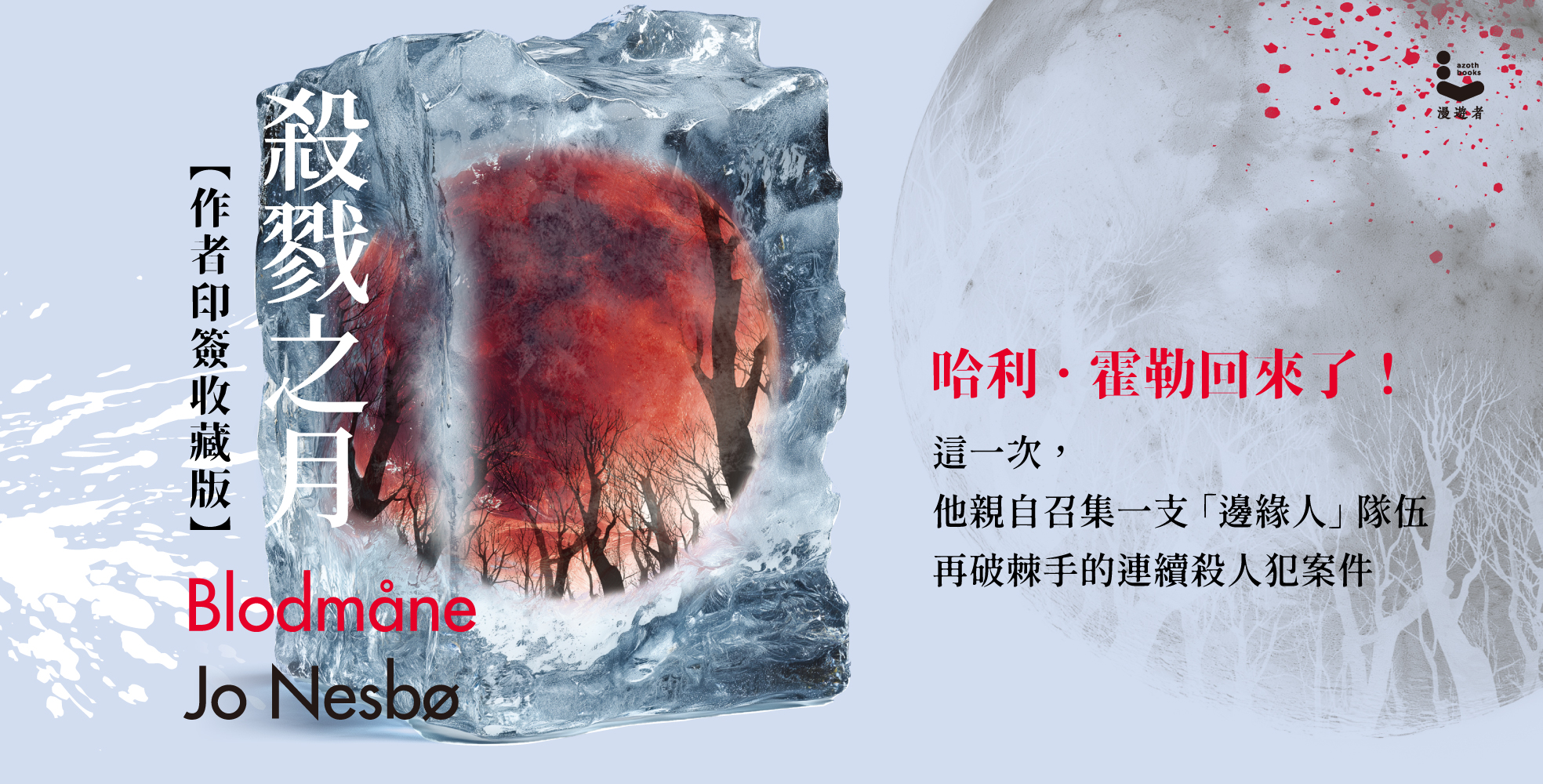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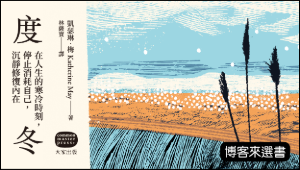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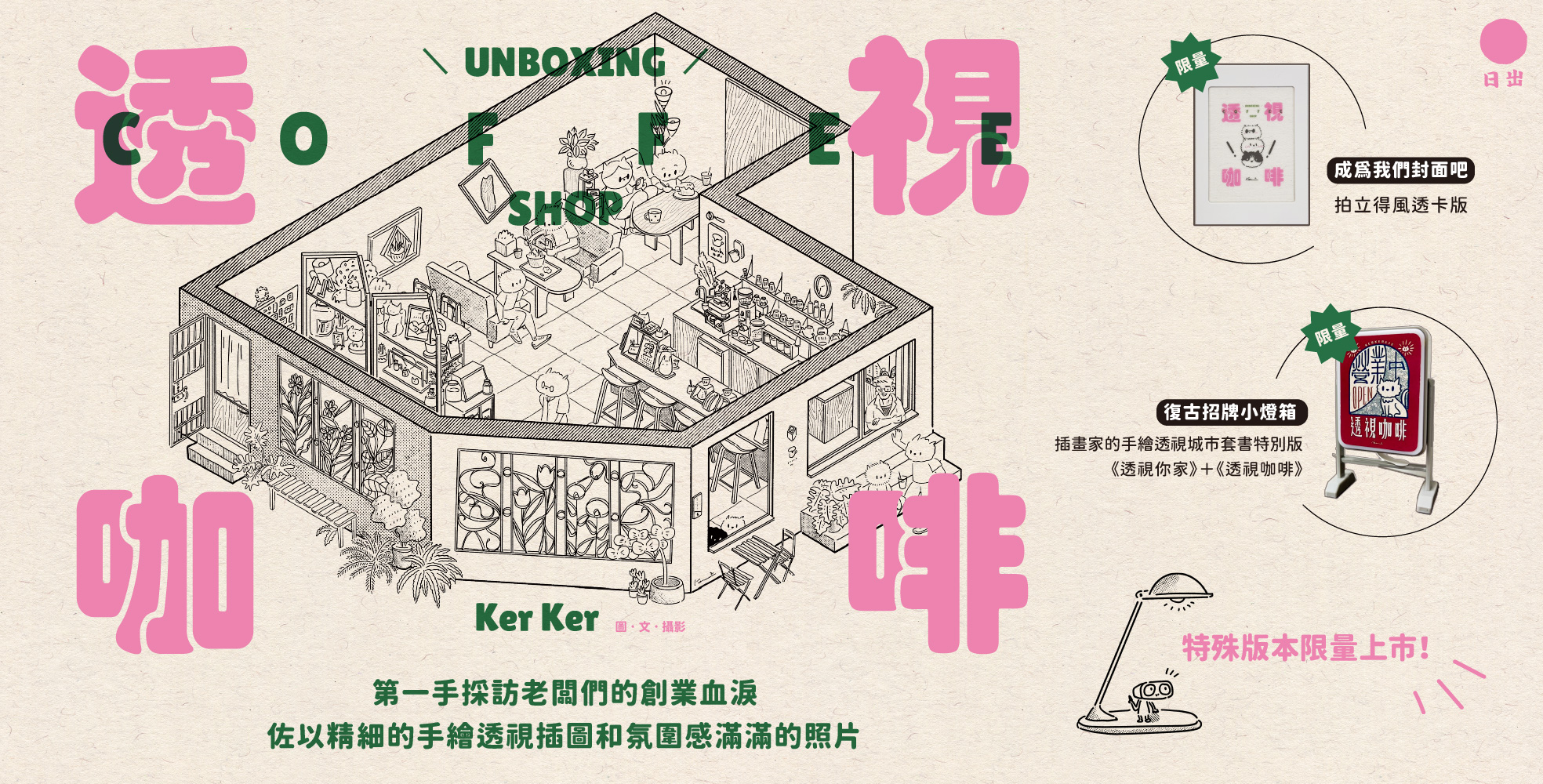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