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象的抓力(與抵抗力)
閱讀麗莎.史蒂文森(Lisa Stevenson)《生命之側》的時候,我同時在準備一個面對六到九年級學生的講座,希望談「氣味」或者「意象」在寫作中,如何具有牽引、召喚的功能。原本預備的一個例子,是班雅明的《柏林童年》。他如此描繪童年記憶中的西洋景:「我走進放映棚,繼而發現那種挪威海岸邊峽灣裡椰樹下的光亮,與晚上我在做家庭作業時將斜面書桌照亮的燈光如出一轍。燈源系統偶而會突然發生故障,這時就會有那種罕見的微光出現,那美妙景觀裡的色彩完全消失於微光中。灰色天空之下,它默默靜臥。即便是這樣,只要我稍加留意,好像依然可以聽到裡面的風聲和鐘鳴。」在一個關乎「視覺技術」與「移動想像」的場景裡,童年的「我」與寫作的「我」都在追憶,交互補充看得見與看不見的光線。即便班雅明的追憶路徑如此糾結複雜,應該也可以是適合「教學演示」的例子?不過我其實沒有預料到,《生命之側》這本在販售通路上被歸類為人類學著作的書裡,也一再出現《柏林童年》:「班雅明在書中回憶一個又一個童年畫面,試圖為自己抵擋即將跟他出生的城市永別的痛苦。」「班雅明在《柏林童年》提供的印象,不只是逐漸消失的過往的閃亮紀念品,而是真正形塑和造就了一種思維,或許甚至是一種生命的形式。」
生命的形式。《生命之側》的寫作關乎生命,書中內容與加拿大努納武特地區因紐特人的兩大「事件」牽連在一起:一是1940年代到1960年代早期,肺結核大流行期間的隔離治療,二是1980年代後至今因紐特人的自殺現象。這本書並不只是描繪、反思與批判加拿大政府對因紐特人的「醫療」、「照護」系統而已,她在意的也是「一種容許遲疑的人類學傾聽方式」、「事實開始動搖的時刻」,以及「我們如何可能去關注那些存在於自身之外、永遠無法變得完整的生命?」結核病流行時期,被強制移送至南方療養院的因紐特人,面臨的不只是病痛,而是語言不通的割裂、與家人的(永遠)分離、身分混淆(或喪失)、成為編號與統計數據而非「人」。史蒂文森認為描繪這些「事實」仍然是不足的,「意象」(images)是理解(因紐特人)生命的一種方法。
在詮釋何以「意象」是方法之前,她描繪了一個故事:一位因紐特孩童「普塔貢」,在母親阿奇奇亞上船前往南方接受治療時,他只有六歲。母親上船前給了他三包口香糖,他清楚記得是黃色包裝。他是家中最小的孩子,後來他始終將口香糖放在枕頭下,不讓人搶走它們——這個章節的標題是「意象的抓力」,在我的紀錄片觀看經驗裡,有一位導演也非常擅長此類「有抓力的意象」。智利導演帕里西歐.古茲曼(Patricio Guzmán),有一部臺灣翻譯作《深海光年》的紀錄片,片名原本的意思其實是「珍珠鈕扣」(The Pearl Button)。1830年,來自英國的船長羅伯特.菲茨羅伊(Robert FitzRoy)從火地群島帶走了四位原住民,其中一位原住民是以一枚珍珠鈕扣「交易」得來,因此他得名 Jemmy Button。Jemmy Button 沒有永久流離在英國,只是「當他的雙腳重新踏上故土,他脫下了英國服裝,他一半講英語,一半講母語,他讓頭髮又開始長長,但他再也不是原來的自己了」。紀錄片後來還出現了另一顆鈕扣:智利前獨裁者皮諾契特統治期間,以各種方式屠殺異己,包含將屍體綑綁重物(廢鐵軌)丟棄海中。四十年後,從海洋中打撈起的鐵軌,附著了一顆殘存的鈕扣,那可能是追查死者身分的唯一線索,古茲曼說,「兩顆鈕扣講的是同一個故事。」珍珠鈕扣是一個「好意象」嗎?它小巧凝縮、精緻、容易被剝除(脆弱如生命?),卻又回應著更大的整體?不,它不應僅是隱喻的、暗示的,在紀錄片《深海光年》如此,在《生命之側》如此。

「意象」是固執的。另一個故事是,年幼的薩奇亞西,明明知道了乘船離去接受治療的祖母已經過世,但他仍舊年復一年在大船靠港時探聽消息;他始終記得那畫面:船離開港口直到消失在視野裡。在史蒂文森的寫作中,「意象」(載著祖母的船消失在伊努克舒克海岬之外)是抵抗生命被簡化為「事實」(祖母死了)的一種途徑。被視為事實,很多時候即等於被「不屑一顧」。
▌我們為什麼蒐藏這些
閱讀此書時,很難不受其中一個接著一個,看似空白卻又充斥意義的畫面所吸引,甚至需要抗拒「分析」它們的欲望。史蒂文森認為自己不是為了呈現完整的脈絡、關係,而「更像一個收集者,把不同的物件、意象和故事拉在一起⋯⋯藉由將不同時空的事件帶入對話中⋯⋯來打斷班雅明所說的無所不在的『同質的、空洞的時間』。」《生命之側》的第五章是〈為什麼放兩個鐘?〉,提及外來的管理者、照護者認為,因紐特人的「時間管理」是不良的,例如在白日漫長的夏日裡,青少年常常凌晨才睡、漫步街頭,游離在「正常的時間之外」。史蒂文森告訴讀者,因紐特人的時間感與「kajjarniq」(渴望)的情感息息相關,kajjarniq 有沉浸於當下、樂在其中、安適於存在的意思,也形成「美」的感受。因此 kajjarniq 的時間感,絕不是「九點鐘應該睡覺」、「八點鐘起床工作」——書中來自多倫多的精神科實習醫師認為,因紐特人只要都能夠九點以前睡覺,自殺問題多半會消失。
《生命之側》的推薦人中,有一位是學者蔡友月,她的著作《達悟族的精神失序:現代性、變遷與受苦的社會根源》曾使我震盪許久。書中提到一個關鍵的達悟語詞彙「zipos」,意味著親族關係、親屬連帶,也是精神與情感的支持系統。因為社會變化、遷移帶來zipos的弱化,是精神失序的根源之一。我想起三部與臺灣原住民有關的文學創作,也與某種「精神失序」有關:夏曼.藍波安作品中出現不只一次的人物「安洛米恩」、日本作家坂口䙥子的〈番婦羅婆的故事〉、瓦歷斯.諾幹的〈哀傷一日記〉。夏曼.藍波安在《安洛米恩之死》的〈後記〉說:「願野蠻與落伍與我長在。」安洛米恩的「精神失常」與蘭嶼島/人在「現代化」下的支配與抵抗有關,當然,被視為失序者、不配合者的,不只是安洛米恩而已;〈番婦羅婆的故事〉裡,「羅婆」是霧社事件後失去丈夫的倖存者。羅婆在移住川中島的路程中,(疑似)拉下日本巡查墜崖而死。墜崖的原因是因戀情而瘋狂、未能守節的愧疚?或是出於獨活、失去自由的痛苦?小說設計了一位身分是內地女性的敘事者,透過訪問、調查(田野?)的情境,凸顯「挖掘真相」的欲望與不切實際。即便小說未能道盡(或刻意不道盡)真相,我們都不可能忽略殖民者對賽德克族人無所不在的生命控管;瓦歷斯.諾幹〈哀傷一日記〉中有一位形象強烈的瘋狂角色:小說主角Voja是白色恐怖受難者的遺族,他聽取父親的遺言:「我死的時候你一定要用力地哭,而且要哭到發瘋為止,你身邊的任何一個人包括你最親近的人都不能相信!日後,你要澄清我的罪名。」他住在部落面北的小屋,以「護城河」隔絕了他人,「我的腦袋告訴我與其在此憂天憂地還不如跟風、跟雨水或自由自在的白雲交談」。
這些作品中的「問題」,對殖民者來說解決了嗎?
1999年的3月,南海路的國立歷史博物館,有一檔名為〈台灣與加拿大原住民藝術巡迴聯展〉的展覽,同月出版了展覽專書《加拿大因紐特女性藝術家作品展》。其中一位藝術家歐薇露.特里尼(Ovilu Tunnillie),曾經在五歲、七歲時離開部落,前往醫院接受隔離治療。她因為在南方太久,回到父母的帳篷後,相當不能適應:「當有人送來醃肉而我也分配到一些的時候,我真覺得他們是企圖要殺了我。我無法以因紐特語跟他們溝通⋯⋯但後來我才了解,這種肉是一種美味。我很想喝牛奶。因為我不喜歡喝沒加牛奶的茶,我以為母親是很想把我弄哭。」這似乎是《生命之側》的另一側。歐薇露.特里尼有一件作品〈This Has Touched My Life〉,以五件石雕組成,包含一位男性、兩位覆上面紗的女性、被其中一位女性摸頭的小女孩、一台尺寸縮小的汽車。女孩的頭髮被剪短了,表情不安。藝術家在石頭上鑿下細密的孔表現面紗的質地,那厚實的石肉下,看不見她們的表情是嚴肅或溫和。在這帶有自傳性格的雕塑中,除了疏離,或許也有不安而細微的依戀?《生命之側》的最後一章名為「歌」,不只談因紐特人的 katajjait(喉音唱法),而是喚起、伴隨與存在。不只丟出話語、丟出聲音,我們必須傾聽與被抓住。

歐薇露.特里尼(1949-2014)作品〈This Has Touched My Life〉。(圖片來源/Art Canada Institute)
因而,我心中還有一些其他(不及表述、等待傾聽)的蒐藏品(湯米.奧蘭治的《不復原鄉》、藝術家武玉玲的〈山林中的藤蔓〉、夏威夷王國最後一位女王 Liliʻuokalani 被囚禁期間縫製的拼布棉被⋯⋯),它們似乎一同抗拒被「事實」所侵襲,在名字、死亡、夢境、時間的面前猶豫不決,以「共同去描述出那個被不確定性包圍的世界」。
作者簡介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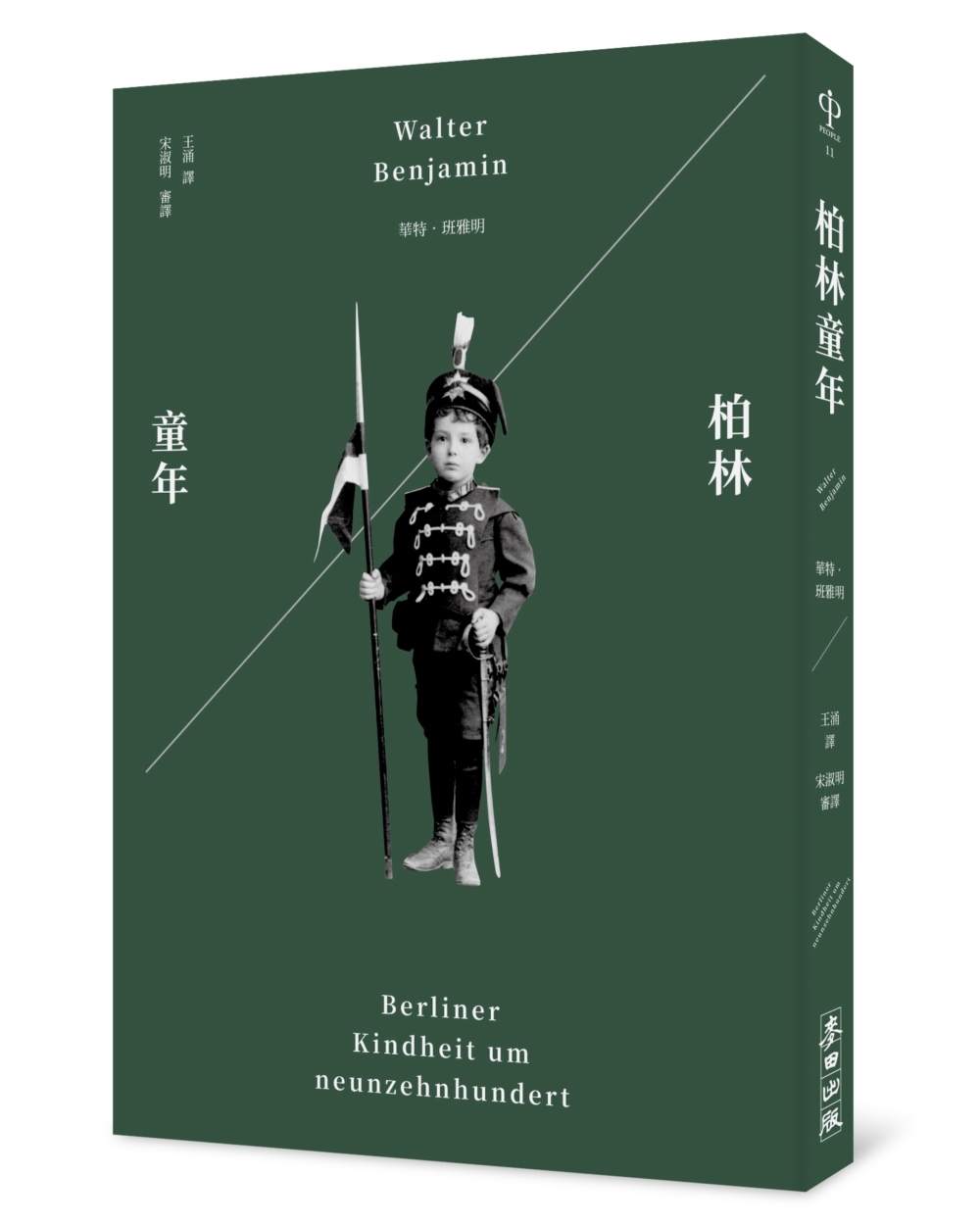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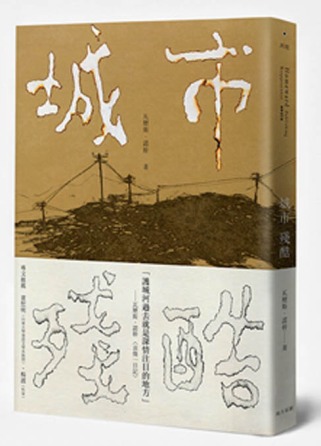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