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愛禪宗的讀者,常提及惠能大師有一個指與月的比喻。據說惠能年輕時,其姑無盡藏尼曾問《涅槃經》於他,他道不識字但懂經,進而把文字喻作手指,真理喻為月亮,以告人勿執指忘月之理。然而翻查《六祖壇經》,僅有「師曰:『諸佛妙理非關文字』」一語,執指忘月,應該是弟子們日後的聯想,實出自《愣嚴經》:「如人以手指月示人,彼人因指當應看月。若復觀指以為月體,此人豈唯亡失月輪,亦亡其指。」
如今倒是這個聯想佔據了吾人的想像,有趣的是,這恰恰證明了文字的力量,如果不是手指與月的比喻鮮明,「諸佛妙理非關文字」這一道理也不會被吾等深切領會。這是一個悖論嗎?抑或是:明月與手指同樣重要的隱喻?
我愛讀禪宗公案以及禪詩,最大樂趣也在於其文字與道理之間的距離,是超現實主義一般的富有詩意。在頓悟的一剎那,手指與明月並無隔礙。
說這一通,盡落言詮,無非是想解答我讀一行禪師詩集時的種種喜悅和思疑。為什麼我同時喜歡讀越南裔美國酷兒詩人王鷗行的詩又喜歡一行禪師的詩?王鷗行又為什麼喜愛一行禪師並為其作序?禪宗主張不立文字,為何喜歡以文字「遊戲」使人頓悟?說到底,不立文字,是不離文字的另一種說法,說的是不依賴邏輯實用思維的文字,尋找更直指人心的文字。這文字,就是詩。
一行禪師少年時適逢越南比較開放的時代,亦有殖民時代遺澤,遂能於西貢大學文學院的法越文學專業畢業(1954年),可以想像他的現代詩寫作根基從此而來。但其詩人的自覺,早在此之前數年萌發,他1949年便出版了第一本詩集《秋昏笛聲》——顧其名,似越南傳統詩歌的意境,其詩意莫非來自戰亂前越南自然的恩賜?天賦感覺,後天修習,再加上佛理領悟,足以成就一個優秀詩人。然而還不夠成就大師。
一行禪師也自問:
我還在睡,
何必張開眼睛?
應該靜靜地躺著,直到驚訝時刻來臨。
為何你還想寫一首詩,
給依偎在竹林邊的小草屋,
給籬笆外盛開的向日葵,
給園子前蜷縮著的狗兒,
給適意躺在稻梗堆上的貓兒?(〈色彩繽紛的小孩〉)
這個問題在另一首《淵源》裡得到呼應與回答:
我內在有一個小孩……
請和我一起去問孩子:
你在找什麼,要去往哪裡?
淵源在何處?歸處在何方?
哪條是回歸的路?
孩子只是微笑。
他手上的花,
忽然變成極亮的紅色太陽,
然後獨自在群星之間漫步。
結尾的意象,會令現代詩的熟讀者想起葉慈的名作〈當你老了〉的結尾:「愛如何竟已/逸去了並且在頭頂的高山踱蹀/復將他的臉藏在一群星星中間。」(楊牧譯本)
是愛,愛並沒有消逝,即使對於一個出家人,愛也是會日益加深,而成就一個詩人。我們可以看到一行禪師有的詩作憶及早年的愛(如〈春天無意〉)以及與同學、同道的情誼,這些同道有的在亂世中遭難犧牲,但一行禪師的愛使他堅信犧牲不是虛無的,如〈詩的火把仍在史頁上燃燒〉寫道:「夢見蝴蝶來去,/東海波浪拍岸,/鯨魚依然在。」
詩是有為法,有詩為證,修道者能說出「船著陸星月之岸,/呼吸是錨,/我守護宇宙。」(〈錨〉)這樣堅定的句子。因為他的修行,在歷史的重壓下化成行動,作為人間佛法、入世佛教(Engaged Buddhism)的倡議與積極踐行者,一行禪師的詩便成為他經歷的世變和參與的救贖的證言。
此時回首,全書最感人的,是以散文詩形式寫的一組〈小水牛追逐太陽〉,裡面寫及兩個小沙彌逢春和心滿的情誼,就是覺有情,亦無礙。這種覺悟與眷戀,最終指向對詩與人世的覺悟:
「逢春不可能不成為詩人,但詩不只是月光。你和我都知道,造成詩歌的元素,是泥沼、污水,也是空中的暴火、河邊苦苦等待的窮困茅草屋,是救援團隊的船槳,也是突破險境、紫竹黃花和真如本體。那清晰、莊嚴如銅鐘般雄偉的誦經聲,仍永遠在我之中,我與它一起生活——我在它之中生活,它在我之中生活。」一行禪師真懂詩。尤其當我們知道,逢春(Phùng Xuân)就是他的戒名之後,我們當能在這樣的詩前面低首含笑,繼而起行。
作者簡介
香港詩人、作家、攝影家,現居台灣。曾獲香港文學雙年獎,臺灣中國時報文學獎,聯合報文學獎等,香港藝術發展獎2012年度最佳藝術家(文學)。
曾出版詩集《八尺雪意》、《半簿鬼語》、《櫻桃與金剛》、《一切閃耀都不會熄滅》等十餘種,講演集《玫瑰是沒有理由的開放:走近現代詩的四十條小徑》,評論集「異托邦指南」系列等。
曾出版詩集《八尺雪意》、《半簿鬼語》、《櫻桃與金剛》、《一切閃耀都不會熄滅》等十餘種,講演集《玫瑰是沒有理由的開放:走近現代詩的四十條小徑》,評論集「異托邦指南」系列等。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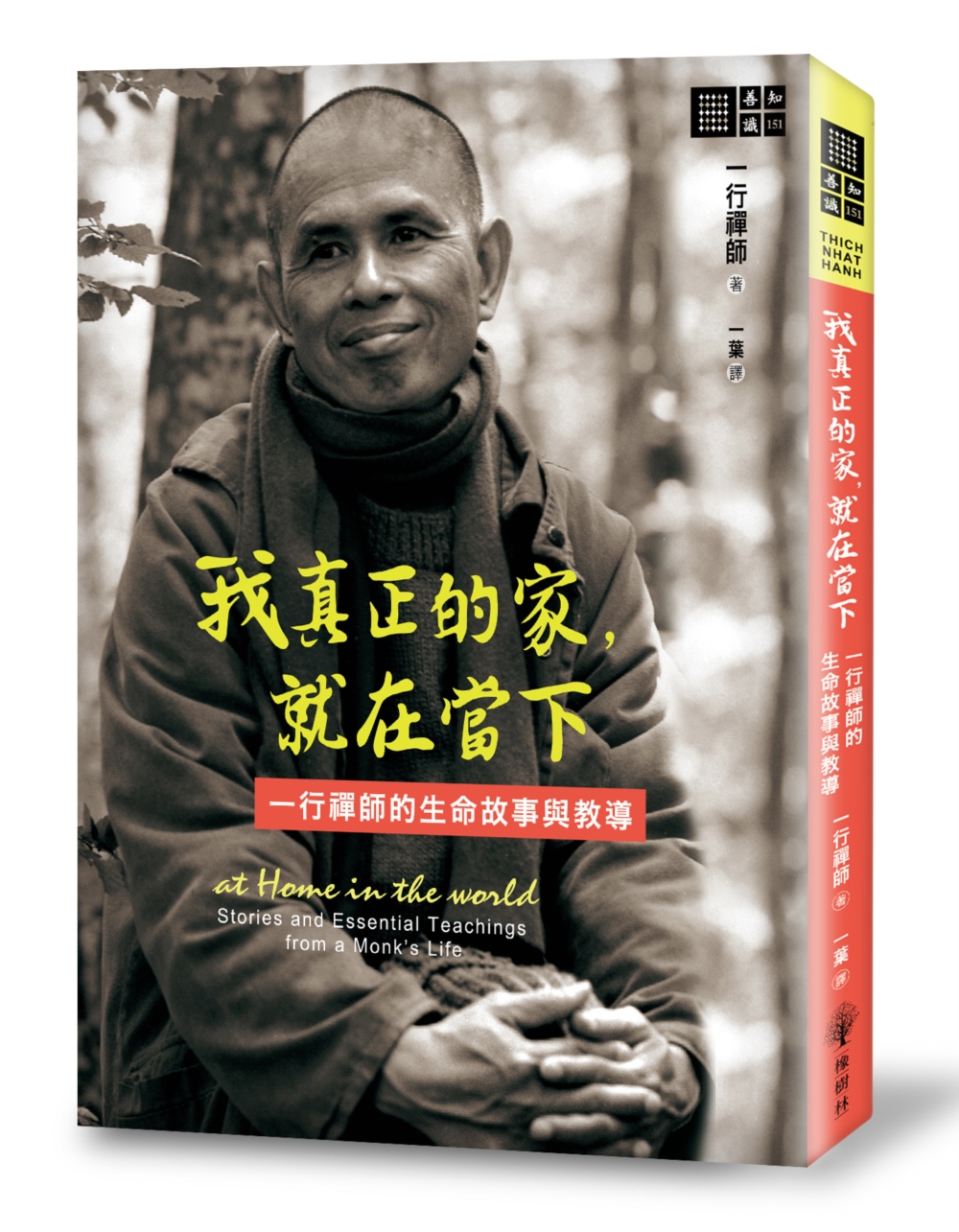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