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謝旺霖(左)與朱和之(右)談小說《當太陽墜毀在哈因沙山》
謝旺霖(左)與朱和之(右)談小說《當太陽墜毀在哈因沙山》
一九四五年九月十日,清算者號於沖繩起飛,本應是一趟為戰俘們平復創傷、慰藉心靈的返鄉之旅,最終卻成為令全機二十五人魂喪臺灣高山的死亡航行。儘管處在權力交接的空窗時期,臺灣仍由島內日、漢、阿美、布農等族群組成一支搜救隊伍。眾人必須趕在接連的下一個風暴來襲前,開拔前往哈因沙山,完成救援。戰爭結束,讓臺灣島上所有生民全都回復為平凡而純粹的人,卻仍止不住生命的殞落。朱和之用《當太陽墜毀在哈因沙山》記錄這場場因天災而起的空難,繼而引發搜救隊死傷慘重的山難,照見多種族群對臺灣的深刻情感。本篇訪問也邀請作家謝旺霖一起暢談創作背後的故事。
▌故事自己想要被說出來
朱和之:哈因沙山是布農族對三叉山的稱呼,這座百岳就在近年很熱門的嘉明湖旁邊。這部小說是受到三叉山事件的啟發,一九四五年戰爭結束之後,美軍把被釋放的盟軍戰俘用改裝過的B-24轟炸機從日本載運到菲律賓,再讓他們各自搭船返回母國。九月十號,有一架B-24因為飛進颱風暴風圈,結果墜毀在三叉山附近,機上二十五個人全部罹難,接著關山郡派出加起來九十七個人的兩支搜索隊上山,卻又遇到第二個颱風而犧牲了二十六人。
我第一次聽到這個事件就覺得有幾個非常特殊的地方,格外吸引我的注意。首先是時間點,飛機在九月十號墜毀,介於八月十五號日本投降之後,十月二十五號中華民國政府接管台灣之前,台灣總督府進入看守狀態,整個政治、社會、文化、身分甚至信仰都處在一個即將劇烈轉換前的真空期,墜機和搜救事件在這個時候發生,帶有強大的象徵意味。
其次是罹難者的身分非常多元。飛機上面有美軍,也有荷蘭和澳洲士兵,搜索隊成員死的最多的是阿美族人,還有日本、布農、閩南、客家、平埔和卑南,可以說是當時台東廳,乃至於用寬鬆一點的標準來說,好像整個台灣族群結構的縮影。盟軍那邊有三國的成員,搜救隊這邊又有七個族群上山,我腦中忽然浮現一個念頭──這簡直像是一場獻祭,在如此慘絕人寰的戰爭將要結束的時候需要一個儀式,每個陣營都必須要有人成為犧牲品。
而真正讓我產生書寫衝動,想用小說來描述這個事件的核心提問是,他們為什麼要上山?殖民政府在看守狀態下,保甲動員系統失效,台灣人已經不再需要接受日本警察的強制動員,沒有義務去做這件事,但最後卻仍然有兩批搜索隊,總共近百人前往陌生的高山地區,然後遇到颱風死掉二十六個。我很好奇他們為什麼要去?罹難的日本人再怎麼說都是警察跟憲兵,還是必須忠於職務,比較容易理解。但犧牲最多的是阿美族人,有點違反常識,高山搜救不是應該以布農族優先嗎?為什麼阿美族死了這麼多?再來是為什麼漢人、平埔族人也去了很多?這是疑問的起點,也是小說發想的開端。

謝旺霖:那些人為什麼上山?也是我最感好奇的問題。而小說裡並不那麼立即就可知道他們為什麼上山。你花了很多篇幅建構出他們還沒「上山」前的生活面貌,賦予他們血肉、個性、風俗、文化和信仰,然後推動他們一步步地進山,走向命運也許早已為他們安排好的所在。
朱和之:三叉山事件的直接史料非常少,你可以想像在時代劇變的當口,戰爭剛結束,政權馬上就要轉換,大家都在茫然混亂,要擔心的事情太多,不太有人真的注意這件事,《台灣新報》只有兩個很小的方塊提了一下。一直要等到五十幾年後,師大地理系施添福教授透過田野調查,才把搜救過程的始末寫成一篇不到六千字的論文,在二○○○年發表,往後大家談三叉山事件大致都不脫施老師的研究。
過去我寫歷史小說,大量參考文獻,貼著歷史事實來寫,可是這次我要在不到六千字的論文基礎上去發展十五萬字的長篇小說,必須從周邊去建構它,借助很多間接的史料,包括當時人怎麼生活、社會情境是什麼,來虛構跟重建那個場景。
最奇妙的是,這個寫作計畫發表之後,陸續發現有好幾組人在彼此不知道的情況下同時默默以這個題材進行創作,其中最受注目的當然就是甘耀明老師的《成為真正的人》,還有高炳權導演的影視製作團隊、記者和前輩軍史作家,大家分別用不同的形式切入這個曾經被遺忘了半世紀,非常冷門的空難複合山難故事。我那時候有一種強烈的感覺,冥冥中有一股力量要讓這個故事被說出來。它不是那種靈異奇幻的,亡靈想要申冤叫屈之類,而是說在今天的時空環境,這個事件重新浮現出來被大家注意到,背後一定有什麼東西擊中了台灣社會集體潛意識裡面的某個情結,讓我們想要重新跟這段歷史對話。這更堅定了我要搞清楚那到底是什麼,故事裡面蘊含著的,同時讓這麼多人有共鳴的那個內在的力量是什麼?


▌漢人、日本人、原住民
謝旺霖:在你的小說,可以看到三條主軸,包括漢人、原住民,還有日本人的部分,三條軸線裡都有中心人物,比如漢族以潘明坤為主,日本人是城戶八十八,原住民是海朔兒。那些還未「上山」的前生活,歷史模糊不清之處,正是小說家介入的時候。能為我們介紹一下你怎樣介入嗎?為什麼鎖定這三條主軸?
朱和之:漢人、原住民和日本人是那個時代台灣三大族群,但總督府強制把漢人和山區原住民領域隔離開來,禁止漢人任意進入「蕃地」,也不能互相接觸貿易。三叉山事件很難得由三個族群共同參與,所以我藉此去描寫三者之間的關係。
這三個角色裡面我最先建立起來是日本蕃地警察,他也是唯一實際存在的人物,另外兩個都是完全虛構出來的。
我高中畢業旅行的時候去了南投東埔,一群同學就說去走八通關古道,體驗一下在父子斷崖上開鑿出來的驚險道路。我們不是登山隊,只是輕裝出發的高中生,走累的就回頭,最後剩下幾個人走了兩小時到雲龍瀑布,停留一會兒拍個照就折返。臨走時我往前方看了一眼,道路沿著山腰延伸,隱沒在稜線後面。聽說這條路一直走可以走到花蓮,我覺得很不可思議,怎麼會有人在那個時代硬要炸出這樣一條路,沿途又有什麼風景,而我將來會不會有機會實際走過去看看?那時候還不知道清代古道和日本時代越嶺道的差別,後來才知道這是日本的理蕃警備道路,從東埔通往花蓮玉里。
大學剛畢業的時候在公共電視「我們的島」當了半年攝影助理,有一次跟拍黃美秀的黑熊研究,從八通關越嶺道東段,也就是玉里這一頭出發,最高上到多土袞。在那兩三個禮拜拍攝的過程中,看到沿路上有幾個紀念碑,比如喀西帕南事件殉職者之碑,還有一個警察戰死碑。我現在都還可以背出碑上的字,故花蓮港廳巡查野尻光一,隘勇潘阿生、潘阿武、潘納仔、ルスカウ、ババイ戰死之地,大正某年月日戰死,印象很深。一直到二○○九年春天,我參加一個隊伍,花八天從東埔走到花蓮玉里,第七天在薄霧瀰漫的杉林裡再度遇到這座野尻光一的碑,那個時刻非常震動,覺得相隔十年之後,我終於從山的那一頭走過整條越嶺道,而這個碑還在這裡。
水泥在山上是很珍貴的東西,因為很重,不好運上來。房子是就地砍樹蓋的,水泥只用來做彈藥庫跟紀念碑這兩種東西,設紀念碑的用意是為了激勵後面的警察士氣,要他們效法前輩,不惜身命為國家付出。諷刺的是後來原住民被強制移住下山,日本人戰敗離開台灣,整個山區回歸大自然,只剩下這些孤零零的碑,幾十年間沒有多少人看到它們。這讓我感觸很深,一直對日本蕃地警察的生活和來歷感到很好奇,所以這部小說更遠的源頭其實是這個,我最先建立起來的角色是日本蕃地警察。
而在拍攝黃美秀那次,我遇到她的研究夥伴,布農族傳奇獵人林淵源大哥,從他那裡第一次認識布農和一些山上的事。林大哥的族名是Qaisul,這是巒群的發音,相當於郡群的Haisul。這次我把小說裡的布農少年命名為海朔兒,也有紀念林大哥的意思。
對我來說,漢人反而是最難去設定的角色。身為漢人,閱讀原住民研究,或參與部落課程用身體去學習時,比較容易找到小說的切入點。可是自己一輩子在漢人的世界裡,反而不太能夠很快掌握漢人代表性的樣貌。最後我決定借用外公外婆的故事,並不是把阿公直接寫成潘明坤、阿媽寫成劉滿,而是在小說人物身上尋找那個年代的台灣人可能的樣子。包括把潘明坤設定成跟阿公一樣在一九二○年生,而潘明坤有一個冥妻林紅緞,是因為我阿公真的有一個冥妻,每到她的祭辰我們家是要拜拜的。我透過這些方法,其實也是繞著彎子試圖認識我的長輩,因為從那個年代過來的台灣人非常沉默,跟孫子輩不親,幾乎都不講往事,雖然我是阿公阿媽養大的,一起生活很久,可是我長大後才發現自己並不認識他們。我在寫小說的過程中揣摩他們的生命歷程,而且竟然有些巧合,譬如我把潘明坤設計為雜貨店的員工,後來發現阿公出社會第一份工作就是在雜貨店,有點嚇一跳。

▌「斷裂」跟「召喚」
謝旺霖:讀完這本小說,我重新梳理「他們為什麼要上山?」在日本人的部分,我會知道那可能是他的職責所在,這個職責不像我們現在一般認為的工作責任,而是有某一種日本性,肩負著使命,帶有精神性的寓意。
原住民的部分,你聚焦海朔兒身上,我覺得他上山除了幫忙搜救,更是因為他跟祖父有一個非常深的連結,但那個連結斷裂了。他上山,是為了重返,為了尋回某一種關於祖父的情感,縫補他自身與土地、文化、自然情感的斷裂,並有一個成為「真正的人」的召喚在裡面。
而漢人這一部分,我覺得漢人的上山動機沒有那麼強,可能因為他的位置比較曖昧吧,雜貨店商人的角色,使他在許多過程和關係中,常處於一種擺盪的狀態,包括他的婚姻,最後上山的原因,好像被塑造得壓抑且不明所以。他不太明白為什麼要上山,但他還是上山了,最後一同葬在了山裡。
若用比較武斷的說法,他們為什麼要上山,我閱讀時常浮現的兩個課題就是「斷裂」跟「召喚」,這斷裂跟召喚的聲音,我覺得不旦可適用或貫穿這三者,也許等一下我們可以再回來小說裡討論,它們也可能是一個當代課題。
朱和之:舉一個例子,布農族稱呼三叉山為Hainsaran,哈因沙山,但我問了幾個布農朋友,他們都不知道這個名字的意思。有些人甚至連自己名字的意義都失落了,問老人家也不知道。布農族人面臨的困境是他們留下了一些古語,可是已經丟失了意涵,這當然是在被連續殖民的過程中,文化產生了巨大的斷裂。
其實同樣的事情在漢人身上,乃至移居到台灣的日本人身上又何嘗不是?我在思考這個故事的時候,那個斷裂性很自然而然就浮現出來,在三個主要人物身上都是。以漢人來說,太平洋戰爭開始之後,皇民化運動到達最高峰,日本官方先推動寺廟整理,把傳統信仰的媽祖、王爺和關公這些神明集中起來,舉行「寺廟神升天」,放一把火燒掉,從此只能信仰日本的神明或佛教。接著推動正廳改善,把一般人家裡的公媽(神主牌)撤下來,連祖先都不能再拜,改奉天照大神。很多人偷偷把神像和公媽藏起來,埋在防空壕或其他地方,戰後再重新請出來祭拜。
於是我在楔子裡描寫,當日本戰敗,時代轉變的時候,不是只有政權交替,連神都要換手,日本人把神明送回天上,而漢人敲鑼打鼓把藏匿的媽祖請回廟裡。但問題來了,從人類學的角度來看,神明靈力來自香火,越多人拜越多人燒香,神明的靈力就越強,沒有人拜的神是沒有靈力的。那就產生一個信仰上的危機,這個神曾經有好幾年不在這個位置上,好幾年沒有香火,祂回來的時候還是同一個神嗎?神明作為文化的整體象徵,我們去思考到社會各方面的時候,你的生活習慣,你一度被取了一個日本名字,戰後又改回來,你還是原本的你嗎?那個斷裂之後的恢復是不完整的,有些部分就此消失了。
這斷裂也發生在我自己,就是剛才說的,跟阿公的家族記憶的斷裂上。我小時候很喜歡看阿媽拜拜,拜大節日和祖先忌日,還有初一十五犒軍,自己殺雞,包粽子,搓湯圓。我最喜歡燒金紙,最後火熄了還要把祭拜的酒水淋下去。但回想起來,小時候視為理所當然的各種細節,從來沒有深究,只記得表象的東西。就像現在婚喪喜慶我們照著司儀指示做一些動作,也常常不知道背後的意涵。這些都吸引我在小說裡面試著去想像、去還原。

朱和之作品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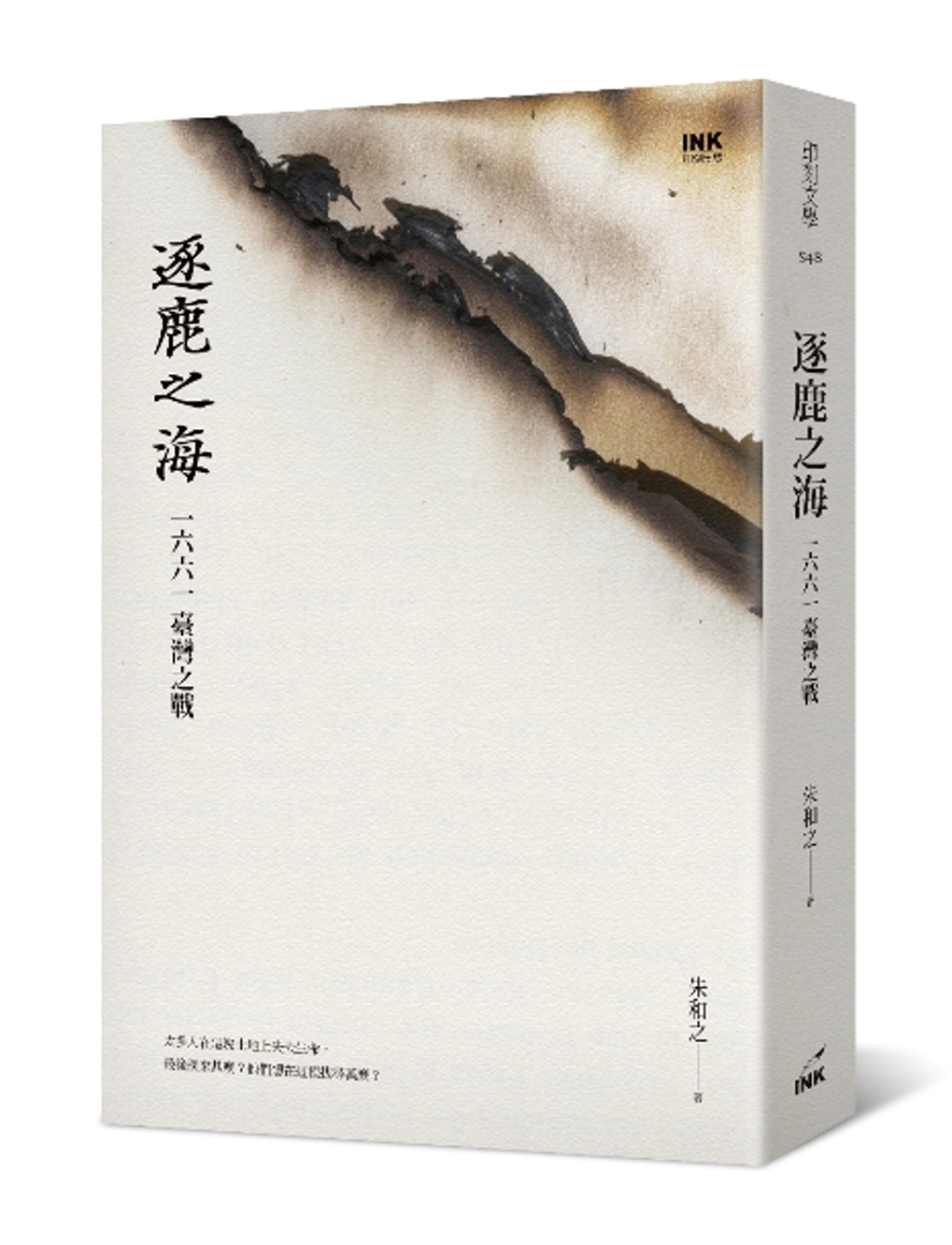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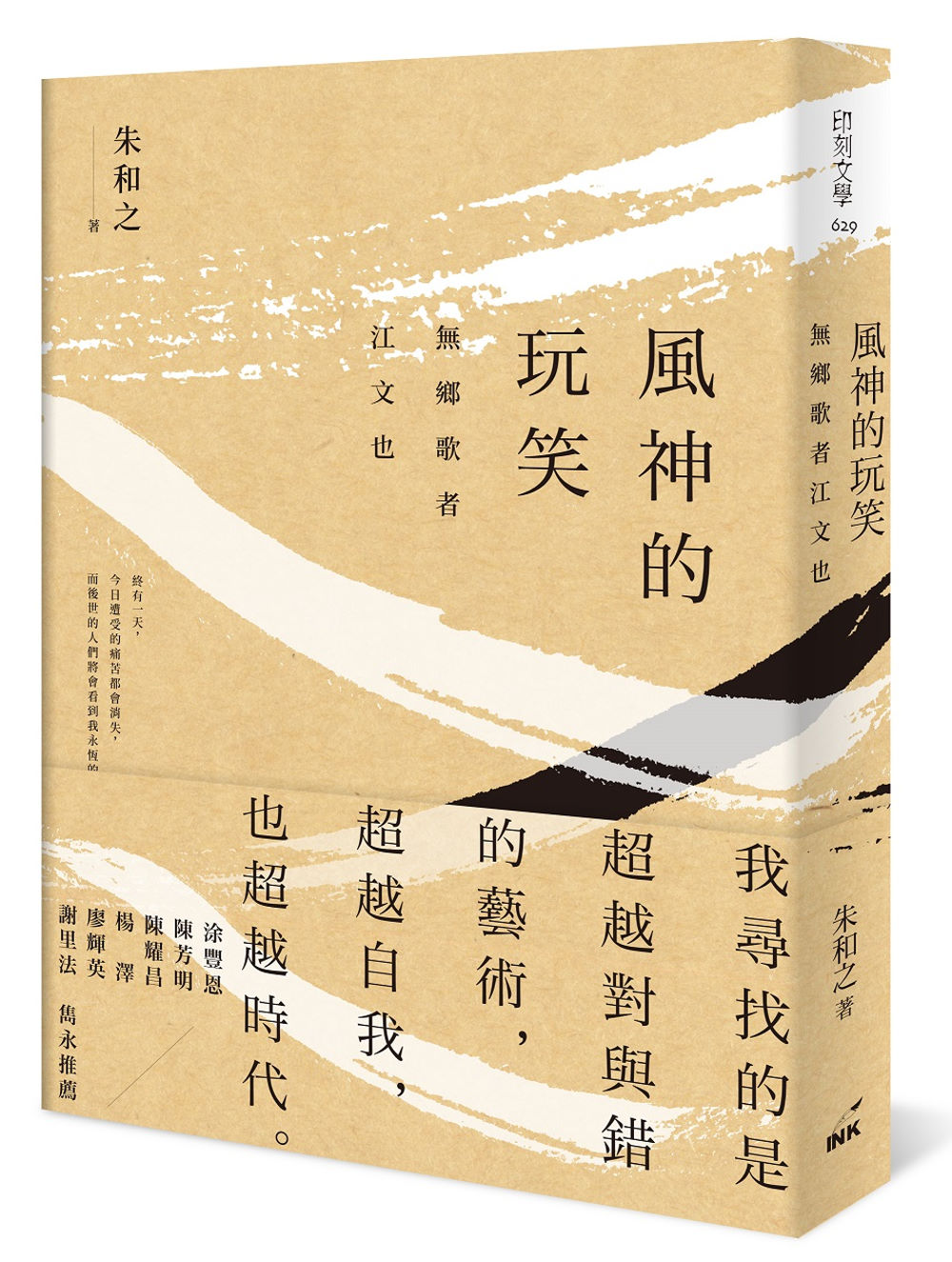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