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厚心得
楊佳嫻/為彼此披掛鱗片──讀陳思宏《第六十七隻穿山甲》
作者:楊佳嫻 內容提供:鏡文學 / 2023-12-29 瀏覽次數(4688)
繼「夏日三部曲」(《鬼地方》、《佛羅里達變形記》、《樓上的好人》)後,長住德國柏林的臺灣作家陳思宏交出了最新長篇小說,《第六十七隻穿山甲》。
讀者都愛看Kevin Chen社群媒體上分享歐洲與美國的浪遊、花襯衫與冰淇淋、德國阿嬤或臺灣姊姊的故事,荒謬與笑淚並進,故意寫得哇啦哇啦好鬧的樣子,其實都藏著暖暖包。而《第六十七隻穿山甲》也是如此,兩個主角,一個吵得要命,一個沉默到天涯海角,從童年到中年,多少鳥事、內傷和狼狽,人卻又如此耐摔耐打,內裡養著溫泉不歇,相互滋潤乾裂的歧路人生。
「家」、「性/別」和「自由」一直是陳思宏作品裡的核心關注,三者相互糾纏,相剋相生。在現當代文學裡,「家」複寫社會主流與保守價值,將孩子視為領土與資源,他們可能被要求要肖似父母,或被要求彌補父母的遺憾,他們被視為父母是否合於社會要求的象徵,尤其在管束「性/別」(包括性別認同、性慾取向、性別表現……等等)上施加力道,無法符合既定框架的孩子往往必須抗家、離家,來追尋自由。
因此,「家」是創傷的根源之一,抗家、離家的孩子,又往往不由自主地追尋新的「家」,在個人親密關係裡,同樣充滿了創傷的反響。但是,「家」不見得只有一種定義,並非只有一男一女生育後代才能組成,它也可以是一種緊密、能提供撫慰與修補的恆久連帶,樣貌與組成份子多元,而《第六十七隻穿山甲》就向讀者展現了這種可能。
另一方面,身體的乾渴也是小說主題之一。「他」總能留意到那些勾引起身體渴望的男體,隱密交換眼神,勇於冒險;「她」則從來沒有滿足過身體的乾渴,只能日復一日隱身在異性戀婚姻裡行禮如儀。
▌屁股與床墊齊飛
本書處處「屁股」,處處「床墊」,試驗著情欲和人性的彈性。「床墊」是主角兩人拍過的廣告,使「她」備受嘲笑,卻也成為反諷的存在。曾在廣告拍攝現場沉睡於床墊上的「她」,後來卻變成長時間難以好好入眠,直到遠赴巴黎,睡在「他」身邊。如果說睡眠偵測了一個人生命的安穩程度,「床墊」雖為商品,同時承托了身體,成為安穩的象徵。
至於「屁股」,是欲望的對象,也是欲望的主體輻射欲望之器。欲望直來直往,挺拔,深入,「他」永遠能迅速從他人的「屁股」接收到訊息。在若干段落裡,甚至寫出「屁股」教戰守則──想獲取人間最大的歡愉嗎?那你得要先從某些基礎細緻做起──。容我斷章取義陳克華名作〈肛交之必要〉,一旦啟蒙,「我從肛門初啟的夜之輝煌醒來/發覺肛門只是虛掩」,虛掩處永遠等待打開,無論你是新手,想一探究竟,或熟門熟路者,虛掩是愛欲的戲劇,逐漸推進,為了奔赴煙花高潮,「我們在愛慾的花朵開放間舞踊/肢體柔熟地舒捲並感覺/自己是全新的品種」。
而當年拍過床墊廣告以後,「她」和「他」也在同儕間成了「全新的品種」,是明星,也是怪物。「他」自我封閉,遠逃他方,在那裏他不必是明星,也不必是怪物。
▌「惡」之所在
「她」可說生活在「惡」的包圍底下。母親剝削她的身體,同學基於嫉妒而嘲弄、破壞她的生活,男人則將她視為領土與工具,摧枯拉朽,劃定界線。更進一步,成為廣告形象的女性身體(再年幼也一樣),被陌生人當作性占有的投射。
張翊帆在小說裡是最不把女人當人看的一位,除了通過強暴來得到女人的依附,隨時隨地以性羞辱女人,同時也私藏不堪照片來做為威脅。女人恐懼裸照與性照被散播,恐懼聲名變形受損,恐懼不被當作一個值得愛的人。「她」的自由竟因此剝奪。
有如《陽光普照》裡父親為兒子做的,《第六十七隻穿山甲》的「他」也為「她」做了類似的事。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他人之身。裸照與性照難道只有女人恐懼?男人呢?以暴力來彰顯陽剛氣概、取得女人宰制權的男人,最恐懼的就是更大的暴力,最不願遭遇的,就是自身陽剛氣概被侵犯。陳思宏或許也邀請讀者思索:當某件事情為惡,複製惡的形式來制衡對方,是否也算「惡」?或者更「惡」?兩樁「惡」同時存在,或者相互抵銷?複製「惡」來遏阻更多的「惡」出現,能否算做「善」?
▌人生何處不孤雛
小說裡,總聒絮不休的「她」,到巴黎尋找惜字如金的「他」。他們曾是童星,一起拍過床墊廣告,也成為密友,熟知彼此生命裡的天坑。「她」因為演藝事業,在成長路上受盡霸凌,母親把她當搖錢樹,女同學把她當障礙物,男孩子則將之視為可攻克占有的堡壘。「他」曾是臺灣同志人權史上的「常德街事件」受害者,因為同志身分遭到父親排斥,繼續拍了得大獎的電影,把自己放逐到遠遠的巴黎,游牧於不同男體。當「她」和具有政治野心的丈夫經營著婚姻這樁合夥事業,擁有光環,也必須承受無邊的檢視和笑罵;「他」則遠遠地住在不比一個停車位大多少的房間內,擔任外送員維生,曾獲得最美好最高熱的愛,然後失去這份愛。
換言之,「她」和「他」都是有家人卻宛如孤雛,即使一個在臺灣組成自己的家庭,另一個漂流於巴黎,其實都一直無法開解孤雛般的處境。做為男同志,「他」強烈感受不被理解與接納,但是,順性別異性戀女性的「她」,看似屬於大多數的一方,卻更逃不出社會期待形塑的窄門。
「她」的愛情經驗攤開來:張翊帆強暴得逞又讓她兩度懷孕墮胎,還有律師蘇大仁、副導陸宏明,都未見真情,卻充滿了自戀與欺騙,最後花落政壇明日之星江海濤,因為他們最相像,「天造地設」的匾額高掛,最討厭因為最真實。「她」和江,都被訓練得能夠不斷抬出自己、不斷亮名與亮相,最大恐懼是被遺忘。當然,做為女性讀者,對於「她」這個角色難免有點「恨鐵不成鋼」的同情與憤怒──母親的非人性對待,是否因此長期取消了她異議的能力?她的婚姻選擇,等於肯定母親為她捏塑好的形狀,找一個和自己相似的、追逐名聲內在空虛的人。唯有當她走出家庭、走向遠方,在聒噪的要求和讚嘆裡,才好像把那個壓抑的自己說出來,一直走,一直說。
從「夏日三部曲」到《第六十七隻穿山甲》,那些曾懷抱著希望、收穫了絕望的人,逃得老遠,以為自由了,卻發現一條無形而執著的線,從那個破碎的「家」輻射出來,拉不住手腳,卻能綁住心。怎樣理解、重置自身與「家」的關係,怎樣從親密關係的破損中拚回自己,仍是一門好大的功課。
大人把死掉的穿山甲放在床墊上,牠們是商品;躺在床墊上,攝影機環伺,兩個孩子是否也是商品呢?但是,這兩個孩子建立了情誼,彼此披掛鱗片,在往後的生活裡,家人一般,一起活下去。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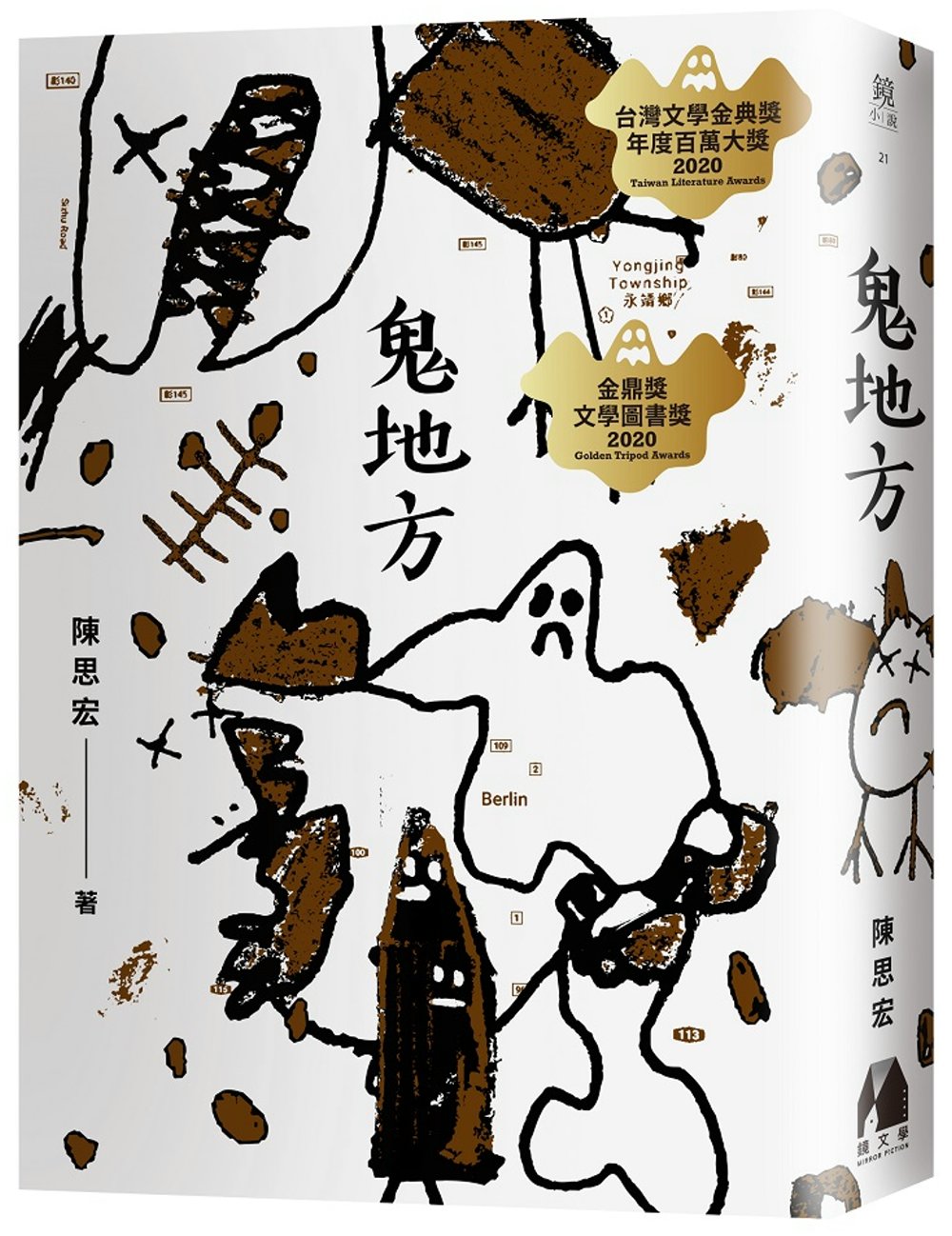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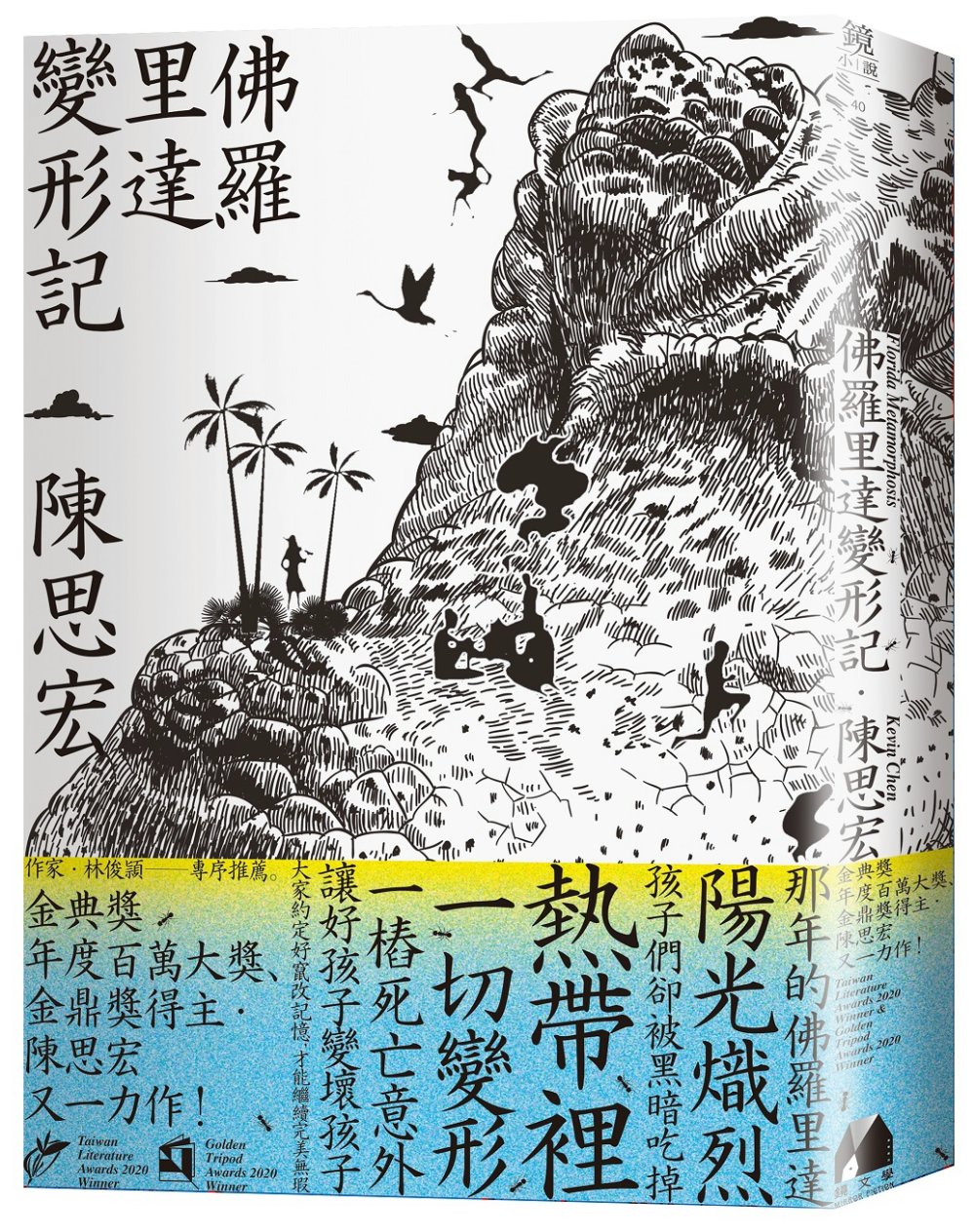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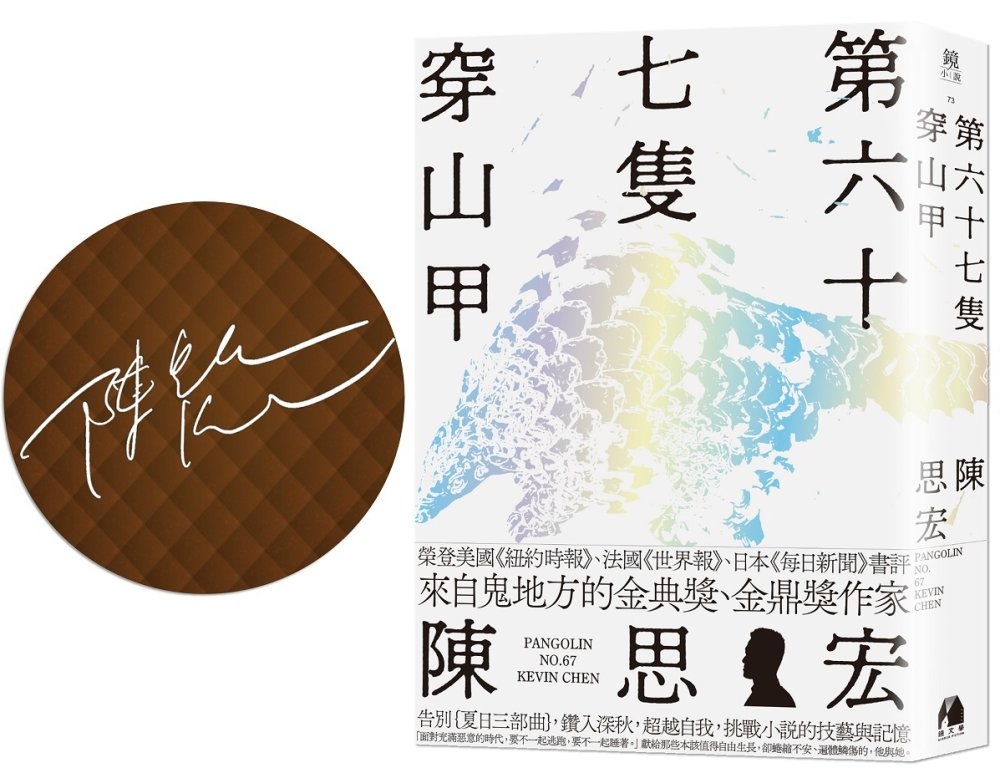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