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始終有主權危機的「亞細亞的孤兒」,我們台灣人很怕被遺忘,總想世界看見台灣。但我們其實不那麼熟練於「賣台灣」——不是那種膝蓋彎彎捧灣灣的賣台灣,而是如吳明益一般,懂得用蝴蝶和腳踏車讓世界對台灣文化買單。
可惜。我們並不那麼認識世界,也不怎麼理解台灣。不習慣從外國人的角度看台灣,也就習慣孤芳自賞,甚至自怨自憐。若非我們的對手恰好是全球公敵,讓我們享有一點「賣慘紅利」,否則看在非洲或大洋洲人眼裡,我們的「孤兒情懷」更像是「國際巨嬰」。要比慘,終會碰上「一慘還有一慘慘」。
「台灣之慘」確實是我們蠻值得說嘴的「負面遺產」。但我們有責任自己先釐清我們到底有多慘。台灣本島人最基本的慘,慘在連續殖民,慘在我們經歷二戰後,仍得繼續面臨全世界夭壽長的軍事動員體制——台灣本島38年,金門馬祖45年。
從日本殖民,到96年總統直選前的國民黨殖民,軍事動員和戒嚴體制帶來的,不只是女性與性少數的屈從、白色恐怖的菁英戕害、黨國特許事業的文化遺毒,更有延續至今的諸多「校園怪狀」——從制服、教官、鐘聲、銅像到「學長學姊制」,還有讓許多人從小葬送運動細胞的躲避球。當然,服儀禁令能靠高中生爭取變不見,躲避球也能隨技術更迭變泡棉。只是「戒嚴」至今仍體現在我們日常生活的諸多細節,如果沒有比較觀點,我們仍多習焉未覺。
有助於我們打開「戒嚴」之眼的兩本作品
就像台灣人經歷的「國語運動」,仔細想想,真是世界級慘烈。其他國家面臨的,大多是如我們各原住民族一般,少數族群的語言如何受威脅。台語卻曾是本島多數人民使用的本土語言,竟然會因優勢少數的殖民政權,不到半世紀就從主流變瀕危。時間尺度如此壓縮的「國語運動」,二戰後還真舉世罕見。
更怪的是,雖然我們的新書出版種類名列全球前段班(這本身就不太正常),但我們竟然到今天,才有《請說「國語」》這種面向大眾,反省「國語運動」的語言政治專書譯介。某種程度上,也顯示台灣出版界,跟台灣的同志電影史一樣,有數量雖多,卻難見真正多元的「視野困境」。我們始終在服務特定同溫層。
明明是個經歷連續殖民的國家,但台灣對「去殖民」的關注,卻遠遠不及我們對「第一世界」的重視。談殖民,也有重文化而輕政治經濟的特質,就像法農在台灣紅的,不是《全世界受苦的人》而是《黑皮膚,白面具》。當反省歐美中心主義的「南方理論」盛行,學界已建立起反叛奴隸制的「海地革命」不輸法國大革命的全球意義時,我們不只沒什麼討論,也沒有多少「全球南方」或「南方理論」的作品。
當然,我們什麼主題的書都很缺。或者對很多人來說,我們其實什麼都不缺。沒有中譯書,老實說也不會死。既然走這行求的不是賺大錢而是帶來一點觀念轉變的樂趣,多花心力引介這樣的作品,或許更能有助於我們重新培養自己「如何賣台灣」的能力。讀 James Griffiths的《請說「國語」》,就頗能啟發我們展開「語言運動」的不同想像。
▌恁阿嬤自在上要緊的語言運動
出版過《強國誌》的James Griffiths,是生活在香港的英國北威爾斯人。《請說「國語」》原書副標題是「帝國、認同與語言政治」,書中主要討論三種語言:反抗英國的威爾斯語、反抗美國的夏威夷語,以及反抗中國的香港粵語。處理粵語,就讓這本書跟《一詞一宇宙》等瀕危語言專著很不一樣,也是《請說「國語」》可能更容易讓台灣人有感的原因。
就像本書對應英國威爾斯語案例的「插曲」中,討論在南非只佔二成人口的「阿非利卡人(Afrikaners)」對於當地黑人的宰制,讓我們看見同樣面臨「少數族群宰制(dominant minority)」的南非黑人,可能是距離我們更近的盟友。而香港粵語面臨中國共產黨推行「漢語拼音」時,如何以「粵語白話文」(如「佢係咪鍾意我」)抵抗,更成為當今台語復振運動,力爭以羅馬字拼音「Pe̍h-ōe-jī」對抗「漢字本位主義」的思考對照。這是我們讀這本書,除了受其他語言復振運動者的熱情感動外,首先容易有的基本收穫。
我更喜歡這本書的原因,是因為這本書討論「語言運動」——無論是殖民政權推行單一語言的「國語運動」,或是反抗者解放語言想像的「復振運動」——的方式,與既有討論不盡相同。過去談到「語言運動」,我們心中常想的是「國族建構」(只是作法倒更接近「文資保存」)。儘管James Griffiths未以分析性語言點明,但他在書中鋪排三種語言的方式,頗能啟發我們:語言運動不只能放在蕭阿勤《重構台灣》式側重文化菁英的「民族主義」框架來理解。關於語言運動的分析視角,更有階級化、性別化、民主化的不同可能。
討論威爾斯語,Griffiths從《濟貧法》講起。國語運動的強項,在於這常是與經濟發展綁定的「階級化」運動。統治集團將特定文化貶低成「貧窮文化」,與他們剝奪特定族群階級流動機會、鞏固自身經濟特權,常是一體兩面,甚至顛倒因果的事——例如有英國人辯稱:「威爾斯人的處境之所以困苦艱辛,是因為古老的威爾斯語還存在」。更重要的是,發展過程藉「經濟剝削」來剝奪語言,不代表經濟地位平等後,語言就能跟著平等。復振運動的弱點,常在於語言復振與經濟發展的「脫鉤」。我們能如何更有野心地設想百工百業的經濟起飛,能附加上什麼本土語言紅利,而不只是把「加分」用在升學考試而已?起造本土語言復振的經濟誘因,永遠是比「愛台灣」更關鍵也更實際的事情。
討論夏威夷語,Griffiths談公主、女校、草裙舞,讓我們看見語言運動也是個「性別化」的過程。所謂語言與知識的性別化,往往也在於將本土語言所乘載的智慧,貶低成怪力亂神的迷信,一如歐洲女巫、台灣廟婆和原住民女祭司的經歷。剝奪夏威夷語,就是在剝奪夏威夷阿嬤們的智慧,而更崇尚男性宰制的科學知識。我們除了在重建各原住民族語言和文化時,復振台語與客語的運動努力,有找回多少民俗智慧嗎?還是我們只想用台語談哲學、聊太空,用現代知識「啟蒙」你阿公阿嬤而已?
討論香港粵語,考量「港獨」可能帶給粵語復振更大的威脅,Griffiths的行文除國族建構外,更側重語言復振運動背後即在「反獨裁」的「民主化」思維。任何反對運動,想強化運動實力,總會思考怎麼達到「盟友最大化」。如何在推行語言復振的過程中,堅守「語言民主」的深化,不是只讓另一堆「菁英男性獨裁者」體驗做皇帝,出征不識字的外邦蠻夷。這想必也是各國語言復振運動的嚴峻挑戰,在多語的台灣民主政治下尤其如此。
《請說「國語」》以當代語言復振的新思維,帶給我們對於語言運動更寬廣的想像。正如同Griffiths在本書最後,援引《語言復振指南(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Language Revitalization)》三位編輯的一段話:「語言復振真正的重點不在於語言。真正的重點在於其他事物,包括自治和解殖、了解傳統價值觀和風俗習慣、重新了解和關注土地、找回社群的凝聚力和歸屬感,以及為下一代建立強烈的身分認同。語言是達到上述的關鍵之一,而語言復振是關於上述全部。」
我們還能如何重新設想台灣的本土語言復振議程?面對威權體制遺留的族群不平等,台灣因選舉政治和公共治理邏輯走上的路徑,是族群委員會的分治。這讓台灣文化目前確實仍有許多「不尋常」的現象,如以「語言分類」的金曲獎和各式補助資源。我們的補助模式也已經上路超過二十年了,繼續循此法而未重新思考全局,我們就只是在造就更多治標不治本的「貧民窟美學」──沒能把圈子闖大,最後就只剩圈內人仰望政府標案和公部門補助,彼此內鬥競爭。如何在民間成為公部門調整的動力,如何回應標案和補助食利者「斷炊」後的惡意反擊,這是我們早該共同面對的治理難題,需要更堅定的政治意志與實力。
總之,如果我們既不想要一種柯文哲式的「性別盲」復振、不要郭台銘式的「階級盲」復振、更不要侯友宜式的「民主盲」復振,那我們就只能告訴那個曾經想推「雙語國家」的賴清德,請跟大眾、女性與民主站在一起;追問我們現在的總統候選人們,怎麼設想全體國人都可能因此受益的語言政策。畢竟,「國語運動」帶來的傷害,從來就不只有台語使用者獨受其害,席慕蓉不也因此與她深愛的蒙語斷根?
▌我就是看到「方言」或「Pe̍h-ōe-jī」就心煩
要走到下一步,我們至少得要擺脫公共輿論的不斷跳針。社群網路時代,論戰頻繁程度遠勝以往,論戰品質卻不見得因此提升,讀朱宥勳《他們互相傷害的時候》特別有感(也是因為朱宥勳把戰場梳理得非常好看)。以台語復振運動為例,拜託酸民不要再來浪費時間的三大考古題,莫過於(一)台語只是一種「方言」;(二)堅持叫台語「閩南語」,說閩南語叫「台語」,要客語情何以堪;(三)攻擊台語沒字。
關於這幾題,強力推薦劉承賢的《語言學家解破台語》。《國家語言發展法》既已保障不同國家語言的法定地位,文化部也基於尊重原有母語自稱,提出「台灣台語」、「台灣客家語」等方式解套,前兩題也就沒什麼特別好再吵的了。倒是「攻擊台語沒字」,我對於這題的回應方式,倒是有點不同意見。
破解本土語言不同迷障的兩本作品
關於「攻擊台語沒字」,回應路線有二:一是解放「獨尊漢字思維」,直接用羅馬字來的「Pe̍h-ōe-jī(白話字)」取代漢字,以另一種系統拼音也是字,就如同韓國發展「諺文」現狀。或許因為這題主要在反擊那些不將「Pe̍h-ōe-jī」當字看的酸民(照他們不當拼音文字是字的邏輯,「word」也不是字了),更因為想刻意迴避漢字的「中國性」,此解成為台語復振運動的主流回應方式。
然而,我覺得我們應該更大力強調的,是解放漢字的「華語優位想像」,就像我們若不用粵語讀「屈臣氏」,就永遠不懂這名字跟Watsons有什麼關聯。當我們鬆綁「獨尊華語」思維,體認漢字是許多語言共同使用的文字體系(就像劉承賢《語言學家解破台語》指出的日語、韓語、越語等)後,「漢字」(或稱孔子字)就是台語名正言順的字,會隨台灣人的使用過程不斷替代、假借、新造,如同香港粵語的發展狀況。只為「抗中」,將「漢字」拱手讓「華」,卻說不出「漢字」技術可能內建的政治性,等於是輕視自己國家的國人,有將他國文化據為己用再創生的能力(就像義大利人不認的「香菜豬血糕五更腸旺比薩」⋯⋯),彰顯的只是後殖民國家的不自信。
請別誤會,我並不討厭「Pe̍h-ōe-jī」,也知道拼音在學習語言音韻的重要性。畢竟若沒先建立起不同讀音的知識與意識,現存島民在看見與華語不同的台語文法或詞彙前,最直覺的膝跳反應仍是以華語讀字。我感到厭煩的,是許多人忽視「白話字」以降低識讀門檻為原意的精神。如果你在意的是「白話」,那最好的工具就不是「Pe̍h-ōe-jī」,甚至不是「台語漢字」,而是最容易被炎上的「台語火星文」,這也是史明為何在訪談中會直覺答:你看阿公阿嬤唱歌用什麼字就用什麼字。這不見得是他不懂,而是對於許多台灣人來說,從「國語運動」解放的核心目的,是讓恁阿嬤過得自在較要緊。
要堅持展望未來有一天,我們能徹底改變教育體制,讓後代台灣人對「Tâi-uân bûn-ha̍k」的理解比看「台灣文學」還快,跟韓國人讀「대만 문학」一樣,這也不是不可能。畢竟在「雙語政策」下,英語與各國家語言的交集,就是羅馬字。只是這總有點捨近求遠。重構歷史的過程,為崇洋羅馬字而貶抑孔子字,也勢必面臨更多難符歷史考據,以及論理邏輯不一致的挑戰。沒必要把主流語言的復振戰略,自限局勢變成「ABCD看無 卡憨就攏免教」的瀕危語言文資保存。
沒錯,到頭來,我確實是因為已經能識讀漢字,基於閱讀效率而比「Pe̍h-ōe-jī」更在意漢字的人。但,難道不是像我這種人佔台灣現狀多數嗎?此刻的我們已經比起日本殖民時期三〇年代的台灣人,更有條件能達成《他們互相傷害的時候》回顧「台灣話文論戰」中,郭秋生、黃石輝等前輩的理想。總之,對我來說,能在大家現有漢字識讀基礎上推廣台語正字當然最好,就像武雄、伍佰正在音樂界做的事;摻著寫「現此時e台語文字」也行,儘管用e不用「个」給我的感受,跟「信長ㄉ野望」一樣,雖有警醒讀者台語讀音效果,但總有點中二。如果許多台語復振運動者實務上都是這麼做,那我們回應「台語沒字」這題的方式,就更該側重解放漢字的「華語優位想像」。
「台羅」不會因為在網路上四處征戰就能成功復振,畢竟「論戰」從來就不是文學,或任何文化運動的全部。我讀《他們互相傷害的時候》,最啟動思考的一刻,是朱宥勳寫在後記的「赫然發現」——女性在台灣文學史論戰的缺席。除了強調「漢人、男性、異性戀」在台灣文化界的宰制地位,「女戰神」不是沒有,只是勢不可免地被邊緣化,我們更該意識到另一種解讀可能——實際做事的女人們,可能根本不屑跟愛談大道理的男人們論戰。
比起男人們「不斷論戰」,永遠吵不出個所以然(是說,我們本來就不太可能因為「被戰」而改變自己的信念,甚至只會激化),台灣女人們「沒有煙硝」的行動,其實更深刻地改變台灣文學的樣貌。正如同朱宥勳在《他們沒在寫小說的時候》提及:林海音擔任《聯合報》副刊主編媽祖婆般的豐功偉業,台灣女作家們撐出來「散文」這種與洋人 essay 獨樹一格的文學體裁;或是比「現代詩論戰」更能代表今人對「現代主義」台灣文學認識的《現代文學》(讀他們的作品,誰說「現代主義」沒左翼也沒在地關懷呢?):她們都不怯戰,只是不好「論戰」,卻一件件完成了「戰神們」嚷嚷著該做卻做不到的事。
回到《請說「國語」》,James Griffiths討論夏威夷語,以一位母親的話收尾:儘管她鼓勵孩子們學夏威夷語,並以身為夏威夷人為傲,但孩子們高度的自信和自我肯定,不是父母能教的。而這些世界觀早已跟她們這輩不同的孩子們,就是她能回送給祖母最好的禮物。同樣的,如何讓未來將與我們共同生活的台灣人們,無論她用的是台灣手語,或任何語言,都能具有同樣的文化自信與自我肯定,不會再因任何族群認同或語言經驗感到自我貶抑,就是我們該共同努力的事。
作者簡介
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博士生,曾任文化部首長幕僚、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研究員。著有《毋甘願的電影史》(榮獲台灣文學獎金典獎、Openbook年度好書獎,並入圍國際亞洲研究學者大會研究圖書獎),現正將 BIOS monthly〈弄髒電影史〉專欄改寫成書。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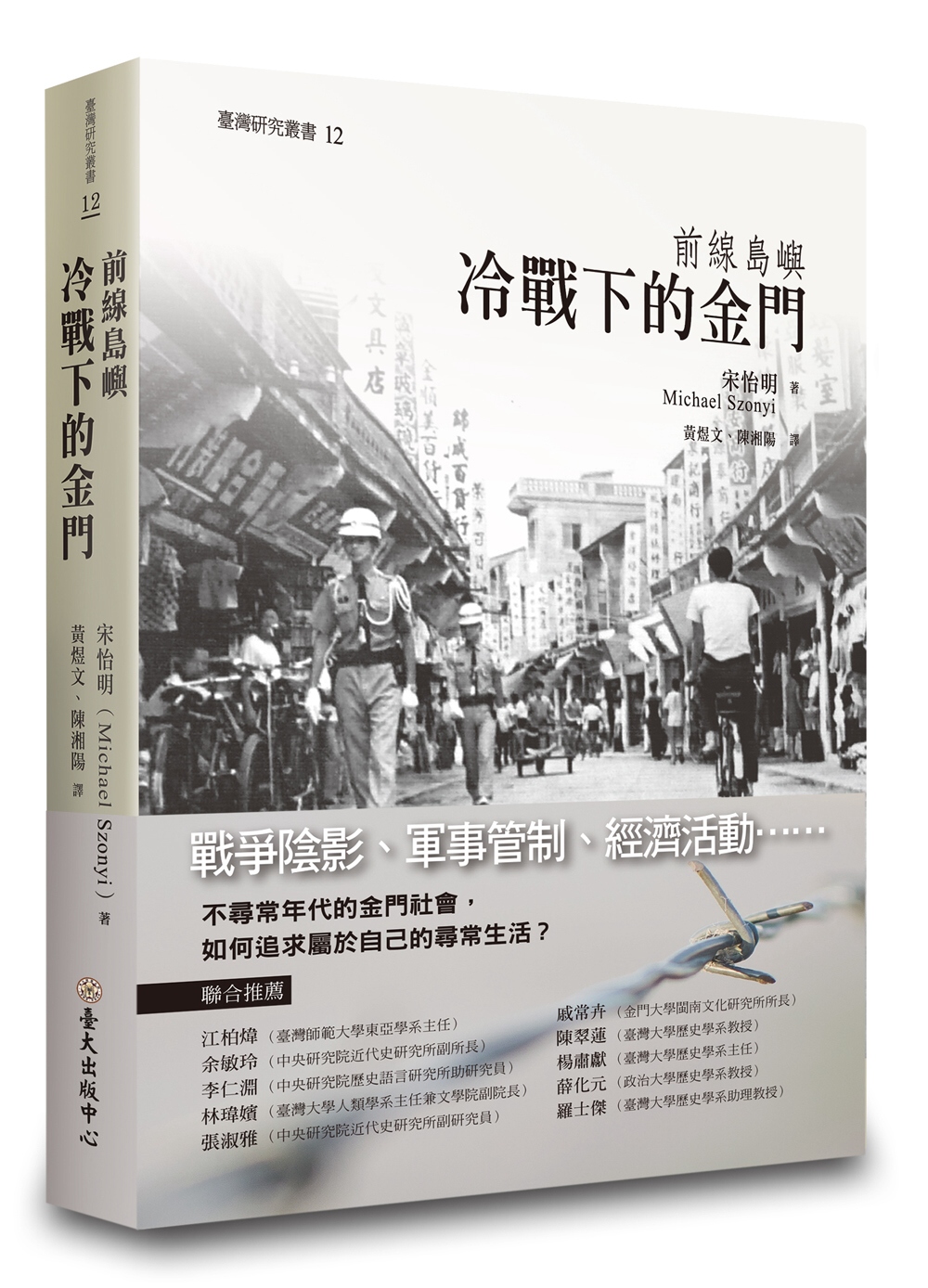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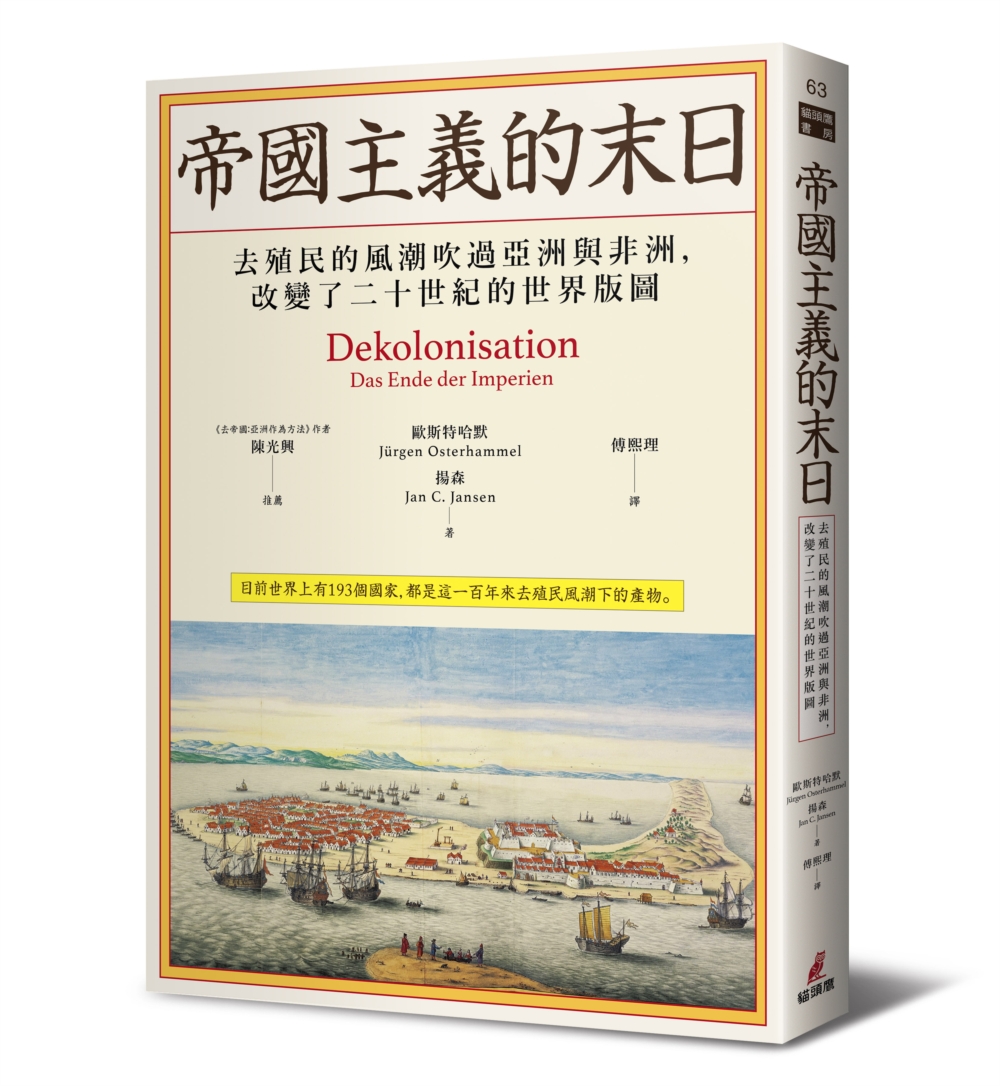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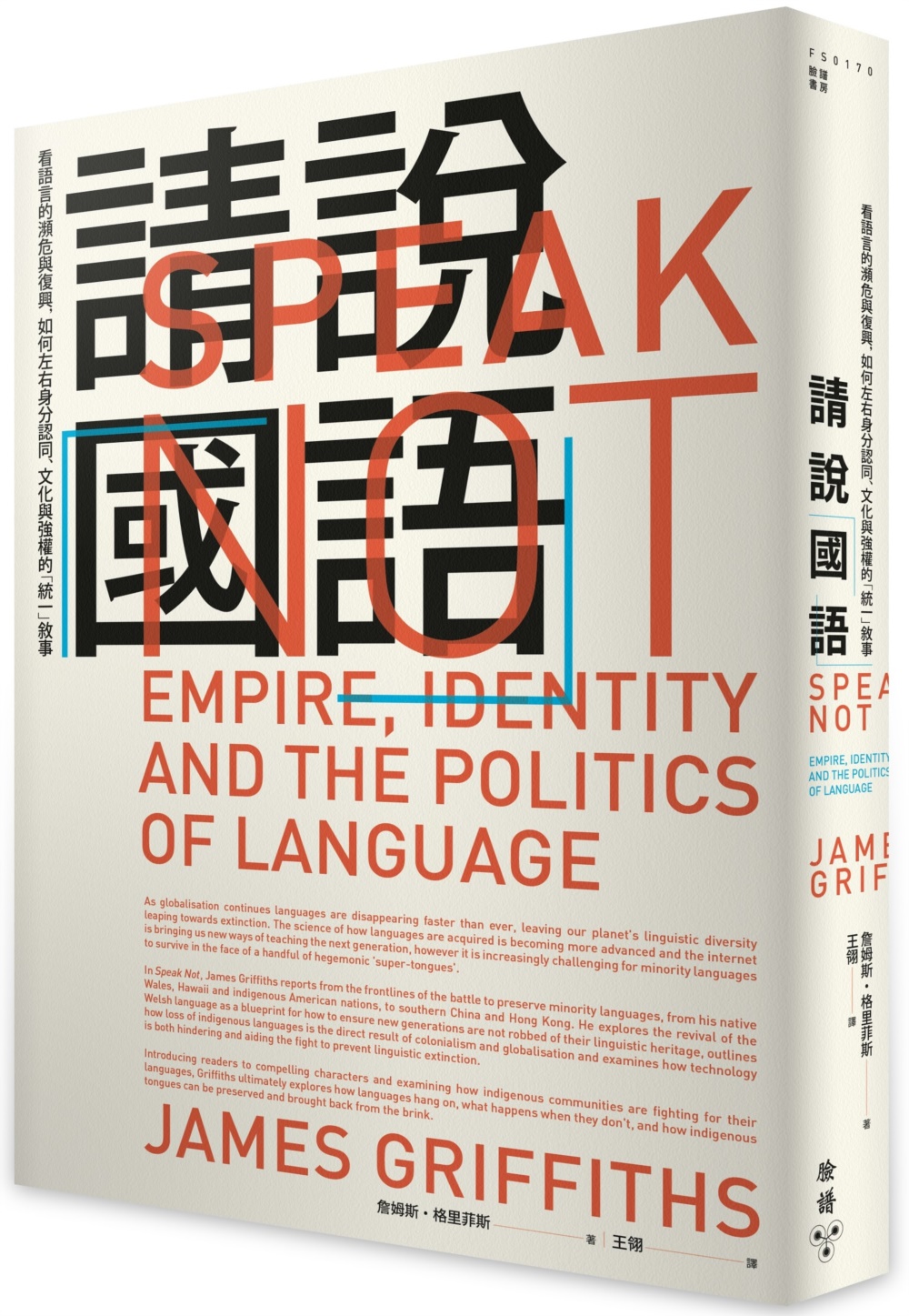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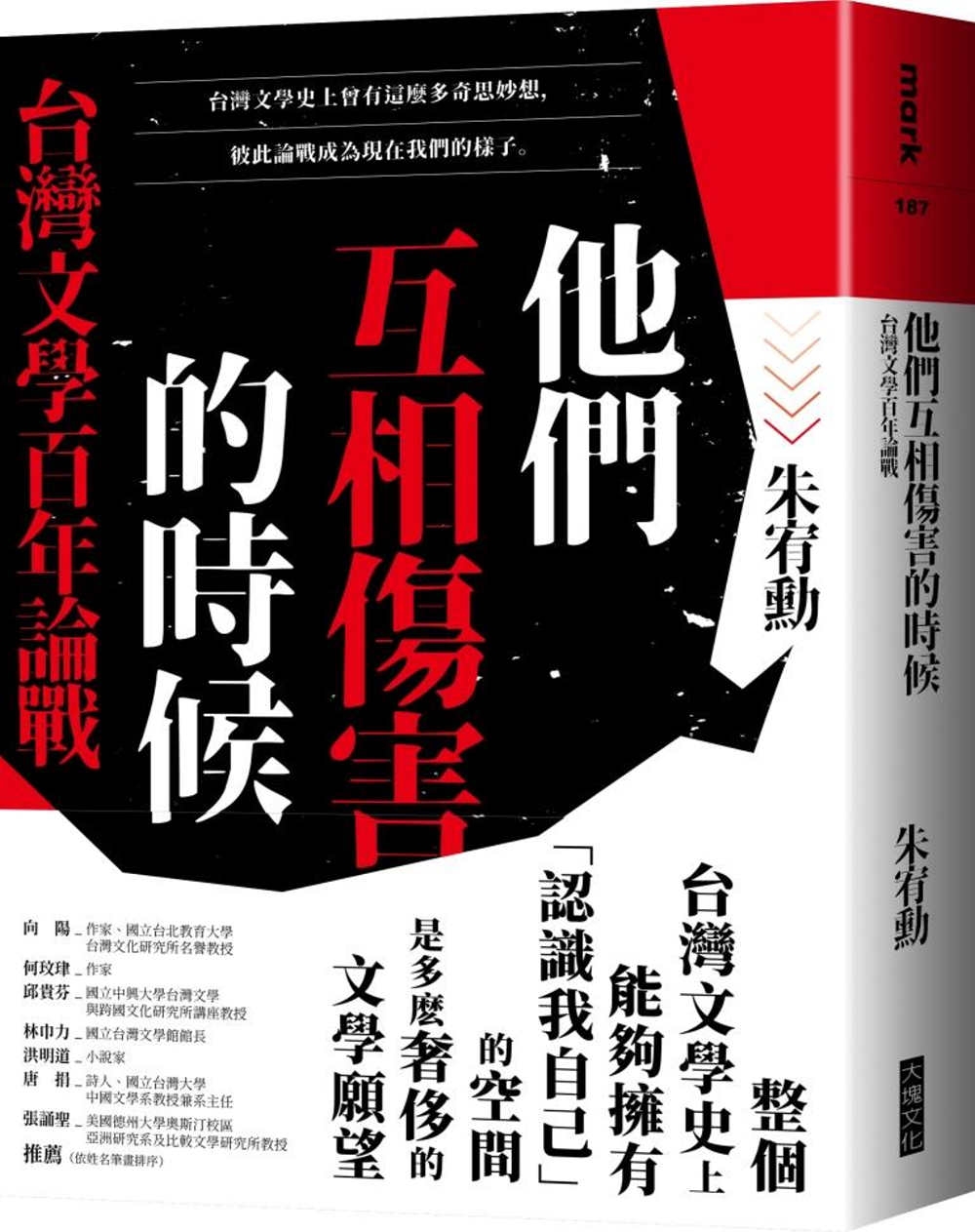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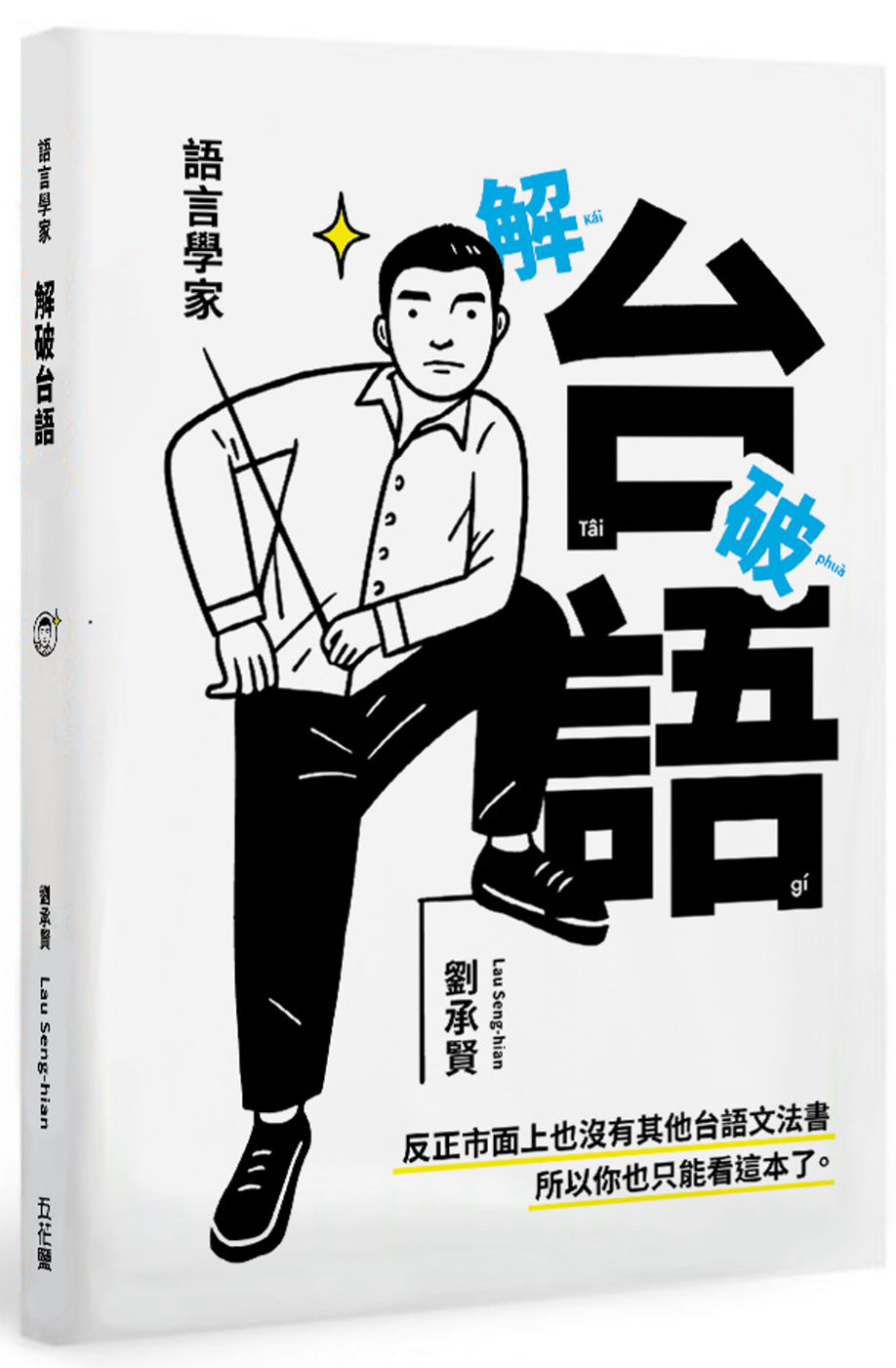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